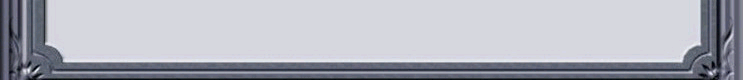第十六章 “撒手”
将近半个世纪过去,台湾畅销作家三毛以张的这段恋情为素材写成了电影剧本《滚滚红尘》,很快搬上了银幕,张爱玲再度成为一个传奇性的人物。贵族的出身、非凡的才华、怪僻的性情,加上这段很快夭折的恋情,构成了世人心目中的张爱玲传奇,而不幸的婚恋无疑被当做了这传奇中最富于戏剧色彩的部分。作为张爱玲的崇拜者,作为一个愿意相信感情至上的女子,三毛也许愿意相信,即便结局归于苍凉,这恋情也是生命中真正的华彩乐章。电影里的传奇加进了三毛的想象--那是她的一种诠释。换了张爱玲,即使里面有传奇的成分,她亦将以她清洁的理性将奇归于不奇。但是,尽管人物被笨拙地敷上了公式化的理想色彩,人们仍然知道而且对他们的原型感兴趣,他们知道女主人公写的是张爱玲,而那个叫做章能才的男主人公就是胡兰成。
胡兰成生于1906年,浙江嵊县人,家在离县城几十里的下北乡胡村。幼时随母亲过活,家境贫寒,然他读书聪明,是个乡间才子。小学毕业后到杭州蕙兰中学念书,二年级时考取杭州邮务局邮务生,三个月后因与局长作对被开除。二十一岁赴北平,在燕京大学副校长室做抄写文书工作,又旁听该校的课程。北伐时回到家乡,先后在杭州中山英文专修学校、萧山湘湖师范学校任教。这以后南下广西,辗转南宁、百色、柳州等地,当了五年中学教员。
但胡兰成显然不能安于教书生涯,他对政治、时局皆有兴趣,且以雄才大略自负。1936年两广事件发生,兵谏中央政府抗日。他受第七军军长廖磊之聘兼办《柳州日报》,即在报上鼓吹“发动对日抗战必须与民间起兵开创新朝的气运结合,不可利用为地方军人对中央相争,相妥协的手段”,引人注目。事件平息后曾因此在桂林受到第四集团军(桂系)司令部的军法审判,被监禁了三十三天,后白崇禧送了他500元钱,算是礼送出境。
胡兰成虽因文字惹祸,却也因此引起各方的注意,有汪派背景的《中华日报》邀他撰稿,他的几篇政论发表后又受到日本刊物的青睐,当即译载,他亦因此更被《中华日报》器重,曾邀他出任总主笔。抗战爆发,上海沦陷后,胡被调到香港《南华日报》当总主笔,用“流沙”的笔名写社论,同时又供职实为汪派机构的“蔚蓝书店”,每月为其写一篇报告。此时胡兰成写政论文章已颇有名气,俨然是个知名的政论家。汪精卫有意栽培他做自家的笔杆子,曾派亲信慰问他,后陈璧君到香港亦与他见面,将他的薪水由60元港币加到360元港币,另给2000元机密费。这以后汪精卫搞所谓和平运动,胡自然地成了入幕之宾,而且是骨干分子。
和平运动初起时,实际的活动还止于宣传鼓吹造声势,弄笔杆子的胡兰成成了要角。《中华日报》成立社论委员会,决定宣传方针大计,该委员会主席是汪精卫,总主笔胡兰成,撰述则有周佛海、陶希圣、林柏生、梅思平、李圣五等人,胡在回忆录中开出这张名单,俨然他只在一人之下,而在众人之上了。汪政府成立,他先后有过中央委员、宣传部次长、行政院法治局局长等头衔,又在一段时间里当过汪精卫的机密秘书,常向汪精卫进言,而汪亦时常问计于他,故他又是“公馆派”(与周佛海派相对)的一分子。
胡兰成以一介布衣,在短短两三年的时间由一个普通的中学教书匠居然爬上政府大员的高位,出入民国元老汪精卫的公馆,真可说是平步青云、飞黄腾达了。甚至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会交上这样的好运,事过多年他说起“和平运动时位居第五”犹透出得意之情。胡兰成骨子里是个旧式的中国文人,满脑子进退出处、江山新朝、布衣卿相之思。他在柳州撰写政论就有秀才纵论天下事的派头,那时还无人拔识,而今一朝得道,便颇以新朝人物自许。旧文人入世的最大抱负是治国平天下,一个个又都自以为是文韬武略安邦定国之才。才略要“货与帝王家”,无人赏识就是“不才明主弃”。不论是在治世里“学而优则仕”,还是在乱世里充幕僚、当师爷,建功立业的关键在遇到一位明主。胡兰成自认遇到了一位“明主”--汪精卫,汪精卫称他“兰成先生”,殷殷垂询,岂不是待以卿相之礼了?他由议政而参政,由幕僚而智囊、心腹、入幕这条道走得顺当,比起来,他在汪公馆里的地位或者还要在蒋介石身边的“文胆”陈布雷之上。胡兰成自言他曾相信过共产主义,但他真正相信的还是“明主”,相信他这样的“能臣”治世,相信成则王败则寇。所以此时他不能不受宠若惊,不能不感到踌躇满志、意气扬扬。
虽然他知道日本人卵翼下的傀儡政府实在算不得“新朝”,但他何曾这般风光?况且以他的狂妄自负,似乎只要汪精卫对他言听计从,虽是危难之局也可扭转乾坤,开出“新朝”的。但是胡兰成很快又失意了。
和平运动到组成“政府”,一个大摊子渐渐铺开来,舞笔杆造舆论已非首要之事了,又有形形色色的人物冒出来,胡的位子往后靠了许多;在尔虞我诈的权力倾轧中,文人又毕竟是文人,不是实权人物的对手,加上他的狂妄自大、自说自话常惹得“故主”汪精卫不喜,到1943年下半年时他已被晾到了一边。但是胡不甘寂寞,还是舞文弄墨论天下事,或是为了日后证明他的见识,或是再因此而令新主赏识。通过日本使馆的官员清水、池田笃纪,他又和日本政界军界的少壮派人物接触频频,其文章也译成日文发表,在日人中造成颇大的影响。这文章与汪政府的口径不一,而此时汪政府与日本人之间正矛盾重重,一时不知此文有何背景,如临大敌,将胡兰成抓了起来,胡甚至以为命将不保,后因日本军人出面施压,终获释放。
胡兰成与张爱玲相识,恰在胡获释以后不久。
事实上在被捕之前,胡兰成已知张爱玲其人。《天地》创刊后,因胡是有名的文人,而且不仅是文人,还是要人,苏青大约也想请他写稿,故每期都给他寄上。胡兰成平日不大看报章杂志,现在失意赋闲,不再涉足官场,也便拿了《天地》消遣。他对杂志主持人苏青的文笔颇为欣赏,说是“女娘笔下这样落落大方,倒是难为她”,也仅此而已。不过看第二期《天地》《今生今世》中胡兰成说他在创刊号上读到《封锁》,又称他在第2期上见到张的另一文章及照片,显然都是误记。,翻到一篇《封锁》,署名张爱玲,他原本是躺在藤椅上看的,看这一篇却是才看得一二节,不觉身体就坐直起来,而且居然细细读完一遍之后又从头再读一遍。过后犹觉不足,又让画家朋友胡金人看。
意下未足是读其文还想知其人,他便写了一封信去问苏青,苏青回信告诉他作者是个女子。也不知信中有无更详的介绍,反正胡接信的感觉是“世上但凡有一句话,一件事,是关于张爱玲的,便皆成为好”。后面几期《天地》来,上面除张的散文《公寓生活记趣》、《道路以目》之外,还登了张的照片。有照片,散文又不比小说,是写实,胡兰成感到“这就是真的了”。他的旧文人气里还有一面是名士的风流自赏,多有才子佳人的绮思。也不知是刻意要制造佳话,还是当真兴奋得颠颠倒倒,他在回忆录中记他看了文章、照片后的情状,如此这般地写道:“见了好人好事,会将信将疑,似乎要一回又一回证明其果然是这样的,所以我一回又一回傻里傻气地高兴,却不问问与我何干。”
这应该是1944年1月胡出狱以后的事(登有张爱玲照片的第四期《天地》是1月份出版)。2月初他到上海,一下火车就去找苏青。和平运动是以上海为基地,《中华日报》报社也在上海,胡的家即安在那里。后伪政府成立,他到南京去做官,又在南京大石桥石婆婆巷有一住处,但家室仍在上海,时常两边走动(汪政府官员多在两地皆有公馆)。胡兰成未及归家即去寻苏青,固然是对苏青的文章及所办杂志颇为赏识,然此番匆匆而来,主要动机却是向她打探张爱玲其人。苏青告诉他张爱玲等闲不见人,胡心有不甘,还是一意要访她,便讨她的地址,张的住处向来秘而不宣,只有极少数人知道,而她又是不大管对方身份的,所以苏青迟疑了一阵才将地址写下。
其实此时张爱玲对胡兰成其人也已略有所知了,而且听说胡在南京下狱,还同苏青去过一趟周佛海家,想看看有什么法子可以救他。后来胡兰成说她此举是因“动了怜才之念”,但胡的“才”见于他的政论,张爱玲素不过问时事,未必会读他的文章,何以知道他的才?即使略知他的才名,读过几篇文章,以她的性情,替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去奔走也是不可想象的事。较为合理的解释是,与她关系密切的苏青曾将胡写信打听她的情形(或许还有赞语)一事对她说起,她对胡有了印象,有了好感,因其知己而心存感激,这才在他落难之后随苏青--苏青那时显然比她更知道胡兰成,与周佛海一家也更熟一些--一道去周佛海家打探情由。
但是,尽管已知胡兰成其人,尽管已经有过“救人”之类,张爱玲觉得来访得突然,她没有准备,也还是不见:第二天胡兰成找到张的寓所,果真吃了闭门羹,张爱玲不开门,从门洞里朝外张望,他只得了个通报姓名的机会,从门洞里递进去一张纸条。胡扫兴而归,但是隔了一天以后,张爱玲又打电话给胡兰成,说来看他,而且她的住处距胡的寓所不远,说来很快也就到了。
胡兰成读过张的作品,见过她的照片,但是在他客厅里出现的张爱玲与他想象中才华横溢的女作家全然不合。《天地》上登的那张照片是正面头像,只有面部,文静清秀的样子,看上去会让人以为是个单薄纤巧的人,胡兰成没想到她竟是个子很高,而且“像十七八岁正在成长中,身体与衣裳彼此叛逆”;张爱玲的文章从容老到,令人猜想她会是个深通世故,应对自如的人,胡兰成此刻见到的张爱玲却是没见过世面怯生生怕见人的样子,有几分不知所措,似乎“连女学生的成熟亦没有”,更不像是个作家。想象与实际相去太远,胡兰成一时也感到愕然,只觉客厅里的气氛有些不对。
张爱玲生活圈子狭小逼窄,并没有与多少人打过交道,她在有些场合似给人咄咄逼人的印象,但她出现的场合多是于她有利的,或是有亲近的人呵护左右,或是众人群星捧月似的围着她转,轮到她一个人应付局面,特别是骤然面对不大熟识的人,她还是怯场,感到窘迫,不会寒暄,亦不知从何说起。好在怯场的人不必为冷场负责,也更耐得住冷场。胡兰成见状倒生怕伤害委屈了张爱玲,不住说这说那,问这问那,用滔滔话语填塞可能会出现的冷场。他议论时下流行的作品,谈她的文章好在何处,又讲他在南京、在伪政府的种种,还问她每月稿费收入之类的具体问题。张爱玲曾说她习惯于当听众,人说她听,她便感到很自在。现在也是如此,她一言不发只管坐着静静地听,唯问到自己头上才答上几句。
二人头一次见面,竟一坐坐了五个小时,也不知是双方都不无恋恋之意,还是张爱玲曾想告退又不知如何不着痕迹地告退,而胡兰成一时竟也不知如何收场。天色向晚时胡兰成送张爱玲出来到弄堂口,两人并肩走着,胡兰成忽然说:“你的身材这样高,这怎么可以?”似有诙谐玩笑之意。张爱玲听了很觉诧异,一则初次见面,此话实在问得突兀,二则以她受的淑女式教育,以她孤傲冷僻的性情,何曾有哪个男人这样随便唐突地对她说话?她几乎要起反感了,但到底也没有怎样。事后回过头来想想,当又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胡兰成对他“涉笔成趣”的轻言撩拨颇为得意,从后面他与另几个女人的关系中可以看出,在没有经验的女子面前他常有这种从容自信,若即若离的撩拨也是他的惯伎,甚合他落拓不羁的名士做派;而后来他与张爱玲有了那样一层关系,忍不住回过头来自赞一回,说“这一声就把两人说得这样近”,似乎这一问也是他在两人关系中出奇制胜的得意之笔。
这一问也只是出于他的名士派积习。第一次见面之后,胡兰成有惊奇之意而并无多少爱慕之情。他甚至并不觉得张爱玲漂亮--张爱玲貌不惊人,看上去似还不及照片给人的印象;他也不觉得她有何招人喜爱之处,她的文章才华毕露,在人前却毫不聪明外扬。假如没读过她的作品,不了解她的家世,即使在街上擦肩而过,胡兰成也不会特别注意到她。但是胡兰成此前满以为读其文已知其人了。他走南闯北几十年,见过些场面,阅人颇多,当然自负知人论世是虽不中亦中的,而今张爱玲的出现将他的既成概念统统打翻。张的文与人,他的猜度与实际之间的反差皆过于触目,令他惊异。不言其他,单是这份惊异就已经足以促他第二天急急地再度去叩张爱玲的家门了。
这一次张爱玲是在自己的房里迎他,穿了宝蓝绸的袄裤,戴着嫩黄边框的眼镜。她请周瘦鹃喝茶,她姑姑坐陪,周说那是在一间“洁而精”的客室,或许是她们姑侄二人共用的客厅。张爱玲的房间更见她的口胃性情,自又是一番景象。“一种现代的新鲜明亮几乎是带刺激性”,令满室陈设俱显出华贵之气。加上她的一身装束,胡兰成见了心中大感惊讶,大约前一天他得到的印象与此情此景又对不上号,大大出乎他的意料。这回是轮到他感到不安了。据说偶尔有文化人到这里来勉强坐得一回,也是但觉“不可逼视”,不可久留。胡兰成更觉这里有“兵气”。
不过胡兰成倒是一坐坐了很久。仍然是他侃侃而谈,大谈理论,又讲他的生平。张爱玲只管坐着静听。但这里是她的天地,她熟悉的环境,她到底不似上次的拘谨。胡兰成也在文人圈中,当然知道《孽海花》中影射李鸿章、张佩纶的那段掌故,遂问到此事。张爱玲把她祖母亦即书中那位李家女才子的诗抄给胡看,辨正说她祖母作诗并不高明,这一首也是她祖父改过的。胡兰成听了对张又有一份佩服,觉得她肯这样破坏佳话,这才写得好小说。
然而胡兰成自己是喜欢而且愿意制造佳话的。他出身寒门,做了高官也是贫儿暴富,如寻常旧文人一般,对门第出身暗自还是有讲究。他虽要做脱略状,不止一回称他更不自比张佩纶云云,骨子里却是不能免俗。后来他逢别人夸耀门第,便要抬出张爱玲的贵族出身来镇人,颇为自得。在南京时他又曾专门去踏看张家老宅,于废池颓垣、残砖瓦砾之中遥想张家当年的亭台楼阁之胜。他当然把他同张爱玲这位不世才女又兼名门之后的情缘视做可风可诵的佳话,常常在人前说起。他之倾慕张爱玲,她的家世令他惊羡,觉得脸上有光,也是一个不大不小的诱因。
这次会面,张爱玲还说到她听说胡入狱后与苏青一起去周佛海家打探奔走的事。胡兰成听了又是大感诧异,感激之情还在其次,他没想到张对政治会这般幼稚可笑,异想天开:且不说他与周佛海素来气味不投,身属两派(周自领“周佛海派”,胡是“公馆派”;后周暗通重庆,胡却是与日本人关系密切),宦海风波又岂是她能过问插足的。他又没有想到与他素昧平生,很少出门的张爱玲会对他大起关心。而今他刚刚出狱,正当落难之际,不禁要想到当年张佩纶发配热河归来,一介囚徒,待罪之身,却有中堂大人的千金做他的红颜知己,他这一番过往,正堪比拟。以他风流自赏的名士习气,日后他还要想他与张佩纶一般,也是已届中年,比小姐大了许多,也是已有妻小(只是张原配已过世,而他的发妻虽亡故,却已经续娶),同时他主持《中华日报》,书生论政,时时搅起轩然大波,似乎也是个“言官”的身份,“直言不讳”,又俨然是个“清流党”,而他两次下狱,似乎也像张佩纶一般命途多舛。
那日回到家中,胡兰成给张爱玲写了第一封信。前次相会他将人比文,印象大跌,“竟是并不喜欢她”,惊异、怜惜,多少有居高临下之意;此次相会,张在她的背景中出现,二人的位置纵不说是互为颠倒,至少也是大大调整,而谈话亦由浅渐及于深,他惊异之外更有了欢喜,竟也生出攀附爱慕之心。这封信写得有似“五四”时代的新诗,张是才女,他又满腹苏小妹三难新郎一类的佳话,要博张的好感,在信中卖弄才情是可以想见的,写毕胡亦自感得意。
张爱玲读信后大为惊奇。她素不喜“新文艺腔”,嫌其矫揉造作、幼稚可笑,换了别的人写一封“五四”新诗味道的信或情节来,她会弃之不顾,或者大大地寻一番开心。然而写信的是胡兰成,并非文学青年。他年近不惑,是有名的政论家,又是在政坛上打了几个滚的人,写出这样幼稚笨拙的信来,这又当做何解?但是信中称张爱玲“谦逊”,却很中她的意。认识张爱玲的人对她都有冷漠孤傲的印象,没有谁会道她谦逊,她却自有--至少是自认有--一种对现世、对人生的虔敬,这也就是她所解的“谦逊”。胡兰成才见了她两面即出此语,也许与张的怯扬、静默不语给他留下的印象不无关系,但张爱玲是高兴的。她在回信中说胡“因为懂得,所以慈悲”。“懂得”二字在张爱玲的词典里非同小可,似比寻常所谓“理解”还更深一层,她对“懂得”犹为看重,轻不许人。茫茫人海,又有几个解人?--她对胡兰成已是油然生出知己之感了。
这以后胡兰成每隔一天必要登门去看她。可是去得三四趟,张爱玲忽然变得烦恼,且生出凄凉之意。她显然已觉难以把握自己的情感和两人之间的关系,无法向自己解释也无力面对两人的这段交往--交往既深,她已是难以淡然处之。也还谈不到长远的打算,也未及顾到具体的问题,单是澄清自己的感情就大是难事。张爱玲不是苏青,很难做到全部投入,临事必要想个明白,求个“恩怨分明”,这一次却是身陷其中,难以决断。
她送了张条子给胡兰成,要他不要再去看她。胡兰成阅人既多,对男女之间自然更有经验,对张情绪的骤变不难猜出大概,但他是个脱略自喜的文人,不愿负责任,也无心为张设身处地。他权作不知,接条的当天就又去看她,不解释,也不作表白。张爱玲对胡兰成已萌生恋情,请他不要登门出于心烦意乱,对自己的感情无奈,见他仍来看她,心里只有高兴,似乎不言中亦有一种证明。以后胡兰成索性天天都去看她了。
不久以后,有一次二人见面时,胡兰成说起登在《天地》上的那张照片,第二天张爱玲便取出这张照片相赠,她在相片的反面题了辞:
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
在张爱玲,这不啻是石破天惊之语。她对现世生活有端然的虔敬,对世人也自有一份敬重谦逊,但这“现世”、“世人”皆是无方之物,面对了一个个具体的人,她多的是矜持。以她的矜持,她何曾在哪一个人面前有过如此的谦卑?这张照片直可视做她以心相许的定情之物。
从初次见面到赠送相片,胡、张二人在极短的时间里已经结下了不解之缘。张爱玲此时尚不满二十三岁,尽管笔下皆是痴男怨女恋爱婚姻,本人却是从未有过恋爱的经验。她寻常足不出户,极少与男人打交道,也许她头一次与胡见面,与一个男子单独在一起,面对面坐了五小时,在她就是前所未有之事。胡兰成比张大十五岁,至少已经结过两次婚,但都是家长之命,媒妁之言,从未有过这般浪漫颠倒的恋情。两人出身不同,经历悬殊,性情互异,生活在全然不同的圈子,其相逢相赏相爱亦有偶然。最初的交往简直就是相互间一连串的惊异。惊异之中有吸引,有莫名的兴奋,二人的关系从一开始就不是平实的。
然而恍惚的兴奋中也透出凄凉之意,张爱玲宛转幽怨说“懂得”,说“慈悲”,说自己“低到尘埃里”,细若游丝地泛出悲凉之音。难道她在爱意没顶之际已经预感到未来的结局?--已得其情,哀矜难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