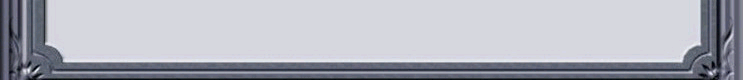第十七章 欲仙欲死
有个村庄的小康之家的女孩子,生得美,有许多人来做媒,但都没有说成。那年她不过十五六岁吧,是春天的晚上,她立在后门口,手扶着桃树。她记得她穿的是一件月白的衫子。对门住的年轻人,同她见过面,可是从来没有打过招呼的,他走了过来,离得不远,轻轻地说了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她没有说什么,他也没有再说什么,站了一会,各自走开了。
就这样就完了。
后来这女人被亲眷拐了,卖到他乡外县去做妾,又几次三番地转卖,经过无数的惊险的风波,老了的时候她还记得从前那回事,常常说起,在那春天的晚上,在后门口的桃树下,那年轻人。
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唯有轻轻地问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
张爱玲这篇题作《爱》的小品空灵飘忽,不着痕迹。她给了我们一个辛酸的故事的梗概,却是为了替她所理解的“爱”(比“爱情”的意思更丰富?)作注脚。这里当然没有新文学作家赋予爱情的神秘浪漫的色彩--爱不过是偶然的相逢与相逢留下的遗响,只是这个故事是否也意味着,爱本身就包含着悲苦与怅惘?
谁也不会将故事中的女孩去比张爱玲,但对爱的理解以及这里面寄托的遐思、感慨又千真万确是属于她的。“千万人”、“千万年”中的邂逅相逢亦不过是偶然的巧遇,然而遇见的居然正是所要遇见的人,“偶然”也好似成了宿命,成了奇迹。纵然是聚而又散,纵然不过是擦肩而过,对这千万千万中的巧遇也应有无以明言的珍重与感激--这也许就是张爱玲对现世的虔敬?巧的是,此文发表于1944年4月,也就是说,它写在她与胡兰成刚开始恋爱的那段时间里,而且那个故事她正是从胡兰成口中听来的,故事中的女孩就是胡的岳母(因她是胡发妻玉凤的庶母,胡又算是入赘俞家,故又称她“庶母”)。参看《今生今世》。胡兰成岳母的经历与《爱》中那女孩的身世一模一样。
但是她对恋爱,对恋爱中的人还有其他的解释,有未来的迷惘,也还有今日的良辰美景,“现在还是清如水,明如镜的秋天,我应当是快乐的”。她在《自己的文章》中为她只写男女之情辩护,拿恋爱和战争、革命作比:“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也更放恣的。战争与革命,由于事件本身的性质,往往要求才智比要求感情的支持更迫切……和恋爱的放恣相比,战争是被驱使的,而革命则有时候多少有点强迫自己……恋爱……是放恣的渗透于人生的全面,而对于自己的和谐。”恋爱本于人性之常,是人而非超人,所以“素朴”;她又几次用“放恣”,因为恋爱中至情至性得以无所顾忌地展露,本于常却又能超于常,逞意而行,不知所止,这里面就有“撒手”、“飞扬”之意。张爱玲还曾对友人这样谈到爱情:“一个人在恋爱时最能表现出天性中崇高的品质。这就是为什么爱情小说永远受人欢迎--不论古今中外都一样。”见林以亮:《张爱玲语录》。与胡兰成的热恋正使张爱玲体验到一种她从未领略过的飞扬的喜悦。
张爱玲到底不比她笔下那些恻恻轻怨、脉脉情思的女子,她也曾为爱而烦恼,有过凄苦之意,但一旦有了决断,也便不管不顾。
他们谈情说爱的方式似乎在二人最初的接触中已经定下了。张爱玲不像一般新派的人物,要以亲近自然来证明情调的高雅浪漫,于都市的街上“道路以目”,在她要比游山玩水,刻意去寻胜搜奇,还更来得自然、惬意;而不必花前月下,不必山盟海誓,单是共处一室,相对笑语,也就有不尽的喜悦。胡兰成也不喜出游,于风景不留心,且二人在一起谈艺论文,也令他温习到一种他所喜欢的才子佳人的情调。所以他们在一处哪里也不去,多的是一席接一席的长谈,只是说话说不完,一次次见面从早到晚就这样过去。胡兰成虽宦海失意,但不甘寂寞,还同“朝”中有千丝万缕联系,又要与日本人保持密切的接触,所以平日还是住在南京。但他每月必要到上海住八九天,而一到上海,不回美丽园家中,先就去看张爱玲,一直要盘桓到黄昏时分才打道回府。而且他现在已是反认他乡作故乡,一踏进张爱玲的房间便要说道:“我回来了。”
张爱玲在大欢喜中,没有了初见时的拘谨,在胡兰成面前她可以比在外人面前更多更自如地袒露自己:从孩童似的幼稚到与年龄不相称的成熟世故,从女学生式的零碎喜好到对于尘世生活庄严的感念,从大俗到大雅;知道胡倾心于她的聪明才华,她更有自信将她的奇思妙喻、如珠好句一一搬演;既然许为知音,从人生到艺术、历史、戏文、凡人琐事,无不可谈,她也皆有可谈。胡兰成不再唱独角戏,张也不再专司听众之职。而一旦张爱玲打开腹笥张了口,胡兰成便顿觉自己言语乏味,毫无机趣,一次又一次领教张爱玲一开始就让他感到的惊奇。
最多的话题还是文学艺术。胡兰成说张爱玲“把现代西洋文学读的最多”,张也时常将萧伯纳、赫克斯莱、劳伦斯等人的作品讲给他听,胡没有喝过洋墨水,张的洋文又是极好,他自然惊服。张又与他一同看画册,谈音乐,她自己的画就别有意趣,音乐和钢琴她从九岁学到十五岁,不论喜与不喜,她皆能谈得头头是道,活色生香,而单是这份淑女式的教养,也就令胡兰成羡慕。
但是他没想到讲论他自以为可以自恃的中国古代文学,他竟也不是张爱玲的对手。张读小说心细如发,一些传神的字句,躲在套语滥调的旮旯里旁人万不会留意,她却是脱口便出,她知道《金瓶梅》中写孟玉楼是“行走时香风细细,坐下时淹然百媚”,就为“淹然”二字好;她又一口报出《水浒传》里描写九天玄女娘娘的句子是“天然妙目,正大仙容”,谁看《水浒》会注意到玄女的长相?胡兰成自愧不如。他古书读的不少,时而也作旧诗,两人一道读《诗经》,有一首才读了开头两句“倬彼云汉,昭回于天”,张爱玲惊道:“啊!真真的是大旱年岁。”读古诗十九首,念到“燕赵有佳人,美者颜如玉,被服罗裳衣,当户理清曲”,张诧异道:“真是贞洁,那是妓女呀!”又同读子夜歌,有两句是“欢从何处来,端然有忧色”,她叹息道:“这端然二字真好,而她亦真是爱他!”胡不得不叹服,枉读诗书,竟是都未读懂。这也不干学识,尽有名家的考订解读,他是不知也还有这样不阻不滞、直见性命、与世人万物照胆照心的读法。
张爱玲读书又如游戏,《诗经》中这里也是“既见君子”,那里也是“邂逅相见”,她看了高兴,说:“怎么这样容易就见着了!”汉乐府诗中有一首写一男子身在异乡,店家主妇替他洗补衣裳,“夫婿从门来,斜倚西北眄”,张念到这里就笑道:“是上海话眼睛描发描发。”下面是“语卿且忽眄,水落石自见,石见何磊磊,远行不如归”,她又诧异感叹道:“啊!这样困苦还能滑稽,怎么能够!”她单是目接神遇,解来皆是无由而皆能得其神韵,胡兰成不禁要叹她“其人如天”,两人同看一书,书上的字句竟是“像路上的行人只是和她不住点头打招呼”。
但是最令胡兰成吃惊的还是张爱玲不受名词术语禁治,不为定型情感态度拘囿的头脑,对于常人思想中的应该不应该,对于种种来头大的或是时髦的理论,她好像已是“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胡兰成尝与炎樱谈话,炎樱也是思想没有多少束缚的,他听了也觉新鲜,但那似乎是真正的“童言无忌”,他说事实是如此,她道:“真可怕!”他说社会本来如此,她道:“怎么可以这样愚蠢!”全是孩童式的责怪,与他的逻辑不接茬。张爱玲的种种“离经叛道”之论却不是出于无心,也不是年轻人盲目的反叛,它们有其内在的理路,有自身的完整,有她过人的理性为依凭。
张爱玲不喜理论,不喜体系的严密,但她要理性。胡兰成吃政论的饭,自称是“受过思想训练的人”,凡事“皆要在理论上通过了才能承认”,所仗恃的也是理性。但他发现,张爱玲的理性比他还更来得彻底。真正的理性面前没有偶像,没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没有“绝对”的存身之地。胡兰成面对她的这个没有高下森严秩序,没有只能如此、不可如彼种种规矩的自由世界,开始是惊异瞠目,不习惯,后来却是循循受教,觉得自己也得了解脱。
他在香港时买了贝多芬的唱片来听,听后不喜,但不敢说音乐不好,因为贝多芬被尊为乐圣,他只能怪自家水平低,把唱片拿来一遍遍硬着头皮下工夫听,必要听出道道,做文化人身份的证明。张爱玲坦言她不喜,不仅贝多芬,西洋隆重的东西如交响乐、壁画、悲剧她都不喜,举世公认的大作家莎士比亚、歌德、雨果,她都不好,而且是理直气壮的不喜不好。看西洋画册,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基罗这些古典大家她一页一页不停地翻过,偏是看到塞尚画中那些小奸小坏的人物,她却要细加玩味,对着画家不同时期为妻子作的几幅肖像,她更要登堂入奥体贴入微猜度猜度二人的心理。文学革命以后中国文坛西风劲吹,托尔斯泰、歌德、莎士比亚等西方名家代替曹雪芹、吴承恩、施耐庵,成为作家心目中的偶像。胡兰成素不敢对权威质疑,此时大约受了张爱玲那种百无禁忌的态度的鼓舞,有一次竟大着胆子说出《红楼梦》、《西游记》胜过《战争与和平》或《浮士德》,自以为是冒了天下之大不韪,不想张却无需这种戏剧性的夸张姿态,只很平常地道:“当然是《红楼梦》、《西游记》好。”
胡兰成后来悟出张爱玲的大胆,她的理性原也简单,她的理性就是情感,情感就是理性,二者打成一片,底子就是“不自欺”--忠实于自己。她为人行事也是如此。历来读书人耻于言钱,孔方兄讥为阿堵物,正经说来便浑身不自在,张爱玲“一钱如命”,声称只知钱的好处;文人雅士不愿与引车卖浆者流为伍,肯于抬举“第四阶级”的激进文学青年也还要对小市民表示鄙薄不屑,张爱玲则向小市民认同,对那些被视为垃圾的小报、章回小说读得津津有味,而且理直气壮。文人的另一标志是多愁善感,古人临风洒泪、对月长叹,“五四”以后则换了西式的浪漫感伤,又有一套规定情境。应该说张爱玲是敏感之人,甚或可说是病态地敏感,但她不要做作藻饰。胡兰成因与妻子离异,要做感伤状,那一天到她处面上有泪,似是对夫妻一场而至于分离,终觉可伤,张爱玲却不肯勉强自己,不陪他落泪,也不为言宽解,她不同情就是不同情。
胡兰成竟是对张爱玲入迷了,他简直看她是无所不晓,无般不能。而且他的向往之诚形之于外,一篇《论张爱玲》写得天花乱坠,把张爱玲描画得有如天仙,迥非政论家的手笔,实在令外人大感惊讶:“稳坐政论家第一把交椅”,一向两眼向天的胡兰成何以如此神魂颠倒,如醉似狂?
胡兰成说“天下人要像我这样喜欢她,我亦没有见过”,又言那些赞她,喜她文章的人如同逛灯市,她是她,我是我,终不能像他“喜欢她到了心里去”。这都是真话。他是才子,有那份聪明领略张爱玲其人其文的好处;他又是名士派的人物,他塌得下架子拜倒石榴裙下,而且要演为艳异的传奇佳话。他的周围官僚政客、儒雅君子、骚人墨客尽皆有之,又多是已届中年之人,官有官的威仪,雅士有雅士的清高,君子要摆君子的端方。他当然知道周围的议论窃笑,但他只有更得意,所谓是真名士自风流,他有文人的脱略,做过高官亦可以到小户人家吃青菜豆腐,亦可以随了苏青到街上吃一客蛋炒饭,至于他的这段“奇缘”,旁人的私议笑谈好似只是给他提供风流自赏的机会。
胡兰成的喜欢也并非是浮面的,真有所知所识,他也就有真的拜服。他听张爱玲讲谈时如承大事,好似她句句皆是在泄露天机。与张同看画册,“听她说那一幅好,即使只是片言只语的指点,我才也能懂得它果然是非常好的”。听张说民间的戏文好,他本来不喜,也就觉得有意思。张文章里写民间小调里的鼓楼打更,有江山一统的安定,他对这些东西也就另眼相看。他将他写的论文给张爱玲看,张说这样体系严密,不如解散的好,他当真就不再去为体系操心。
《论张爱玲》一出,立时就有人发现胡兰成的文风有变,而他与张相识后放下专写政论的笔,勉力追随张爱玲的感悟方式,写下许多随笔。他有一篇《瓜子壳》,开头有一段“破题”文字写道:
我是喜欢说话,不喜欢写文章的。两个人或者几个人在一道,随意说话,题目自然会出来,也不必限定字数,面对面的人或是挚友,或是仇敌,亲密或是泛泛之交,彼此心中雪亮,而用语言来曲曲表达,也用语言来曲曲掩饰,有热情,有倦怠,有谦逊,有不屑,总之是有浓厚的空气。倘是两个十分要好的人在一道,于平静中有喜悦,于亲切中有一点生疏,说的话恰如一树繁花,从对方的眼睛里可以看出最深的理解和最高的和谐。又倘是夹在不相干的人群里,他知道自己是为谁而说话,知道有谁在替他辩护,也有一种高贵的感觉。
然而写文章,是把字写在白纸上,没有空气没有背景,所以往往变成自说自话。那么把谈过的记录下来怎样呢?记录下来也不过是瓜子壳,虽然撒得一地,可是瓜子仁已经给吃掉了。然而又非写不可,好吧,就拿瓜子壳出来待客。见《天地》月刊八、九期合刊(1944年5月),署名“兰成”。
命意笔致都追摹张爱玲的路数,虽然没有张的神采亦且显得嗦。他在此时对文艺感兴趣,写过不少这方面的文章,而其中观点几乎是对张爱玲见解亦步亦趋的演绎。这当然还是细小之处,最重要的是,张爱玲的百无禁忌使他得了解脱,影响及于他的思维方式、人生信念,以至于他要说,“我在爱玲这里,是重新看见了我自己与天地万物。”自传开首的序中就要交待“《今生今世》是爱玲取的书名”,书中又有对张的感激之言,说没有她,他亦写不出那部《山河岁月》。《山河岁月》是胡的一部纵论中国历史文化与“天下大势”的书,他避居温州时曾以化名将其中某些部分寄给梁漱溟看,梁颇为赏识,亦以此有邀他北上之议。胡对此书的自矜自得,自不待言。而他自谓没有张爱玲他写不出这样一部看似与张风马牛不相及的书,亦可见张对他的影响之大。
张爱玲年岁比胡兰成小了许多,经历的事情少,生活的天地狭窄,按照常理,在他们二人的关系中,她应该是受影响更多的一方。事实却恰好相反。胡兰成时常发一通议论过后想想不对,便告张爱玲:“照你的样子就好,请不要受我的影响。”张笑答:“你放心,我不依的还是不依,虽然不依,还是爱听。”他又能影响她什么呢?热恋或许多少改变了一点她的孤僻冷漠,但是至少从人生观到审美趣味,我们看不到胡兰成影响的一丝痕迹。
然而热恋中的张爱玲是欢悦的,她需要的不是一位导师--不管是人生导师还是文学导师,以才女的身份,她要的是一个能欣赏她、懂得她的知音,以女人的身份,她要的是一个疼惜、呵护她的男人。有研究者不无根据地指出,张爱玲一派内省内倾,恰似“水仙子”型人物,水仙子临水自照,顾影自怜,心理学范畴的这一概念除自恋之外又有自我膨胀、自我中心、利己、自私等意。李焯雄:《临水自照的水仙》,见郑树森(编):《张爱玲的世界》,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89,103页。而前面对张的描述相信已能使人对她产生这样的印象。她不仅孤芳自赏,也希望别人欣赏她。就张爱玲对婚姻恋爱的态度而言,如果是一桩平实的婚姻,她也许不会过多地有这方面的要求,但恋爱与婚姻不同,恋爱是生命的“飞扬”与“放恣”,能够让她“放恣”的人应该助她完成临水自照的心理环境,具体地说也就是应该接受一个出色的欣赏者的角色。欣赏她的什么?当然是她的全部:她的才、她的貌、她的喜好、她的趣味、她的一言一动、一颦一笑。
她最可以骄人的还是她的聪明,胡兰成恰是个聪明人,不仅懂得她,还能将她的意思引申发挥。他是一个悟性很高的听众,而且还不仅仅是听众,因为懂得,他的欣赏赞美之意就格外地令她感到熨帖。与他接谈,张爱玲喜之不胜,以至于有时忍不住要说:“你怎这样聪明,上海话是敲敲头顶,脚板底也会响。”他是她的崇拜者,又岂是寻常的崇拜者可比?历史上尽有男人仰慕才女的佳话,但有几人似他这般颠倒?20年代有李惟建崇拜黄庐隐,终成佳偶,那人才情稍逊,年岁也比庐隐小,圈内人说笑要戏称“小男人”,胡兰成不比毛头小伙子,纵不是伟丈夫,也是自有身价的人,何况他又是个两眼向天的才子。
张爱玲曾说女人在男人面前会有谦虚,“因为那是女性的本质,因为女人要崇拜才快乐,男人要被崇拜才快乐”。她大约没有把自己算入其内,但她毕竟也是女人,至少她不要在她面前唯唯诺诺、诚惶诚恐,只知做低伏小的男子,若是俯就,做女皇也还是委屈,哪来“飞扬”?这个人必得也有她可以欣赏可以仰慕之处--胡兰成见多识广,阅历丰富,倜傥不群,正是合适的人选。在他面前她可以有欢然的顺从,这样的顺从在她恰是女性需求的满足,于是顺从也成了“放恣”,屈抑怨意中也有欢喜。所以她有时不无快意地将自己安排在爱慕谦卑的位置上,说自己“很低很低”,要从房门外悄悄窥看里面的胡兰成,写出虔敬的喜意:“他一人坐在沙发上,房里有金粉金沙深埋的宁静,外面风雨淋漓,漫山遍野都是今天。”
唯其她对胡也有顺从,有爱慕,甚至有屈抑,接受他的香火供奉才更令她喜不自胜。她不是那种一味浪漫的女人,她也要一个平凡的女人要求于一个好男人的那些东西。胡兰成则是风流秉性,如果他愿意,他就可以是一个讨女人欢心的能手。他但凡有空就守候张爱玲身边,与她谈笑,陪她逛街散步,拿她喜看的书籍画册玩物来与她同看,张将她的小玩意搬出来看,他虽要表明自己是男人,不喜女孩的把戏,也还是陪侍在侧。他喜赞张爱玲的美,有次接了张的话说她就是“正大仙容”,又称张的绣花鞋漂亮,偶然瞥见张接茶的动作,也惊叹她姿势的艳,他赞是赞得有来头,决不肯落俗套。他挡去许多无为酬酢,将张什袭珍藏,不让俗人来扰;每肯介绍识面,他在一旁则又都是“如承大事”。张爱玲从小到大,何时得到过这样的宠爱?而这一切来得又是这样突然,令她由欢喜生出恍惚之感,有时禁不住只管问:“你的人是真的么?你和我这样在一起是真的么?”又要道:“你这个人嗄,我恨不得把你包包起,像个香袋儿,密密的针线缝缝好,放在衣箱里藏藏好。”欢喜疼惜,情见乎辞。
人逢喜事精神爽。在同胡兰成热恋的这段时间里,张爱玲逸兴湍飞,意气扬扬,她的写作维持着高产,而且可以说是高质。小说又有《红玫瑰与白玫瑰》、《桂花蒸阿小悲秋》等上乘之作,而这些作品在《传奇》诸作中也最能体现她小说风格的独特完整(《沉香屑》、《金锁记》等借用旧小说的套路,尚食而未化,不能说完全是自出手眼);散文最见性情心境,更是手挥目送,议论风发,《流言》中除初以英文写成的几篇外,重议论而最洒脱自信,最见才气的几篇如《谈音乐》、《谈跳舞》、《谈画》等篇均作于此时。将这些文章与《今生今世》中胡记下的某些内容相对照,可知文章的议题也就是那时两人谈论的,这些谈话显然给张带来了灵感,激发了她的想象。胡兰成的许多随笔无疑也是源于这些谈话。她本是有笔如椽却口齿艰涩,而今正当大欢喜中,她的不善言辞也不见了踪影。与胡兰成接谈,她感到轻松欢然,时有灵感忽至,好句如珠。胡兰成的惊羡也给她更多的自信,她在他面前相信任何物象意念她都能用词语形容尽致。
谁也不会荒唐到以为张爱玲的才情要依赖胡兰成的爱情和赞美才得以维持不坠,但这段热恋带来的欢悦使她更加才气焕发,却也是不争的事实。
如此男欢女爱,一个以为得了红颜知己,一个以为得了闺中良伴,其乐融融,不似人间。胡兰成似乎在一个绝妙好词中找到了对这惊喜、欢然之情的最佳表述--“欲仙欲死”。
但是他们毕竟是凡人凡胎,身在红尘。张爱玲与胡兰成的关系,以传奇的眼光去看,是天上人间,艳异佳话;以政治的立场去断,有人要觉得有玷清白;而从世俗的眼光看去,在冷眼旁观的世态剧里,它不过是一场婚外恋。以她对政治的态度,胡兰成的身份她可以不以为意,甚至对他日后的处境暂且也可以“不愿意看见什么,就有本事看不见”,但是作为一个女人,她不能不面对胡已有妻室这一事实。在胡兰成、他的妻子、张爱玲这个准三角中,胡以他一贯的名士派作风处之泰然,若无其事,其妻是不能忍受,张的处境却是最为尴尬。不管表面上如何,她不可能不想。胡曾问起她对婚姻的态度,她答不去多想,等到要结婚的时候就结婚,也不挑三拣四。但那是过去,现在她是在恋爱,当然有别样的期待。
有一次她不无幽怨地对胡兰成说:“你说没有离愁,我想我也是的,可是上回你去南京,我竟要伤感了。”她也想到婚姻,在信中写道:“我想过,你将来就只是在我这里来来去去亦可以。”胡又有许多女友,乃至于挟妓游玩,张也表示大度,不会吃醋,倒愿意世上的女子都喜欢他。愿天下女子都喜欢他是真,但爱情是排他的,过了界她岂能无动于衷?后来她与炎樱在《双声》中就说起过,在男女关系上,她免不了妒忌之心。
张爱玲的难堪之处在于她做不到胡兰成那种无可无不可,一场游戏一场梦的洒然,她还是企望世人幸福安稳的婚恋,但是以她高傲的心性,以她的矜持要强,她再不会去勉强胡兰成,那样即使如了她的愿,她也会感到是委曲求全,如此又何谈“飞扬”,何谈“放恣”、生之浪漫?矛盾之中,她只能以对当下的忘情挡开种种不快的念头。胡兰成把张的态度全解作她的不同凡俗,大赞她的“慷慨”--他乐得接受这样的解释,这样他便无需负责,无需歉然,保持他脱略不羁的一贯作风。
准三角中的另一角却不堪忍受了,终而提出离婚。胡兰成在回忆录中对离婚的原委过程含糊其辞,只写他与张爱玲“都少曾想到结婚,但是英娣竟与我离异”,倒像是实际上已被他抛弃的妻子的态度不可思议。不管怎么说,胡兰成的离异使二人的关系不可能维持现状了--他们从恋爱走向婚姻。二人由“少曾想到婚姻”转为议婚嫁,当然是因为没有了那个障碍。但是如果他们都不以结婚为意,他们也可以维持现状。二人中显然张爱玲更希望结婚。胡兰成说:“有志气的男人对于结婚不结婚都可以慷慨,而她是女子,却不能如此。”多少也透露出这一信息。结婚可以有种种不同的动机,为经济,为名分,为爱情,为安全感,第一条张爱玲无需考虑,第二条或者是一因素,但她也是可以我行我素的人,第三条则她当然知道爱情无需婚姻来证明,也不待婚姻做保证,所以最关键的是第四条--她素来缺少安全感,她需要一个家,不是要拴住男人,是一种家的感觉。胡兰成无疑是“有志气的男人”,是“都可以”的,而在离婚之后,按照常理,他若不主动提出此事倒是反常的了。总之,相恋大半年之后,他们结婚了。胡兰成担心日后时局变动张会因这桩婚姻受连累,没有举行仪式,只写婚书为定:
胡兰成、张爱玲签定终身,结为夫妇,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
前两句是张爱玲写的,后两句则是胡兰成所撰,旁边写炎樱为媒证。
这是1944年,再过一年日本人就要投降,在此情势下,他们结婚时会作如何感想?张爱玲真敢存有天长地久的心念?假如是这样,时间也很快就会告诉她,那是枉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