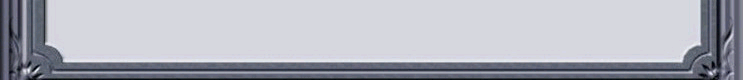第十五章 三人行
炎樱是位锡兰女子张爱玲称炎樱是锡兰女子,胡兰成《今生今世》中说她是印度人,有些介绍张的文章也说她是印度人,或者是从胡处来。不过炎樱当是混血儿,因张爱玲与她谈话说到杂种人云云,曾有一点担心自己说走了嘴的意思,见《双声》。,本名Fatima,中文名字按音译叫做莫黛,“炎樱”是张爱玲为她取的名字。张爱玲在香港并无来往密切的亲朋故旧,港大三年,除了放假,她皆在校园中度过。终日与同学相处,不论交情深浅,总该有不少朋友,但她没有。她似乎是圈外之人,只是以她略显挑剔的冷眼把周围同学一一看了个透。独对炎樱她不以冷眼相向,反倒亲如手足。《烬余录》中将男男女女的同学都嘲讽挖苦惨了,轮到炎樱的却是好话:“同学中只有炎樱胆大,冒死上城去看电影--看的是五彩卡通--回宿舍后又独自在楼上洗澡,流弹打碎了浴室的玻璃窗,她还在盆里从容地泼水唱歌,舍监听见歌声,大大地发怒了。她的不在乎仿佛是对众人的恐怖的一种讽嘲。”
张爱玲发奋攻书之余,偶亦出校门去看电影、逛街、买零食,做伴的往往就是炎樱。有时与熟人有些来往,两人也是一道。张爱玲小说中一些人物,如《连环套》中的霓喜、《沉香屑:第二炉香》的男主公罗杰,其原型就是与炎樱一同认识的。炎樱的家也在上海,所以放假回家两人也多是结伴而行。张爱玲敏感却不多愁,不哭则已,要哭就是号啕大哭。据说她只大哭过两回,其中的一回便是某次港大放暑假,炎樱没有等她就回了上海,她平时并不想家,这次不知怎么觉得落了单,倒在床上大哭大喊得不可开交。
炎樱与张爱玲有同好,两人都爱绘画,都喜欢服装,都善领略日常生活中的情趣。在港大时她们就一起作画。张爱玲勾图,炎樱着色。张爱玲又为炎樱画过肖像,还颇得人赞赏,他们的一位俄国教授居然要出五元港币买下。两个人陶醉其中,全忘却身边的连天战火。事隔多时,张爱玲还记得一幅画里炎樱的用色,说那不同的蓝绿色令她想起“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两句诗。《传奇》初版的封面不知是何人设计,或者也征求过张本人的意见,所用蓝色与张联想到李商隐诗句的蓝绿色或者有几分接近。炎樱不是画家,没有画作发表,但是她为《传奇》设计的封面仍使我们有机会看到她的才华。《传奇》再版时用的封面就是炎樱起的稿,张爱玲说她“为那强有力的美丽的图案所震慑,心甘情愿地像描红一样地一笔一笔临摹了一遍。”《传奇》增订本的封面也是张爱玲请炎樱设计的,借用了晚清的一张时装仕女图,画着个女人在桌边玩骨牌,旁有奶妈抱着小儿,安稳静谧有“古墓的清凉”,然而身后突有一面无五官、现代装扮、比例不对的人形出现,探身朝里张望,画外人的有似鬼魅与画中人的浑然不觉造成一种怔忡不安的气氛。这个封面较前面的那一张更见出色,构思巧妙,不落窠臼,与书的内容配合得天衣无缝。
炎樱的画见出她的聪明才气,张爱玲也特别欣赏她的聪明。张爱玲自己的聪明常与她的冥想苦思分不开,炎樱则更有一种不假思索的急智,她的聪明以此也更多散落在脱口而出的俏皮话里。张爱玲觉得任其随意挥霍掉实在可惜,便记下一些在她看来是机趣天成的妙语,又描摹说那些话的环境,与读者共赏,《炎樱语录》、《双声》等就都是的。事实上,她常向炎樱身上找灵感,特别是一时找不到东西的时候--很可能也就是编辑索稿甚急之时,炎樱便被拉了来作题材,沦陷期最末的一段时间里的散文,除上举《双声》外,《我看苏青》、《吉利》、《气短情长及其它》等,也都写到炎樱,几乎是无炎樱不成篇。因为常与张爱玲同行同止,又常在张的散文中出现,她也成了文人圈中熟知的人物,像诗人路易士(即后来的纪弦),便也以她为题材写过文章。
炎樱不谙中文,中国话说不了几句,汉字也识不得几个,但她对中国人的生活、中国的艺术充满了好奇,比如,她跑去听苏州故事(张爱玲告诉她是苏州评弹),居然也听得津津有味。因为是在完全不同的背景下长大的,她觉得中国的种种事物特别有趣,也有更多的讶异。这些地方,当她与张爱玲谈论着的时候,对张必有所触发,张爱玲对中国人生活的张看,里面有些或者借重了炎樱好奇的眼光,至少我们可以想象她须时常向炎樱解说她所不明了的中国人的生活和艺术,并且要对付炎樱刨根究底的追问,而这同时就是对自己的认识的澄清。
炎樱也想当作家,曾将自己的随感和身边趣事写下来。不会中文不要紧,张爱玲欣然效劳,将炎樱的好几篇小文《死歌》、《女装、女色》、《浪子与善女人》等从英文译过来,替她在《天地》、《苦竹》等杂志上发表。文中少不了要提到张爱玲,可以让人想起当时她们在一起的情形。比如《浪子与善女人》中写到张爱玲成名后,她们上街变得招人耳目了,在街上走着,就有一群小女学生跟在后面唱着:“张爱玲!张爱玲!”大一点的女孩子也回过头来打量,有一次更有一个外国绅士尾随其后,慌张叽喳着,状甚可怜,原来是嗫嚅着要请张爱玲在他的杂志上签名,炎樱简直当是个乞丐,差点要掏零钱闹出笑话。更有趣的是下面的一段慨叹:“从前有许多疯狂的事现在都不便做了,譬如我们喜欢某一个店的栗子粉蛋糕,一个店的奶油松饼,另一家的咖啡,就不能买了糕和饼带到咖啡店去吃,因为要被认出,我们也不愿人家想着我们是太古怪或是这么小气地逃避捐税,所以至多只能吃着蛋糕,幻想着饼和咖啡;然后吃着饼,回忆到蛋糕,做着咖啡的梦;最后一面啜着咖啡,一面冥想着糕与饼。”炎樱:《浪子与善女人》,载《杂志》,1945年7月,93页。炎樱的文章不事雕饰,不讲究章法,轻松俏皮,如闻其声,有时就像女学生快嘴快舌,在抢着说话,前言未毕,后语又至。有些地方,因为与张爱玲情味相投,所写常常可能就是二人闲谈的话题,又因是张的翻译,感觉、文风笔致,都有张爱玲散文的影子,比如这一段:“有一张留声机片你有没有听见过,渡边×子唱的‘支那之夜’。是女人的性质的最好的表现,美丽的、诱惑性的,甚至于奸恶,却又慷慨到不可理喻。火星的居民如果想知道地上的‘女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只要把这张唱片奏给他们听,就是最流畅的解释。那歌声是这样热烘烘的暖肚的,又是深刻的、有利爪抓人的,像女人天生的机灵,同时又很大量,自我牺牲到惹厌的程度。”炎樱:《浪子与善女人》,载《杂志》,1945年7月,93页。因为见解、趣味太合拍了,她谈服饰,谈艺术,谈女人,竟可视为张爱玲的补充,像《无花果》里“中国女人在男子大众的眼光里是完结得特别快”,驳将女人形容为花的比喻,称她见到的女人多是无花果,“花与果同时绽开了,果实精神饱满,果实里的花却是压缩的,扭曲的,都认不出是花了”之类的议论,都闻得见张爱玲的气息。
张爱玲喜在人前说炎樱的好话,知道亲近的人如姑姑、胡兰成也喜欢她,她便很高兴。炎樱自然与张爱玲亲近,而且不用说也极佩服张的才华。她因语言关系读不了张爱玲的作品,但其中情节人物张肯定都对她说过。因为张爱玲朋友圈子中唯她一人是过去的交情,她似乎是张最忠实的捍卫者。张在公开场合露面,她几乎次次都很乐意地随了去“保驾”、捧场。纳凉会上,先是众人围着李香兰提问,李香兰俨然主角,似是很有风头。后有人向张问一问题,张尚在思索,炎樱立时替她抢场子,声音响亮地插上一句“旁白”道:“可以听得见她的脑筋在轧轧转动”,言毕又用手做出摇开麦拉的架式。又有一次是在《传奇》座谈会上,与会者赞美之余多说张的作品整篇不如局部,单个的句子又更见其好。炎樱又替张辩道:“她的作品像一条流水,是无可分的,应该从整个来看,不过读的人是一勺一勺的吸收而已。”这也许是张爱玲想说而在这场合不便说的话,炎樱直可说是她的代言人了。
事实上从性格上讲,张爱玲与炎樱完全是两种人。炎樱有一次突发奇想,撺掇张爱玲两人一起制新衣装,各人衣服前面都写一句联语,走在街上碰了面会合在一起,忽然上下联成了对--她们两人的性格也有这种相映成趣的互补之妙(炎樱曾戏称她们两人在一起是“很合理想的滑稽搭档”)。张爱玲冷漠好静好独处,炎樱却是热情好动好热闹。张敏于思讷于言,炎樱则虽张说她“俏皮话之外还另有使人吃惊的思想”,却滔滔不绝说上许多理论,结果只像一阵风来去得无影无踪,好似是智力的游戏。张的矜持也恰与炎樱的毫无心机相对。后者的大说大笑,口无遮拦多少有几分像《红楼梦》中的史湘云。她曾将西方的一句谚语“两个头总比一个好”(意谓两个人比一个人更聪明)篡改作“两个头总比一个头好--在枕头上”,而且这句话是写在作文里,而且看卷子的教授是教堂里的神父。张爱玲戏说:“她这种大胆,任何以大胆著名的作家恐怕也望尘莫及。”
虽说性格判若霄壤,张爱玲却喜与炎樱相伴。她曾说她不喜小孩,但她却喜欢炎樱的孩子气。她们一起谈天说地,从东西文化一直谈到男女私情、妒忌,谈到衣饰,谈到圣诞会上的游戏,相熟的某一个人;她们一起忙《流言》的出版,为选用哪几张照片商议来商议去;她们一起买鞋、做衣服,一起筹划搞时装设计;她们一起逛商店,泡咖啡馆,吃冰淇淋,一起为谁该付多少钱锱铢必较地争来争去……在一起总是兴兴头头。甚至炎樱买东西时硬要抹掉零头,与卖主讨价还价,张爱玲也觉得开心有趣。胡兰成说他们三人在一处时但觉他的笨拙多余,由此也可想见二人到一处有似女学生的聚首,自顾自笑谈不了,将他人晾在一边。
也许炎樱之于张爱玲,比张爱玲之于炎樱更重要。唯有和炎樱在一处时,张爱玲与她自己年龄相称的那一面才得以更充分地显露出来。她们即使谈严重的话题也可以做到轻松,而张爱玲的文章每写及炎樱,笔调也便轻松起来。在炎樱面前,她也许是最放松的,没有了她一贯的矜持:也许是因为炎樱的性情,也许是因为她们相识时毕竟只有十七八岁,总之与炎樱在一起时张爱玲似乎更容易回到,或者说是领略到一种少女的心境、少女的情怀。
如果说同炎樱在一起张爱玲面对的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少女的世界,那么和苏青在一起,她则进入到一个更带世俗气然而也更有人生酸甜苦辣滋味的女人世界。
苏青原名冯和仪,浙江宁波人,比张爱玲大四岁。苏青大学未毕业就承父母之命结了婚,婚后生活颇不顺心,苦闷中遂寄情于写作。她的第一篇文章《产女》投给林语堂系的刊物《论语》,编者将其更名为《生儿育女》,很快在1935年的4月号上登了出来。其后她一发不收,接连写了《我国的女子教育》、《现代母性》、《论女子的交友》、《论离婚》等文章,成为《论语》的撰稿人之一。她的文章多是从自身经历去探讨妇女的命运、权利和义务,文风直白泼辣,不事雕琢,令人感到她是有动于衷,不吐不快。
她丈夫的大男子主义使他不容妻子红杏出墙,即使是文字也罢。苏青也感到忍无可忍,不再坐而论道,真的与丈夫离了婚。
苏青在文坛上出道要比张爱玲早好几年,但她变得大红大紫,人人皆知,却是在上海沦陷以后,“苏青”这个笔名也是这时候起用的,此前她一直署的是本名。在读者当中,她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是自传体小说《结婚十年》,其内容基本上都是她的亲身经历,于夫妇纠葛、姑嫂勃谿、婆媳矛盾之外,也写到性的苦闷,按当时的水准称得上大胆,结果也就如张爱玲所说:“许多人,本来对文艺不感兴趣的,也要买一本《结婚十年》看看里面可有大段的性描写。”抗战胜利后,有报章杂志给苏青加了顶“性贩子”的大帽,这本书就是主要的罪证之一,然而此书反而因此名气更大,到1948年年底,《结婚十年》已出到十八版。
在文人圈子里,苏青出名更倚仗她的散文和她创办的一份杂志--《天地》。或许是受到成名的鼓舞,或许是周围有一帮人喝彩捧场,她在沦陷时期的文章与前相比更是直白无隐,言人所不敢言、不愿言,虽然仍不失其严肃,但有时也就有几分是在卖弄胆子。她曾将孔子的一句名言“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重新断作“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虽然不过是重复“食色,性也”的意思,但因专讲女人,又从女人口中说出,似乎大可演绎成女人离不得汉子,女人心里就想着汉子之类,于是一班名士派文人不禁眉飞色舞,要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了。实际上苏青此语不过道出女人对男人之“爱恨情结”,又兼有几分恨女人自家不争气的意思,但到了一班文人口里,便徒有谐谑乃至轻薄之意。
最初使苏青扬名上海的杂志是《古今》,因《古今》编者实为《论语》的班底,而苏青算得上是《论语》旧人,故也成为《古今》的撰稿人,她也许是该杂志最为器重的女作家,是经常为其撰稿的唯一女性。朱朴搞所谓“朴园雅集”,与会的女性只有她一个。但苏青不是张爱玲,她喜欢社会活动,不满足单是投稿,终在1943年自己办了“散文小说月刊”《天地》。当时社会上风传苏青能办起这份杂志,是凭借了周佛海、陈公博的支持之力。又传她是陈公博的情妇:她曾在伪上海市政府做职员,其时陈公博正兼着伪上海市长,她遂成为陈的“女秘书”之一云云。战时纸张紧张,“陈设法配给她很多白报纸,作家坐在满载白报纸的卡车上招摇过市,顾盼自喜,文化界一时传为笑谈”刘心皇:《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120页。。这段“艳史”是否属实无关宏旨,但周佛海、陈公博对苏青很赏识却是无疑的。苏青可以出入这些贵人的官邸,周、陈及周的老婆周杨淑慧、儿子周幼海均有文字在《天地》上发表。而《天地》办得也很是热闹风光。令我们感兴趣的则是以下两点:张爱玲的散文多刊登于此,而且她为该杂志出的力还不止于此;胡兰成最初知道有个张爱玲,就是因为读了登在上面的《封锁》。
张爱玲成名后,上海文坛上似乎形成了苏张并称的局面。搞批评的人谈到张爱玲,时常顺笔就写到苏青;写苏青,时常不免就提到张爱玲,专门研究女作家的谭正璧更有一篇文章,题目就叫《苏青与张爱玲》。她们两人的相似处与相异处同样明显,都是大名鼎鼎,又私交甚笃,正是比较的好话题,所以两个名字往往捉对在报刊上出现。
苏青的大胆感言、毫无忌惮,常令一般女人要避她三分,而她似乎也对女人表示不耐,女作家中也没有什么人令她佩服,更多的时候她倒是乐于同男人为伍。但她对张爱玲却是另眼相看,虽说她出名更早,虽说文人相轻,出了名的女作家更易相妒,她却是不存芥蒂,无保留地称道张的才华。《传奇》座谈会上她言道:“张女士真可以说是一个‘仙才’了,我最钦佩她,并不是瞎捧。”她的《天地》也是张爱玲径可视做自己的园地的,编者例言中常有对她作品的特别推荐。
张爱玲恃才傲物,一般女作家根本不放在眼中,独对苏青肯于抬举:“如果必须把女作家特别分作一栏来评论的话,那么,把我同冰心、白薇她们来比较,我实在不能引以为荣,只有和苏青相提并论我是甘心情愿的。”张爱玲又是脾气古怪、不能容人的,苏青的要强与直来直去使她很容易开罪人,张却肯对她行谦让之道:“在日常生活中碰见他们(指形形色色的人),因为我的幼稚无能,我知道我同他们混在一起,得不到什么好处的,如果必须有接触,也是斤斤计较,没有一点容让,必要个恩怨分明。但是像苏青,即使她有什么地方开罪我,我也不会记恨的。”这也不光是说说而已,她和苏青对谈,苏青总是抢话说,而她竟肯于附和。
在女作家座谈会上,这许多的女作家当中,就是她们两人惺惺相惜、厮抬厮敬。写作上两人似乎也有一种默契,有时就像是在唱和。张爱玲有《我看苏青》,苏青投桃报李,还一篇《我看张爱玲》。张爱玲写过一篇《自己的文章》,苏青也有一篇同题的随笔。张爱玲要为形形色色的女人画像,曾打算写一组人物素描,集成“列女传”,苏青有同样的念头,要写“女像陈列所”,仅写成的一篇又有张爱玲配的图。
一份《天地》是她们文字之交的纽带。潘柳黛曾说,“张爱玲的被发掘,是苏青办《天地》月刊的时候,她投了一篇稿子给苏青。苏青一见此人文笔不凡,于是便函约晤谈,从此变成了朋友,而且把她拉进文坛,大力推荐,以为得力的左右手。”潘柳黛:《记上海几位女作家》,转引自杨翼(编):《奇女子张爱玲》,24页。其实张在《天地》露面之前已发表了她最著名的几篇小说,正不必等苏青来发掘,而张肯降尊纡贵,充苏青的“左右手”,当然也是笑话。不过张爱玲倒一直是《天地》的台柱子。《天地》共出二十一期,张爱玲无作的只有三期。她又还为这个杂志专门设计过封面,后面几期直至终刊一直用着。苏青最初给张的索稿信,一开头就写“叨在同性”,张说她看了总要笑,大约从中可见苏青其人,也喜欢这样的人。当然好感可能在此前她们彼此看到对方的文章时就已经存在了。
张爱玲与苏青的关系不像炎樱,她和炎樱常来常往,与苏青则实际上很少见面,她们的交情似也不在女人间特有的“推心置腹”或“私房话”。苏青的一些消息和苦衷,张爱玲反倒常是从别人口中得知,或是从她的文章中看到。但身为女人,又同是希望把住“生活基本情趣”的,自然也有女人日常生活中的那些内容。某次苏青做一件黑呢大衣,张爱玲和炎樱就跟了去当参谋。她在《我看苏青》中很传神地记下当时的情形:
……炎樱说:“线条简单的于她最相宜。”把大衣的翻领首先去掉,装饰性的裥也去掉,方形的大口袋也去掉,肩头过度的垫高也减掉。最后,前面的一排大纽扣也要去掉,改装暗扣。苏青渐渐不以为然了,用商量的口吻说道:“我想……纽扣总要的吧?人家都有的!没有好像有点滑稽。”
张爱玲的衣装总是标新立异、独出心裁的,对苏青衣着随了街面上的时髦走,单讲派头、考究,自然不以为然。其实二人的歧异又何止这一端?她以《我看苏青》为苏青画像,勾出的轮廓正见出她与苏青的不同。且看她对苏青的描述:
她是眼高手低的。
即使在她的写作里,她也没有过人的理性。她的理性不过是常识--虽然常识也正是难得的东西。
苏青在理论上往往跳不出流行思想的圈子,可是以苏青来提倡距离,本来就是笑话,因为她是那样一个兴兴轰轰火烧似的人,她没法子伸伸缩缩、寸步留心的。
她又有她天真的一方面,很容易把人想得非常崇高,然后很快地又发现他的卑劣之点,一次又一次,憧憬破灭了。
张爱玲不会塌了架子去敷衍着写捧场文章,她这些话都说的极实在也极有分寸。而把这些话题颠倒一下,就可用到她自己身上去:张爱玲手不低,但眼是高的;张爱玲富于理性,思想不为流行见解所缚;张爱玲与人与事总是留着距离;张爱玲不会心血来潮,她总是能冷眼看人的。
就仗着眼高与距离,她敢说她能“纯粹以写小说的态度加以推测”苏青,而“我喜欢她超过她喜欢我,是因为我知道她比较深的缘故”。“我知道她比较深”言下之意即“我对她的了解超过她对我的了解”,或者是“我之能懂得她,更甚于她之懂得自己”。你能看透别人而别人吃不准你--与苏青这样的人交往,张爱玲是有一种安全感的。
文如其人,苏张二人的文风也是大异其趣。虽然同为作家,关系又非同一般,应有相互影响一说,但她们尽管在内容上时有呼应交叉,风格上却是各不相犯。张爱玲的蕴藉、含蓄给人印象之深,一如苏青的直白、泼辣。最主要的还是在与读者的关系上,苏青是直来直去,无甚保留,张爱玲则始终保持适当距离,即使在散文里,“私语”、“童言无忌”之外还有游戏三昧。张的为文之“道”且按下不表。苏青基本上是没有“第二自我”的,在创作中也不耐烦为自己找个替身,写散文固不必说,就是写小说,她也爱用第一人称,素材不做什么伪装就塞进小说里,而且这素材全来自她的亲身经历,她书中的人物无一例外全是她自己。
虽然性情不同,处世方式各异,文章路数大相径庭,张爱玲对苏青仍怀有好感。她说她与苏青谈话,到后来常有点恋恋不舍。这也并非故作姿态的虚语。因为她常在苏青那里看到和得到她所匮乏的东西。她的矜持是否有时也使她“生活得轻描淡写,与生命之间也有了距离”?她的怕受伤害、易受伤害是否使她有时候转过头来羡慕苏青感情上屡屡受挫却依然能全身心投入的“健康的底子”?她把种种自己尚未经历过的事事先就想清楚了,是否生活也因此而成了“第二轮的”?所以我们宁说张爱玲对苏青是既感到优越,又不无恋恋。一方面,以她的聪明,她当然明白她的判断力比苏青高明,知人论世更有见地;另一方面“人是不能多想的”,多想万事皆悲,高明的结果经常是“高处不胜寒”,那优越守着也就有些心虚。情与理的平衡悬于一发,过犹不及。所以张爱玲要恋恋于苏青让她感到的暖意:苏青凭常识看人、行事,与物质生活同一--用张的话说,苏青对于她“就象征着物质生活”,而物质生活是现世的、常识的、安稳的、实实在在的。
但是张爱玲与苏青的投合也不仅仅是出于性情上的互补,她们毕竟还有许多看法上的一致。张在女作家座谈会上称近代的女作家中她最喜欢苏青,“踏实地把握住生活情趣的,苏青是第一个。她的特点是‘伟大的单纯’。经过她那俊洁的表现方法,最普通的话成为最动人的,因为人类的共同性,她比谁都懂得”《女作家座谈会》,《杂志》,1944年4月。。又说她们“都是非常明显地有着世俗的进取心”。“伟大的单纯”正来自对生活情趣的把握,来自“世俗的进取心”。革命、理想、罗曼蒂克的爱情,这些都是超世俗的,世俗的则是名、利两端,身为女人,她们的进取心又可解释为,她们想得到普通妇女希望得到的那些东西。这就是她们的现世关怀,这也就是她们基本的取材范围:婚姻、爱情、家庭、女人的挫折、女人的处境--一个充满女性气息的世界。张爱玲的经历限制她把重心放在婚前的女人,苏青结过婚又离了婚,将更多的笔墨用去写女人为妻子、为母亲的甘苦。以女性生活的历程和天地看,她们的创作倒又是相互衔接、补充的(虽然《结婚十年》的素材若让张爱玲来写必定另是一个面目)。她们牢守女性本位,常是非常自觉地从女性的立场去看社会,看人生,而亦时常返顾自身,说她们有一种女人情结也不为过。
就因为看中两人的默契之处,知道她们对女性处境的关怀,当然也是因为张爱玲、苏青这两个名字的号召力,《杂志》的记者为她们搞了一次对谈。这次对谈是一天下午在张爱玲的寓所里进行的,过后记者将谈话内容整理出来,登在1945年3月号的《杂志》上,题作《苏青张爱玲对谈记--关于妇女、家庭、婚姻诸问题》。为求醒豁,记者分节分段,加上了如下一些小标题:“职业妇女的苦闷”、“用丈夫的钱是一种快乐”、“职业女性的威胁--丈夫被人夺去”、“科学育儿法”、“母亲的感情”、“被抑屈的快活”、“女人最怕‘失嫁’”、“大家庭与小家庭”、“同居问题”、“谁是标准丈夫”。
将谈话的内容一一复述未免小题大做,因为记者的提问常是具体琐碎,而苏、张二人的回答也是顺水推舟,随意漫谈,不似为文时那样经意和深入。但是写文章做不到这样直白而及于细微--尤其是张爱玲,而在这里,即使从小标题我们也能更具体地察知“世俗的进取心”、“生活情趣”的一些基本的方面,同时这些标题本身已经明确地向我们透露了她们的态度,即接受、认同女人的性别角色和社会角色。
新文化运动以后,个性解放、人道主义成为知识界的主流,妇女解放当然是其重要的方面,贞操、女子就业、离婚、妇女的社会地位等问题都曾是激起热烈讨论的话题。作家常是社会感应的神经,女作家身在局中,更有不可不言者。冰心、绿漪、凌淑华、沅君、丁玲、白薇等人,或颂扬女性的伟大,或描摹女子的心态、处境,或抒发受歧视、被压迫的愤懑,总之或隐或显、或浓或淡,皆含着女性觉醒的题旨。二三十年代在侪辈中领风骚的冰心、丁玲恰好也代表着女性觉醒的两种路向。当时就有人给二人分别冠以“闺秀派”和“新女性”的头衔毅真:《几位当代中国女小说家》,收入黄人影(编):《当代中国女作家论》,上海光华书局,1933。,其间的分别在于:前者并不跳出礼教之外,在既成规范以内张扬女性精神的伟大崇高,后者则与男权中心的社会正面对抗,要成为像男子一样的强者;前者接受性别角色而加以神化,后者则挣扎着要摆脱这一角色取得与男子一样的社会身份。
张爱玲对这两种取向都不能接受。“女作家座谈会”上被问及喜爱的女作家时她说道:“冰心的清婉往往流于做作,丁玲的初期作品是好的,后来略有点力不从心。”说的是创作风格,然结合她对苏青的赞赏来看,里面也含着对妇女问题的见解和对于女性角色的判断。她不愿对了母爱的祭坛顶礼膜拜:“普通一般提倡母爱的都是做儿子而不做母亲的男人,而女人,如果也标榜母爱的话,那是她明白她本身是不足重的,男人只尊敬她这一点,所以不得不加以夸张,浑身是母亲了。”其他对于女性的神话她也一概看破:“‘翩若惊鸿,宛若游龙’的洛神不过是个古装的美女,世俗所供奉的观音不过是古装的美女赤了脚,半裸的高大肥硕的希腊石像不过是女运动家,金发的圣母不过是个俏奶妈,当众喂了一千余年的奶。”这些议论尖刻犀利,见出她清醒自觉的女性意识,简直是标准的女权主义姿态。但是她又绝对讨厌西方人称做“蓝袜子”的那一型的女人。苏青有次说她看看自己房里的东西都是她自己所置,但并不觉得有何自豪,细想回头倒有几分伤心。张爱玲对此大表赞同和理解,那些梗着脖子称自己如何自立的女人,她只觉那是负气。她称她“不喜欢男性化的女人”,而且在她看来,那些从《娜拉》学会了“出走”的人往往不过是自己向自己戏剧化地扮了一个“苍凉的手势”。
不管是对女性神话的不耐,还是对负气姿态的不屑,里面都有一种不肯自欺的理性精神。她对“男性化女人”的拒绝说明她接受女性的角色,但她并不以为要把女性抬上神的宝座是接受的条件,她有她自己对女人性别角色的理解和把握:“男子偏于某一方面的发展,而女人是最普遍的、基本的,代表四季循环、土地、生老病死、饮食繁殖。女人把人类飞跃太空的灵智拴在踏实的根桩上。”又说:“超人是男性的,神却带有女性的成分,超人与神不同。超人是进取的,是一种生存的目标。神是广大的同情、慈悲、了解、安息。”
然而这只是理论上的认知。另一方面她须面对的是女性在社会中的现实处境。身为女人,她时时感到这是一个男人中心的社会,像上面引述过的文字表明的那样,她一语道破对母爱的膜拜后面藏着的男性话语,在《借银灯》一文中她亦看破所谓“妇德”,实质上乃是“怎样在一个多妻主义的丈夫面前,愉快地尊行一夫一妻主义”;现实中女人的命运则更令她“悲怆”:“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然则如何既坚持了女性传统的权利,又能摆脱加于女性身上的非人性?张爱玲不会开药方,也不相信有什么简单的又是根本的解决办法。和苏青谈妇女问题,她持的是极其务实的态度,比如关于妇女走出家庭寻找职业,似乎是“解放”的一条途径了,她赞成妇女走出去,可是她的理由却是很实际的:“常常看到一种太太,没有脑筋,也没有吸引力,又不讲究打扮。因为自己觉得很牢靠,用不着费神去抓住她的丈夫。和这样的的女人比起来,还是在外面跑跑的职业女性要可爱一点,和社会上接触得多了,时时刻刻警醒着,对于服饰和待人接物的方法,自然要注意些,不说别的,单是谈话的资料也要多些,有兴趣些。”谈到女人的早婚,她说道:“早婚我不一定反对。有些女人,没有什么长处,年纪再大些也不会增加她的才能见识的,而且也并不美,不过年轻的时候也有她的一种新鲜可爱,那样的女人还是赶早嫁了的好,因为年轻,她有较多的机会适应环境,跟着她丈夫的生活情形而发展。”这些议论的前提似乎是接受男性中心的事实了,但是对于张爱玲,断然的理论是空洞的,关键是如何就近求得实在的幸福。即此而论,重要的就是各人的自处之道了。
事实上,她与苏青对谈之时,她自己正结结实实地碰触着普通女人感到困扰的、往往构成了女性生活的中心的那个问题--恋爱、婚姻。那么,她何以自处?“撒手”以下三章的材料多取自胡兰成的自传《今生今世》。文如其人,此书虽写于晚年,应是“不惑”、“知命”之作,而仍大言不惭,沾沾自得之意随处可见。书中《民国女子》等章详写与张的关系,虽然裁剪、渲染,有刻意制造佳话之嫌,亦且不脱自我标榜之意,但以他的为人行事及张的性情判断,书中所述及张爱玲的部分大体可信,笔者所为是对这些材料做出自己的理解。以下凡从该书引录者不再一一注明,读者度上下文之意当可知何者出诸胡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