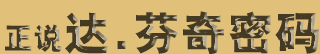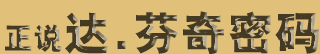|
藏在罐子里的手稿
现在让我们来审视这些让人想入非非的著名的死海古卷。先是一些贝督因人①在死海附近库姆兰的山洞中发现了几个筒状物。1947年,这些东西出现在当地的古董市场上。这只是这个传奇故事的开始。随后,这些曾经藏在陶罐中的筒状物转到了专家手中。经检查,专家们确认这是一个重大发现。需要确定藏着这些手稿的那些山洞的位置:专家们设想并希望那里还有其他的手稿。联合国的一个比利时籍官员在约旦阿拉伯军队的协助下找到那些贝督因人并询问他们。1949年,这些山洞终于被找到。约旦文物处的领导G.L.哈丁和耶路撒冷圣经学校校长、多明我会教士罗兰·德沃(RolanddeVaux)负责系统的发掘工作,这项工作持续到1956年。这次发掘使藏在其他山洞中的一些新的手稿重见天日。埋藏手稿最多的第四号洞是另外一些贝督因人在1955年发现的。
到60年代末,专家们发现了一笔无价的、令人震撼的考古“宝藏”:成书时间约为公元前250年到公元68年,写于绵羊皮上的八百篇文献。这些羊皮一部分保存完好,大部分成了碎片。其中四分之一的文献是《旧约》中也有的希伯来《圣经》,但是,它比当时知道的最早的希伯来《圣经》早了一千年!这些经文随后被承认并被确定为正典(这是由流亡到巴勒斯坦的Yaneh的拉比们在公元1世纪确定的)。
另一部分是正典希伯来圣经未收录的文献。其中有一些后来被天主教的圣经收录(这就是“外典”)。相反,基督教圣经把它们排除在外(基督教徒称它们为“《旧约》的伪经”)。
库姆兰手卷里还有一部分。这是到那时为止,人们完全不知道的经文(《圣殿卷》、《社团规章》),它们是一个犹太社团,即艾塞尼派的生活和宗教信仰的准则。当时,人们只知道存在这个教派,但有关他们的情况却完全不知道。
在深入探讨这个教派之前,让我们首先更正一下雷·提彬论点的一个大错:这些手书中没有任何一篇谈论到耶稣或者基督教。这些完全是犹太经书。布朗通过提彬之口,把库姆兰手稿定义为“最早的基督教经文”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完全不要指望这些记述中有与耶稣和抹大拉的马利亚有关的揭示。
相反,这些经文对于探讨耶稣时代犹太教的多样化是很重要的。在这些文献被发现之前,人们想象这个时代的犹太教在教规和信仰方面是相对一致的。自此,人们了解到耶稣与法利赛人的激烈的争吵并不是《新约》中的一个特例:在当时的犹太团体之间,各种针对解释法的论战很激烈,有时还携带着暴力。这些文献也让我们理解了希伯来《圣经》,并表明《圣经》的文本史比我们想象的复杂。最后,这也让我们最终了解了艾赛尼派。
艾赛尼派信徒
犹太史学家弗拉维乌斯·约瑟夫斯简短地提到过这个犹太社团的存在,提到它的还有亚历山大里亚城的斐洛①(Philond′Alexandrie)。老普林尼②(Plinel′Ancien)提到过位于“EinGedi湖畔”——相当于库姆兰的位置——的一个艾赛尼派组织。自1947年起被陆续发现的这些手稿让我们对这个犹太教活动团体有了更完整、更细致的了解,它可能诞生于马加比家族③起义失败后的公元前2世纪中叶。这是一个因信仰世界末日临近而对后世影响很大的团体(这一启示录般的预言在当时多个对现状不满的犹太人团体中相当流行)。
库姆兰的艾赛尼教徒把自己视为“阳光之子”,与“地狱之子”相对。他们组成一个可能是独身的男人的社团,选择脱离社会的生活,并且狂热地为世界的末日和最终战胜恶做准备。教规确立了一种超脱而非常苛刻的纯洁理想(里面有众多的洗涤的仪式)以及固定的祈祷和教理研究的时间。同时规定物质财产共有。艾赛尼教徒反对耶路撒冷圣殿,他们认为圣殿已经落入大逆不道的教士之手。他们等待着一位终将完善他们的健康行为的一位弥赛亚①的降临。在手卷中他们还提到一位与大逆不道的教士(圣殿的教士)相对立的“正义大师”。很难给这个人下定义。一些专家把他看作是教派的领袖,另一些则认为是教派的创始人,是被圣殿驱逐的一个宗教改革者。
耶稣是一个艾赛尼派教徒吗?
等待世界末日,等待以正义大师面貌出现的弥赛亚的预兆,与圣殿对抗——这些艾赛尼信徒的信仰和早期基督教徒的信仰之间立即就有了联系。另外,在死海古卷发现之前的19世纪末,埃内斯特·勒南②(ErnestRenan)就已经肯定地说:“基督教是大获成功的一种艾赛尼教。”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二世①(FrédéricⅡ)在1790年10月给达朗贝尔②(D′Alembert)的信中也说:“耶稣纯属艾赛尼教徒。”
1950年,铭文与纯文学科学院的常务秘书安德烈·杜蓬-索梅尔(AndreDupon-Sommer)在他的《死海古卷初览》一书中说:“‘加利利大师’③,就像《新约》为人们描述的,很像正义大师令人吃惊的一次转世……”在艾赛尼信徒和早期基督教徒之间假定的,甚至是可能的联系一直引起争论。它主要围绕着三个基本点展开。
1.施洗者约翰。他在库姆兰附近地区从事活动,他是独身者并预言天国的即刻降临。因此他很有可能知道这个社团的什么事情,甚至是曾经加入过,后来又脱离了这个社团。然而,没有任何证据能够确切地证明这个论点。
2.耶稣和正义大师。两者相似的地方是明显的,但是在传播教义时也有重大的不同之处。正义大师面对的是脱离社会的一小群人,而耶稣则向所有人,绝大多数是以箴言的形式传教,并意欲“为大众”献出生命。另外,如果我们相信弗拉维乌斯·约瑟夫斯在他的《犹太史》中的记载,艾赛尼教徒“摒弃女人、罪人和残疾人”,而福音书则向我们表现了一个周围有女人、罪人和残疾人的耶稣——这点对他的诽谤者非常不利。
3.第一个基督教社团。某些艾赛尼派的教规可能对早期基督教徒产生过影响,例如,集体进餐或者财产共有,还有启示录的经文和对弥赛亚的期待(另外,这种期待是其他的犹太教组织所共有的)。这种接近还表现在一篇库姆兰的经文和《路加福音》(Ⅰ,26—38)上。这篇库姆兰经文对一个神秘的人使用了“上帝之子”的称号。同样,“虚心的人”(《马太福音》,Ⅴ,3)这种表述在“库姆兰经文中虽然没有一对一的表达,但从文字上,或者教义上也有足以把它们联系在一起的说法”,库姆兰文专家让·皮·雷莫农(J.-P.Lémonon)解释说。
当然,尽管如此,这种相像仍然让人吃惊,并得出结论说,两者之间的关系如果不是影响,至少也是殊途同归。它们体现出一种共同的精神状态,可以更好地让人理解基督教在当时的犹太教背景下的诞生和扎根。卢万(Louvain)大学教授、格罗宁根大学库姆兰学院院长弗洛伦蒂诺·格拉西亚·马丁内兹(FrorentinoGraciaMartinez)说:“我们或许在库姆兰经文中发现了已经得到详尽论述的每一个基本因素,这些基本因素构成了《新约》的救世主(弥赛亚、教士、仆人、上帝之子)的形式多样而复杂的形象。我觉得这是确实的,不容置疑的。但是没有受苦的和救世的仆人的形象,所有这些元素都被堆砌到惟一一个并不是不可想象的人物身上,但在我们看过的资料中,还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证明它;这个等待世界末日的正义大师在经文中从来没有被详细地阐述过。”
耶稣与独身
总之,专家们一致指出了艾赛尼教与基督教的相似,但并没有对两个组织之间的直接联系下结论。然而,对于我们关心的耶稣的独身问题最终只有一个观点。无论耶稣是否经常与艾赛尼教徒交往,根据我们对这一派别的了解,它增大了苦行和单身的可能性,而不利于性和婚姻的说法。死海古卷的发现宣告了《达·芬奇密码》主题的无效。
同样,这一发现让一个主要论据相对化了,这个主要论据本来可能有利于某些犹太教专家认为的耶稣已婚的论点,即在基督的时代,在犹太教堂中传教的一位拉比不可能是单身的。多亏了库姆兰经文,使我们对艾赛尼教徒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如今我们知道,在基督的时代,存在着一些独身的宗教导师,为天国即将降临而主张禁欲。他们中的某些人在犹太教堂中传教并不令人惊讶,即便他们的生活方式并不符合主流犹太教。
如果丹·布朗提到死海古卷,那也不是为了参考其中的内容,因为死海古卷所支持的论点与小说正相反。在引用库姆兰的经文时,他更想让人联想到长期以来伴随着出版死海古卷的论战,这场论战激起了所有的幻想,尤其为教会的阴谋的理论提供了素材。
论战:教会的一个阴谋吗?
其实,死海古卷自发现之日起就激起了热情和双重的论战。一方面,有人指控天主教会试图掩盖秘密。另一方面,专家们指控他们的同行出自纯粹的野心把持死海古卷,损害了研究工作。这两种争论都因为同一个原因:死海古卷出版工作的不寻常的缓慢,即使已经考虑了拼合羊皮碎片的困难因素。
让我们来审查教会阴谋掩盖库姆兰发现的“案件”。首先,这一指控是荒谬的。因为天主教会没有任何东西需要掩盖。但是,历史背景,第一个研究团队的特点,出版的缓慢引起了许多猜疑。让我们回顾一下这些事情。1953年,德沃神父组建了由多个国家(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波兰)的年轻研究人员组成的小组。其中包括六位天主教徒,一位基督教徒(美国的弗兰克·格罗斯),一位不可知论者(英国的约翰·阿利格罗)。由耶路撒冷洛克菲勒博物馆提供资金。但是,预计为十年的修复和翻译期满后,博物馆停止了资助,而修复工作还远没有完成,因为事实证明,修复某些羊皮碎片的工作很复杂。研究人员自此不得不为生计而努力。因为1967年6月的中东六日战争,使情况更加复杂。原来在约旦的库姆兰现场、洛克菲勒博物馆和圣经学校都转由以色列政府管理,而德沃神父公开反对这个政府……此间,团队解散,自1960年起,研究者们全部撤离现场。因为大部分的羊皮(511张)都已修复,他们可以回到各自的国家根据照片进行翻译工作。
但是,一些研究人员比其他研究人员多用了许多翻译时间,尤其是信奉天主教的研究人员。从这儿,到想象梵蒂冈要求他们隐瞒有碍基督教诞生的官方说法的内容只差一步之遥——这个距离立即被某些论战者跨越了。在发现死海古卷三十年后的1977年,小组的一名研究人员约翰·阿利格罗率先迅速地出版了他的研究成果,然后提出了怀疑,但他因为出版了一本关于基督教的谵妄性的著作也在学术界丧失了自己的声誉。谣传自1984年起被由赫尔谢尔·香克斯(HershelShanks)主编的《圣经考古学杂志》(BiblicalArcheologyReview)接了过去。香克斯利用了丑闻,显然是想得到某些研究者出于嫉妒保存照片的消息,这些研究者除了具备野心家的心理之外,再也没有显示完成他们工作的能力。
最后,1987年,以斯特拉格尔内(J.Strugnel)为首的一个重组的小组成立了。小组接纳了一些以色列研究人员。希望被重新燃起。但是,在1989年,并不是所有研究人员都可以随时看到死海古卷的照片。《圣经考古学杂志》施加了更大的压力。库姆兰古卷是受诅咒的吗?1990年,因沮丧而酗酒的斯特拉格尔内对一名以色列记者说了一番话,在媒体上掀起轩然大波(他劝说犹太人改信基督教)。他被送进波士顿精神病院。最终小组交由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艾玛纽埃尔·托夫(EmmanuelTov)、美国圣母大学的尤金·乌尔里希(EugèneUlrich)和圣经学者的埃米尔·普厄什(EmilePuech)集体领导。索尔邦大学教授、古代犹太教专家米哈依·哈达斯-勒贝尔(MireilleHadas-Lebel)解释说:“论战没有说出一个神学的阴谋,更多揭示的是偏见、不称职和采取的僵硬和没有效率的组织结构。”
直到1991年,阴谋的臆想才彻底破灭:亨廷顿图书馆,世界上四个存有死海古卷缩微胶片的图书馆之一,决定把这些对外开放。1991年10月27日,以色列文物管理部门解除了对使用未公开发表的残片照片的任何限制。同年11月19日,圣经考古协会(《圣经考古学杂志》的出版人)发表了两大卷包括1785张残片的照片,四十五名研究人员组成国际研究组开始研究这些文件。2002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自1947年至1956年发现的死海古卷全集,共三十九卷。如今,教会阴谋禁止出版死海古卷的论点已经没有人再提。(惟一使学者们分成两派的论战涉及在库姆兰发现的《圣经》的经文出自哪里:它们是出自艾赛尼派的图书馆还是出自耶路撒冷圣殿?)
死海古卷包含了梵蒂冈的一个致命的秘密,揭示有关耶稣和基督教起源的爆炸性内容,丹·布朗是从什么地方找出这些观点的?是在1992年法国出版的《被没收的圣经,隐匿死海古卷的调查》一书中,该书出版的那年,科学界中的论战已经平息。这本书简述了一些有理由的批评,但也搭载了前十五年所有阴谋派的观点和没有根据的谣言。我们对该书的作者并不陌生:麦克尔·贝吉特和理查德·雷,《圣血,圣杯》三名作者中的两位!
丹·布朗忠实于他的消息人和他们的观点。他的小说的主导主题之一就是阴谋理论:教会自4世纪和尼西亚会议后隐瞒了一个可怕的秘密。让我们继续调查,打开阿里乌教派的教义、君士坦丁大帝和著名的会议的分歧的档案。据说阴谋者们在这个会议上决定抹掉非常惹麻烦的经文。
教会试图隐瞒耶稣和抹大拉的马利亚的婚姻吗?它试图抹掉揭示了这件事和有利于女人的经文吗?丹·布朗认为,大阴谋于尼西亚公会上形成,这是由君士坦丁大帝在公元325年召集的。随后,教会就野蛮地迫害所有企图反对官方真理的人。今天仍然是这样,教会为保守这个可怕的秘密,不是准备好要杀人了吗?无论如何,这是《达·芬奇密码》故事情节的核心:天主教会联合了亲教皇的秘密组织天主事工会,与“大秘密”的捍卫者郇山隐修会之间展开无情斗争。这是一场殊死的斗争:丹·布朗安排了一个致人死命的僧侣,多多少少地受到谋杀郇山隐修会所有成员的梵蒂冈的操纵!
我们对著名的郇山隐修会已经心中有数了。丹·布朗所说的与天主教教会和天主事工会相关的事又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从作者所谓的诞生了天主教阴谋的尼西亚公会开始。
天主教的阴谋?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