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侨居哈尔滨的吟唱班领唱
作者:[俄罗斯]加莉娜·达尼埃尔耶夫娜·克里莫娃
犹太教主教堂吟唱班领唱

所罗门•莫伊谢耶维奇•兹拉特金
1953年11月24日
5714年17日 逝世
所罗门,我找到你了!
这是我们之间的心灵在呼唤,您等待了很久很久,企盼着在人世间关于对您的缅怀得以复活并永存,在您的墓上有人洒下热泪。
是您,所罗门唤起了我对家庭系谱树寻根的渴望。上帝以令人莫测的道路把我带到了您这里,创造了奇迹……我飞到了中国,乘火车到了哈尔滨,仅仅经过两个多小时找到了亲人的墓,难道这不是奇迹吗?这简直像大海捞针。
这是天意神助!
生活中各种离奇的事远比魔幻作品有力得多。
看来,我的这类意外的巧合、难以置信的奇遇具有遗传基因。
在战争期间我爸爸达尼埃尔•费奥多罗维奇•兹拉特金在卡累利阿前线打仗之后到了彼尔姆。他很饿,早上去了市场,想把几包香烟卖掉,或者换点食品,当地卖八百卢布一包烟,他卖七百卢布,一下子排起队来,其中有一个妇女,盯着看我爸爸,他有点不耐烦了,说:
“我说女公民,您总是看着我干什么?站在那里,什么也不买,为什么一个劲儿地盯着我?”
“您让我想起了自己的儿子,他很像您,一模一样,”她大声哭了起来,“您想吃东西,是吗?走,到我家去,我让您吃个够……认识一下我的女儿!”
“瞧,简直是个媒婆……想把我带到她女儿那里去。这可不是无缘无故。当然去,我这个当兵的有什么好怕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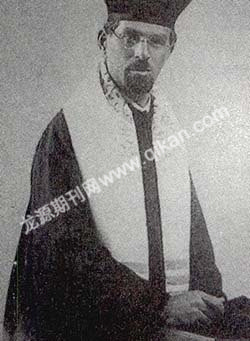
家里虽不富裕,倒也整洁。一位姑娘走上前来,青春已过,闪出犹太人带有愧色的眼神。大家坐下吃午饭,没有问他姓什么,叫什么,他们对此不感兴趣。她只谈儿子死得很惨,而客人与牺牲的儿子出奇地相像,妈妈痛哭之后到另一个房间休息去了。
“你们坐着,好好聊一聊……丹妮娅,给士兵看一看照相本。”
丹妮娅翻着相册,说:“这是爸爸,这是妈妈,这就是哥哥,而这个是我舅妈,她在列宁格勒,这个……”
我父亲当时喘不过气来,泪如雨下,号啕大哭,边哭边指着一张照片,上面有一男一女和两个孩子——男孩和女孩。
“妈妈,妈,你快过来,他感觉不好,”丹妮娅喊着。
她妈妈只穿一件衬衫就忙不迭地跑了过来。
“这是怎么回事?”
“你们怎么会有这张照片,他们是谁?”
“这是法布斯,我的弟弟法布斯,”女主人镇静地回答说。
“就是说,您是我姑姑!这是我父亲、母亲、姐姐和我。”
“啊,真的是你,我的侄子,我的好孩子,我亲爱的!怪不得我一直看着你,你长得和我的儿子一模一样,你那可怜的表哥……这么说妈妈的心——心灵感应!”
就这样,一夜之间我父亲找到了亲姑妈盖妮娅(可能叫盖丽艾塔)和表妹丹妮娅,并且同时还知道他父亲的真名叫法布斯不是费佳。

不久前,我堂姐艾拉全家办理去以色列定居手续时(为此必须提供很多证明他们是犹太人的文件),我们惊奇地发现自己祖母的名字不叫克拉拉,而是叫哈娅……
我站在吟唱班领唱的墓旁,回想1953年夏天,当时所罗门还健在,爸爸第一次领我到尼古拉耶夫去看望祖父、祖母。当时我五岁。他们的长形砖砌的独家住宅坐落在法列耶夫斯基街,祖母早已等候在大门口,看到我之后她用干燥冰冷的嘴唇不停地吻着我的前额,我紧缩全身,大声喊着:
“爸爸,你在哪儿?”
“你怎么这样说话呢?难道没有学会把父母称作“您”吗?”祖母公开斥责说。
我明白了,从第一眼我就不讨她喜欢,虽然爸爸替我说话,他说时代不同了,规矩也改变了。
克拉拉与别人截然不同。
我女朋友们的祖母当中没有一个人在家里穿着高跟便鞋、漂亮的衬衫,别着胸针,或者身穿带有饰物的丝绸连衣裙,几乎所有时间手里都离不开书本。那么她什么时候做饭,洗衣服或者打扫房间呢?看样子她不会干家务、也不关心这些,虽然父亲说克拉拉幼年时曾是孤儿,住在并不富裕的亲戚家里。我当时作为孩子很可怜她,特别想弄明白孤儿是怎样长大成人的……克拉拉从来没有放过牲口,没有挤过羊奶,没有饲养过猪和鸡,不像我的外祖母费妮娅。克拉拉从来没有砍过白菜,没有在散发着刺柏香味的木桶里腌过黄瓜和蘑菇,为了漫长而半饥半饱的冬天,为一大家子人和客人做食品储备。然而,她会烤带水果馅的酥皮甜点和做填馅的鱼。她会弹钢琴,会唱歌,唱的不是费妮娅唱的那些俄罗斯歌曲和乌克兰歌曲,而是表演歌剧,被称作咏叹调、练声曲、独唱短曲。
出嫁前,克拉拉•杰普利茨卡娅在音乐学院毕业后在奥德萨歌剧院当合唱演员,不久嫁给了银行小职员费奥多•莫伊谢耶维奇•兹拉特金,他比她小六岁,他们搬到了相邻的尼古拉耶夫,她开办了私人儿童歌剧院,上演音乐剧目,服装、布景都大获成功,感动了热爱子女的父母和易动情感的亲属们,引起了青少年演员的伙伴们的羡慕。主角多半是由阿妮娅和达尼埃尔——克拉拉和费奥多相差一岁的女儿和儿子担任。他们演出的古希腊神话歌剧的剧照至今还保存着。
这一切都发生在革命前,而十月革命以后,克拉拉只能作为一名默默无闻的音乐老师。

在那以后过了很久,试图寻根时我才感觉到我真的是克拉拉的孙女,在很多方面表现出了遗传性:我疯狂地爱上了小提琴,几乎成为职业音乐家,早在幼儿园我曾多次唱过浪漫曲,独唱短曲,十四岁的时候开始编剧,为了在短暂的夏天能够在诺金斯克儿童剧院演出,服装、道具都是从军官夫人们衣柜中挖掘出来的,还有我第一次接触诗歌……
“兹拉特金的血统,你和这个家族的人一模一样,”外祖母费妮娅一针见血地指出,对我的“艺术天赋”不知道是生气还是骄傲。
夏天在尼古拉耶夫,晚上闷热,吃着透心凉的西瓜,喝着冰镇汽水非常惬意。为此,需要买三公升汽水和红莓苔子果子露,赶快跑回家倒在杯子里趁汽水的泡沫还没有消失喝下去。全家围桌而坐等候吃饭,晚饭通常吃的有盛在深盘子里的大米水果粥(类似煮水果)。非常可笑。清晨我很沮丧,因为我明白了我在梦中自由自在游泳的暖洋洋的河流是什么——床褥上湿了一片,真太丢面子了。连睡在我身旁的胖猫“红毛儿”也溜走了。
我特别喜欢跟费佳爷爷去逛早市,好像在南方城市过节一样,鲜活虾在水桶里翻动着,货摊上摆着大头的虾虎鱼、黄灿灿的鲭鱼、晒干的竹荚鱼、新鲜的鲮鲱鱼,成堆成堆的玉米、茄子还有五颜六色的产品都在向顾客炫耀自己,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丰富美丽的市场,我永远记住并永远喜爱它。爷爷不善于讨价还价,不好意思。他直到生命最后一刻始终是默默无闻、勤于持家的天使。
法布斯和哈娅——爷爷和奶奶的真名。
不,我们叫费佳和克拉拉。
生活,确切地说在生活面前的恐惧把他们弄成什么样子了!父母甚至不能对亲生儿女公开自己的真名实姓,要知道名字是神圣的,有些世袭的名字是命中注定的。他们离开犹太人定居区,为了按新方式适应新的生活,他们只好选择了新的,尽管是别人的名字……以新名登记办理护照,可能他们过的也是别人的生活。临终,也要以别人的名字长眠地下。那么,是什么人用他们的名字生活呢?
父亲很少与他的双亲见面,几乎不通信,这使他很痛苦,尤其是当他接到我祖父的来信哀求他给生病的母亲哪怕写几个字也行,那时他愧疚,甚至在我面前忏悔。克拉拉死于肺癌,此前她已经做过一次乳腺癌手术。有一次,我看见她高高隆起的假乳吓了一跳。克拉拉死在家里,很痛苦。她所疼爱的孙女艾拉准备出嫁,由于祖母病重,婚礼一拖再拖。克拉拉恳求不要推迟婚礼,不要改期,她渴望隔墙听到“苦啊!苦啊!”的喊声——新郎、新娘婚礼上接吻。她希望在自己家举办最后一次欢庆,虽然她已经不能弹琴助兴……是啊,家里早已没有钢琴:在战争期间,他们刚刚疏散到乌拉尔,家里就被洗劫一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