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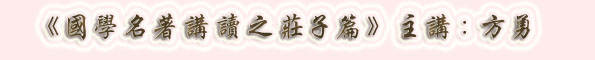
马 蹄
|
|
【题解】
此篇与《骈拇》篇同旨,在着意宣讲恢复人的自然本性。所不同者,此篇主要以马设喻,谓马属性自然,只知食草饮水,喜则交颈相摩,怒则分背相踢。由于伯乐施以各种约束,以致马死过半。因此马也学会“诡衔窃辔”的盗智,此皆伯乐之罪。由马及人,远推所谓“至德之世”(原始社会),禽兽成群,草木遂长,人与禽兽为伍,与万物并生,无知无欲,居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没有君子小人之别,处于“常然”,“是谓素朴”世界。及至儒家圣人,提倡仁义礼乐,以匡正天下,使民自矜好诈,争归于利,真是罪大恶极!
作者反对“圣人”以仁义礼乐禁锢人的自由思想,主张个性解放,在当时来说,自然具有很大的进步意义。同时,作者因主张恢复人的自然本性,而向往愚昧无知的原始社会,显然,这种愤激思想又带有严重的消极虚幻性。
马,蹄可以践霜雪,毛可以御风寒,龁草饮水[1],翘足而陆[2],此马之真性也。虽有义台、路寝[3],无所用之。及至伯乐[4],曰:“我善治马。”烧之,剔之[5],刻之[6],雒之[7],连之以羁馽[8],编之以皁栈[9],马之死者十二三矣;饥之,渴之,驰之,骤之,整之,齐之,前有橛饰之患[10],而后有鞭筴之威[11],而马之死者已过半矣。陶者曰:“我善治埴[12],圆者中规[13],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钩[14],直者应绳。”夫埴木之性,岂欲中规矩钩绳哉!然且世世称之曰:“伯乐善治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过也[15]。
【注释】
[1]龁(hé河):啃,咬。
[2]翘:扬起。 陆:跳跃。
[3]义台:即仪台,天子、诸侯行礼之台。 路寝:即正寝,正室。
[4]伯乐:姓孙,名阳,字伯乐,相传是秦穆公时善相马者。
[5]剔(tī梯)之:剪剔马毛。
[6]刻之:凿削马蹄。
[7]雒(luò洛)之:用红铁烙火印,作为标识。
[8]羁:马络头。 馽(zhí执):牵绊马足的绳子。
[9]皁(zào造):马槽,饲马饮食的地方。 栈:以木排成的地板,马居其上,可以避湿,俗名“马床”。
[10]橛(jué绝):马口中所衔的横木。 饰:马络头上的装饰物。
[11]鞭、筴:都是打马的工具。筴,通“策”。
[12]埴(zhí直):粘土,可烧制陶器。
[13]中(zhòng众):恰恰相合。 规:成圆之器。
[14]钩:木工划曲线的工具。
[15]过:过失。
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1]。彼民有常性,织而衣,耕而食,是谓同德[2];一而不党[3],命曰天放[4]。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5],其视颠颠[6]。当是时也,山无蹊隧[7],泽无舟梁;万物群生,连属其乡[8];禽兽成群,草木遂长[9]。是故禽兽可系羁而游,鸟鹊之巢可攀援而窥[10]。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11],族与万物并[12],恶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无知[13],其德不离[14];同乎无欲,是谓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及至圣人[15],蹩躠为仁[16],踶跂为义[17],而天下始疑矣;澶漫为乐[18],摘僻为礼[19],而天下始分矣。故纯朴不残[20],孰为牺尊[21]?白玉不毁,孰为珪璋[22]?道德不废,安取仁义?性情不离,安用礼乐?五色不乱[23],孰为文采?五声不乱[24],孰应六律[25]?夫残朴以为器,工匠之罪也;毁道德以为仁义,圣人之过也。
【注释】
[1]意:以为。
[2]同德:共同的天然的本能。
[3]党:偏私。
[4]命:叫作。 天放:放任自乐。
[5]填填:脚步迟重的样子。
[6]颠颠:愚朴直视的样子。
[7]蹊:小路。 隧:孔道。
[8]乡:住所。
[9]遂长:繁茂地生长。
[10]窥(kuī亏):通“窥”,从孔隙中窥望。
[11]同:混杂。
[12]族:聚在一起。
[13]同:无知的样子。
[14]德:指人的自然本性。 离:离散,丧失。
[15]圣人:这里指儒家所说的“圣人”。
[16]蹩躠(bié xiè别谢):行走困难的样子。引申为勉强用心力的意思。
[17]踶跂(zhì qí至齐):踮起脚尖。意同“蹩躠”。
[18]澶(dàn但)漫:放纵逸乐。
[19]摘僻:烦屑拘泥的样子。
[20]纯朴:原始的木材。 残:雕斫。
[21]牺尊:刻有牛形花纹的酒器。尊,通“樽”,盛酒器。
[22]珪璋:玉器。上锐下方者为珪,形似半珪者为璋。
[23]五色:指青、赤、黄、白、黑。
[24]五声:指宫、商、角、征、羽。
[25]六律:指黄钟、大吕、姑洗、蕤宾、无射、夹钟。
夫马,陆居则食草饮水,喜则交颈相靡[1],怒是分背相踶[2]。马知已此矣[3]。夫加之以衡扼[4],齐之以月题[5],而马知介倪[6]、闉扼[7]、鸷曼[8]、诡衔[9]、窃辔[10]。故马之知而态至盗者[11],伯乐之罪也。夫赫胥氏之时[12],民居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13],鼓腹而游,民能以此矣[14]。及至圣人,屈折礼乐以匡天下之形,县跂仁义以慰天下之心[15],而民乃始踶跂好知,争归于利,不可止也。此亦圣人之过也。
【注释】
[1]相靡:互相磨擦,表示亲顺。
[2]相踶:用后脚相踢。踶,通“踢”。
[3]知:通“智”,智力。 已:止。
[4]衡:辕前横木。 扼:通“轭”,叉马颈之木。
[5]月题:马额上的装饰物。
[6]介倪:损折车輗。
[7]闉(yīn音)扼:曲颈企图从轭下逃脱。闉,弯曲。
[8]鸷曼:指马狂突不羁,试图挣脱。鸷,猛。曼,突。
[9]诡衔:狡猾地吐出衔子。
[10]窃辔:偷偷地啃咬辔头。
[11]态(tài太):同“能”,能够。
[12]赫胥氏:传说中的上古帝王。
[13]哺:口中所含食物。 熙:通“嬉”,嬉戏。
[14]以:通“已”,止。
[15]县跂:高高悬起,使人企而望之。县,通“悬”。跂,企望。
[16]踶跂:勉强企求的样子。
【文化史拓展】
《马蹄》和《骈拇》两篇主旨很相近,都极力劝说人们应当保有自然本性,摈弃仁义枷锁。只不过《骈拇》篇着重从人性受损的角度论说仁义对人身心的危害,是微观论述;而《马蹄》篇着重从物性受戕害的角度描述仁义对天下的害处,是宏观论述。两篇一大一小,相互呼应补充,浓墨重彩,只为了唤起人们对仁义的反思和对本性的珍视。
《马蹄》开首便从马的本性着笔。庄子笔下的马悠然自得,颇有风骨,食草饮水,奔腾欢跃,活得自由自在。伯乐一来,真性皆失。失却了真性的马儿死者过半,所剩的也在鞭子下和车套中苟延残喘。在庄子看来,让马、埴和木失去真性的是伯乐、陶人和工匠,让百姓失去真性的是仁义礼乐。
西汉初期,黄老学盛行,统治阶级在猛烈抨击秦代“有为”政治的同时,极力主张“无为而治”。如淮南王刘安等在《淮南子·修务训》中说:“夫鱼者跃,鹊者駮也,犹人马之为人马,筋骨形体,所受于天,不可变。以此论之,则不类矣。夫马之为草驹之时,跳跃扬蹄,翘尾而走,人不能制。……及至圉人扰之,良御教之,掩以衡扼,连以辔衔,则虽历险超堑弗敢辞。故其形之为马,马不可化;其可驾御,教之所为也。”这里显然受到了庄子思想的影响,但又对庄子思想进行了改造,认为马与鱼、人都不一样,它的本性是“跳跃扬蹄,翘尾而走”,人们如顺着它的这一本性而“掩以衡扼,连以辔衔”,使之能够“历险超堑”而“可驾御”,这就是不以人易天的“教之所为”。由此可见,淮南王等已对庄子《马蹄》篇的思想内容作了大胆发挥,其目的就是要把因任自然与发挥人的能动作用统一起来,以便为汉初最高统治者提供出一套适应当时社会实际情况的治国理论。
珍视人的天然本性是中国古代思想的母题。它萦绕在每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心头,并在每朝每代幻化成不同的表述和理论。如明代思想家李贽提出了著名的“童心”说,认为“童心”即“绝假纯真”的真心,也就是心的最原初状态。在李贽看来,人还没有长大的时候,所见所闻通过眼睛、耳朵进入头脑,把这些学得了记住了的同时,童心却渐渐蒙尘。到了长大之后,各种道理和见闻越来越多,也就离开童心愈发遥远。时间一长,习得了社会的标准,知道好名气是好东西就多追逐它,懂得坏名声是让人丢脸的就千方百计伪装。他的这些说法的思想远源,显然可以追溯到《庄子》中的《马蹄》等篇。
【文学史链接】
1、文学技法
此篇自首至末,只是一意,其大旨从上篇“天下有常然”句生来,庄文之最易读者,然其中之体物类情,笔笔生动。
(林云铭《庄子因·马蹄》篇末总评)
此篇言以仁义为治则拂人之性,是就害于物上说。前后用譬喻错落洗发,如雨后青山,最为醒露。
(宣颖《南华经解·马蹄》总论)
此篇庄文之尤近人者,西汉人文字多祖之,而字法句法要非秦汉以下所有也。至其巨篇奥旨,则固别成一经矣。
(陆树芝《庄子雪·马蹄》篇末总评)
《马蹄》、《秋水》,乃南华绝妙文心,须玩其操纵离合,起伏顿挫之奇。……一路夹叙夹议,恣肆汪洋,如万顷惊涛,忽起忽落,真有排天浴日之奇。格局极为完密,而正意、喻意,萦回宕漾在有意无意之间,微云河汉,疏雨梧桐,可以想其逸致矣。
(刘凤苞《南华雪心编·马蹄》篇末总评)
【集评】
此篇言圣人治天下之过,其意则自前篇“天下有常然”生下。
(陆西星《南华真经副墨·马蹄》题解)
《马蹄》与《骈拇》,皆从性命上发论。《骈拇》是尽己之性而切指仁义之为害于身心,《马蹄》是尽物之性而切指仁义之为害于天下。
(刘凤苞《南华雪心编·马蹄》篇末总评)
【彙評】
此篇自首至末,只是一意,其大旨從上篇“天下有常然”句生來,莊文之最易讀者,然其中之體物類情,筆筆生動。(林雲銘《莊子因·馬蹄》篇末總評)
此篇言以仁義爲治則拂人之性,是就害於物上說。前後用譬喻錯落洗髮,如雨後青山,最爲醒露。(宣穎《南華經解·馬蹄》總論)
此篇莊文之尤近人者,西漢人文字多祖之,而字法句法要非秦漢以下所有也。至其巨篇奧旨,則固別成一經矣。(陸樹芝《莊子雪·馬蹄》篇末總評)
《馬蹄》、《秋水》,乃南華絕妙文心,須玩其操縱離合,起伏頓挫之奇。……一路夾敘夾議,恣肆汪洋,如萬頃驚濤,忽起忽落,真有排天浴日之奇。格局極爲完密,而正意、喻意,縈回宕漾在有意無意之間,微雲河漢,疏雨梧桐,可以想其逸致矣。(劉鳳苞《南華雪心編·馬蹄》篇末總評)
【思考与讨论】
1、本篇与《骈拇》篇的主旨大致相同,请作比较分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