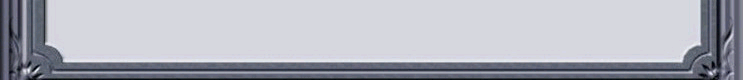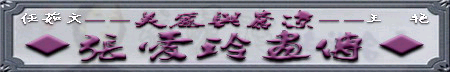
第03章 葱绿:学生天才梦
(1939-1949)
这是她第一次出远门。她母亲与姑姑托了在英国认识的老友工程师李开第先生作她的监护人。这个人后来还成了爱玲的姑父。
爱玲的同学中,大多是东南亚各国有钱华侨的子女,也有本埠和上海的学生,家里也是富裕的。爱玲当然没法跟他们比。但是,她暗暗下决心,要好好用功,用优异的成绩来获得奖学金,这样就可以减轻母亲的负担。而且港大优秀的学生毕业后还可以送到英国去留学。爱玲希望能够获得这个机会。这样,她就可以实现自己残缺的英格兰之梦了。
而此刻,外面的世界正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从30年代起,中国大地上遍燃战火,香港却因为各种因素未受战火之扰。在时代的造就之下,香港变成了离乱的中国文学的洞天福地了。1939年3月26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战协会”在香港成立,由许地山担任主持工作。同时,许先生还在港大担任教授。七七事变后,大批知名作家抵港,茅盾、夏衍、于伶、萧红、端木蕻良、骆宾基、戴望舒、郭沫若、叶灵凤等都活跃在香港,或办报纸刊物,或从事创作,香港新文学呈现空前繁荣,成为中国抗战前期的文化中心之一。大量文艺刊物遍布香港,如《文艺阵地》、《立报·音林》、《星岛日报·星座》、《华商报·灯塔》、《大公报·文艺》、《大风》、《时代文学》、《时代批评》等。那时候,后来在爱玲一生中留下深刻印记的第一任丈夫胡兰成就在香港。他以“流沙”的笔名在大名鼎鼎的《南华日报》担任主笔。但是,他们那时并不认识。
那段时间,爱玲几乎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为着实现自己的理想,她沉浸在“象牙塔”的小天地里。教西方文学的是位绅士气很浓的先生。他最爱讲莎士比亚。讲着讲着,他就会顺手掏出雪茄烟来燃上,当烟圈袅袅上升的时候,他就会沉醉在自己的世界里,陶然欲醉。教古典文学的是一位长须飘冉的老先生,总爱穿一袭长袍,颇有些仙风道骨的味道。爱玲总爱听他念楚辞,“长太息以掩泣兮……”而听他念“唐诗宋词”时,从他的眼里读得出长安风情,汴梁遗韵……爱玲还喜欢一位叫佛郎士的历史教授。他有孩子似的肉红脸,瓷蓝眼睛,伸出来的圆下巴,头发已经稀了,颈上系一块黯败的蓝绸作为领带。上课的时候他抽烟抽得像烟囱。一团黑柱,青烟直冒。尽管说话,嘴唇上永远险伶伶地吊着一支香烟,跷板似的一上一下,可是虽险,却怎么也不会落下来。烟蒂子他顺手向窗外一甩,从女生蓬松的鬈发上飞过,很有着火的危险。不过,幸好,每次都是有惊无险。
爱玲常常流连在图书馆里。她犹如一个欣喜的孩子,扑向一片广阔的海洋。那乌木长台,那沉沉的书架子,淡淡的书香味,那些精装书的厚厚书脊,摸在手上有一种冰凉的感觉。几间旧书库里显然是许久许久没有人来了。那些象牙签,锦套子里装着的清代礼服五色图版,大臣们的奏章……她甚至还找出马卡德耐爵士出使中国谒见乾隆的记载。那种欣喜的心情,真是不亚于当年哥仑布发现了美洲新大陆。她爱旧书库里那略微有些阴冷的空气。她爱这些因长年不见天日,而略微有些霉味的书。轻轻翻动它们,犹如握到了古人瘦骨嶙峋的手,触摸到了古中国一脉滚滚流动的血源。她觉得这脉血缘将永远流在她的血管里,一生一世。当时,爱玲的同学们是来自各地的。爱玲自己虽不善言辞,但她喜欢听她们讲述各自有趣的故事,学她们说家乡话,跳家乡舞蹈。小小斗室,总是盈满了欢声笑语。
在香港大学,爱玲认识了一生中最要好的朋友——炎樱。炎樱姓摩希甸,父亲是阿拉伯裔锡兰人(今斯里兰卡),信回教,在上海开摩希甸珠宝店。母亲是天津人,为了与青年印侨结婚跟家里决裂,多年不来往。炎樱的大姨妈住在南京,在爱玲眼里,那是个典型的守旧的北方人家。
炎樱是个漂亮的、活泼可爱的女孩子,而且常常语出惊人。炎樱个子生得小而丰满,时时有发胖的危险,然而她从不为这担忧,还达观地说:“两个满怀较胜于不满怀。”(这是爱玲根据“软玉温香抱满怀”勉强解释的。炎樱的原话是:“Two armfuls is better than on armfwl.”)炎樱在报摊上翻阅画报,统统翻遍之后,一本也没买。报贩讽刺地说:“谢谢你!”炎樱答道:“不要客气。”
炎樱买东西,付账的时候总要抹掉一些零头,甚至于后来在上海,在虹口犹太人的商店里,她也这样做。她把皮包里的内容兜底掏出来,说:“你看,没有了,真的,全在这儿了。还多下二十块钱,我们还要吃茶去呢。专为吃茶来的,原没有想到要买东西的,后来看见你们这儿的货色实在好……”
犹太女人微弱地抗议了一下:“二十块钱也不够你吃茶的……”
可是店老板为炎樱的孩子气所感动——也许他有过这样的一个棕黄皮肤的初恋,或是早夭的姐妹。他凄惨地微笑,让步了。“就这样吧。不然是不行的,但是为了吃茶的缘故……”他还告诉她附近哪一家茶室的蛋糕最好。
爱玲以一种欣赏的眼光看待着炎樱。炎樱也确实是一个有趣而聪明的人。炎樱说过一些很有趣的话,爱玲把它们记下来,这就是后来那篇妙趣横生的《炎樱语录》,其中,有一些诸如:
我的朋友炎樱说:“每一个蝴蝶都是从前的一朵花的鬼魂,回来寻找它自己。——”关于加拿大的一胎五孩,炎樱说:“一加一等于二,但是在加拿大,一加一等于五。”炎樱说:“月亮叫喊着,叫出生命的喜悦;一颗小星是它的羞涩的回声。”……
炎樱的这些妙语可谓秀气灵动,韵味十足。也许,炎樱与爱玲正好形成一种性格上的互补,因此才会如此互相吸引,彼此相悦许多年。
在港大,为了实现中学时代的理想——有一天能像林语堂那样用英文写小说成名,爱玲苦练英文,停止了中文写作,给家人写信也用英文。她还读了大量英文小说的原著,像萧伯纳、劳伦斯、毛姆、赫胥黎等人的作品。从这些作品中,她比较系统地接受了西方文化的熏陶。那时候,她最开心的便是收到姑姑的回信,姑姑多年游学海外,英文写得地道而流畅。那娟秀流畅的淑女化的蓝色字细细写在极薄的粉红拷贝纸上,还伴着一缕淡淡幽香。信里有一种无聊的情趣,总像是春夏的晴天。渐渐地,爱玲的英文水平大增,逐渐娴熟如母语。即便是随手拿来一本自然科学方面的书,也能毫无障碍地读下来。
惟一一次用中文写作,便是创作她的散文名篇《天才梦》。《西风》杂志创刊三周年举行征文比赛。要的题目是“我的……。”首奖奖金达500元。爱玲心中一动,她希望能获得一笔奖金来弥补学校的日常开支。而且,《西风》杂志在30年代走红一时,它以“译述西洋杂志精华,介绍欧美人生社会”为办刊宗旨,是爱玲颇喜欢的。
爱玲的应征稿是一篇有点自传性质的散文——《天才梦》。虽已有许久没用中文写作,但这篇文章文笔的老练,思想的圆熟,颇有“一鸣惊人”的效果。那是以一个富有灵气的“天才少女”的自叙展开的。她描述了自己种种超乎寻常年龄的孩子的“天才”: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目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
加上一点美国式的宣传,也许我会被誉为神童。我三岁时能背诵唐诗,我还记得摇摇摆摆地立在一个满清遗老的藤椅前朗吟“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眼看着他的泪珠滚下来。七岁时我写了第一部小说,一个家庭悲剧。遇到笔画复杂的字,我常常跑去问厨子怎样写。第二部小说是关于一个失恋自杀的女郎。我母亲批评说:如果她要自杀,她决不会从上海乘火车到西湖去身溺。可是我因为西湖诗意的背景,终于固执地保存了这一点。
我仅有的课外读物是《西游记》与少量的童话,但我的思想并不为它们所束缚。八岁那年,我尝试过一篇类似乌托邦的小说,题名《快乐村》。快乐村人是一好战的高原民族,因克服苗人有功,蒙中国皇帝特许,免征赋税,并予自治权。所以快乐村是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大家庭,自耕自织,保存着部落时代的活泼文化。……
九岁时,我踌躇着不知道应当选择音乐或美术作为我终身的事业。……
对于色彩、音符,字眼,我极为敏感。当我弹奏钢琴时,我想象那八个音符有不同的个性,穿戴了鲜艳的衣帽携手舞蹈。
在文章的后半部分中,爱玲的笔锋一转,写到自己“在现实的社会里,等于一个废物。”并且,列举出种种事例来证明:
我发现我不会削苹果。经过艰苦的努力我才学会补袜子。我怕上理发店,怕见客,怕给裁缝试衣裳。许多人尝试过教我织绒线,可是没有一个成功。在一间房里住了两年,问我电铃在哪儿我还茫然。我天天乘黄包车上医院打针,接连三个月,仍然不认识那条路。
这些在常人看起来非常平常的事,在张爱玲那儿却成了难事。也许,大智若愚。这只能算是“天才的乖僻缺点。”文章在最后得出结论:可是我一天不能克服这种咬啮性的小烦恼,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
在这篇散文里,我们聆听的是一个天才少女的心灵独白。我们读得出那流露在字里行间的自信,甚至有那么一点儿的自负。爱玲是一个有才华,而又勇于向众人展现自己才华的女孩子。后来,胡兰成曾称张爱玲是“民国世界的临水照花人”。他把爱玲比作古希腊那位有“自恋”情结的美少年。炎樱也说:“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喜欢自己作品的人。”也许,这篇散文可作为几年后,爱玲在上海文坛横空出世的一种先兆。天赋、早慧、怪僻、自恋,还有着一种天成的忧郁情调。这些心理情感的潜质,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无疑是非常有益的。
因为征文启示中规定字数。爱玲只好把这篇长文一缩再缩,颇有些“千古文章未尽才”的遗憾。此次征文共有685名应征者参加,其中有13人得奖,照启示原来规定,获奖者应是10人,因投稿踊跃,难以割舍,组织者又增加了三个名誉奖。张爱玲的佳作仅名列荣誉奖的最末位。获得第一名的是一篇悼亡之作《断了的琴弦——我的亡妻》,文笔内容俱一般,且字数是超过规定的。而且,在而后出版的获奖作品集所用的书名也叫《天才梦》。爱玲显然是对这次评奖结果愤然的。这次获奖给她带来的名誉,与她日后在文学创作上所取得的成就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的。然而,这次征文激发了她的创作欲望,也让我们看到了早年张爱玲的一些秩事。《天才梦》成为了爱玲早年时代的“压卷之作”。几年之后,当我们再次读到她的中文作品时,爱玲已是上海文坛上横空出世的才女,已是一个公认的“天才”了。
然而,毕竟是乱世中人。1942年12月,日本人进攻香港,中断了爱玲埋首书本的寒窗生活。战争刚开始的时候,港大的学生大都乐得欢蹦欢跳,因为12月8日正是大考的第一天,平白地免考是千载难逢的盛事。无论如何,学生总是对考试存有着一种畏惧的心理。对待战争,同学们各有各的态度。爱玲宿舍里的一个女同学居然还发起急来,说道:“怎么办呢?没有适当的衣服穿!”她是有钱的华侨,对于社交上不同的场合需要不同的行头。从水上跳舞会到隆重的晚餐,都有充分的准备,但却没预料准备好打仗的行头。后来她借到了一件宽大的黑色棉袍,对于头上营营飞绕的空军大约是没有多少吸引力的。还有一个叫苏雷伽的女孩子。她是马来半岛一个偏僻小镇的西施。瘦小,略黑皮肤,有着睡沉沉的眼睛与微微外露的白牙。爱玲觉得她“天真得可耻”。关于她的笑话在学校里早出了名,苏雷伽曾经顾虑到这一层:她选了医科,医科要解剖人体,被解剖的尸体穿衣服不穿?苏雷伽对衣服也是情有独衷。一个炸弹掉在宿舍的隔壁,舍监不得不督促大家避下山去。在急难中苏雷伽并没有忘记把她最显焕的衣服整理出来,虽然许多有见识的人苦口婆心地劝阻,她还是在炮火下将那只累赘的大皮箱设法搬运下山。苏雷伽加入防御工作,在红十字会分所充当临时看护,穿着赤铜底绿寿字的织锦缎棉袍蹲在地上劈柴生火,虽觉可惜,也还是值得的。那一身伶俐的装束给了她空前的自信心,不然,她不会同那些男护士混得那么好。同他们一起吃苦,担风险,开玩笑,她渐渐惯了,话也多了,人也干练了。战争对她是很难得的教育。可是,即使在生死关头,她还是不忘她的衣服。可见,女人之于衣服,可能有着一种天生的嗜好。
然而,大多数人对于战争所抱的态度,爱玲曾打了个譬喻,“是像一个人坐在硬板凳上打瞌盹,虽然不舒服,而且没结没完地抱怨着,到底还是睡着了。”
是的,八十多个死里逃生的青年人聚集在一起,因为死里逃生,更是充满了一种生气:有的吃,有的住,没有外界的娱乐使他们分心;没有教授,可是有许多书可看,诸子百家、《诗经》、《圣经》、莎士比亚——正是大学教育最理想的环境。可是,在那样的情况下,谁还会真正有心思看书呢?同学们只拿它当做一个沉闷的过渡时期——过去是战争的苦恼,未来是坐在母亲膝上哭诉战争的苦恼,把憋了许久的眼泪出清一下。在百般的聊赖中,在阵阵的炮火中,爱玲读完了《官场现形记》。也许,“谴责小说”的魅力,就在于让你在笑声与谐趣中品尝苦涩与辛酸。爱玲不禁为古小说的魅力所倾倒。爱玲一边翻着,一边又担心能不能在炸弹下来之前把它看完。字印得极小,灯光又是昏昏的,但是,爱玲想着,如果一个炸弹下来,还要眼睛做什么呢?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也许,在战争中,人的本性表现得更为彻底。战争中人们去掉了一切浮华,剩下的仿佛只有“饮食男女”这两项。两千年前的孔老夫子就说“食色性也”。虽然,人类文明的教化,其终极的目的是为了跳出远古兽性生活的圈子。可是,一旦陷入生死存亡的困境,人的精神就会失去依托,陷于极度的虚空。事实正是如此。香港的外埠学生困在那里没事做,成天就只买菜、烧菜、调情——不是普通的学生式的调情,温和而带一点感伤气息的。
与此相随的是,在战乱中,人们承受着无牵无挂的虚空与绝望。人们受不了这个,急于攀住一点踏实的东西,因而结婚了。看看香港报上挨挨挤挤的结婚广告便知道了。学生中结婚的人也有。“一般的学生对于人们的真性情素鲜认识,一旦有机会刮去一点浮皮,看见底下的畏缩,怕痒,可怜又可笑的男人或女人,多半就会爱上他们最初的发现。”爱玲也觉得他们过早结婚的悲剧在于“限制自己的活动范围”。这对于求知欲、交友欲最旺盛的年轻人而言,当然是无益的。爱玲清楚地记得,在“围城”的日子里,有一对男女去她们办公室向防空处长借汽车去领结婚证书。男的是医生,爱玲揣测他“平日也许并不是一个‘善眉善眼’的人”,但是他不时地望着他的新娘子,眼里只有近乎悲哀的恋恋的神情。新娘是看护,矮小美丽,红颧骨,喜气洋洋,弄不到结婚礼服,只穿着一件淡绿绸夹袍,镶着墨绿花边。他们来了几次,一等等上几个钟头,默默对坐,对看,熬不住满脸的微笑,招得那些年轻的学生们都笑了。也许,在那样提心吊胆、朝不保夕的生活里,爱玲觉得“实在应当谢谢他们给带来无端的快乐。”
除了情爱,还有一大主题便是“饮食”。宿舍里的男女同学整天讲的无非是吃。爱玲说:“真奇怪,一件最自然,最基本的功能,突然得到过分的注意,在情感的强烈的照射下,竟变成下流的,反常的。”爱玲和炎樱也被这种气氛所感染。香港陷落后,她们曾经满街的找寻冰淇淋。她们疯狂地撞进每一家吃食店去问是否有冰淇淋。只有一家答应说明天下午或许有。于是她们第二天步行十来里路去践约,叫到一盘昂贵的冰淇淋,里面吱格吱格全是冰屑子。因为没有汽油,汽车行全改成了吃食店,没有一家绸缎铺或药房不兼卖糕饼。在战后的香港,街上每隔五步十步便蹲着个衣冠楚楚的洋行职员模样的人,在小风炉上炸一种铁硬的小黄饼。渐渐又有试验性质的甜面包、三角饼、形迹可疑的椰子蛋糕。所有的学校教员、店伙、律师帮办,全都改行做了饼师。人们立在摊头上吃滚油煎的萝卜饼,却对尺来远之外的脚底下就躺着的穷人青紫的尸首却熟视无睹。没有一点怜爱,没有一点同情心。也许看得太多了,自身都难保,还管得了那么多吗?香港从来没有这样馋嘴过。那些从天上缠绵飘下来的雨丝,是香港流的“口水”吗?今朝有酒今朝醉,明天还知道会怎么样呢?
在百般的空虚与无聊中,爱玲重操旧业,画了许多的画。她仿佛又回到了在圣玛丽亚女校时的中学时代,当时她就常在课堂上躲在下面画画。对线条与色彩的敏感,对她后来的写作也是很有帮助的。爱玲觉得,在战争这段时间是她绘画上的黄金时代,以后再也休想画出那样的图来。即使以一生的精心为那些杂乱重叠的人头写注解式的传记,也是值得的。譬如说,那暴躁的二房东太太,斗鸡眼突出像两只自来水龙头;那少奶奶整个的头与颈便是理发店的电气吹风管;像狮子又像狗的,蹲踞着的有传染病的妓女,衣裳底下露出红丝袜的尽头与吊袜带。无论是爱玲的画还是文字,总是那么的犀利,有一针见血的功力。爱玲后来正如她所愿的,确实从事了“为那些杂乱重叠的人头写注解式的传记”的工作,只不过,不是用画笔,而是用文字,但两者有着某些异曲同工之妙。爱玲与炎樱则不愧是高山流水遇知音。爱玲特别喜欢炎樱有一幅画用的颜色,全是不同的蓝与绿,使人联想到“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两句诗的温馨意境。回到上海后,爱玲多次拿出战时画的画来欣赏。“自己看了自己的作品欢喜赞叹,似乎太不像话。”爱玲想着要重新照着样子再画一遍,但是再也画不出来了。也许正如李商隐诗中所说的:“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香港对爱玲而言,确实是一个有点“宿命”色彩的城市。爱玲是爱香港的,这里有她年轻的美丽的梦。她可能不会想到,十年后,她再次离开这里时,将是永别祖国,开始四十余年异国飘泊的生涯……1942年初,爱玲与炎樱搭上了回上海的轮船。香港海依旧蔚蓝如昔。可是,该死的战争,摧毁了香港大学爱玲门门优秀的成绩单,也摧毁了一个女孩子美丽的“英格兰之梦”。别了,香港!别了,英格兰之梦!
船过浅水湾,爱玲当时也许并不知道,浅水湾坟地的海边,刚刚添了一座新坟。一位才华横溢的天才女作家萧红孤独地长眠在那里。落红萧萧几人知?!1942年1月19日,病重的萧红在医院中已不能说话,惟在纸上写道:“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脸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22日,萧红含恨离开了世间,年仅31岁。从遥远的黑龙江呼兰县到青岛,从上海到东京,再到香港,从《王阿嫂的死》到《生死场》,从《呼兰河传》到《小城三月》,从与萧军的一见钟情到最后的黯然分手,萧红的人生道路是坎坷而曲折的。短短一生,她渴望能够照彻生命的煦阳,却屡遭凄风苦雨;企图飞出宿命的苑囿,却如小鸟过早地折断了羽翅。自古才女多磨难,一代情事痴后人。爱玲是在回到上海后才知道萧红的故事的。扼腕之余,倒颇有一种“心有戚戚焉”之感。船向前行驶着,和活泼的炎樱在一起,爱玲倒也没有多少伤感。毕竟,上海是一个留下她童年和少年时代足迹的地方。虽然回忆并不愉快,但“毕竟是上海人”啊!那一份亲切的故园情是挥之不去的。
船身摇晃着,爱玲却觉得好像坐在火车里,她感觉得到时光的流逝:“时代的车轰轰地往前开。我们坐在车上,经过的也许不过是几条熟悉的街衢,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有惊心动魄。就可惜我们只顾忙着在一瞥即逝的店铺的橱窗里找寻我们自己的影子——我们只看见自己的脸,苍白、渺小;我们的自私与空虚,我们恬不知耻的愚蠢——谁都像我们一样,然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孤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