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与“××”共舞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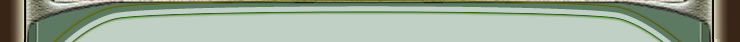 |
 |
|
夏天,“非典”结束,一切又都恢复了以往,外面又闹哄哄地开始有各种活动,市场也好像又搞得热热闹闹了。街上、路上的人,也一下满当当的。总想到“倾巢出动”这个词。
先是有人跑来告诉我,说有人说你老师余秋雨在深圳有别墅啊,是别人送的。我说胡说,我去过他深圳的家,我还不知道。后来又听到一些关于这件事情打官司的细节,尤其听到一审判决在查明余老师并没有收取别墅的情况下,依旧判的余老师输,原因据说一是“商业
社会收取别墅是正常的,无所谓”,二是“这样的造谣并没有影响余秋雨,他的书照样卖得很好”。
这是余老师第一次“打输”官司,虽然还只是一审,但我还是有些替他着急。这个官司是在北京打的,我弄不明白人们是怎么想的,也许商业社会收取别墅确实是正常的,但却不能忽略人家是不是真的收取了别墅这一事实啊!还有第二种说法,认为造谣并没有影响余秋雨的生活——如果在这里换一个比喻也许就一清二楚了,这就好比说有人偷了李嘉诚的钱,却声称并没有因此而影响李的生活,就不算偷了,就偷得有理了!这肯定是不通的。
我给余老师打电话,说我才知道别墅官司的事,是朋友看到报道告诉我的,怎么,你没有生气吧。余老师当然说我没有生气,我不生气,我正在准备上诉。
我从电话里感受到,他还是那样地达观,信心百倍。又要打官司,我在心里想,但愿真的像他上次说的那样,这些事情并不会影响他的写作和生活,他不会让自己成天陷于其中的。
上班的时候,又有人把一张报纸递到我眼前,让我看。我望了一眼,一整版,上面有一张人脸,一些文字,是说有人挑了一百多处余秋雨文章中的“错误”,并为此写了一本长达二十几万字的《石破天惊逗秋雨》。我把报纸推向一边,很淡地说我对这个不感兴趣的。
因为自己一向就对那种吹毛求“屁”的东西提不起兴致,更对别人打着余秋雨的名字搞炒作有反感,所以拒看了那篇报道,对边上的人提到的那本相关的书,更表示要拒看。在我的眼里,这都是些与自己的观念、方式相去甚远的“土人”。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的严重,完全只是听凭自己的第一反应,淡然处之。
后来才知道,事情并非我以为的那么简单和单纯。我低估了大陆多数媒体所谓“颠覆名人”的心理与能量,也忽略了受众对余秋雨这么一位名人、大家的浓烈兴趣。更没想到这件事情的覆盖面会有那么广。
我从一位长期在北京工作的上海人高滨先生的《为上海感到难过》一文中,了解到当时的情况:
“前些天回上海探亲,亲眼目睹了这种机制性弊病的实际运作方式。当时,上海的两家报纸正在大规模地‘开涮’余秋雨先生,也就是被《中关村》杂志评为上海目前有全国影响的仅有的几个文化人中的第一人。‘开涮’的方式非常‘上海化’,有精巧设计有新闻效应,有经济效益。
“先是《咬文嚼字》杂志的编辑金文明先生宣布不满意余秋雨先生发表的反盗版宣言,更不满意余秋雨先生的秘书拒收《咬文嚼字》的赠送,便在上海报纸上发表《我为什么咬余秋雨》的整版谈话,说是找出了余秋雨先生书籍中的一百多处的所谓‘文史差错’,并且宣布已经为此出了一本书,书名叫做《石破天惊逗秋雨》。
“初一看这是一个‘学术争议’,其实不然。如果是‘学术争议’,为什么大规模地交给市民报纸,就像文革中的广场大批判操作?如果是‘文史差错’,哪怕是真有,又哪里谈得上全社会的‘石破天惊’?毫无疑问这是要利用上海小市民的围观起哄心理,用一种消解有资格的评判机制的手法,制造一个低劣的‘文化新闻’。他们预计到余秋雨先生必然会本着‘对产品质量负责’的态度对读者有一个声明性解释,这又被快速组接成了‘两人争论’。争论需要有‘调解人’,上海报纸推出来的恰恰是《咬文嚼字》的主编郝铭鉴先生,他的‘调解’面带笑容,称兄道弟,但用词用语又远比金文明厉害。当主要当事人冒充了调解人和审判者,只能是这个结果。他‘调解’一完,有关报纸可能收到太多读者的反映,立即停止讨论,于是,上海的结论就做在《咬文嚼字》的那个主编身上了。这整个过程,明显有一种故意炒作的‘私设公堂’性质。
“余秋雨先生作为名扬全球华文文化界的作家学者,突然‘后院失火’,当然成为一条重大新闻。据我所知,全国绝大多媒体都报道了,全球绝大多数华文媒体也都报道了,但采用的都是上海报刊的结论。由于如此大规模的操作,金文明的那本《石破天惊逗秋雨》的书因余秋雨的名字而十分畅销,登上了《亚洲周刊》排行榜,金文明先生顷刻之间成了富翁。这个结果也是纯‘上海化’的。”
原来如“比”!这让我这个早对上海人就有成见的人更加地不屑。这位高滨先生作为在北京工作的上海人,身怀双重身份,是上海人的“他者”,也是上海人“自己”,他把上海人看得很清楚,他的文章里更多对自家人所做“不上路”事情的难过,是在为上海这个城市难过和痛心。
其实在上海的文化界,理解和认同余秋雨的人还是大有人在。不久前就看到上海复旦大学周洪林教授的一篇文章《文化人的人文素养——由余秋雨的苦恼想到的》,觉得他文中的许多说法,建立在对余秋雨散文有全面研究与把持的基础之上,最要紧他同样清醒地意识到这次炒作事件所带出的学术上的根本性分歧,也正好是我自己过去和现在所领悟和倾向的。他说:
“长期来下苦功作为专题专门搜集、研究余秋雨差错的批评者,这次‘愤慨之极’是因为余秋雨的一段话触发的。余说:‘我认为,年轻人热爱文史知识不错,但是大量非专业的年轻人没有必要过度沉溺在浩如烟海又真伪难辨的古代文史细节间。因为这样做既是个人的不幸,也是中国文化的不幸。’依我看,这节话不但没有错,而且正说明了余秋雨高于一般文化人的地方,不停留于就事论事,还发展到个人治学道路、特别是中国文化历史与全局上,视野广多了,抓住了主要的倾向性问题。”
周洪林作为一名大学教授,也由此想到了我国现时的中学语文教学状态,清醒地指出其弊端:“长期来我国的语文教学,从总体上、主要倾向问题看,在于过多地钻牛角尖、死抠死记硬背冷僻词语掌故,弄得支离破碎,学生不堪重负、兴味索然;而对于贴近生活、通俗易懂的范文阅读欣赏中思想、情操、意境的感悟、揣摩、影响反而没有突出,实际上这是最重要的。把生动活泼的范文,异化为枯燥乏味的烦琐考证,是语文教学中的左道旁门!我所接触的大中学生,他们之所以喜欢余秋雨的散文,主要在其大气、大开大合、思路开阔,想象力丰富,又通俗易懂、不难读,更无陈词滥调繁琐说教,这是与青少年生气勃勃的特征是相一致的,真正少年老成、之乎者也,也喜欢咬文嚼字的毕竟是极少数。”
我感到周洪林先生作为一名居住上海的学者、研究者,在方式方法上是认同和支持余秋雨老师的。他认为“观念的转变才是根本的转变,观念、整体感、大思路、方向,对所有局部、细节有指导意义”,而文学散文“有别于专门的读史札记,更不同于历史考证专门在小学、掌故、史实等出处、索隐、注疏上下功夫,无证不信、孤证不立、无一字无来历,彼此在兴趣、方法论、价值观念等一系列问题上是有不同的,存在基本区别的”。
对于远在北京的我看来,这整桩事情的运作,最后又一次回到了观念的根本分歧、方法的根本分歧上来。就像周洪林先生说的,“如因批评者长期来细节考证搞多了,总体思想反而被忽视,见小不见大,确实不理解的,那我们应予原谅,不知者不为过嘛!但无论如何,不能明明是自己不理解,却反咬一口、倒打一耙,以两个‘不幸’作为余‘拒谏’的最重要依据而‘愤慨之极’,那就没有道理了!而正是由于这种对明明正确的观点,视为‘拒谏’、因此‘愤慨之极’、兴师问罪,使批评的出发点与归宿发生了根本动摇,掩盖了争议的根本思想分歧!”
这实在是很绝望、痛心的事情。
早些时候听金克林说他们大可堂文化公司要出一本余秋雨《文化苦旅》的线装书,他还答应送我一本。后来知道,这件事情的背后还发生过一次“电话事件”。那时,《石破天惊逗秋雨》一书在大陆和台湾同时出版,并在香港连载,大陆多数媒体自然也争相报道,成为一个重大文化新闻。不过此事并没有影响大可堂文化公司与上海辞书出版社合作制作《文化苦旅》线装书的计划,因为他们认为这样的指责无损于余秋雨著作的文化高度和美学高度。
好玩的倒是,大可堂公司的老总这时突然接到一个“奇怪的电话”,自称《石破天惊逗秋雨》的作者,他强硬地要求大可堂立即停止发行余秋雨的书籍,还说“我们已经组织大批人员,专门批判余秋雨的作品,包括《文化苦旅》《山居笔记》《霜冷长河》《千年一叹》《行者无疆》等”。
我听到这个故事,惊讶得说不出话来。真不敢相信在现在国家这样的氛围里,还有人土到用这样的态度和口气来行事。这让我这样一个悲观消积分子更加地绝望,也更加地替余老师难过。现在是什么时代了,我们边上一些组成我们生存环境的人,他们的观念和作派与我们如此地大相径庭,风马牛不相及。用我自己的话说是“土到了家了”。我们完全处在不同的思维与行动体系里,我们也本来完全可以各行其是平行发展的,但最终不仅遭遇对方挑衅,而且为了保卫自己有可能还要被迫进入对方的价值体系当中,这是万分痛苦的事情。最难过我们生于斯长于斯,必得在这样的环境里共存,想躲也躲不掉,想甩都甩不脱。
我猜想余老师一定很苦恼,那些对他做下这样事情的人们并非都是些陌生人,他们过去都曾在上海的文化大圈子里出入,即使不是熟人也可以是熟人的熟人,有什么样的“学术问题”不可以交流呢。不是另有原因,完全不需要这样弄得满城风云的。又想起几年前要余秋雨“忏悔”文革历史问题的事,也闹得沸沸扬扬,逼得余老师打起了官司,最终由被告向余老师当庭道歉了结。那次是想要推毁一个人的人格,而余老师不得不花费几年的时间来清洗一群人对他的泼污;这次,却又想要摧毁他的文化尊严,我想不出余老师该怎么办才好。如果保持沉默,在中国现在这种文化氛围中,不自救,必然就要失去自己的文化尊严;如果站出来接招“自救”,必然又要进入对方的价值体系,连整个的自己都失去了。
突然联想到自己很多年前和人吵架的事情,就有点这样的意思。也算是一个不太愉快的记忆。
那是一位大我十几岁的女性,有老公有孩子,我那时还没从失恋中缓过劲来,连个男朋友都没有,她却不知为什么十二分地看我不顺眼,总是我说一句什么她就要接住下一句,好要重重地抨击我。
我天性淡漠很少接她的招,依旧和周围别的女孩儿们打闹成一团。但住在同一间集体宿舍,有一天还是针尖对麦芒地接上了话茬。当时正是晚上,大家洗漱完毕都上床了,怎么就锵锵了起来。她的话令我很气,但串起她那些话的主线或者现在说的“理念”,依旧那样地与我所坚守的东西相去甚远,又一下消解掉我与她吵架的激情。她说你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发表了几篇小说吗,狗屁。我毫无激情,只跟着她的话说,是啊我有什么了不起呢,不就是发表了几篇小说吗,狗屁。她又说别以为自己有多大的才,有才的人多着呢。我还是懒散
散地说,就是啊别以为自己有多大的才,有才的人多着呢。
总是她说什么我跟说什么,慢慢地她就在蚊帐里气成一团,一本书在床上乱拍。我还是不急不恼,把她的话照单全收后再还给她。最后她声音都气哑了狂叫一声:我看你早就不是Virgin了!
这话,说一个女孩不是处女,在八十年代那是很厉害的。以她的观念和境界,以为这下总算戳到我痛处,足以击垮我。我的反应大概要么眼泪横飞,要么扑上前去与她扭打成一团,惟此才能一示“清白”。当时我听得自己心里呻吟了一声,倒不是被她的“揭露”击中,而是搞不懂自己为什么要与这样一个完全牛头不对马嘴的人住同一集体宿舍,还朝夕相处!我在心底里对她的方式感到蔑视,说自己是处女和说自己不是处女,那都已经进入了她的价值体系。
我反倒轻松下来,我用讨论学术问题的口气问她:二十四岁还是处女,你说说这是我的耻辱呢还是我的骄傲。我们好坏也同学一场,你又是过来人,女儿都那么大了,我要讨教你,你刚才是真的在骂我还是夸我?
她手里的书在床上又是一阵乱拍,那动作和声音甚至让我想到了辛弃疾的把“栏杆拍遍”。
第二天小师妹们对我说,昨晚一开始差点被你们两个老的吓死了,生怕你们撕破了脸面扭打成一团,让我们不知劝谁才好,不过后来听着听着越听越高兴,就像听相声,都不愿你们停下来。她们说马小痞真有你的,还挺会吵架的,把谁的肺都气炸了。我说我还会吵架?我吵了吗?语言体系不一样,吵不起来呀。
她们不知道私下里我还是很憋气,肺也差不多快炸了。可是我如果真与她对骂兼对打,我也就成她那样的人了。那是连我自己也看不上的。
8月份在北京见到余老师和马兰时,这件事情还笼罩着他们。那天我刚好去采访公安英烈子女夏令营营员,平生头一回穿着警服,笔挺挺坐在港澳中心的瑞士酒店大堂里,很不自然。我说我来不及换衣服了,不过这样也是想让你们惊讶一下。余老师和马兰果然很惊奇,没想到马小娟变成了这个样子。我拿出采访用的相机,说我们干脆来照相吧。于是马兰帮我和余老师合影,余老师又帮我和马兰合影。他们说我们是和警察一起照相啊。
很久以前余老师说过要和穿警服的我照张相,我一直当是件几乎不太可能实现的事,因为我从来就没穿过警服。没想到这次头一回穿上了警服,因为好玩,还头一回想起要和余老师、马兰在一块儿照张相。
那些日子他们在北京的东区挑房子,想在北京安个家。我刚说出我知道的一处东区楼盘,马兰马上说下午就去看。虽然这之前我早和余老师讨论过他们在北京买房子的事情,但这样的情形下,看到他们兴致勃勃、有所期待的样子,不由得就想到“逃离”这个词。心里又有些难过。
余老师说他们刚从海拉尔回来,连那么远的读者都看到了那些报道。他问我看到没有。我说知道这件事,但不看。他苦笑起来,说不是谁都不看,看的人太多,这些报道已经发得全国都是,像你这样拒看的人很少。我走到哪里都有人问起。
我不知怎么回答他才好。这是舆论的悲剧。现在媒体要说一个人好,大家会觉得没多大意思,媒体也会觉得没什么可炒作的。可要说坏,那可就太好了,太有炒头了!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便全体一哄而上。所谓文化的管理者们对这样的事情却完全听之任之,不知如何来引导,更不知如何来保护那些卷入其中的文人们。要等到事情真的闹大了,全世界都知道了,才可能会有政要人物出来说一声“别闹了”。这时倒真的不闹不炒作了,结果却在不该了结的时候戛然而止,一切就都停留在原先的说法上,读者也以为那便是最后的结论。叫人哭笑不得。
熟悉上海的高滨在文章里也说,“这使我想起几年前要余秋雨先生‘忏悔’文革历史问题的事件,事情虽然由余杰打头炮,但真正造成巨大伤害的是上海《文学报》发表的一篇文章,那篇文章也被海内外多数报纸报道。与这次一样,那篇文章发表后,一切讨论也都突然停止,那篇文章也就成了上海的结论。”
这怎么搞。
这种情况下,我总在替自己的老师难过和绝望。不知怎么地想到了年前香港的刘嘉玲“裸照事件”,那时从香港、台湾等地的报纸杂志上看到香港一大批的演员自发站出来抗议的大幅照片,看到他们一个个的表情和装束,心里真的很感动。觉得他们身为影视演员(按他们的说法叫艺员),平时各演各的戏各挣各的钱,也可以说是处在相互的竞争当中,但当遇到自己同类身处外界不怀好意的陷害与欺侮时,决没有那种在一旁看笑话的事出现,而是像现在这样集体肃穆出阵,站立在刘嘉玲的身后。
这是对刘嘉玲的声援,也是对自己作为演员的身份的捍卫。让我感动,并且对这些平时不以为意的香港明星们起了敬意。
还想起一件类似的事情。背景也是在香港。香港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先生,也是一位社会问题专家,他开的专栏据说读者很多,他所表述的社会理论和经济理论既有优美的文字,又有很活泼的思想,在香港自然有很大的影响。有人就在媒体上提出疑问:张五常先生写了
那么多的书,会不会影响他在大学的教学质量?结果是张五常先生所在的大学出面与媒体打官司,索赔了一百多万。
在国外,在香港、台湾,个人名誉是值钱的,诽谤、造谣会让自己付出巨大的代价。我们的法律制度建设当然还需要有一个不短的过程,但至少我们自己要有法律意识才好,尤其对断文识字的人。现在连村里人都知道,在自家屋门口骂大街,还有可能招来乡亲们要求精神赔偿的官司,知道要就事说事,管住自己嘴巴。
有时会暗吃一惊,莫非社会与大众真的已失掉最基本的判断力与良知,成了别人喂什么吃什么的混沌小儿。
后来从一些出版社编辑甚至与余秋雨有点关系的熟人那里得知,这一事件中,其实有许多的读者都站在余秋雨一边,一直就在抗议和反对对余秋雨的围攻,他们也曾写了大量的维护和保护余秋雨的文章。不幸的是,没人愿意刊登他们的文章。也许他们的声音不适合媒体炒作的需要,不足以满足大家围观和看热闹的心理?许多人投书无门,只好把自己的文章投到出版社、投到余秋雨书的编辑,甚至寄到那些可能有途径与余秋雨联系上的人那里!而这些地方、这些人,又都不具备发表他们文章的可能。
一位重庆的退休教师马孟钰先生,就写了一篇《七十岁的愤慨》,说自己“发现余秋雨先生又遭新一轮的攻击,很感伤心;等读完金文明的那本《石破天惊逗秋雨》,我和我的老伴、儿子都一起愤慨了。我们无法袖手旁观,就在三十六度的高温下,拼着我这条老命,挥就此文”。我想这是一位仗义执言、古道热肠的老者,看到自己喜欢的余秋雨先生的遭遇,便一分钟也坐不住了。
他说:“对于金文明这样的人肆意糟践余秋雨、剥夺余秋雨,我们不应该不闻不问,或站在一旁看热闹。古往今来,有几个人能像余秋雨那样,放弃官职,冒险深入不毛之地进行考察,坚持以历史情怀播撒文明的种子?又有几个人能像他那样,能够长久不懈地提供惊动四海的思想和笔墨,引起海内外千百万读者共鸣?
“我相信,不管金文明等人多么嚣张,广大‘秋雨迷’也不可能转化为‘咬嚼迷’。我们希望余秋雨先生不要理他们,保持沉默,继续赶路,但要做到这样,我们大家不能沉默。正直的中国文人,应该用良知筑成围墙,保护奇花佳木,抵御那些连骨髓都想咬的牙齿来咬噬文化创造者。”
老先生的一番话与举动让我想法多多,他只是个退休教师、普通读者,在看热闹的人堆里他能够站出来,支持余秋雨不要理会别人,而要继续走自己的路。更可贵他还想到“我们大家”却“不能沉默”,他用他苍老却有力的声音呼吁:正直的文人要以良知保护真正的文化创造者。这说明老先生自己就是一个有良知、有责任感的人。他希望有更多的人打破沉默,和他一起来保护余秋雨。
这些可敬的老人,他们自己曾在过去的岁月里亲历亲睹过那些动辄揭人“灵魂”致人于死地的噩梦年代,在今天这样的新时代里猛不丁又听到那似曾相识的声音,他们真正地“不寒而栗”了。他们决不容许别人对他们喜欢、珍爱的余秋雨再行“正常文学批评之外”的乱棍攻击。
“中文在线”网站更出于对签约作家和签约作品的保护责任,在几个月里邀请多方文史专家,对金文明一书进行认真的判读,作出四项综合意见,在自己的网站上及时与读者进行了沟通。
这份“中文在线”的声明指出,“金文明先生所提出的一些指责,基本上都是极琐碎的细节,历来更是众说纷纭。对于这些细节的不同阐述,如果一概武断地判定为‘错误’,不是正当的学术态度”;认为“即使有些文史细节确有探讨的价值,也不应该把事情立即交付给对这些问题不具备评判能力的大众媒体。”“这种‘广场大批判’式的炒作,完全不符合正常的学术规则”。
出于保护广大消费者权益的责任,声明指出:由于这种大规模炒作,《石破天惊逗秋雨》一书未售先热,发行量巨大,登上香港《亚洲周刊》畅销排行榜,金文明和出版社都在顷刻之间获得了巨大经济效益。这显然利用了“凡是余秋雨先生的读者都会买这本书”的市场心理判断。但是广大读者买到的这本书,与他们被媒体炒作误导的预期心理完全不符,因为如果真要指出“一百多个差错”,几页纸已经足够,而金文明硬是撑足了厚厚的二十二万字,主要内容是一大堆到处摘抄、东拉西扯的枯燥文字。这对广大读者的消费权益,构成了明显的侵害。
在这里,无论是退休老教师的文章,还是“中文在线”的声明,都涉及到了一个如何更有效地保护文化创造者和消费者的问题。我们正处在文化机制市场化运作的初始阶段,许多问题到来前与出现后,国家相应部门就应该制定出跟得上市场发展需要的相关法律,保护文化建设,为我们自己和下一代创造一个安全和安心的文化创造与消费环境。有了一个好的环境,创造者与消费者的心情都是好的,都不必像现在这样,不上路子的事情一经发生,大家的时间和精力花在你说我我说你上,众说纷纭的,说得清说不清,都平添了阵阵恶心与不悦。
文化环境的种种欠缺,已导致许多优秀人才出走,导致优秀文化的创造力大量流失,这是国家、民族以及城市和地区的损失。
我不知道余老师和马兰那么热衷地在北京选择一所居处,是不是也有对于上海文化环境的失望。希望首善北京,可以有一个博大的胸怀、宽松的环境,提供他们一个身心愉快的创造空间。
21世纪的北京,毕竟与十几年前的八十年代不一样了,许多优秀人才已开始选择北京作为事业的发展基地,留住他们,也就留住了这座城市大量古遗迹之外更加鲜活的文化成份与分量,留住了城市文化建设与国家文化建设的巨大创造力。
作为北京人,我想要热烈欢迎余秋雨老师和马兰作我们当中的一分子,并祝他们在我们的身边生活好、事业好、心情更好。
2003年11月28日
|
|
 
本书由“啃书虫”免费制作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