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他还是积极的悲观主义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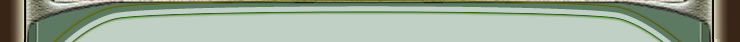 |
 |
|
他总是不放弃他的使命感、责任感。走得再远,看得再多,他的定位没有变,他要把中华文明作为自己思考与研究的依附点的信念没有变。他似乎对这样一段文明的延脉、这样一个民族的未来,更加充满了肯定和希望。
“千禧之旅”归来他说:“离别之后读懂了它——这句话中包含着沉重的检讨。我们一直偎依它、吮吸它,却又一直埋怨它、轻视它、责斥它。它花了几千年的目光脚力走出了一
条路,我们常常嘲笑它为何不走另外一条。它好不容易在沧海横流之中保住了一份家业、一份名誉、一份尊严,我们常常轻率地说保住这些干什么。我们娇宠张狂,一会儿嫌它皱纹太多,一会儿嫌它脸色不好,这次离开它远远近近看了一圈,终于吃惊,终于惭愧,终于懊恼。”
欧洲之行归来,他说:“即便是与欧洲文明有着太多历史恩怨的中华文明,也不会一味执着于各个文明之间的冲突来谋求自我复兴,它正在渐渐明白,自我复兴的主要障碍是近处和远处的蒙昧与野蛮,因此更需要与其它文明互相探究、互相学习、互相提醒,然后并肩来对付散落处处的憧憧黑影。”
这样的话语,至少在我这个暂时还没有能力对几大文明进行实际的考察与比较、还没有发言权的人看来,这是一件非常坚决和勇敢的事情。
这是他的世界观使然吧。总是这样,勇敢地面对和接受现实,从不轻言放弃与绝望。他还是积极的悲观主义,在承认现实的前提下,选择那条积极的路线。就像他看待爱情一样。
曾经有一次,一个很常见的中国现实话题的议论,让我忽生愤懑与决绝,我甚至认为要想以最快的速度改变现状,只有依靠外力。当然国家主权不能丢,但管理层要全部由有过来经验的外方控制,所有规范、准则要对中国人强制执行,要从零开始,强制大家改变骨子里的劣根性。否则要靠“自我改造”,不知又有多少好时光被荒废掉了。现在总说要“接轨”,哪那么容易就接上了。
他笑我,摇头说不对的,我走了这么多国家,“殖民地”的结局就是什么也不是。你看看印度就知道了。
我绝望地说,我不是光指责别人,我知道我自己也是丑陋的中国人。就像我走在澳门、香港的街上,老忘了身处何方,哇啦啦一嘴说不完的话,看见马路上没车就想要过去,倒是周围本地人的安静、乖乖立在红灯下等待的样子,突然就提醒我,我有多么的丑陋,那个时候也一下就把我和当地人划分了开来。
他越发地好笑,说这说明你还算是有点慧根的。
我又开始攻击街上的建筑、城市规划,连带每年一次的春节晚会,绝望得不得了,主要是觉得浪费那么些钱,做点什么不好。好像常去国外考察的倒成了我了。
他有时也会很同意我,但没我这么偏激,他对这个国家的文化与传统,听上去比相对年轻些的我更有感情。比如春节晚会,我一听说有人想请他做顾问,就要他把所有那些土人全部赶走,找一些海外归来的艺术家,一些有现代意识的实力派,从灯光、造型、服装,到演出内容、形式全部翻新,要真正能体能现在中国人的艺术水准的。他听得更好笑,说你对晚会的期望值太高了,它只能是一台通俗的普通老百姓要看的晚会,办了十几年,它已经是一个传统,一样习俗了,你不能要求把传统和习俗都彻底推翻。它现在就像是年夜饭里的一道必上的菜,谈不上好吃不好吃,但一定要摆在那里,图个热闹。
可是有多少人投入其中,要花多少钱啊。我说。
我们谈到现在的白领,他对他们倒是充满了信心,认为他们现在能够在日常中领略最现代的管理方式和生活方式,接触到最现代的领域与人才,将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社会的行为、风尚。
我却依然悲观,一是他们人数太少,二是我担心他们一走出写字楼汇入大街上的人流,原先的许多本性就会被迫呈现。像我这样一个自以为蛮有点自律意识、经常和周围格格不入的人,还时不时地会没于大环境中浑然不觉,更何况那些必须要在现实中求生存并养活一家老小的人。
他跟我说到一些生活在国外的中国文人,他们其实并不像我们以为的那样舒适和舒心。脱离了一个文化的母体,人如浮萍,即使是拿到一个国际大奖,也无法彻底改变生活的境遇和精神的境遇。他说他在境外遇见一位作家,大家都以为他该春风得意忘乎所以,但他不完全开心,一提起祖国大陆眼睛就要红,就想要哭。更有一些完全不愿意了解一下中国国内现状的人,对现在国内发生的变化尤其是经济生活里的变化完全不清楚,人已经很老了,还生活在自己臆造出来的假相里,是很悲哀的。
我说这些事我也听到过一些,我很替他们伤感的。我的一位女友是出版社编辑,手里有一部某著名作家前妻的小说稿,就是写他们在海外的生活境况,其中也写到他们婚姻的失败,写到那位作家与别人国家的主流社会完全不相融的事实,还有他们的孩子在西方社会里的迷失。她讲给我听,我听得都有些难过,老么喀嚓眼的,还要搞那样的自我改造与自我折磨,真正是一团糟啊。我曾鼓动女友干脆把书做成纪实性的,再打上那位作家曾经创作过的几部小说名,做成中国流落海外的文人心态史、精神游历什么的,保管畅销。但是我的女友很有职业操守,作家和作家的前妻都是她的朋友,她不能伤他们中的任何一个,所以还愿意把书做成一般的小说,情愿它淹没在嘈杂的书市里无人问津。
我说我只是可惜了那小说后面的文化背景。
不过我一狠心又会想,一些人留在这里,到头也可能就堕落成无所事事靠国家养着的无聊文人,装模做样的,还动辄内耗生事,还不如把他扔到国外去自食其力,好歹也算是有事可做。
在余秋雨还在走着“千禧之旅”时,本土突然刮起一股“倒余”风,当时我和“博物馆”剧组的人甚至想要往南亚那边打电话,表示我们的声援,只是无法联络他才作罢。那时也不知马兰电话,后来从《千年一叹》里看到,凤凰台安排马兰中途前往南亚与余老师相聚,分手时马兰哭得很厉害,我想她的眼泪里肯定有独守在国内目睹丈夫被流言飞语围攻的委屈和疼心。
几个月后余秋雨随车队刚进入国内,马上有记者各种各样的追问包围住他。
“我无法回答这些问题,但对它们的出现又似乎全部知道。它们让我快速地明白,我真的回来了。”他说。
多么难过和失望的感觉。
但他还不轻言对整体的绝望,依然兴致勃勃地念叨:“它们的出现不会改变我考察的结论,也不会影响我要向海内外同胞报告对中华文明重新认识的好心情。”
我看他在2002年期间的一些“就名誉权官司答记者问”,其中的一次回答被命名为“此心落寞”,让我又替他有些难过。他终于也要打官司了,让我想到很多年以前他说的他有多么羡慕我这样的年轻人,他说我们的将来是一片明亮与希望。有时我会觉得他说的希望并非晚生了十几年的希望,但这次,我又突然替他悲哀起来,哀叹他生不逢时,哀叹他曾经生活过的时代,哀叹他有过的那些同时代人。一些人完全被牺牲掉了,却因缺乏应有的自省与革命能力,毫不自知,依然在有意无意地眷恋着旧有的时代习气。
我们在一起时几乎很少谈论那些令人不愉快的事情,只是通过阅读知道他的经历,他说过,“谎言总是只敢在背后煽动不知情的人,我的读者并不知情,我自己也没有向他们澄清过什么,他们居然还是信任我,可见文学的力量在于构建一种表层文字背后的生命互信”。我也是他们当中一人。
我这个对所谓“政治”厌恶得要吐的人,现在看到一个自以为和自己“一伙儿”的人被迫陷在过去的“政治”里争辩和重拾旧忆,不觉间就会替他难过和气愤起来。
小的时候,所有余秋雨的父亲和余秋雨本人有过的遭遇,都是我老爸经历过的。我那时很小,虽然到现在也不清楚老爸究竟有过什么样的心路历程,但那些年从柔弱的母亲身上传导过来的惊惧,是无边无际的,经常像大浪一样翻扑过来。那些眼泪,那些哭泣,那些黑漆漆的雨夜从母亲颤栗的电筒光圈里看到的大红叉子,还有那个熟悉的名字,一个孩子心里的天随时都会塌下来。我不好意思对余老师说,我后来看他的《隐秘的河湾》,看到他全家人那时的无助,那种无以为继,总是要哭,流很多的眼泪。搞不清是为他和他的亲人,还是为我自己的老爸老妈,为自己。说起来我其实什么也没经历过,但那种阴暗潮湿,那种蹿行在街上的特殊氛围,那种没完没了的随时都会袭来的颤栗,现在叫我想一下都恶心。
现在我的老师在他的一次次答记者问里回忆和细述他二十几年前的遭遇,一次次回到那样的背景当中,我真替他难过。
那时好像所有的人都在谈论他打官司的事。他却安慰我,你不要以为我就什么事也不干了,一头扎在官司里,每时每刻都在那里愤怒,在那里郁结难平。不是的。我还在做很多的事情,我该高兴还在高兴,该写作还在写作,该讲学还在讲学,打官司这件事不会影响我的生活。
他总是这样,任何时候都兴致勃勃,泰然自若。那次谈话,第二天也确实有一场大型的演讲在现代文学馆等着他。他并没有打断自己的日程安排。他还津津有味跟我讲他昨晚看的凤凰卫视中文台的一档节目。
我被他的轻松所感染,也回复原状,我说我看了你的答记者问,里面有一段话特别好玩,记者问你被告说他只是在做学术研究,把你当作研究对象,你怎么看。你说照他的说法,杀人犯还可以声称在做什么来着,还有制毒犯还可以声称在做什么来着,哎呀我都说不出那些词,很专业,特别形象,一针见血。他自己也笑起来,接住我的话:“照他的说法,杀人犯还可以声称自己在做‘心脏穿刺’的学术研究,制毒犯还可以声称自己在做‘兴奋剂配置’的学术研究呢。”
“遭围攻的几年来,我一直想寻找一个论辩对手,只须一个,却很困难。首先是语言风格的等级,我从小对这一点十分执着,近乎痴迷,就像日常生活中我无法与一个满嘴脏话或满口臭味的人讲话。因此前些年当有人把一篇篇与我无关的文章算在我头上时,我最先感到屈辱的不是政治问题而是语言等级,心想:‘我的笔下何曾流得出这种等级的词语!’我觉得‘词语冤案’比政治冤案更让我心痛,因为这是我的业务行当。那么,现在要在围攻者中找一个论辩对手,语言等级也成了一个入门标准。有时好不容易找到一个,但再读下去又立即失望。到后来,我干脆放弃寻找论辩对手的企图,心想,为了不发一言,连读者也对他们的诽谤迷惑起来,这多不好!那么,不妨降格以求,找一个稍懂点法律的对手在法庭上论辩几句也好,不管他属于什么语言等级。”
“我太失望了。我怎么就找不到一个稍稍像样一点的论辩对象和诉讼对象呢?此中情景就好像:一群人围着我伸胳膊蹬腿地叫嚷好些日子了,我正不耐烦,转身刚摆出一个出拳的架势,谁知那个嗓门喊得最高的老兄立即逃奔到一个根本无法藏身的帘子后面哇哇大叫。我不得不长叹一声,当然也不想立即收拳,但心中的落寞,无以言表。”
打官司本是件很严肃、很烦人的事情,可我看到他这样的话语就觉得好玩,就想笑,那
种笑着笑着慢慢就难过、绝望起来的过程,简直被他掌控得如丝如扣。这还不是黑色幽默!即便是一场官司,也难弃他自身的天赋与才气。
所以用“此心落寞”来做这样一次访谈的标题,真是再恰当不过了。
不知为什么,我有时会突然感到他像塞万提斯笔下的绅士“骑士”堂吉诃德。我知道我这样子想他,他一定哭笑不得,但他总那样兴冲冲的、总不轻言绝望与放弃的姿势,尤其是总忍不住要流露他对本土的历史与人文的好感、信念,却又总是被一些象征这个国家文化事业的人们的攻击最多,受伤害最深,有时真没法不让我这样想。
他自己,则更愿被当作“铁汉子”,对香港报刊称他为“铁汉子”“心里有点暗喜”,因为“他们看出了我斯文外表下的刚毅”。
当然,我心里也还是很明白,他的“中华大文明、大文化”的定位与取向,是他理性与感性结合的结果,他所以成为有无数拥趸的作家、学者,而非一般意义上的游记作者,也是因为他紧紧地把自己依附于中华文明这条血脉之上的结果。
这是2003年4月底,我躲在这个旧家写这本书的尾声时,全北京人在大战“非典”。晚上回新家吃晚饭,妈妈说你的导师打电话来,叫你这段时间小心些,不要再到处乱跑,要注意身体。
再打电话,他并不在深圳。五一假期,又接到他的电话,他说这段时间好清静,再没有接不完的电话,应答不完的邀请,他也在写东西,写他父亲,许多不为人知的事情。他的助手说他又在“挑灯夜战”。
非典让我们一下子多出来许多的时间,有人读书有人写作。他问我在干嘛,我不好意思地说自己也正在写作。他鼓励我,好,瘟疫正是产生名著的时候,还记得《十日谈》吗,正是一帮人为逃避瘟疫躲在花园里编的一百个小故事,多好,世界名著。
我记得他说过要写他的家乡写他的亲人们,他已经开始了。他也许又要给他的读者带来新的惊喜。
|
|
 
本书由“啃书虫”免费制作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