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为游历归来的余秋雨欢呼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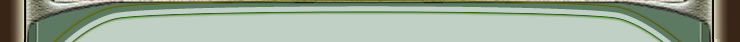 |
 |
|
2000年,结束“千禧之旅”的余秋雨,被《中国博物馆》摄制组请来北京,参加片子的宣传活动。余老师看过其中的几集,把我们大夸了一通,肯定的依然是我们看历史的方式与姿态。据说他还在记者见面会上说,在这个片子的主创人员里有一个他的学生,这是他的骄傲。事后我听了,膨胀得不得了。
那时我已疯狂地转入另一个摄制组,到处跟人说要拍专给白领看的旅游片。当时我正在
上海的世茂大楼顶上假装小资喝着咖啡,在夜上海的酒吧里嗅着张爱玲留下的气息。深圳官员在电话里大骂我不够意思,关键时刻找不着人影。我关心的却是余秋雨什么时候离开北京,我必须赶回去和他见一面。深圳一别,他去了“千禧之旅”,那里一直是战事不止;我也游荡了大半个中国,穿越了几千年的时光,我有一肚子的想法要跟他交流,也更想听到他在更远处、更陌生地带的经历和收获。
晚上回到北京,家里人说余秋雨老师打电话找你,你快回电话。我给余老师打电话,房里又总没人。等到他打过来,第一句就说,马小娟,什么时候可以见面。
一见面,他还是老样子,那么艰难险阻地走了一圈回来,看不出一点疲惫。他挺挺身体,得意地问我,怎么样,你看我是不是瘦了点。我说真的,真是瘦了。我又说,我怎么每次见你都是老样子,不会像有些人,好久不见猛一碰头,马上会有“老了”的感觉,你好像一直都是那个样子。他听得高兴,说我心态好呀,心态好就能保持年轻。
他跟我说起他昨天参加的一次朋友聚会,是由一位一同走过“千禧之旅”的记者和她的新婚丈夫发起的。他说不得了,我们喝了好多好多的酒,喝到大半夜,真是太开心了。
难怪电话打不通,原来他被别人拉去喝酒了。他津津有味跟我讲起那一对新婚夫妻的浪漫故事。他说那位和他一同走“千禧之旅”的女记者,每天都要往自己的报纸发回报道,她现在的丈夫那时也只是个每天读她文章的读者,并不认识她,开始也不知道她是个女的,后来知道她是个女的,就开始一边赞赏一边担心,到处跟人说这个女孩太勇敢太了不起了。女记者回到北京后,有次他们在一个地方偶然认识,他才把文章中天天见面的女记者和面前的女孩对上号。故事再发展,自然是被征服的男读者最终又征服了我们的女记者。
他完全像讲故事一样讲着那对年轻人的奇遇,满怀热情,每一个转折、每一处细节都让他讲得喜气洋洋。他说那位女记者一定要他见见她的丈夫,一定要一起喝酒。我知道她也一定想让余秋雨老师见证一下她的浪漫和幸福。
看得出,一夜过去,余秋雨还在为他的“千禧之旅”伙伴高兴。
这一次游历归来的余秋雨,精神状态特别的好,简直可以用“亢奋”这个词了。他一直在说着他们一路的趣事。我无意间提到的任何一个话题,都能引得他思路大开,滔滔不绝。我们谈呀谈呀,把酒喝完,移师楼下的茶楼,又谈呀谈呀。不停地续水,不停地起身小解。
现在想,他那时刚结束一段远行,身体和精神的高度紧张与兴奋刚刚解除;他又刚收获一本厚厚的旅行笔记,这本凝聚他一路的考察与多年思索的大书正处在一系列的暗中运作当中,即将投放市场,和他的读者见面,他整个的人处在松弛、轻快与有所预料的期待当中。那是一个享受轻快、享受收获的愉快时段,是一个类似假期一样的悠闲时刻。
我们在保利,照例是一边喝酒一边聊天。饭前他问我吃西餐还是中餐,我想他刚从国外回来,西餐吃得够多了,就要求吃上海菜。他说他不清楚我们这边喝什么牌子的红酒,我说刚好我点上海菜也不灵光,于是我们分工由他点菜我来叫酒。
有那么一两下我会在心里暗笑,我们师徒在吃菜的问题上好像不如说话那么更像“一伙儿”的,他一直生活在江南,吃得还是挺精细讲究,一边吃菜,一边点评。我意识到在北京要他吃本邦菜,他肯定挺失望的。他说等有机会,他要做地地道道的上海菜请我吃。
他是一位真正的美食家,对每道菜来龙去脉了如指掌,色、香、味自有标准。他儒雅安静,即使是多喝了两口,也只是脸红一红,说话还那样平缓清晰,不失风度。
记得有一次看到他在文章里说,一些乡野村舍中的饮食,说起来会非常诱人,但真要吃起来,却难以下咽。我当时看了哈哈大笑,设想有机会能请他一同走到村子里去,让他看我坐在苍蝇满天飞的小板凳上,胡吃海塞那些想起来就要流口水的乡野菜。他会不会对我这个没出息的学生摇头?
我早把自己放任为吃货,土人,一进到穷乡僻壤,就开始惦记着要吃一顿人家“家里的菜”。吃得高兴,免不了还手舞足蹈到处给乡下孩子塞城里带来的小玩意,扮扮“狼外婆”。曾经想过凡吃一道土菜,都记上菜谱,要吃遍乡野土菜,出一本牛哄哄的土菜大全。可惜吃是吃了不少,菜谱却一次也没顾上记。有道新疆大盘鸡,最适合一帮人胡撮时下啤酒,在辽阔的新疆大地停下车一屁股坐进路边小店,大盘鸡的那个诱人,让我回到北京还千里迢迢托人抄来菜谱,躲在厨房操练手艺,在朋友面前炫耀。
每回和余老师喝酒吃饭,都在城市里,从未有过在路上的感觉,不知道脱离了这样雅致的用餐环境,他会是个什么样子。他在《千年一叹》里偶尔谈到过他们的用餐,似乎都没留下过美食的记忆,他说到过有一种什么大黑萝卜,难吃得不得了,吃得好像很受罪。
我们吃一盘炸小虾,他告诉我这不对的,挑的虾就不对,要比这个小,他说他做的这道菜比这个好吃多了,等什么时候到上海,他去市场买了他要的那种小虾来做给我尝尝。
我问他你和马兰谁做饭啊。他马上说有空就我做呀,我做的菜味道不错的。我马上羡慕起马兰来,吃别人做的菜,尤其是男人做的菜,是最愉快的事了。不知当初马兰与余老师结为秦晋之好,除了折服于他的才华与风度,是不是也被他亲手烹饪的好吃和愉快的美食所俘
虏?
他说有机会要做上海菜请我,一定是对自己的做菜手艺颇为自信才这样说。我想我是打死也不敢在他面前露一回我的“厨艺”的。
我还发现,一趟“千禧之旅”走下来,余秋雨的酒量也见涨,比过去更能喝了。我们喝红酒,不急不慢,我总想着给他加酒,他说你要多喝。我说没事,你也挺能喝的。他一直说“千禧之旅”的伙伴们太能喝酒了,酒量大得不得了。可是有一回他们全醉了,只有他还稍微清醒一点点。看来近朱者赤,他们把他们的余老师也连带得快成酒仙了。
后来常与余老师一道喝酒的刘半仙告诉我,余老师现在爱喝洋酒,喝洋酒更厉害。
大概也是“千禧之旅”“欧洲之旅”一路喝下来的收获。
游历归来的余秋雨,真的是越来越洒脱,看问题也越来越开阔。他本来就有一个大开着的思维定势,这一趟集中的时间与空间里的行走,是真正的厚积薄发了。
他主动跟我说起在埃及的一处古文明遗迹边上,那里的人还专门给某位西方考古学家树立起雕像,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我立刻想起自己在做敦煌那一集片子时与他文章里情感的不相溶,没想到这次一见面,我们不约而同地就又想到了一处,真叫人愉快。虽然我们也不至于会无动于衷到要去立什么雕像,但至少我感觉得到,他的表达已平和了许多。他跳得更出来了,他在更加自觉地把中国放到世界这样一个大的范围里去看待、去思考。因此他也更年轻,更活跃了。
我一直都很在意他散文当中的“中国情结”,有时会想,一个把自己最初的文化基座定在欧洲,又受亚理斯多德、黑格尔、狄德罗、萨特这些思想大师影响极深的人,对中华文明的情感竟会这样深重,有时深重得都妨碍了他思想的放达,干扰了他散文中现代意识的流程。有时甚至一厢情愿地替他惋惜。
以后,我总是一个劲地向他表示,“我喜欢你的《千禧之旅》,我喜欢你的《行者无疆》”。至少不下三次,我与人争辩他的散文创作历史。余秋雨的散文读者群,是一个非常广泛、非常复杂的群体,有中国传统文化情结浓重、带些文人气质的“老式”读者,也有极为活跃的、现代意识很强的“新型”读者,他们都喜爱余秋雨的散文,但偏好各有不同。我是他的一个亲近的、细心的读者,我注意到,在行行重行行的游历中,他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改变自己,他后来的散文一直在充实和补充过去的篇什,他的观念与风格都并非一成不变。
用他自己的话说:“与笔端相比,我更看重脚步;与文章相比,我更关注生命;与精细相比,我更倾情糙粝。荒原上的叹息总是糙粝的,如果要把它们调理成书斋里的柔声细气或沙龙里的尖声尖气,我如何对得起自己多年前就开始的辞职远行?”
我总在为游历归来的余秋雨欢呼。
他问我,听说你给我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却没有发出去,里面有很多对博物馆这个片子的想法,现在摄制组想要你寄出,要我来写个回信,在报纸上宣传一下。
我笑起来:哎呀我都忘了具体都写了些什么,发泄了一通也就不管了。我那都是泼妇骂街,谁敢登呀。
事情都过去了,那是在剧组里和人吵架吵得急了,理念与方法完全不同,无处发泄时,很自然地就想到要与余秋雨来交流交流,向他倾诉倾诉。我是不愿回头去想已经过去了的事情的,但当时的郁闷和苦恼却是很真实的。一边觉得那是一个很好的表达和叙述的机会,一边又觉得永远甚至每时每刻在与一些完全处于不同语言体系中的人们争吵,消耗,无异于浪费自己的生命。那时对中国历史,对中国文人的生存模式,对余秋雨的“千禧之旅”,对“余秋雨现象”的意义,有许多的想法、火花。终于在某一次“空中之旅”的两个多小时里,脑子里那些四处乱飞的句子,被我不顾一切地铺堆在十几页纸上。完全地情绪化。就像一名半疯的泼妇,盘腿往地上一坐,嘴巴就停不下来。
我说我还是实寄给你吧,不过发表是不可能的。那都是我们师徒之间的“黑话”了。我说我在信里除了骂大街,就是吹捧你和我自己,发出来要给人骂死的。
他听得一直在笑,一再说一定要实寄一定要实寄。
送走余老师后,我果真把那封长信从抽屉里拿出来,寄去了深圳。那封信虽然不好给别人看见,但我还是希望让余老师看看,让他知道我的许多想法和思考。我知道,无论我用什么样的态度什么样的句子去表达去叙述,他都会喜欢听我那些话。
几天后他立刻回了电话,我听出来他读了我的信非常高兴,也非常兴奋。这时我已经看过了刚刚出现在市面上的他的新作《千年一叹》,我也把自己写的几篇游历散文塞在那封信里一起寄给他,他知道我和他又有了一些相似的经历。两个都是刚结束了游历归来的人,虽然起点和终点都不一样,但游历之后的充实、喜悦,却是一致的共同的。
我知道,这一次的“千禧之旅”,以及不久后的“欧洲之旅”,对他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这是他早就期待着的,这也让他一次性地占有了一名现代学者、文人所应有的制高点。
又一年后,欧洲归来。再见余秋雨,他精神饱满,谈笑风生。我感觉得到他更加地游刃有余。
他还有点小小的遗憾,他说自己长胖了点,都有肚子了。
我请他给我们的一本书做主编,出版社不放心我与余老师的关系,也为慎重起见,非要我“逼”他亲手写一行表示同意做主编的字据。我不太好意思,咕咕嘟嘟在他面前表示对出版社的不满,他倒也没说什么,一字一字照我说的写。我随手把他的“字据”放在宾馆的椅子上——后来它们干脆滑落到了地上,我也浑然不觉。
我说我喜欢《行者无疆》里那张举着酒杯的照片,还有那张哥伦布塔柱照片后附带的文字:“正是这个月夜,我乘电梯升至他的脚下。”他愉快地接过我的话:“还有接受美女的访谈。”
我那天穿了一身黑,只在脖子上挂了一串木头项琏,他注意到,指着它评点:这串项琏,你看上去像个妖怪,从一个很远很奇怪的山洞里出来的妖怪。
我们一起去吃饭喝酒,他套上一件立领外套。这是他和熟人在一起时爱穿的衣服。我注意到,若是第一次见面或接受采访,他会选择穿西服,他很注意。我想他是越来越在意自己的仪表了,这也是文明的体现吧。
喝酒喝得高兴,我把来的目的忘得光光的。
和他分手钻进出租车里,开出去一段路,发现“逼”他写的字据不知放哪去了。
我重新冲进宾馆,冲到楼上,没找到他。再冲下来,在大厅里疯转一圈,一边骂自己:怎么搞的怎么搞的!见到余老师怎么说,难道再要他写一个?
终于在大厅的小书店里看到余老师的背影,正立在那里巡视书架上一排排的书,看上去非常认真和仔细,外人根本看不出这位读者先生刚刚还喝过不少的酒。我犹豫一下,无可奈何叫一声余老师,我好像把你的“手谕”给丢在你房间里了。
是吗?那我们上去拿。他离开书架领我上电梯。
他的“手谕”最后被我从椅子底下找出来,我嬉皮笑脸表示我的歉意:你肯定觉得我这个学生太粗心大意了吧。
没有啊,他说,谁都有这样的时候,没关系的。
我嘻嘻笑,心里好温暖,不是谁都肯原谅这样的事的。有一回我去福建看一位木偶大师的表演,他要到剧场门口迎接我,我又怕耽误他老人家的演出,婉拒后混在一帮看演出的官员中自己进了剧场。结果大师误以为我当晚没去看他的演出,在电话里马上对我淡淡的。我急得一口气提供了众多演出过程中的细节,他才相信我确实是看过演出的。相形之下,余秋雨的方式更让人难忘,也更让我记得不要再犯这样的错。
我听他说话,他果真已经站在另一处山头,他涉猎的范畴已超出文学与艺术,就像他自己说的,他现在反倒喜欢和文化之外的人交朋友,我发现他现在更像个少年人一样,喜欢了解和触碰他从前不曾接触的事物和领域。我必须要努力才能跟上他的思路。他现在思考问题的那种开阔,已经不再是单一领域里的那种活跃,而是跨区域、跨领域的宽带作业。有时我又像在上戏读书时那样,要暂时丢下些不能回应的问题,跟着他往前走。我知道,又要等到十年、二十年后,在自己也像他那样把大半个世界跑了个遍,才有足够的发言权,也许要到那时,我在一些问题上才有能力来与他对话。
他总是远远地走在我们的前面。
他总是能够抓住最好的机会,让自己纵身一跳,焕然一新。
我在一旁看得目瞪口呆。
从最初的走出书房游历本土的“人文山水”,到相对完整、连续的南亚与欧洲之行,他已走得很远跑得很远了。
他早就看到了游历对一名学者的成就。
“饶先生(饶宗颐)年纪大了,他的国学水平非常高,长时间集中来研究经典;但同时他又非常了解世界各国的文明史。他不像我们内地学者由于种种限制,没有条件到海外作长时间的考察,他却行。就在我们内地知识分子受磨难的时候,他走遍世界各地,对很多世界文明胜地作了长时间的考察,包括印度文化,他在印度就待了好多年。这样,他就成了一个非常有优势的学者,既有国际思维又有深厚国学修养的大学者。这种学者在大陆很难找得到的。”
看看那位写《宽容》的房龙先生,1882年出生在荷兰鹿特丹,1903年赴美国,在康奈尔大学完成本科课程。1911年获德国慕尼黑大学博士学位。回到美国,在美国几所大学任过教,之后又充当记者、编辑,甚至播音员,并同时游历过世界许多地方。
近的再看看黄仁宇,1918年生在湖南,1936年在天津南开大学读书,学的是电机工程,做过报社编辑,读过国民党成都中央军校。作为军人被派去过印度、缅甸、日本、美国。最后他成为一名美国学者。用他自己的话说:“在我六十一年的生命中,绝大部分的时间可以平均分成中国和美国两部分,我在中国住了二十八年,在美国住了二十七年,其中最后五年是以美国公民的身份。其它六年则呆在印度、缅甸、日本及英国。”他说自己:“我的文化背景和语言训练来自中国,但我对历史的了解,是住在美国数十年所发展出来的。我可以说,如果我没有离开中国,就不会有今天这番认识。如果我只在这个国家住了五年或者十年,也不会有相同的了解。”
更不要去说那位爱尔兰人乔伊斯了,他离开家乡都柏林时只有二十二岁,三十岁以后再没回过故土,一直都处于流亡、离乡之中。他的一部《尤利西斯》,虽然写的只是一天里的事,但他在结构上又要与荷马史诗《奥德赛》并驾齐驱,就让我有一种强烈的游历的感觉。
他自己——
十五年前他说:
“纽约大学的著名教授Richard Schechner比我大二十多岁,却冒险般地游历了我国西南许多少数民族地区,”“那天他送给我一部奇怪的新著,是他与刚满八岁的小儿子合著的,父子俩以北冰洋的企鹅为话题,痴痴地编着一个又一个不着边际的童话。我把这本书插在他那厚厚一叠名扬国际的学术著作中间,端详良久,不能不开始嘲笑自己。”
“如果每宗学问的弘扬都要以生命的枯萎为代价,那么世间学问的最终目的又是为了什么呢?如果辉煌的知识文明总是给人们带来如此沉重的身心负担,那么再过千百年,人类不就是要被自己创造的精神成果压得喘不过气来?如果精神和体魄总是矛盾,深邃和青春总是无缘,学识和游戏总是对立,那么何时才能问津人类自古至今一直苦苦企盼的自身健全?
我在这种困惑中迟迟疑疑地站起身来,离开案头,换了一身远行的装束,推开了书房的门。走惯了远路的三毛唱道:‘远方有多远?请你告诉我!’没有人能告诉我,我悄悄出发了。”
十五年后,在经过了本土、亚洲、欧洲游历后,他说:
“这种寻找当然不是躲在万里之外作学究式的考订,而是直奔那里,既疑惑又信赖地面对陌生的土地,叩击一直与蒙昧和野蛮裹卷在一起,又搏斗在一起的文明。”
“就这样一圈一圈越走越大,每一个新空间都带来新责任,终于从国内走到国外,从中华文明走到了其它文明。既从其它文明来审视中华文明,又从中华文明来察试其它文明,然后横下一条心,只要对人类发生过重大影响的文明,哪怕已成瓦砾,已沦为匪巢,也一个不能缺漏。”
|
|
 
本书由“啃书虫”免费制作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