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女弟子偷练“余氏功夫”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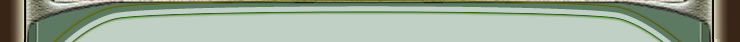 |
 |
|
那段时间,从行动的方式,到对历史对人文的思考与情绪投入,真是一次彻头彻尾的追随和摹仿。
过去听他课看他文章,他就像是一名导游,我这个学生是在他的引领下,看尽了一路的好风光的。那样的过程,还来不及有自己的发现,就早被他话语与文章的气势裹挟而去,更多的还只是停留在倾听与阅读的快感层面上。
这次太不一样,是自己一次次去面对那些历史的场景,进入历史的现场,自己去体悟那些曾经活过的人、发生的事。总是在路上,天上、地上、水上,越走越强健和放松的肢体,举着一只思绪乱飞的脑瓜子,在大地上狂奔。总是这样,刚刚还没在都市的人群中,刚刚还在为买到一件漂亮衣服兴奋,刚刚还在博物馆黑乎乎的大厅里凑近了辨认那些文物,转眼就行进在山高水远的乡路上,混迹于一大群世代相守在本土的当地人中。我贼头贼脑四下打探,我蹲在墙根儿下,甜腻腻地叫着大爷大妈,缠住人家打探他们祖辈的来处与去向,有时还被领去他们的家里,看他们今天的生活与习俗,老实不客气地吃他们那些土土的菜肴和点心。总是坚持称自己为“闯入者”“外来者”,但是是非常善意的“闯入者”和“外来者”。
也是在那样的情状之下,我对余秋雨式的写作姿态也突然有了很强烈的认同。
以前对他散文的喜欢和维护,主要还是在对他才华和情感上的趋同,而真正对于他创作《文化苦旅》《山居笔记》等一系列文化散文的冲动和坚持所在,我除了在他的言谈和文字里去了解,去体会,其实并不能完全达到感同身受。总是隔着一层。只有当我自己也放胆在中国大地上独自游历了一圈之后,自己也有了写作和发言的冲动、激情时,才自然而然了悟了那一切。
那其实是一个非常自然和合理的结果。
一个稍稍有点悟性有点感觉的人,一个对人类的过去与未来稍稍有点好奇有点想法的人,让他突然穿越几千年的时光,一下跌落在早已物是人非或者人去楼空的历史舞台的前景中,他脑瓜子里不活动活动情绪上不激动激动,那真是不可救药了。
还是抄录一段余秋雨的话,最能表现我后来也有的那种感觉:
“我站在古人一定站过的那些方位上,用与先辈差不多的黑眼珠打量着很少会有变化的自然景观,静听着与千百年前没有丝毫差异的风声鸟声,心想,在我居留的大城市里有很多藏有古籍的图书馆,讲授古文化的大学,而中国文化的真实步履却落在这山重水复、莽莽苍苍的大地上。大地默默无言,只要一二个有悟性的文人一站立,它封存久远的文化内涵也就能哗的一声奔泻而出;文人本也萎靡柔弱,只要被这种奔泻所裹卷,倒也能吞吐千年。结果,就在这看似平常的伫立瞬间,人、历史、自然浑沌地交融在一起了,于是就有了写文章的冲动。”
那是当然的,就像我,常常会被自己满脑子里的滔滔话语涨得想要发狂,整个人都会被它们催得弹跳得起来,飞起来。
于是也庆幸在片子的操作伊始,我们坚持要让撰稿每一个博物馆、每一处历史遗迹都要走到的决心,也多亏了深圳方面有那么大的魄力,主要是有那么强的经济实力,舍得拿出钱来让摄制组两次甚至三次四次前往同一个外景地考察。
记得刚听到余秋雨他们去中东和南亚走“千禧之旅”消息时,除了激赏,还挺嫉妒的。这之前我曾在三联生活周刊的书讯上得知一位西方记者从欧洲出发,沿中世纪十字军东征路线,一路前往中东,沿途记录下那里的战火与人民的生活现状,出了厚厚的一本书。她也把自己这次行动当作二十世纪末的一次行为。当时我还对剧组的人说起过,觉得那个西方记者选择的路线和区域很有历史感,相隔1000年,时间和空间的两头恰恰又都是战火,两头又都是宗教。什么也不用说,光是客观记录,就足以让世人震惊和警觉了。当时说要是我们也有能力搞这么一次远行,光是这么个形式就能牛倒一大片。没想到很快就传来余老师他们的“千禧之旅”消息,搞得我还有点小小的失落。可见在中国,很多创意不是没有人想到,而是没人有魄力和实力去实施。
不过话也说回来,像深圳这样一个远离内地的经济特区,能想到以拍摄中国100个最具魅力的博物馆的形式,送别二十世纪,真的是一个了不起的大手笔。
也真庆幸自己糊里糊涂就参与了这么一次跨世纪的行动,并且愣头愣脑地坚守住了自己一贯喜欢的方式。这样一来,简直就像在同一时间里,几乎和余秋雨老师在做着同样性质的事情。
不知以后还会不会有这样的好事撞上门来。
记得余老师在他的几部书里都提到过在外面游历时,肢体与精神上的历险。现在想,连这一点都是极其相似的,也都是事后想起来很好玩当然也有点后怕的事情,每一次都会成为记忆中有趣甚至神奇的体验。同样在国内游历,他说“一次为了赶早班渡船在山间迷了路,我顺着几声苍老的咳嗽声,找到了一间看山人的小屋,得到了指点;又有一次夜间迷路见对面来人,心中疑惧故意哼曲壮胆,对面来人也同样哼曲,等擦肩而过后才彼此放心,回头一笑”。这都是让一些具有相同经历的人会心一笑的趣事。
有一次我在新疆,钻进一辆长途汽车,要去木垒哈萨克自治县看丝绸之路遗迹,在十个多小时的长途奔袭里,包括司机在内的所有当地人都在猜我究竟是从哪里来的。最后下车,可爱的哈萨克司机实在忍不住,问我是不是四川人。他说如果我真是四川人,他就算赌赢了,能挣一块钱。我好不得意,因为有句话说只要是有人的地方,就有四川人。是赞叹四川人顽强的生命力的。看样子,我跑得也够远的了。
也许更年轻些,也许性格使然,那两年里我走得差不多成了“野人”,胆子大得不得了,一出了北京就想方设法与所有组织脱离联系。我又不爱用手机,经常让北京的“指挥中心”担心把我这个总撰稿给走丢了。我想余老师可能完全想不出我这个学生走在外面的二流子样子。本来去每处都会有国家文物局开具的要求当地接待的介绍信,但我自己平时在政府机构呆腻了,好不容易有次机会,哪里还会老老实实地跑到外地还有人“全陪”着!我喜欢自己安排一切,像所有的自助旅行者那样,背着我的大背包,把该看的看了,该听的听了,该吃的吃了,然后站在博物馆的大门前长舒一口气,这才从容不迫走进馆长办公室,掏出那纸“尚方宝剑”放在桌上,就几天来自己对当地历史、人文的所有考察与想法,作一个总结性的对话。
那些自由自在的游走。
又想起余秋雨说的一个人在外面吃饭太醒目。还是想乐。名人嘛。而我这样的,就不必在乎这些,我常学着王朔的话说:我是流氓我怕谁。
他在《文化苦旅》里说,他是靠去各地讲课来完成游历的,还暗笑自己将成为靠卖艺闯荡江湖的流浪艺人。我也老实承认,我是靠做这个博物馆的片子完成在中国版图内的东游西逛,完成我的“中国之旅”的。
以前刚到北京工作时,也曾一厢情愿以为可以利用工作出差的机会遍游中国,后来发现这个方法对我并不可行,其间要付出的,肯定比得到的多。当然问题可能还是出在自己身上,既不能适应周围又没那么大的能耐让周围来习惯自己。好在最终还是借助于别人的财力完成了最初的行游,对这片土地有了一个完整的初步“体”验。接下来的,应该就是再次、再再次的进入。虽然许多地方不会再像第一次到达时那样兴奋、惊讶,感触和发现也不会那样一个接着一个,但多少也能体味到余秋雨说的,那都是些把思考甚至生命融进去过的地方,是留下过你的气息和身影的地方。在许多高兴和不高兴的时候,你突然想起它们,荒野上的某座弃庙,路边的一个憨笑,脏得苍蝇满天飞的一顿美味,会觉得,你的世界还有另一处存在,你和它们有某种联系。在远处有另一个你。那是很叫人充实和愉快的。
后来我跟人吹牛,说我这次算是上了一回余秋雨的博士生了。我们的片子请的余秋雨作艺术顾问,他总谦逊地表示他没做什么具体的事情。他不知道,没有他在前面开辟的那条风光独特的大道,没有我这个学生一心一意地追随,这个片子至少不会是后来的样子,它只能是一头扎进我们的黑乎乎的博物馆里,对着一堆文物和古董就事论事。那是很不好玩的。
现在想,远离了北京,远离了嫌我有“反骨”的专家,远离了所有的争吵,那些行走在路上的时光,那些不断穿梭于史料——博物馆——人群当中的惊喜与发现,还有把老少皇帝、历史名流一把从历史里揪出,像谈论张家哥哥李家嫂嫂一样,数叨他们一生中哪些事好玩哪些事不好玩的情状,真是太愉快太过瘾了。
这次的学习,还像是上研究生那会儿一样,照搬的只是方式、方法。不同的是,那会儿更多的是在课堂上与余秋雨相遇,这会儿是在遥远处时空长廊中的大大小小驿站上与“余氏功夫”相遇。就像一位仙踪难觅的大侠,他总是留下些招数、密诀在某个停留处,而我随后而至,领得几句精华,便独个在山林空地间舒筋展骨、上下飞跃起来。一番参悟与比划之后,收掌定势,仿佛已自成一派。
我总是从他那里得到启发,有时会连他原来的句子都不舍得丢掉,急了就干脆照抄在解说词里。
我从不担心他会有什么说法,我大言不惭表示,学生抄老师的嘛,应该的。
也不是没有分歧。
十几年前,我们一群研究生曾在他的安排下去过敦煌,那是我今生头一回见到沙漠,真的像三毛歌里唱的,“一匹黄沙万丈的布”。一头扑进去,疯玩了一天一夜,感知里已装不太进第二眼才看到的莫高窟壁画。
这次再去,把余秋雨的《道士塔》《莫高窟》,还有《沙原隐泉》,一读再读,自以为是有备而来的。可是立在莫高窟前,扬起头一看到窟顶上那些十几年前并不存在的防沙罩、防风网,还有众多测试风向、风速监测仪器上旋转着的镀缭诙劣嗲镉晡恼率被钇鹄吹母芯跤肭樾鳎幌戮捅览A耍⒌袅恕
总是这样,对黄沙的感觉,总是会先于那些深藏于洞内的壁画来到跟前,突现出来。
我怔在那里,那是怎样的一个情形!一整面的山墙,窟门前有滤沙网,窟顶上有防沙网,防沙网的后面再拦起一道防风障!所有的测算——风向风速、沙丘活动规律、窟内温度与湿度——都精确无误,所有的试验都只为抵挡那无声无息流泻下来的黄沙。
博物馆的资料说,每天静静地从平缓的窟顶泻下的流沙,一年就需要人工清沙大约2000立方米,相当于600辆卡车的载重量。
它们只是些沙呀!
这真有点螳螂挡车的情状。
而这众多的伸开双臂想要挡住流沙的螳螂里,又有那么多的美国螳螂、日本螳螂、西欧螳螂,甚至有一个美国的盖蒂研究室,就专门来与中国人合作防沙、挡沙。这是那位最初开凿莫高窟的乐和尚没想到的,也是那位臭名昭著的王道士想也不敢想的。
世界都走到这一步了,敦煌完全是全世界的了。
那些感觉没了,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和十几年前的余秋雨老师有了分歧。
余老师在《道士塔》里写:“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比我恨得还狠。他们不愿意抒发感情,只是铁板着脸,一钻几十年,研究敦煌文献。文献的胶卷可以从外国买来,越是屈辱越是加紧钻研。”
可我却非常反动地想,没有王道士卖出那一卷卷的经文,没有斯坦因的贪婪,它们很可能毁得连影儿都没了,你连胶卷都买不到!
我一直在那集片子里跟编导强调,一定要采用历次由中国敦煌吐鲁蕃学会组织的国际学术会议音像资料,注意会议上不同国籍、不同相貌、操不同语言的人们,我想让它们不断地出现,穿插在对敦煌历史的述说过程中,让过去和现在平行出现。我不想在片子里一心一意追究敦煌的“被盗史”,我只想在还原莫高窟壁画历史本来的同时,也客观地展示一下敦煌现在所具有的世界性,它应该是人类的、世界的共同文化遗产。
事实上,对敦煌莫高窟的保护,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吸引了众多文物保护专家来到中国,用人类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来保护这起人类文化的共同遗产。我甚至不惜它搞得不好会像科教片,也一定要在画面里强调这一点。
这一集的争吵更是可想而知的。我不仅要面对本来就存在的分歧,我还第一次要脱离余秋雨的“文本”。
|
|
 
本书由“啃书虫”免费制作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