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第一次见面,他穿着条牛仔裤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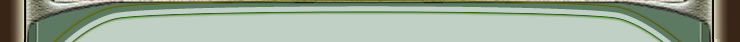 |
 |
|
想好了是要按时间顺序慢慢道来,可感觉总是不听话,纷纷涌来,还有记忆。它们像跑道上的运动员,争着往一条道上挤,让我如此着急,总定不下顺序。
那次我怎么说来着?
我说现代作品应该同时描述一切,表达全部,我说我现在不喜欢文字表达了,它们总要
一个字接一个字地铺摆开来,思想和情绪是单向流过来的,对于运载一次饱含生命原动力的最真实与最真诚的表述,它们太慢太朝着一个方向了。一段文字记录下来,过程中已遗漏掉那些跑得最快最迅猛的。堵截到的,只是来得及捕捉住的。
我说我现在喜欢戏剧的表达,现代戏剧可以用整座舞台、整个剧场来表现,语言、肢体、灯光、音响,甚至多时空,所有手段可以同时表现情绪和感觉,最大程度立体化和多向性。我说我可以把我所有的表述指向,在同一个瞬间里泼洒出去,传递出去,我可以一下子裹挟住观众,击中观众。这个过程一定既痛快有力,又美妙通畅。而文字相对戏剧,简直就是力不从心,强拉硬拽——
那是在研究生面试时,第一次见到余秋雨说的话。
所以记得这么清楚,因为相对于后来自己对戏剧的放弃与撒手,这些大话更像一次骗子行骗时的天花乱坠。而余老师,因为最能感知这些话语,成为被骗最深的——
不要着急,慢慢来。这是一只键盘,这是一个一个的字的排列。没有舞台了。让自己一个字一个字敲过来,不要性急。
有人说你是余秋雨的学生,你每次见他都应该带上笔,最好带个小小的录音机,把他的话全录下来,整理出来就是一本书。
我哈哈笑,饶了我吧,那我们还说不说人话。
真的,那样的事我不需要做,我只需去感觉。所有的话语只要我感觉到了的,即使不原话照录,它的本质也会深植在我脑中,好像是我自己的了。
人们爱说些“好记性不如烂笔头”的话,我却总是不爱记东西。只喜欢那些感觉到了的。喜欢把书本上有感觉的东西变通为自己的,也喜欢把余老师的话变通为自己的。
听说我要写关于他的书,即使是余秋雨,也开始担心我对资料的占有。他不喜欢我用媒体上的那些东西。他说你不要急,我们还有好多事要做,我怕你写不长。
我说我才不搞那些理性的把你作品分析来分析去的东西,我只写我感觉到的,我看到的。
毕业离开上戏后,我们一直在通信、打电话,再一次的见面要等到深圳。
那次在深圳喝酒,他突然觉得好笑,说第一次听到马小娟的名字,竟然是在上戏的澡堂里。
我们于是都想起上戏的澡堂。那年头,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大家都端着个脸盆,里面尽是些肥皂蜂花洗头水什么的,手里还拎着装换洗衣服的塑料袋,一路喊着“打油(洗浴)了打油(洗浴)了”,一路在澡堂看门人严厉的目光注视中分头进入男女浴室。洗完澡回来的路上,会有男生故意问女生:“澡堂里人多吗?不多?不多那我也去。”
他说起他写过一篇文章,专门写澡堂的。他说多数小男孩的成熟可能就在进入澡堂的一刹那,满目都是赤条条的男人,一定会被吓坏,也一定一下就明白了什么是男人。他还说起好多年前上戏的老教授在澡堂被工宣队罚站,光着身低着头一站就是几小时,平日的学生们就在眼皮下来来往往。那样的情形那样的方式,真是太有戏剧性太有舞台感。
他的回忆让我想起大学一年级时在南大女澡堂洗澡,看到我们的哲学老师(我们管她叫马列主义老太太,她总爱说“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事物是螺旋式发展的”)的裸体,几个女生回到宿舍就笑翻了天,总没法把一个赤裸裸的身体与一堂严肃的死板板的哲学课联系起来。以后上哲学课,上头一本正经刚开讲,底下就趴在桌上一大片。现在的大学生恐怕都没有我们那样的幸运和愉快,可以看得到老师们的裸体。
沪宁一带的男澡堂我一直没有机会进去参观过,据说是所有人泡在一个大池子里,各搓各的泥,搓得满池汤色,搓完后起来舀一瓢冷水,淋一下就算完事——听着有点吓人。我认识的一个北方男生抗拒了四年,结果就是躲在宿舍楼里洗了四个冬天的冷水浴。上海有一家澡堂,门口赫然写着“大观院浴池”,每次路过看见那几个字,想到男澡堂里那吓人的情形,都要笑。
共同的回忆一下把我们带回到上戏时代。
在热汽蒸腾、人影绰绰的澡堂里,戏曲研究生司群华追着余秋雨,要说说他的一位大学女同学。余老师说那是他第一次听到马小娟的名字,在男澡堂里。
我笑起来,想起那年自己写信到处找导师的事情,我那时也算是“身心困顿”期,写给司群华的信洋洋洒洒几大页,许多的思考、想法,还有情绪化,都在纸上,他说害得他上课、看书时满脑子里都是马小娟信上的那些话在嗡嗡乱飞,莫名兴奋。他一定也带着那样的情绪向余老师推荐我,所以才让余老师有那么深的第一次印象。
很久以后在上海的一次大型活动中,司群华看见嘉宾余秋雨,有点不太敢上前去握手,他怕余秋雨“贵人多健忘”,不认得他这个十几年前的上戏学生了。可是余老师握着他手,开心地说我怎么会不记得司群华,是司群华第一次对我提到马小娟的。
真该隆重地感谢司群华一下。
第一次见到余秋雨的面,在1986年春天,从南京到上海参加研究生面试。
之前的笔试在头一年冬季完成,那些试题涉猎西方、中国艺术史上的所有领域与方面,还有中外文学生活的各个层面。并不生僻,却又让我感到不同一般。我知道这样的考试,不是任何我的大学同班同学可以招架得住的,也不是任何单一艺术院校的学生能够对付得了的。那些问答题,让我笔底的文字滔滔不绝铺天盖地。问题果然来得和他的学术方式一样,铺开着一条宽敞的大道,让我可以在上面伸展双臂奔跑、欢跳。那是一年的跟跑之后,第一次在书面上向他作出回应,我几次向考场老师要求加纸。笔完全停不住。
后来知道,这次研究生考试的范围与方式,对上海戏剧学院的应届考生也是一个不小的打击,所有优秀的应届考生,都在竞争中被淘汰掉。最终接到通知前来面试的考生,大多是接受过中国一流的综合性大学教育的考生,他们不仅具备很强的文艺理论素质,同时又都是大学各类艺术活动与实践中的中坚力量。我还听说,一位满腹经纶却没有接到面试通知的书呆(袋)子考生愤愤不平,把余秋雨的招生取向大大抨击了一番。我在心里说,倒霉的家伙,你连自己要报考的教授的学术立场都没摸着,还考什么考。
那是在江南的雨季里,司群华介绍我住在导演系一个南京女孩儿的床铺上。那个小女孩热情漂亮,落落大方,把我关照得很好,我倒像个小妹了。我完全蜷缩在自己的内心里,木木地任由别人来安排、照应。陌生的环境,没能从失败中缓过来的情绪,加上一会儿一飘的雨丝,这些都让我心神不定,恍恍惚惚,大多时间忘了围墙外边就是热闹的大上海。
我糊里糊涂跟在司群华后头去上戏食堂吃饭,路上遇见未来的师妹们,她们早和在上戏读书的老乡嘻嘻哈哈打成一团,司群华告诉我她们也是来面试的,她们平时就常来上戏玩、看戏,和学院的老师学生已经很熟了,应该是上戏的准研究生了。我的心境更加一落千丈,倒不是非要考上个研究生,而是不想再回南京,不想再回南大。因为坚持要报考研究生,做事又总不留后路,系里、教研室里的关系都被我给搞僵了。南京成了我的伤心之地,失了爱,又失了长辈一样“管教”我的中文系的“同事”们的关心,好似一条丧家之犬,整个人是浑浑噩噩的。
上海的雨雾,失了浪漫与迷离,全是看不见的秤砣,拉着我往下沉。
上戏陌生的小院儿,说不上喜欢,也说不上讨厌,现在是我惟一的选择,避难所。我没地方可去了。
现在看那时的自己,像在看别人,22岁,一个形单影只、消沉恍惚的小女人,被深深地陷在里头,不知道自己正处在每一个成熟女人都得经历的过程中。
我就那么等在红楼那间教室的外面,被叫到名字的考生进去了。等他出来,我们马上围上去,拉住他问:“怎么样,怎么样?”大家都很紧张。出来的人里,有的说“没事儿,挺好的”,有人说“你要当心,他们问的问题很不好回答”,也还有的出来时还是一副懵懂样儿。
我走了进去,先吓了一跳,没想到里面有那么些教授先生,坐了一堆。正前方独独放把椅子,给我的。简直就是末日审判。我往那一坐,完全不知道谁是谁,不知道哪位是神交已久的余秋雨教授。
现在想我那个时候的样子一定够傻的,我从素有“大萝卜”之称的南京来,又土又木,灰头土脸;又刚刚失恋,还没有新的男朋友,意志消沉,毫无光采。完全像只南京人嘴里的“呆头鹅”。我傻楞楞地坐在那儿,手脚僵硬,当初面对试题时的那般飞扬、张显,消失殆尽。我看着自己的希望正在溜走。
直到一个声音响起,我意识到这竟是一个对自己很熟悉的人。
我记得他问我还会不会接着写小说,小说和戏剧有什么不同吗,又问我以后想不想试着写戏。他还问我对“黑色幽默”怎么看——前一天来参加面试的考生刚看过那出著名的话剧《屠夫》,我在当场完成的观后记里大谈“黑色幽默”——这样的问话,我的那根喜欢思辩和横向比较的神经,一下就被激活过来。我暂时忘了自己的傻样儿和处境,朝另一条路上去。我奇怪自己紧张到极点时会突然思路流畅,仿佛拥堵的洪水终于冲挤出了一道决口,奔腾而下。我脑子里亮堂开来,一下又找回了冬天考场上的感觉。
同时我也知道,就是他了,这就是余秋雨了。
他比我想象的要稍稍年轻些,文气些。戴副眼镜,说话声调平缓,不急不慢的。这种平静和缓,与他文章里的气势、走向,不太一样。好比我,随着思维的向前进,声音总会越来越尖,速度会越来越快(用余老师的话是小娟的音频很高),不太控制得住。而他却始终是从容的,镇定的。他的话天生就只让别人激动,自己却不动声色。
最让我觉得亲切的,竟然是因为他当时穿着条牛仔裤,这至少在当时的南大是不可思议的——我的一位同窗就曾发誓,他找女朋友决不要穿牛仔裤的——所以我立刻觉得余秋雨这个人一定是非常随意和好相处的。
整个的面试过程中,好像只有他在不断地向我提问题。
司群华告诉过我,他会喜欢我这样对戏剧、美术、音乐各艺术门类都感兴趣和有所涉猎的学生。他果真问我平时爱不爱听音乐,听什么样的音乐。我老老实实回答说,上学时最爱听罗大佑他们的校园歌曲,现在工作了,开始迷上交响乐,最爱听贝多芬的第三和第五,每天都要听。
这是真的,倒霉的我一边要准备考试,一边要和内心的软弱与犹豫作斗争,那种年龄总
以为自己遇到了一辈子都不会再有的痛苦,这时只有贝多芬的《英雄》和《命运》里那些雄洪浩大的旋律与气势,才能把我从水底打捞上来,拎将起来。难过得不行的时候,我会把那台双卡录音机放到最大音量,然后蜷缩在宿舍的一角,闭上眼睛,把自己扔进聋子贝多芬的波澜壮阔中。那聋子在喃喃自语,在咆哮,我就跟着在他旋律的浪尖上漂流,翻卷,跟着他向上冲,向上冲,无限地扩张膨胀,直到全身心注满动力与力量,以为无所不能,心志再不被困扰。
完全是灵光闪现,我跟第一次见面的余秋雨大谈《英雄》和《命运》带给自己心灵的洗涤,我说每次听过贝多芬之后,全身心都像是历经一场大雨的冲荡,所有的软弱、消沉洗劫一空,这时会神志清宁,心绪通畅。他果真听得高兴,完全不知面前坐着的“小骗子”哪里有多高的音乐鉴赏力,不过是把贝多芬当作了郁闷时的救命稻草,一味挣脱痛苦必须依赖的毒品。
他的身体略略前倾,眼镜片儿在光线里停留着,很认真地听我表述。我接受到他的友好、亲切与鼓励。当我谈到自己对文化与艺术的某种感觉时,他会诚恳地问我:“为什么现在会有这样的感觉呢?”他不像是在考问我,更像是在与我交谈。我渐渐开始活跃开来。
我真把他当久违的交流对象,对他说流行音乐带来的愉悦是表面的,已经没法进入到自己的内心了,现在精神上更能与古典音乐相通和共鸣,听起来也再不像音乐鉴赏课上老师引导的那样,这段是快乐的,这段是忧郁的,这段又开始紧张了,而是一种情绪的自然带入,慢慢地就化入进去,融为一体。而事实上,我那时脆弱得听不得流行歌曲里的词儿,一听就伤感,就想要往下沉。贝多芬也好,古曲音乐也好,都是我的强心针或者迷幻剂。坐在那些教授们面前,与其说在谈自己对音乐对艺术的感受,不如说是在变相倾遣当时的郁闷、不顺。但因为发自内心最真切的感受,又一直处在一种鼓励的气氛里,临时一发挥自我感觉还挺好的。
总之恋爱的失败,以及和大学时的老师后来又都成为同事的人们之间同样失败的人际关系,这些挫败感,可能让我显得沉静、成熟,看上去更像个有点思想的人。而余先生友好、对路子的提问,让我的身心放得很开,思路和语言的表达也越来越松弛。虽然做了一年的大学教师,但因为是留校,一直都没能摆脱做学生的感觉,那时关于我所谓事业的未来、甚至恋爱、每天该干什么看什么样的书,哪个关心我的同事都可以教导几句,我又不会装假,最后弄得大家都对我很失望。我相信谁都有过走投无路的时刻,有时候,哪怕是一个再任性、再自以为是的人,在困顿、处处受挫的情况下,能得到别人的一点点支持和鼓励,都会温暖、感动得不行。复试中的交谈,余秋雨和上戏教授们的亲切、随意,让我的情感一下就投靠向他们,走出红楼的时候,连周围的陌生感都消减了不少。这样的交流,余秋雨他们似乎并不在考核我有多广泛的知识面,而更像是在试探我的感性与直觉。
我的感性与直觉,已经有一年多时间被压制得不能动弹,应该说是上戏的氛围唤醒了它们,那是一种群体性的弥漫在整个上戏天空中的气息,学生们感知的毛孔与触觉张开着,年轻的生命在自然和自由中开放。所有老师的手里都像握着根无形的鞭子,不是把学生往圈里赶,而是一个劲地朝外面轰:去,去,去脱掉你的拘谨与胆怯,去张开你全部的感觉,到艺术的殿堂里去呼吸,去飞舞!那是我这个一直处于严正肃穆的大学教育中的人一下就能接受到的不一样,带给我一阵阵的惊喜。即使不被录取,我已从余先生他们友好欣赏的目光里获得了足够的自信。
无论如何那都是一次转机。
后来我从消息灵通的师妹那里听说我的面试分蛮高,但是笔试分里仍有分数比我高的人没有被录取。她们说完全是余秋雨坚持要录取我的。在她们眼里,我完全就是余秋雨的“嫡系”了。
我一直都没有想过要搞清楚这件事,尤其是问问余老师是不是真有这么回事。在我这里,分数本来就不是最重要的,并且分数还偏偏一直是我的一个“死穴”——上南京大学时我的总分就比不过班里其他同学,以后我也就干脆厚着脸皮对别人说,我混进了大学,又混上了研究生。
但是因为心里有那么一个“结”的客观存在,依了我的个性,竟然又对别的导师横生出几分疏远与陌生,总觉得在他们面前有些气短。而对余秋雨,除了觉得大家对路子,还平添了所谓“知遇之恩”。
真正到了上海进了上戏,懵懂的我才知道,余秋雨在上海的学术界、文化界早已是一个响当当的名字。
一位比我年长十几岁的大姐,也是我的一位好朋友,曾在南京大学外语系进修,待我考入上戏,她又刚好在上海师大中文系进修。她的进修班同学年纪都与她相仿,他们是大学里教外国文学的老师,他们都读过余秋雨的文章,听过余秋雨的讲学。他使他们自觉地把自己放得低低的,对他的学术成就充满敬畏,对他活跃开阔的思维满怀钦佩。同为教师,他们对他讲台上的风度更是念念不忘。他们的集体表情,让我对那个时代最常用的“精英”一词,有了最直接的认知。而我这个余秋雨的学生,一进入他们的圈子,就沾光添彩,大受欢迎,成为他们当中的宠儿。他们喜欢唱前苏联歌曲,他们喜欢带我玩,他们喜欢和我讨论外国文学话题。我还那样,总不爱用教材上的那些语言,我用自己的话表述对西方文学的热情和理解。他们都比我大十几岁、二十几岁,但他们喜欢我的话,他们看重我的思考。
|
|
 
本书由“啃书虫”免费制作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