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上海――深圳――北京 它的三个城市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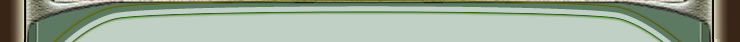 |
 |
|
从未像看上海那样,漫不经心和优雅地远看我居住了十几年的北京。
这座城市仿佛一个巨大的漩涡,无数青年自各地而来,然后一转眼,就被吸了进去,卷了进去。多数无声无息,无影无踪。这座巨大的城,还在不断地往外扩张,一环,二环,三环,四环,五环......等到退出城来,早远得再难看清。有一回听说,毛泽东进北平前第一次看北平就在香山上,那里可以看到北京全景。我和别人半玩笑半认真爬去看过,天气不佳
,雾尘满天,连颐和园都没怎么看清。
离开上海时余老师问我为什么要去北京呢?我傻乎乎地回答“北京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
因为不知道自己究竟要去哪里,要干什么,所以选择北京。在心里,我完全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去北京,天性散漫,总是在一个地方呆不长,只觉得北京嘛,位置最高,若再呆不住了,往哪儿去都是往下哧溜,省事。
我们谈起二三十年代的北平,那是他心目中旧时文人学者的家园。很多大学在北京,很多大学者在北京,那时的教授、学者完全不必为生计劳神奔波,大学里的薪水足够租得起一座四合院儿,养活妻儿之外,还好雇一名老妈子,包一辆黄包车。自北大、清华讲完课回家,就在火炉边看书、著书,而首都远在南京,这里的天空相对宁静、高远。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晚期的北京,身份还有些模糊,政治味道很浓,观念也相当陈旧,生活条件相对南方,更是艰苦、滞后,我的一些同学视进京择业定居为畏途。
这之前我去广州的广东省艺术研究所找过工作,可能因为我发表过一些文章和小说,更大的可能还是因为我是余秋雨的研究生,广东方面挺当回事地接待了我,所长副所长还有戏剧、舞蹈、音乐、美术好几个研究室的负责人都聚集到一间屋里,一个个地与我来探讨艺术,仿佛又一次的毕业答辩。
后来他们真的来函欢迎我去工作,我又犹犹豫豫对余老师说:“那儿是做生意的地方啊,我对做生意又没有兴趣。”
余老师认为选择广州可能更好一些,它毕竟是中国经济崛起的前沿地带,是中国目前最有活力和希望的一片区域。
他的话我并没有认真听进去,我以为他只是理论上那么认为罢了。
几年后他自己也去了深圳居住。他的话其实并不停留于理论的,那时他已开始采取强有力的行动,来实践他的想法,甚至预感——有人就称此为“文化预感能力”。
后来上戏的学生当中,无论戏文系、导演系,还是舞美系、表演系,都有一批不错的学生也都去了深圳,或者搞文化,或者经商,都做得有声有色。我知道他们都会以余秋雨的学生、朋友自居,他们常常见面,互通信息,还像在上戏的小院儿里那样。
离开北京的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去了深圳“锦绣中华”的刘半仙,印象中他总在参与策划大的文化演出,不是把国外的弄到国内来,就是把国内的介绍到国外去,我们在北京见面时,他说的那些事情里有两件我印象最深,一是他说到一位他认识的女校友在深圳活得那么死气沉沉,他怎么想办法帮助她她都不开化,完全地自我封闭,滴水不进,难以融入深圳的活力中去。他说的时候那么着急,很有些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表情,我记得很清楚。还有一件事,他说起一位女演员穿着一套“难看得不可理喻”的裙子参加金鸡奖还是百花奖颁奖典礼,他当时的语气和表情是嫌弃中又夹带些气恼甚至羞愤,好像她是他家的什么人,他对她这样在外头丢人现眼是要负责任的。他随即对我说,他就要去做一个纯粹的商人了,要真正地富有起来后,再回过头来搞艺术,搞文化,要让艺术处于一种文化的氛围当中,这样至少让我们看上去会体面一些,不至于和国际脱轨得太远。他的话和行动让我觉得他是那种我没法与其相比的人——有想法,更重要的还有积极的行动。
看到女演员穿难看得不可理喻的衣服上台领奖,我可能会在私下里用极鄙夷的口气嘲笑她们,看不起她们。记得有一次在杂志上看到一大帮的女演员里,只有闯荡过好莱坞的陈冲穿着晚礼服出席典礼,结果在一大堆胳膊、大腿捂得严严实实的女人堆里,她反倒显得好像是穿错了衣服一样。后来果然再看到她出席类似场合,装着上就开始往回收,开始向大陆女演员品位那个级别上靠。也许这正好说明中国大陆根本就没有、或者说得好听点是还没有形成电影的文化传统,当然也就没有什么所谓电影的盛典之说了。像戛纳电影节、奥斯卡颁奖典礼、新片首映之类,所有出席现场的演员,无论男女都得在穿什么的问题上煞费苦心,稍不留神,就要铸成大错,就连一些著名演员也都曾有过因穿衣不当被媒体攻击得几年缓不过劲来的时候,那无疑就像被人当众扒光了衣服一样丢人。相比之下我们的演艺人员的确要潇洒许多,套用王朔的话,“我是流氓(无产者)我怕谁”。
刘半仙的可爱之处在于当时还挺有一种想要建设点什么的责任感与牺牲精神。那时离开北京的文化艺术圈,就是挣脱一种封闭、死旧的文化生态。我还记得刘半仙要去深圳却弄不到边防证跑来问我有没有办法时的情景。
深圳的上戏校友里还有一个女孩丛容,是我毕业前夕在我的剧作指导老师陈加林先生家认识的。之前陈加林也是她的剧作指导老师,她的毕业论文就是创作一个话剧剧本。她总在提出自己的剧作构思,一出关于爱情的戏,根椐她对爱的理解与体验。陈先生又总在否定她的构思,当然是根据他的社会生活经验和戏剧创作经验。她总要去他家,他们总要讨论她的作业。她脑子很灵,有一天突然想到,这样的情景本身就是她要创作的戏:爱的一次次被否定,被扼杀,所有的清纯,所有的不合规矩,所有的不切实际,不再发生了。最终,女孩儿的“爱情”生活终于被理顺,终于得到了承认,而其实早已不再是那个最初的“爱”,本真的“爱”。她的剧名就叫《爱的构想》,结构完全是开放式的,在上海人艺剧场演得很好。全校的学生都统一去看了,大家议论说这个戏的编剧是我们上戏出来的。很佩服的样子。她后来分到上海人艺工作。
在陈加林老师家,我们一边喝着红酒一边谈些话题,两个女孩都有些相见恨晚的意思。出了陈先生家,她一定要我去她的人艺宿舍。我们躲在她的小屋里叽叽喳喳聊了一夜,隔壁总有人在敲墙壁抗议,但我们依然不肯停下来,一直在说。都是些女孩们最隐秘的记忆与体验。她的天真和率直,让我一想到这丫头写的话剧曾轰动过上海滩,忍不住就要惊讶几分。
后来这个叫丛容的女孩儿在深圳搞过一部电影,应该说那部电影在国内也小有影响,再
后来她成了深圳文化部门的小官员,我从北京这边的报纸上看到对她的一次采访,虽然想象不出她如今身为官员的严肃与成熟,但听到她说,不管搞创作还是做官,她的心态都没有改变,一直都是在从事一项文化事业,在为建设和营造深圳的文化氛围做着事情。我就觉得她可能还是和以前那个与自己一起谈心、一起逛街淘衣服的丛容一样,是可爱和自然的。
那也正是余秋雨一直在倡导的我们应该有的文化生态。他并不喜欢把自己和学生都限定在一种生活模式里,他嘴里和眼里的所谓“事业”总是一个更大的概念,往往是一项工程,这个工程是不断变化和丰富着的。
许多上戏学生在这点上深受他影响,从思维到行动,都更像是余秋雨的“嫡系”。余秋雨和上戏众多校友本身的加入深圳,已经为新型的深圳文化增加了不少的分量、色彩和活力。
一个城市,哪怕就是一个社区,文化人士的加入会为这一地区增色许多,无形中它的重量和价值也就会提升了。一些共同的志向与观念,有时候还会像星星点火一般,不知不觉就形成气候带动全盘。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我认识的两个广播学院的朋友突然就去了香港,后来才知道他们的一个院长去组建凤凰卫视,“一根线上连着一串蚱蚂”,带走了一批广院毕业的学生,一帮人把凤凰卫视经营得有声有色,感觉上既不同于香港的电视文化,更不同于大陆的那些个电视编排,说它打擦边球也好,说它独辟蹊径也好,那都是因为大家有着相同或相类似的电视消费理念,才会在那么短的时间里让那只凤凰飞得那么高,让他们的凤凰产业有了那么骄人的成绩。
我知道深圳人曾把“深港接轨”当作深圳与“国际接轨”的第一步,想要形成所谓“内地——深港——国际”这样的开放格局。
而余秋雨,好像一下就站到了深圳这个最有希望成为中国文化桥头堡的阵地跟前。后来也是在深圳,他更加远离了内地的“文人”群体,更多和更加频繁地接触香港、台湾及东南亚地区的文化界,他很快以自身的国学底子与现代理念征服了海外。
在深圳,他不仅走出书斋而且彻底抛弃内地“文人”圈,更独立地迈向完全的现代化、国际化。后来,他还曾就深圳文化发展的前景有过一篇文章,引得少数的人议论纷纷,其中也包括我在北京这边听到的那些中式文人的不满。他提出的“中国文化的桥头堡”、“深圳学派”等概念,被看作是一时性起,是不谨慎。
我自己想,这根本就不是一个等量级别下的对话,其中必有误读或者误听。人们以为的“文化”,和他心目中的“文化”应该不是一件事。人们大概以为守着几座皇帝老儿家呆过的古城、拥有众多历代官方史料记载,就有了“文化”。
而他喜欢对我说,你一定要强调“人的文化生态”,要强调人对自己生态的自我选择,这才是文化。
他是主动的,一如他一向的风格,而他们是被动的,将要淹没的。
听他说话和表述,常有这样的感觉,在别人还停滞于表面,被现实中不断缤纷而落的现象罩牢、糊住时,他的话语总像是对着镜头过来的一只大手,越伸越长,穿过众多屏障,一下就抓住那个实质的核。让你的心、眼跟着也要一亮。
他说经济的发展与流通,将使珠江三角洲地区成为人来人往的流通码头,而现代文化非常关键的就是它的流通。如果没有流通,没有相互沟连的大网络,文化就会处于一种粘滞状态,僵死状态。文化的高深失去现代价值,也就没法焕发出来了。
“只有借助现代流通,文化才会成为现代产品”。他看到这些,并且会积极动作起来,以自身的行动去完成和证实,这令他总是超然于外,总要先行一步,也让他时不时地会引得一些人不满意。
我一直惊讶,他身上那些感性的、天真的气质,让他会有许多与众不同的仿佛突然而至的念头,然后他会把这念头拉入自己的语言构架里头,让它稳稳地落在一个强有力的、厚实的、极具理性的平台上。
我总是惊讶这个过程的转换,突变,它们是怎么样实现的呢?一个人怎么可以从那样的感性、天真好奇,一下子就到达那样的理性、深思熟虑?这应该是他自身最突出的个人魅力,是他总能征服谈话对象、征服读者的力量所在。这让他总是大气和宽广,会让我对他产生盲目的迷信,觉得他会在任何领域任何年代里独辟蹊径,成为强者。
过去做他研究生时,熏染得多,我几乎也快要有点这样的意思了,但后来离开了学术的氛围,完全放弃,就把自己放任为洪水泛滥凡事不过脑子的糊涂女人。
因为胸中有那样超前的想法和认识,余老师对我毕业后选择北京有些不以为然。他说你男朋友不是做生意的嘛,光是做生意,也应该去广州啊。
我自己却是一派懵懂。我总是对周遭大事、形势变化不闻不问,一派漠然,更不要说会有什么理性的见解与预知。对自己的未来哪怕是家居生活,也从来没有计划,一直是放任自流。
本来也是想在南方开始一种更有活力、更加宽泛些的生活的,可是到了广州,在从广东省艺术研究所到借住的老同学家途中,公共汽车上身边拥挤着的男人的长相,突然令我对未来的广东生活心生畏惧。他们长得实在太难看了(请所有广东俊男别太生气),怎么好去亲近。
一个这样直接的理由,让我还没离开广州就起了不去那儿工作的念头。我只有自嘲,称自己好色,怕在广东找不到英俊男人作伴,北京嘛毕竟“藏龙卧虎”。
对广东和深圳的更进一步感觉,要等到十几年以后的世纪末。因为深圳市委宣传部要与国家文物局合拍100集的电视片《中国博物馆》,我这个总撰稿之一跑去深圳找余秋雨老师喝酒,在推杯换盏间“偷取”他脑子里的博物馆概念。片子在北京运作,但过关得在深圳官方。片子的进展,让我对开放的深圳现代文化、文化人颇有好感;而北京这里的种种波折,所谓文化积累的无限沉重,与现代文化发展趋向的格格不入,也让我对余秋雨的生存状态有了最直接的体会和感悟。关于要写一本余秋雨的书的念头,也是在那个时候跳出来的——
我让自己别太急,还有的是篇幅慢慢道来。
十几年后,我和余秋雨老师在北京常见面,更多的时候他来去匆匆。
那天我们在方庄喝茶。本来说好我去宾馆找他,他说他要介绍一位女编辑和我认识,因为他曾向她谈起过我,引得那位女编辑起了兴趣,想要看看这位让余先生津津乐道的女弟子究竟何方妖怪。约好大家一起吃中饭,我兴致勃勃刚在余老师下榻的宾馆坐定,女编辑打来电话说她的领导大人也一起来了,正在大厅。我马上起身告辞,对余老师说我不要和陌生人一起吃饭,尤其是当官的。他还是笑,放我一马。我们一起进电梯,我跟他说一出电梯我们就假装不认识。在宾馆门口等出租时,眼睁睁看着余老师被一帮人“劫持而去”。
晚上他无意去三里屯喝酒,说去那里的熟人太多了。也许怕再次冷落我?我只好让余老师自己打车来方庄的茶馆喝茶。我们总算又能一对一地聊天了。
我突然说每次见你你都是一个人。在北京,我几次去找你,梅地亚,保利,中旅,你都是独来独往,然后——绝尘而去——对,就是这个词,绝尘而去,仿佛大侠一样——之后报纸上才有新闻报道,说你又在北京干了件什么,仿佛你正在这件事情当中,但我知道这事已结束,你已经在做另一件事了。
他自己也笑:总是这样,有人就说我永远在人们的射程之外,这有点好玩吧。
我看得出,他对自己的状态满意和自得,这是他理想中的状态。
我有时会主动提起媒体对他的褒贬,他已谈笑风生。既然已成公众人物,只要不是人身攻击恶意栽陷,评说也就任由他人了。他依旧地我行我素,独往独来。
那次见面,他说第二天一大早在现代文学馆还有一场演讲,我问他哪里组织的,都是些什么人去听。他随意地说,谁都可以去听,什么样的人都有。
这就是他的状态,人在江湖,他却有本事不让自己身不由己。无帮无派,却总是搅动一泓漩涡,自己又总在这漩涡之外。
就像北京总是一个平台,他喜欢在这里展示他自己,却从不让自己深陷其中。
一次次地进出北京,让自己的书一本本从北京这里问世,撒向全国。
他的形象一次次出现在中央电视台的屏幕上,让全中国的观众都记住了他。
他的影响和名气太大,许多找他的人却遍寻不着,不知他究竟身居何方。
偶尔也会有电话打到我这里,又有人要找他参加某个活动,我总说我不知道,真不知道余先生他人现在在哪里。我这个铁杆学生,竟然也学会应对这样的事情。
北京是什么?北京是他需要时才出现和存在的一座城市而已。他完全可以选择它的好处,回避它的种种不足。他和马兰把家分别安在几座城市里,从不把自己固定在任何一处。这是他以自身实力最终为自己和家人选择的生活状态。
我眼里的强者就应该是这样的。
他的写作与生活状态,让我羡慕不已,也让我生活其中的北京变得愈加模糊。
|
|
 
本书由“啃书虫”免费制作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