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看余秋雨告状于光远 又读了余秋雨的两篇自白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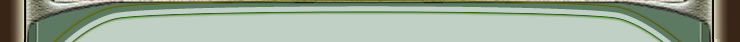 |
 |
|
也是在送给我的那本《余秋雨现象再批判》中,我又读到余秋雨的两篇自白。一篇是《余秋雨郑重声明——我不是“文革余孽”》,还有一篇是《余秋雨:对于历史事实我从不谦虚》。不过这两篇都不是余秋雨自己写的署名文章,都是由一位杨瑞春记录下来的“杨问余答”。第一篇发表在《文学报》2000年的第1127期上。发表的时间未查。第二篇发表在《南方周末》上,时间是2000年4月28日。发表后未见余秋雨出来更正。同时杨又是2000年1月22日余秋雨同余杰在四川作家魏明伦家会面的促成者。因此,我认为可以把这两篇视作余秋雨自己的东西。不过我想还是应该给余秋雨更正杨的报道的权利,如果杨的报道不实,我据以发表的言论自然该相应改正。
先讲我对余秋雨的这两篇后来发表的自白,第二篇我不想说任何话,第一篇涉及一般性的问题,在这里就说一点看法。
首先我是从来不赞成随便使用“文革余孽”这样的语言。如果余秋雨不接受,他当然可以发表声明。我也不想对这写什么文章。现在我之所以产生再写一篇的动机,是看到余秋雨在回答杨瑞春的问题时所说的下面的那两段讲话。
第一段是“如果用强迫的方式要别人对自己的行为做出思想结论,而强迫者又没有搞清楚行为的真相,那么缠来缠去,争论不休,反而把反思这件大事降低了、庸俗化了。总有一些人至死不肯反思自己的罪行,但只要理性群体深入反思了,中国就有希望。”
这一段话讲得很深奥,曲曲折折地表达了以下几点思想:
1.今天发生的问题是作家中有一些人提出余秋雨应该反思,这些作家手中并没有权,也不像当初“文革”中的那些写作组,他们有政治权力的支持。这些人写文章,实在说不上什么“强迫”。最近一阵子有这种议论的人多一些,余秋雨因此受到不小的舆论压力:但是余秋雨可以听也可以不听。别人强迫不了他。事实上余秋雨就没有听,没有去做什么反思。这怎能说他受到了强迫,而且存在了“强迫者”了呢?他的“道理”实在太深奥了。
2.在他这篇话中,还包含这样的意思:在同他有关系的问题上,该反思的不是他,而是同他作对的别人。他认为要看那些人肯不肯深入地反思。而中国到底有没有希望,还要看那些人够得上或者够不上属于“理性群体”中的成员。真是妙不可言!
这是就他的第一段话。
这段话属于一般性议论。下面一段讲的就是关于他本人的具体情况。他说“如果就具体经历讲,我和我的家庭在‘文革’中的经历真可以说悲惨之极,远远超出那些年轻评论家的想象。我不是年轻人,让年轻人去提高认识吧。”下面讲:“文革”初期十九岁的我,是全院第一个领头写大字报反对“造反派”的人。(那时造反派还没有掌权,以后情况变化了,他和跟着他写大字报的人失败了)“结果造反派掌权以后承受了长时间的批判和侮辱。我没有向他们有过一丝一毫的屈服,他们曾经威胁要与我父亲单位联合起来抄我的家,如果这样的事真的发生了,我可怜的祖母和母亲可能难活得下去,但我也没向他们求饶。”余秋雨说到这里,对后来他怎么又成为写作组的成员就没有说下去。这一点人们还是不知道。他答非所问。不过他完全可以不说。要不,他又会说有人强迫他了。不过他对他当时的情况所讲,倒使人们可以知道他当时和现在的觉悟水平有多高。这是容易看得出来的。我们知道,就是在余秋雨参加写作组写那样的文章的同一历史时期,而且在他活动的同一个城市上海,也有一些年轻人,他们不顾本人的安危,也顾不了对父母尽孝心,大义凛然地坚持反对“四人帮”的立场,作出了光辉的行动,成为大家学习的楷模。对当时余秋雨这样的青年,自然不会有过高的要求。
2000年8月31日
(选自《跨世纪门槛》,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
|
 
本书由“啃书虫”免费制作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