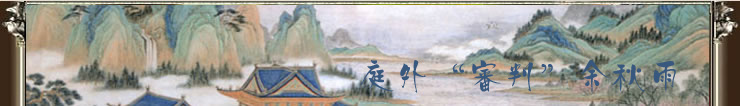 |
 |
|
我和余秋雨打官司 胡锡涛葫芦里卖的什么药(2)
|
 |
 |
|
“当时朱永嘉要我写,我说还是让《文汇报》组织内行写比较好。1968年10月16日,《文汇报》为此专门成立了五人写作组,其中余秋雨公认文笔最好,徐企平最内行。第一稿是来自国棉十七厂的王亚伦写的,他10月31号拿出第一稿,六千多字,打印成铅字后,上头一看,完全是工厂大批判的水平,没抓住要害。第二稿由我交给余秋雨写,他当时关在一个小房子里埋头苦干了十天左右,从不抽烟的他也抽起了烟。他的稿子拿出来后,大家传阅时感觉像学术论文,于是我原封不动把尚没来得及排成铅字的手稿退还给余秋雨。之后,我闭门苦干了一个多月,两易其稿,一万二千字的文章最后一字没动,1969年发表在《红旗》6、7期合刊上。而余秋雨早在1969年1月就到吴江县军垦农场劳动去了。当时的讯息渠道并不畅通,日后我看了有关资料,才知道孙维世的死亡时间是1968年月10月14日。”
“记得参加五人写作组时,余秋雨的毕业鉴定还没有做好,他白天到学校去,晚上来《文汇报》社报到,后来我才知道原因:他当时很穷,父亲被关起来,叔父又自杀了,正长身体的他根本吃不饱,每天步行一个半钟头来报社,主要为了吃一顿肉丝面夜宵。记得他的英文很好,能看得懂莎士比亚英文原版剧本,我经常在《文汇报》的楼道内听到他朗读外语的声音。”(《华夏时报》2002年8月24日)
胡锡涛这篇谈话,一边为余秋雨开脱,一边又在开脱时褒中带贬的损余秋雨为了“吃一碗肉丝面”不惜卖身投靠“四人帮”写大批判文章。他这次谈话破绽甚多,经不起推敲。 我曾写了一篇《评胡锡涛自相矛盾的“证词”》:
原《红旗》杂志文艺组负责人胡锡涛为了替余秋雨开脱,在过去的回忆录中追加了“我原封不动把尚没有来得及排成铅字的手稿退还余秋雨”这段话,以说明《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定稿时一个字都与余秋雨无关。这一情节很可能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即余文有可能已排成了铅字。因“工厂大批判水平”的一稿都排成了铅字,最能写的余秋雨写的二稿却没有排成铅字,这可能吗?二稿经“大家传阅”,这“传阅”的不太可能是手稿。而只要排成了铅字,余秋雨就无法当场全部撕掉,胡锡涛写三稿时就必须参阅。当然,这还有待证实。此外,胡说重写此文时自己“闭门苦干了一个多月,两易其稿,一万二千字的文章最后一字没动”,也颇值得质疑。
一是他在《余秋雨要不要忏悔?》中讲的是“我在《文汇报》顶层熬过了寒冷而苦恼的三个月”,而不是他现在说的一个月。
二是他写三稿时是否“最后一字没动?”据他自己原来的回忆,他两易其稿后,徐企平看过清样,又被姚文元在“文章开头”“加上一段林彪在‘九大’政治报告中的套话”。另有司马东去在《浩劫上海滩——一个中央工作组成员的耳闻目睹》(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1月版)中回忆可作旁证:“《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一文,由姚文元定稿,登在《红旗》杂志上”。可见,胡锡涛说他写完后“最后一字没动”,是不真实的,有为代他人受过和作伪证的嫌疑。他说这些自相矛盾的话,其目的是为了保护与此文有关的二稿执笔者余秋雨。
但洗刷只会越刷越黑。胡锡涛的证词倒是从另一方面证实了笔者说余秋雨曾参加过批判“斯坦尼”小组,成了五人小组成员之一,以及笔者在《南方文坛》上说的余秋雨“只是奉命参与讨论执笔并非是最后定稿人”的真实性。余秋雨为写批判“斯坦尼”一文二稿“关在一个小房间里埋头苦干了十天左右,从不抽烟的他也抽起了烟”,这和胡锡涛过去说的余秋雨为完成江青、姚文元布置的重大政治任务“写稿很下功夫,不走捷径,直接查阅原著,四本斯坦尼全集被他翻得卷起了角”,同样证明了余秋雨当年为了完成江青的批判“斯坦尼”的政治任务,是何等的投入和用功!
到底余秋雨写的批判“斯坦尼”一文的二稿有无排成铅字,或定稿时他有无参加,这不是本质问题。本质问题是余秋雨确实参加过批判“斯坦尼”五人小组。这个“五人小组”,显然不是今天的学术研究小组,而是打着学术研究幌子在“四人帮”控制下从事革命大批判的“爆破”小组,这可从此文于1969年在《红旗》第6、7期合刊上用“上海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的名义发表得到反证。
郑雪来作为中国研究“斯坦尼”的首席权威,他对胡锡涛的质疑比我的看法更显得力透纸背和打中要害。他在《我看“余秋雨状告古远清”事件》附录的《疑点之三》中说:
胡锡涛在受访中说,“第二稿由我交给余秋雨写,他当时关在一个小房间里埋头苦干了十天左右,从不抽烟的他也抽起了烟……”,“十天左右”的时间写出一篇洋洋洒洒的“学术论文”,当然还要加上反复阅读四卷本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全集,这真是奇迹!我作为“斯坦尼”全集的主要翻译者,当然知道这四卷本的总数足足有二百万字,而且第二至第四卷全是相当枯燥的理论性东西,读一遍少说也要花十天时间。那么,按照胡锡涛所说的“四卷本斯坦尼全集被他翻得卷起了角……”,他得反复读多少遍呢?连读带写,这十天够用吗?胡锡涛还特别声明:“因为它像学术论文,于是我原封不动把尚没来得及排成铅字的手稿退还余秋雨。”胡锡涛可谓用心良苦,为证明此文“确实与余秋雨无关”,他力争做到“滴水不漏”,只可惜他所谓的“十天左右”和“四卷斯坦尼全集被他翻得卷起了角”的明显矛盾使他的“证词”露出了破绽,令人难以置信。
|
|
 
本书由“啃书虫”免费制作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