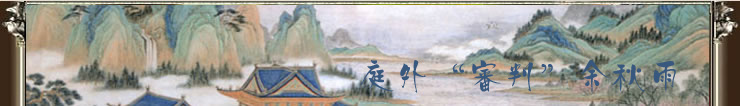 |
 |
|
我和余秋雨打官司 庭外“审判”余秋雨(4)
|
 |
 |
|
余秋雨:我打官司就是要通过法律行为,为中国文化界的有顺序操作,打下一些基础。我要为中国建立一个法治意识。(摘自《亚洲周刊》2002年9月1日和新加坡《联合早报》2002年11月23日)
陈冲(河北作家):这在逻辑上可就是一招险棋了。因为一旦官司没打赢,莫说打输了,就是打成个大体平手,例如以达成调解协议了结,中国的法治就没有希望了,中国作家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界就更没有指望了。(摘自陈冲:《把自己诉成被告》)
周萍(山西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余秋雨作为古教授近二十年的个案研究对象,搞清楚余秋雨究竟“文革”有无问题,应该是学术研究者在对历史和人民负责,对余秋雨本人负责。公开自己的研究结果更是研究者应负的义务。可是,不论文坛多么热闹,正义者如何谴责,人们多么疑惑,读者如何期待,余秋雨却始终对那段历史的真相三缄其口,对人们关注的“核心问题”避之又避,这正为“真相”添加了浓厚的神秘色彩,再加上他有躲躲闪闪的嫌疑,更让读者疑惑丛生。何况忏悔声源自北京城,古远清远在武汉,又不是最先指责余先生应“忏悔”的人,哪里算做是“源头”?这其中原由怕是只有余先生心知肚明了。作为读者心存疑惑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不由想问,余秋雨:您到底害怕什么?(摘自周萍:《余秋雨:您到底害怕什么?》,菲律宾,《商报》2003年3月24日)
孙光萱(原“石一歌”成员):我再想劝余秋雨先生一回:希望你好好学习公民道德规范,“为文”、“做人”都要以“诚信”为本,多作一点自我批评,须知这对你是“无损”的,不要再使广大读者失望。(摘自孙光萱:《再劝余秋雨一回》,未刊稿)
余秋雨:几个在“文革”中翻云覆雨的人物,趁一些老人逐一死去,突然指证一个在“文革”中受尽磨难的青年有问题,为什么人们不怀疑他们的身份,而只怀疑被指证者?如果两个老纳粹对一个当年奥斯维辛的幸存者也作出这种逆反性指证,会产生这种情景吗?(摘自《华夏时报》2002年8月24日)
郑雪来(全国政协委员):余秋雨如果把追查他的“文革”问题的古远清等人看成是“两个老纳粹”,而把自己打扮成“从奥斯威辛集中营中历尽磨难侥幸逃出来的受害者”,那可真叫做“角色颠倒”甚至是“是非颠倒”了!上海大批判写作组是什么东西?它不就是炮制了许许多多“以笔杀人”的黑文章的“四人帮”的御用工具吗?许多深受其害的文化界、教育界的人士在当时就如同奥斯威辛集中营中的囚徒,而身在写作组的余秋雨却把自己看成是“受害者”,这不是很荒唐可笑吗?上海大批判写作组可以说就是许许多多中国知识分子被囚禁的“奥斯威辛集中营”,在那里面为“四人帮”亦即“纳粹”效劳的人不一定都亲手杀过人,但不能不承担一定程度的罪责。(摘自郑雪来:《五问余秋雨》,《澳洲日报》2002年11月4日)
钟固(新加坡作家):余秋雨信心十足,他在新加坡对媒体说:对古远清的官司将于12月开庭,他“有百分之三百的胜算把握”。可是,半年已经过去了,还没有听到他“胜算”的消息,对他不利的消息倒有所闻。打官司不是写文章作演讲,而是靠事实、靠法律取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余秋雨名气再大、傲气再足,都得放低身段,尊重法律。(摘自钟固:《余秋雨赢得了官司吗?》,菲律宾,《商报》2003年6月2日)
邓京芳(澳大利亚评论家):近年中共提倡“党讲正气”,不是江湖兄弟者,法官们是很难挺胸两肋插刀的,尤其“余古之讼”这样影响力大的名案,即便插刀,亦会引起中国和国际文坛的揭露与评判。笔者祈望法官能辩证考量,辩正断案,尤望学术问题仍用学术方法解决。(摘自邓京芳:《余秋雨兴讼与法律公正及“党讲正气”》,悉尼,《澳洲日报》2003年3月22、23日)
一把老刀(网友):余秋雨尽管有权起诉,也有可能胜诉。但舆论并不必然以判决为尺度。舆论不但可以批评判决不公,也可以批评立法不公。纠纷最终要通过法院解决并不意味着舆论应该就此闭嘴,相反舆论的监督倒是保证司法公正所必可少的。(摘自2002年9月6日网页)
某网友:好像余秋雨自己认为中国只出了一个文人就是余秋雨,怎么那么想成名,总想站在新闻的第一线,成为焦点人物,是不是自己才尽了做不出学问了,变得俗气起来,不要因为你叫人觉得上海人就是小家子气。你这两年好叫人讨厌的。所以忠告你几句。(摘自2002年搜孤网页)
韩浩月:俗话说“大人有大量”,虽然我们不能以宰相肚量来要求余老师,但撑不了大船起码也能过只蚱蜢舟吧。照目前为止余老师的表现看,想在他肚里飘一片树叶子都难。尽管如此,我还是想给余老师进一言,不要老惦记着什么 “文化名人”的形象……(摘自韩浩月:《拿什么来拯救秋雨》,《天津青年报》2003年7月20日)
何家栋(原中国工人出版社总编):名人酷爱打官司,足证他们不仅爱名,也爱自己的声誉。动用法律保护自己的权力,例如盗版、剽窃,也是正当的。但名人的不利之处在于,他在出名之外,也要受社会舆论监督,而社会舆论是各种各样的,有好有坏,有负面的影响,也有正面作用。余秋雨似乎有点得理不让人,不仅要借诉讼证明自己的清白,还要将对手打翻在地过几年“紧日子”。好像他只图报一箭之仇,没有想过他自己也受社会舆论监督?被誉为“文化大师”的余秋雨,居然要剥夺他人言论自由的权利,岂不是犯了本行的大忌?这种败德之事,无论何时,都难逃公议。(摘自何家栋:《文化人的沉沦》,《南方周末》2004年1月29日)
|
|
 
本书由“啃书虫”免费制作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