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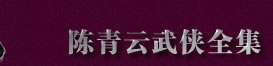 |
|
 |
|
 |
| |
|
第十二章 春梦留痕
|
|
姗姗望着房门皱眉,粉腮一片潮红,这种阵仗对一个十八九岁的少女而言,冲击力是相当大的。
“有人吗?”声音自楼下传来。
“什么人?”姗姗急步冲到楼栏,只见一个英姿焕发的剑士正仰头上望。王雨是美书生,而来者却是俊武士,俊但不失英挺,是武林少女心目中最理想的对象。她呆了一呆,这是她所见江湖武士中最最令人倾心的人物。当然,她明白自己的身分,不敢作非分之想,只是心理上必然会产生的正常反应而已。
“武林公子韦烈!”
来的是韦烈,凭韦烈的本领,除了蓄意逃避的人,要探查—个人的行踪并不难。他是出山之后会合了王道和洪流,然后再查出王雨的行踪,上了小峰头,正碰上急如热锅蚂蚁的立仁、立义两名书僮,不过,对这边的状况并不了解。
“武林公子韦烈?”姗姗重复了一遍。
“不错。”
“何故擅闯私人禁地?”
“找人!”
“哦!找谁?”
“多事书生王雨!”
姗姗窒了一窒,不知该如何答复。
韦烈可不那么斯文,飞身掠上了楼栏,姗姗没有思考的余地,人家已经硬闯上来,织掌一扬,拂向韦烈,用的竟然是武林中不多见的“兰花拂穴手”,而且功候十分到家。
韦烈随便一翻腕,便把这凌厉的一击化解。
姗姗已退开数步。
“外面什么事”房里传出“神女翠姬”的话声。
“有人硬闯竹楼!”
“是什么样的人?”
“他自称‘武林公子’韦烈。”
“噢!”
里面的五名少女已闻声而出,齐集厅门,一群莺燕,韦烈直觉地感到这地方有些邪门,有女无男,通常都是不大正派的,尤其王雨一表人才。
房门开启。
厅门里的五名少女退了开去。
韦烈一眼便看清了,心头震动了一下。出现在房门外的,是一个美艳娆媚的女人,云鬓蓬松,脸上的红潮未褪,眉眼还含着浓浓的春意,外衫没扣,用手掩住,隐隐露出白玉般的肌肤,那份姿态说多撩人有多撩人。
翠姬上前数步,笑意上了粉靥。
韦烈心里又悸动了一下,如果王雨就在房中,一男一女做了什么不问可知了,这女人的年纪比王雨大了许多,他是这样的人吗?
“你刚才说……你叫什么?”声音柔媚得颤人心弦,像是十六七岁的少女,煽情的眸光直照在韦烈脸上。
“在下‘武林公子’韦烈!”韦烈是一脸正气。
“武林公子,嗯,听这名号想来是响当当的人物,可惜久不出江湖,变成了孤陋寡闻,来此何为?”
“找芳驾的楼上佳宾!”
“你……是找王公子来的?”
“正是。”
“嗯!天生的一对,羡慕煞人,你们是什么关系?”
“朋友!”
“仅只是朋友?”翠姬眉毛挑了挑。
“那还会是什么?”韦烈心中犯了嘀咕,尤其那句“天生的一对”是什么意思?这女人邪得实在可以。
“我以为你们……”说了半句停止了。
王雨从房中踉跄步出,衣衫不整,脸色也不正常。
韦烈直皱眉,对王雨的人格大打折扣。
王雨手扶桌角,人似乎还在晃。
“他喝醉了!”翠姬笑着代王雨说明。
“在下看得出他是喝醉了,醉得不知自己在做什么!”韦烈的声音很冷,他的心也同样冷,为王雨而冷。
“我跟他还能做什么?”翠姬嫣然一笑。
这种女人在面对这种见不得人的事时,居然还谈笑自如,不知天下尚有羞耻事,还有什么可说的。
韦烈摇了摇头,望向状极狼狈的“多事书生”王雨,心想,“不管他有多大本事,毕竟是年轻了些,面对这种女人又喝醉了酒,有几人能把持得住,听两书僮说,他是听到琴声才来的,八成是以前遇到了知音,在有意的安排下,不自觉地坠入陷阱是可以谅解的事。”
“王老弟,你怎么会醉成这样子?”
“我……韦兄……牡丹滴露……够强!”
这句暖昧不明的话,听得韦烈大不是意思。
“你还没醒吗”
“小弟我……心里明白。”
“明白就跟我回去。”
王雨摇摇不稳地举步,翠姬伸臂拦住,这一伸手,外衣便放开了,酥胸便袒露了一半,但她似乎不以为意。
“韦公子,来者是客,稍坐何妨?”
“在下有事在身,改日再来拜访。”韦烈以最大的忍耐力按捺住心火。
“你真的会再来吗?”翠姬一厢情愿地问。
“必要时就会!”韦烈话中有话。
“何谓必要之时?”她毫不放松。
“在下看不必作言词之争,以后的事以后再说。”
“不给我面子?”翠姬语气已变。
“面子?”韦烈冷冷一笑。“在下的确没考虑到芳驾是这么爱面子的人,真是失礼之至,不过……这也只有留待以后再说了。老弟,你还赖着舍不得走?”目光转向王雨已变为严厉。
“你不走我可要走了?”
“韦兄……”王雨想举步但手臂被对方格住寸步难移。“小弟是酒后乏力,再稍稍休息一会儿便好。”
“哈!居然称兄道弟,像真的一样!”翠姬作出非常好笑的样子。“韦公子,他走,你留下如何?”
“在下的确有事。”
“你两个都走,这竹楼岂非又要冷清了?”
“芳驾如果怕寂寞,可以再找别的,天下男人比比皆是,以芳驾的这份能耐,何愁座上无客?”韦烈这两句话可以说极尽讥讽。
翠姬不以为忏,故作不懂。
“我一向讲究‘缘份’二字,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韦烈已经不耐了。
“王老弟,我扶你走!”他边说边挪步。
六名少女蠢然欲动,但被翠姬以眼色制止。
“站住!”翠姬娇喝,但声音不大,笑容也没敛。
韦烈已到对方身前三步之处,止了步。
“芳驾想说什么?”
“我一向和平处世,不喜欢暴力血腥。我跟你的王老弟既是有了缘,琴箫共鸣,对你当然要留三分情,日后也好见面,你既然执意要走,我也无计留宾,请吧!”她说完,侧移三步,作了个送客的手势。
“在下会记住这份情!”韦烈极有风度地微微一笑。
王雨挪步,仍有些不稳。
韦烈伸臂拦腰抱住。
“不要!”王雨挣扎。
“老弟,别逞强了,你下竹楼都难,就甭说过涧了。”另只手伸出手把王雨横抱了起来,转身出到楼栏,纵身而下,疾行到涧边。
王雨闭上了双眼。
韦烈相了相形势,重新把王雨抱牢。
王雨轻“嗯!”了一声。
“用力搂紧我!”韦烈叮嘱一声。
“唔!”王雨扭侧环臂。
就在王雨扭动之际,韦烈感觉到手臂弯环处似有异样,一个男人的胸脯不可能软绵而有弹性,心弦“咚!”地一震颤,但他无暇再往下深想,蓄足势,飞旋而起。
王道、洪流与两名书僮已在对面睁大眼巴望。
王雨身躯出奇地轻软,出乎韦烈的预估。
巨鹰升空,一个盘旋,落在涧谷中央的树帽,准备借力再起,就在向下一用力之际,韦烈突觉双足似被什么柔韧的东西缠住,裤脚衣摆也碰上了钩刺,立知不妙,还来不及应变,人已往下沉,瞬间没入翠盖之中。
“啊!”谷边爆起一阵惊呼。
“这怎么回事?”洪流一向惜话如金,现在却先开口。
“有文章!”王道目注谷中。“以公子的能耐,绝对不会失足的,这树帽子里定有古怪,这下可惨了!”
“怎么办?”立仁差点想哭。
“不要紧,总会有办法的。”王道自慰似地说。
“王大哥,你快想办法!”立义接上一句。
“我正在想!”王道抓耳搔腮。
韦烈紧抱住王雨,勉强腾出一手想抓住树枝以免直坠谷底,但无枝可抓,树幕是半壁间横出的树木结成的,不是由谷底上长,树幕一破,下面是空的,而下坠是加速,他又不能放弃王雨,两人直坠,势非粉身碎骨不可。
心念才一转,忽觉被软软的东西兜住,惊魂未定,已意识到下面张了网,是刻意布置的,网的张力有限,重点集中下陷,两个人被兜成了一个人,巧的是韦烈在上,王雨在下,叠得很实在。
王雨经一吓,酒意已消了八成。
“韦兄,我们……侥幸不死!”
“老弟,后果还是难料,这种布置太巧妙了。”
两人只交谈了一句,那网忽然收摆,朝壁间移去。
这一来,两人被裹成了肉粽。
韦烈可不敢冒失破网,网一破人必再次下坠,下望一片乌沉沉竟不知有多深。壁间出现了一穴口,网朝口里收。
刚入洞,有手指重重点来,什么也没看清人便失去了知觉。
韦烈醒来,发觉自己是躺在一间华丽的房间里,锦帐绣衾,软绵绵褥子很厚,照明的是一盏雪亮的银灯,幽香沁鼻,证明这是女人的寝卧。
他想起身,但全身似被抽去了骨头,成了个肉人,软嗒嗒使不出四两力,头晕得很厉害,仿佛是大醉之后,转头用眼扫瞄,房里除了自己没第二个人,显然对方把自己和王雨分开了,不禁苦苦一笑,接下来会是什么花样?
空气是死寂的。
韦烈测试了一下,穴脉畅通,就是功力无法提聚,显然是先被制住穴道,而后又以别的方式取代。
定下心来,百无聊奈,他忽地想到抱住王雨时那分异样的感受,是真实的,绝不是错觉。
王雨先拒绝自己抱他,而后闭上双眼,再加上那娇女暧昧的言词,这说明了什么?难道王雨易钗而弁,他是女儿之身?
心念及此,心头怦怦乱跳起来。
可是那娇女与王雨先后从房内现身时,两人都衣衫不整,尤其那妖女仅披外衣,里面空无所有,眉目之间春意未消,如果王雨是女的,两个女的会做什么事?难道那女的娇女淫荡到表演假凤虚凰?
王雨是出于自愿吗?应该不是,他已醉得不能自立。
如果王雨是女的,她是何来路?
想着,脸上一阵势。
房门开启。
进来的那娇女,一身整齐的宫装,看上去还真的有模有样,只可惜那双媚眼似乎随时都带着春意,使他华丽但高贵不起来。
翠姬笑吟吟,仪态万千地步到床边。
“韦公子,这可是你自己失足不能怪我。”
“当然,在下一向是讲理的!”韦烈火在心里。
“你大概还不知道我是谁?”
“正要请教。”
“神女翠姬,听说过吗?”
韦烈震得几乎要蹦了起来,可惜没力气,他听师父提到过这一代娇姬,算年纪当已在花甲之外,而竟如三十许人,荡风依然不改,的的确确是个人妖,怪不得她的手下一出手便是武林绝技“兰花拂穴手”。
“啊!失敬,在下听说过。”
“韦公子,‘失敬’二字对我是一种讽刺,免了!”
“在下那位朋友呢?”
“他与你之间仅止于朋友?”这是第二次的怪问。
“不错!”韦烈已经想过,所以答得很勉强。
“你是故作不知,还是有意搪我?”
“芳驾这话……怎么说?”
“我脱过她的衣服,解了她的肚兜布,也摸过她的全身,你该明白了吧?”翠姬说这种话是面不改色。
这话已经说得很露骨,韦烈不能再装浑了,他非承认这事实不可。王雨是女儿之身,这对他的冲击很大,双方的情谊已经很深,竟然被蒙在鼓里,这实在相当窝囊。转念一想,江湖儿女只要信守一个“义”字,又何关乎男女,男女之间一样有友情存在,为什么非要扯上私情?想到这里,心结豁然解开。
“那又怎样?”以反问代替答复,非常技巧。
“你还是承认了!”翠姬笑笑。
“她现在人在何处?”韦烈重新拾起话头。
“当然也在此地,不同房间罢了,你放心,此地没有男人,她不会被侵犯的。”诡异地笑笑又道:“三天之后,你们就可以—道手牵手离开。”
“三天……为什么要第三天?”
“韦公子,相逢即是有缘,奇缘岂能错过,这三天你好好陪我……”她用男人无法抗拒的异色目光望着韦烈,不能说是“荡媚”,只能形容为“诱惑”,因为她不是一般邪荡的普通女子。
韦烈是男人,男人就应该有反应,但他克制住了。“如何陪法?”
“谈话,喝酒,作乐!”她坦然地说。
“作乐包括什么?”这是重点,他非问不可。
“随兴所至,爱怎么乐就怎么乐。”
“应该有个限度!”
“限度?啊!我明白,你的意思是不上床?”
——个女人谈这处男女之事有如家常便饭,像喝茶吃东西一样平常,实在令人吃惊,当然,这因为韦烈是正派人,换了别的男人如“花间狐”者流,那就另当别论。
“对!”韦烈硬起头皮回答,他想到对这种女人说话不必保守含蓄诸多顾忌,那完全是多余的,而且是白费。
“哟!你要为她守贞?”
韦烈几乎想吐。
“可以这么说。”
“你真是迂腐得可爱,韦公子,美食当前不好好享用一番,宁顾空着肚子,多没意思。”
她越说越不像话,眸子里那股原先包藏的火焰已冒出了头,娇躯也似在振颤,她自己已先煽起了火不可自持。
“在下吃东西一样很挑嘴!”韦烈再无顾忌了。
“你不先尝尝怎知不合口味?错过珍肴多可惜?”
“在下宁错过也不轻尝!”
翠姬坐上床沿,伸手握住韦烈的手,摇动着。
“我们喝几杯,我为你抚琴,如何?”
“敬谢。”
“你是木头人?”
“木头人的传人!”韦烈是将话答话,但却是半真半假,事实上他师父“枯木老人”的另一外号便是“木头人”。
“你说话满风趣的!”柔荑抚上了他的脸、胸……
韦烈用手扒开。
“报告主人!”门外突传声音,是姗姗。
“什么事?”翠姬扭转娇躯对着门。
“楼里发生了怪事!”
“哦!什么怪事!”
“那瓶牡丹露不见了!”
“有这种事?我马上来!”说着,又摸了摸韦烈的脸颊道:“韦公子,可人儿,待会我再来陪你。”说完,起身款摆而去。
“牡丹露?”韦烈自语了一声,忽然想起王雨曾说过“牡丹滴露”这四个字,当时以为她是说的“风话”,想不到真的有牡丹露这玩意。是了,王雨之醉是受制于牡丹露,自己是否也是同样情形?看“神女翠姬”的反应看来,这东西在她心目中必相当珍贵。牡丹露失窃这意味着什么?只“雾里鼠”王道有这本领……
心念未已,忽觉眼一花,似有人影闪入。
果然,王道已站在床前。
“公子,您怎么了?”
“我无法行动!”
“那跟王公子一样!”
“什么,你……见到王公子了?”
“是的,就在隔壁房间,跟公子一样瘫床上。”
“你是怎么来的?”
“我们在对在眼看公子抱着王公子双双沉入树幕,急得不得了,我冒险潜入谷道,先发现吊网和几根上盘的绳索,既而发现半壁间的洞口,我用飞爪索荡过来,胡闯了一通,误打误撞进了王公子被困的地下房间。”
“地下房间?”
“是的,在竹楼之下的山腹里。”
“对!”王道眨眨眼。
“那我现在是在山腹里?”
“那‘牡丹露’怎么回事?”
“是王公子告诉我他是被这捞什子露弄醉的,同时告诉我藏处,所以我就上竹楼把羊顺手牵了来。”
“嗯,牵得好,我一听有人来报牡丹露不见了就猜到一定是你王道上门光顾,你能设法找到解药吗?”
“试试看!”
“好,那你就去吧!”
“我是想……先把公子送出去。”
“不行,我不能用逃的!”
“死要面子!”王道这一声说得很低。
“你说什么?”偏偏韦烈听到了。
“没什么,没说什么,我这就去设法借解药!”王道讪讪地笑了笑,一溜烟般消失在门外,他的确是有几套。
韦烈的心定了下来,他相信王道鬼点子多而且管用。
静静等待。
也只一刻光景,王道去而复返,胸前鼓崩崩的像个怀胎足月的女人,韦烈看了好笑。
“你的肚子怎么了?”
“东西太多,我分辨不出,只好全借了来。”
“嘿,有意思,外面怎么了?”
“我略施小计,够那些娘儿们忙一阵子。”
王道从怀中掏出一个小瓶,递与韦烈。
韦烈接过一看,瓶上有标签,写的是“止血生肌丸”五个古体篆字。
“这上面不是标得有药名吗?”
“这些鬼画符不认识我!”王道咧了咧嘴角。
“不是!”
“好,换一个!”王道收回,另掏出一个。
不停地换,韦烈不停地念——“导气丸、和合丸、止痛丹、接骨散……”到了第九个“解露丸”。“是这个,解露丸,错不了。”
“阿弥陀佛!”王道念了一声佛号,倒一粒放到韦烈的口里。“希望对路,弄错了可不是玩的,这……”
极轻微的声音突传。
“有人来了”韦烈说。
“我的妈,事情还有一半没办完。”王道一头钻入床下。
进门的是“神女翠姬”。
“韦公子,想通了没有?”
“想通了!”
“那好,你一定饿慌了,我要她们备酒。”击了三下掌。
“候命!”声音在门外。
“快备酒,在楼头!”
“遵命!”
“神女翠姬”喜上眉梢,定定地望了韦烈片刻。
“韦公子,怎么想通的?”
“这……也许是芳驾的魅力使然吧?”
“咯咯咯……”笑声是非常悦耳的。
韦烈暗中一试,这解露丸果然神秘,功力已在复归之中,他不敢运功助药力推行,如果露了破绽被这女人识破,就将功亏一篑。”
“我们走吧?”翠姬靠近床。
“要是能走,岂非早已下了床?”
“噢!我倒是忘了!”伸食指在韦烈的“气海穴”上一点。
“现在你可以下床了!”说着,把韦烈拉起,扶下床,然后一只手环上他的腰,另只手把他的右臂拉上自己的香肩。“我们上楼去。”
两人搂着走,俨然一对如胶似漆的新婚夫妇。
体香,脂粉香薰得韦烈有些晕陶陶。
出了门,是条甬道,有灯照明,石级在尽头处。一列四个房间,韦烈特别瞄了一眼隔邻这间紧闭的房门,照王道的说法,王雨就在里面,他压抑住冲动,乖乖地让翠姬搂着走,现在还不到采取行动的时候。
到了甬道尽处,登上石级。
石级尽处的出口连着木梯,四边用排竹围住,从外面看绝对看不出来。爬完木梯是一间还算考究的卧房,出房门便是楼头的客厅了。酒菜已摆整舒齐,画烛高烧,竹帘之外一片黑,原来已是晚上。
扶着韦烈坐下,成了并排。
姗姗斟上酒。
翠姬环在韦烈腰间的左臂还舍不得移开,仿佛两人已经连了体,这情景如果有外人在侧,连骨头都会发麻。
韦烈已默察出禁制全解。
不吃白不吃,反正是真的饿了。
“先干一杯!”翠姬右手举杯。
“请!”韦烈也举杯,但他的右手恰在中间,而她又搂得死紧,这一端杯子,无可避免地便碰上了丰盈的酥胸,他的心弦不由一颤。
这是喝交杯酒吗?
翠姬以为韦烈已臣服在他的石榴裙下,他阅人无数,但像韦烈这种特级品她还是头一次碰上,心里那分兴头就不待言了,眸子里所表现的那份贪婪,似乎想把他一泡口水吞到肚子里去。她夹菜,直喂到韦烈口里。
“韦公子,你愿陪我一醉吗?”
“当然,喝酒不醉,焉能尽兴,不过……”
“不过什么?”
“如果在下醉成王公子那样子,岂非大杀风景?”
“哦!”这一声哦既悠且长。“绝对不会,我也不愿意抱一个醉汉,那完全不是味道,我要你生龙活虎。”
“我现在这样能生龙活虎?”
“到时候我自有道理,喝呀!”
“来,喝!”
韦烈在等机会,同时也要给王道办事的时间,故而虚与委蛇,其实对方的表现已足令他作呕三日。
气氛似乎很融洽。
翠姬色迷心窍已失去戒心。
“姗姗,你下去歇着吧,这里不需你伺候了!”
“是!”姗姗狠盯了韦烈一眼才转身退下。
翠姬愈来愈放浪,韦烈完全不动手,洒菜全自动送到口里。
气氛步步升高,已到了狂荡的程度。
翠姬满含了一口酒,凑向韦烈的嘴,她要度酒,双手改抱脖子,人整个贴在韦烈的身上。
嘴已对嘴。
韦烈当然不会喝这口酒,双手并食中二指朝她的背后用力疾点,他是存心要这女人多躺几个时辰。
酒喷了韦烈一脸,人瘫痪,但双眼圆睁,她做梦也想不到韦烈会突然来这一手,心里无防,点得很结实。
韦烈把她摆趴桌上。
“翠姬,算武林辈份你是前辈,在下真不好意思得罪,但事出无奈,你就委曲一点吧!”
他说完起身准备离开,一想不妥,如果被她的手下发觉,难免要动干戈。这事件从头到尾没伤过人,又何必留一条不愉快的尾巴。
左右瞻顾之后,他把她抱起,送到房里床上,用被盖好,朝里闩上门,灭了灯光,然后依来时路快速奔下去。
原先判断是王雨被留置的房间门已洞开,里面没人。
韦烈知道人已随王道离去,于是急急找到出口,特别带了盏壁灯从容地步了出去。到了洞口边缘,把灯放在地上,这也等于是一个号志。抬头望去,一张巨网停在涧谷中央,不见王道的影子。
“公子!”声音从身后传来。
韦烈侧身靠壁,王道已出现身前。
“王公子人呢?”
“在对过上边等公子。”
“他没事了?”
“完全正常,只放心不下公子。”
“你又进去了?”
“是呀!要是公子真的跟那娘儿们上了床,没个人提醒,那岂不糟糕?”他说完,耸肩笑笑,他的嘴是怎么也省不了的。
“胡说!”韦烈脸上发热,他想到酒桌上的奇形怪态,多份已完全入了王道之眼。
“公子!”王道开玩笑是有限度的,对韦烈他不敢太放肆,忙改变话题。“等那娘儿们醒来,发现她凭以对付男人的那些宝贝瓶子全部失踪,不气了上吊才怪!”王道竟然笑出了声,似乎非常欣赏自己的杰作。
“闲话少说,我们快离开!”
“是。”
王道甩出飞爪索,只一下便扣牢在巨网边缘上端的一根横枝上,用手拉了拉证实已经扣牢,这才把索头交到韦烈的手上。
“公子,您先过去。”
韦烈手执飞索,拉紧,后挫,双脚一用力,人便标了过去,抓牢壁间树干,松手,飞索荡了回去。
就在此刻,三名少女出现王道身后。
韦烈心头一紧,想不到她们这么快便发现。
三名少女同时疾扑王道。
“我的妈呀!”王道怪叫一声,返身应战。
三名少女身手煞是不弱,加上洞口地方狭窄,只几个照面,王道便已手忙脚乱,而三名少女攻势更紧,只消把王道迫落谷中,目的便已达到。
飞索荡了两个便静止垂在中央,距洞口有三四丈。
韦烈大急,正待采取行动……
王道的武功并不高明,对付普通高手还可以,碰上一流好手他便要吃亏了,但他有他的一套,只见他几招快式之后,抓住一丝丝空档,人标起,抓住悬空两丈远的网缘,喘息了一下,飞扑那根飞爪索。
暗器密集射到,他正好离开网缘,同时也抓住了飞索,他不能荡,因为在空中来回一荡便成了活靶。他抓住飞索之后,立即下滑,沉下暗中,这样对方便失去了目标。
韦烈仍很紧张,他帮不了忙。
飞索开始摆动。
“割断索子!”一个女的大叫。
飞刀旋出,飞索立断,只剩下一小段索头虚悬着。
“王道休矣!”韦烈脱口叫了出来。
现在是在树帽之下,上面的根本看不到下面的情况。
韦烈起了杀机,他准备利用那张巨网,飞回去大开杀戒替王道报仇。
“沙!沙!”声中,有人顺山壁攀爬的声音。
“王道!”韦烈低头叫唤了一声。
“公子,我没事,只可惜那条飞索。”声音不远。
韦烈大喜过望。
洞口的三名女子退回洞中,同时携走了灯笼。
远近变成一般黑。
“公子!”王道已攀到韦烈身边。
“我在这里!”韦烈伸出手。
两人已在一道。
“好险!”王道喘口气。“一发之差便得永远躺在谷底安息了。”
“总算大家平安,我们上去。”
登上涧边,苦等的拍手欢呼,他们当然不知道两人经历了生死一发的凶险。
“韦兄,都是小弟闯的祸,抱歉之至!”王雨作揖。
“老弟!”韦烈已经知道王雨是易钗而弁,心里难免有些怪怪的,但他尽量保持常态,上前握住他的手。“不经一事,不长一智,祸福本是无常的。”
“神女翠姬怎样了?”
“够她休息一个长时间。”
“韦兄伤了她?”
“没有,只是送了她两指头而已!”吐口气又道:“怎么,老弟对她还有些依恋不舍?”
韦烈头一次开玩笑。
“不,不是这意思!”天黑,看不见他是否脸红。“小弟的意思是她将来可能会报复,她不会甘心的。”
“以后的事现在不必烦,我们走!”
垣曲。
客店里。
“梅花剑客”方一平在房里不安地踱步,由于他觉察出师父司马长啸已对他起疑,要是所有的案件全部爆发将是死路一条,他离开凌云山庄之后便不敢再回去,亟思有所突破,但一时之间想不出可行之路。
而最令他感到心神不宁的是那晚在山庄里发生疑似司马茜鬼魂现身的那一幕,他素来不信鬼神,但又无法解释这古怪的现象,这阴影一直压在他的心头。再就是“武林公子”韦烈一定会找他算帐,他不知该如何应付?
夜已深,人已静。
方一平了无睡意,仍在房间里打转。
“咯咯!”有人叩门。
方一平大为紧张。
“外面是谁?”
“方老弟,是我!”
方一平听出是“鬼算盘”冷无忌的声音,大为意外,他不告而别,等于是出卖合伙人,怎会自动找上门来?
打开房门,来的果然是“鬼算盘”。
“冷先生……”
“还是叫老哥吧!”
“好,老哥请进!”
“鬼算盘”入房,门只关上,双方坐定。
方一平连转了无数个念头。
“老哥此来必有指教?”
“有件事先加以说明,不久前因为会坛里发生了一件大事,老哥我奉召漏夜兼程赶回去,来不及通知老弟,希望老弟不要见怪。”
“那里话,小弟也不断在想,老哥定是因了什么不得已之事才不告而别,果然被小弟料中,说明也就没事!”方一平当然不会相信这只老狐狸的话,但不想撕破脸,彼此维持现状是最好不过的事。
“言归正传,老哥我对任何事都是信守不渝的。”
“这……小弟知道。”方一平不知对方的用意,更听不懂这句没头没尾的话,但他虚应着,心里在提防。
“记得我们三人共同的目标吗?”
“共同目标?哦!记得,当然记得,宝镜……”
“对,‘宝镜’已经在老哥我身上。”
方一平两眼突然瞪大。
“老哥已经得手?”
“不错,老弟很意外吧?其实这是机会问题,只要机会来临,略施小计便手到拿来!”
他没说什么小计。
“是,小弟绝对相信老哥的能耐!”方一平专拣好听的说,心里却在疾转念头,因为这也等于是他自己的机会。
“我们是三人行,谁得手也不能独占!”
“是!”方一平忖不透对方的心理。凭“鬼算盘”的为人作风,绝对不会是讲义气的人,此举必有用意。
“另外,老哥我最初向老弟的准岳丈司马庄主提供线索之时,曾要求过一旦得了宝藏,只求分一杯羹,所以老哥我准备把‘宝镜’交给老弟,由老弟作主处理最为恰当,不知老弟意下如何?”鬼算盘脸上的神色是诚挚的。
“这……”方一平不由喜出望外,这简直是磕头碰着天,想也想不到的事。当年曾经掀起武林血腥风雨的宝物,竟然乖乖送到自己手上,谁敢相信?但他表面上丝毫不动声色,因为他对“鬼算盘”有戒心,天底下那有这么便宜的事。
“怎么?老弟不接受?”
“小弟只是不明白,为什么要由小弟处理?”
“因为你是凌云山庄的乘龙快婿,你的泰山大人最先接受这建议的,由你处理最合适不过。”鬼算盘一脸至诚。
“可是……”
“可是什么?老弟一向明快果决……”
“老哥还有什么附带条件?”
“没有,一切如当初与司马庄主的约定。”
“好吧,小弟会好好处理。”
“鬼算盘”果然爽快地掏出“宝镜”交与方一平。
方一平兴奋得身麻手抖,反复看了好几遍然后才揣入怀中,到手才算功名,现在这宝物是属于他的了,仿佛是梦,但又那么真实,他想:“鬼算盘来这一手,多半是想到匹夫无罪怀璧其罪,自己无力保有,不如坐等分肥。”
“老哥如此信任小弟?”“如果不信任,当初就不会合作。”
“小弟荣幸之至。”
“我该走了,以防隔墙有耳。”
“以后如何联络。”
“我会找你。”
“好吧!”
“鬼算盘”出房离去。
方一平用手按了按胸间,很想大笑一场,这福运是平空飞,来的,他关紧房门,坐在床边想,忽然发觉不对,“鬼算盘”是“大刀会”总管,他出来的任务便是谋取这面宝镜,他不带回去呈献会主反而交给了自己,这是为什么?
怎么想也想不透其中道理。
突地,灵机一动,想到了一步绝棋,他笑了,非常开心的笑,脱口自语道:“这叫两全其美,不必担负任何风险,自己也有了安身亡命之所。”
人。太得意便会忘形,再聪明的人也不例外。
方一平步到桌边,掏出“宝镜”就灯下细看,镜面上是圆,刻上去的,有山有水有道路就是没有标明名称,也没特殊的记号,有句古话说“按图索骥”,像这种图如何按起,山水道路无处无之,如何对照,不由大为气沮。
“宝镜到底宝在何处?”
如果当初有个捉狭鬼故弄玄虚,放出流言,那真是骗惨了武林天下。
镜就灯,自然就会产生反光,但方一平没察觉这点。
“咯咯咯!”房门叩响。
人,一旦保有了某种秘密便会特别敏感,方一平的心猛跳起来,忙不迭地收起宝镜,回身抓剑在手。
“什么人?”
“是我,龙生!”
“哦,原来是龙兄。”心里电转着念头,冷无忌刚走龙生便来,如果是冷无忌玩的把戏,这就有得瞧了。
房门打开,“花间狐”龙生进房,方一平再关上门。
“方老弟,久违了。”
“是很久没见了,请坐下再谈。”方一平面带笑容。
“花间狐”落座。
方一平强作镇定。
“龙兄深夜光临,必有要事?”他是心虚。
“要事谈不上,只是顺道造访。”
“香妃姑娘好吗?”
“还好,我进店之时,见一个人匆匆离去,背影和行动的姿态极熟,事后才想起是冷无忌,可惜人已不知去向,追也无从追起,他是来找老弟的?”
“是的!”方一平不敢隐瞒,因为“花间狐”来意不明,如果撒了谎就会砸锅,但一颗心在怦怦跳。
“他对不告而别的行为有所解释吗?”
“有,他就是为此而来!”
“他怎么说?”
“他说他们会里发生了大事,被急令召回,没机会通知我们,他为此谢罪。”
“哼!”花间狐撇了撇嘴。
这一声冷哼,使得方一平震动了一下。
“龙兄怎么啦?”
“方老弟,你受骗了,冷无忌的一切作为我查得一清二楚他以你老弟未婚妻的生命和毁韦烈亡妻之墓为要挟,骗得了‘宝镜图’,为了想独吞,所以不告而别,还谋杀了他的副手宋世珍,而宋世珍又是大刀会主的宠信人,明白地说,是她的面首,因此,好几方面的人都要得他而甘心,如果老弟再跟他来往,可能会招来无妄之灾。”
这一席话使得方一平心惊肉跳,但他因此线索又有了新的打算。
“有这等事?小弟我……还被蒙在鼓里。”
“冷无忌就只是为了解释误会冒险来找老弟?”
“是!”方一平应得很勉强,他无法猜测“花间狐”是什么用心。“照龙兄的说法,他说的全是谎言?”
“不错,他定然另有居心。”
方一平在考虑该不该说实话。
“花间狐”紧盯着他。
方一平考虑了一阵之后,觉得还是以不说为妙,一说出来,不知有多少想染指“宝镜图”
的人要找上自己,同时自己的计划也将告吹。眼前的“花间狐”如果有什么不轨的意图自己还能应付得了。问题一想通,心结也就解开了。
“龙兄,这么说冷无忌是在玩弄我们?”
“可以说是。”
“依龙兄的看法,他会有什么企图?”
“很难说,等他有进一步的行动时就可以看出端倪,鬼算盘一生使诈玩诡,心情很难捉摸。”花间狐在虚应故事,对于玲苓受害以及冷无忌窃走“骷髅令”一节绝口不提,他现在的立场已经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
“我们如何对付?”方一平一再用“我们”二字,是想扣住“花间狐”跟自己同一阵线,至于冷无忌,他的看法不一样,介于信与不信之间。
“小心提防!”花间狐这句话说了等于没说,谁不知道对玩阴的敌人要小心提防,这与少喝两杯便不会醉一样空泛。
方一平何等样人,他当然感觉出对方言不由衷。
“是,目前也只能如此!”方一平也同样在应付。
“有个消息要告诉老弟……”
“什么消息?”
“韦烈已经回到垣曲,你我都是他要找的对象。”
方一平脸色变了变,心里立刻开始打鼓,如果被韦烈逮到,毫无疑问会死得很惨,他暗自一挫牙,决定马上实行自己原定的计划。凡是有心机的人,也就是最怕死的人,所以把保护自己摆在算计别人之前。
“还有一个令人头疼的跟他随行。”花间狐又加了句。
“哦!是谁?”
“从南方来的,叫‘多事书生’王雨,相当难缠。”
“多事书生……小弟认识,他怎会跟韦烈一道?”
“也许是投契吧?”起身。“方老弟,夜已深,我该走了,改天我们再欢叙。”
“那小弟就不留了。”
“你我弟兄,不须客套。”
“花间狐”告辞离去。
方一平的脸色沉了下来,眉头皱起,思索了一阵,咬牙自语道:“我得马上离开垣曲,别等火烧眉毛。”立即整装佩剑,把一锭银子放在桌上,灭了灯火,出房迳去。
约莫半刻光景,一条人影悄没声息来到房门之外。
“方一平,久违了!”
没有应声。
房门被推开,人影闪在侧边,过了一会仍无动静,人影进入房中,燃亮灯,这时可以看出来的赫然是韦烈。
一看房里的情形,证明已经人去房空。
“好狡猾的家伙!”韦烈愤愤地说。“他怎么会连夜开溜,难道他从‘花间狐’的身上看出了什么破锭?”
人既已遁走,说什么都是空的。”
韦烈只好悻悻地离开。
|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