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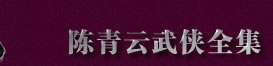 |
|
 |
|
 |
| |
|
第十一章 仁心赐药
|
|
垣曲。
城北汪翰林府,是一栋废宅,“鬼脸罗刹”暂时借住栖身,她怕住客店会有诸多不便,在此完全不受干扰。
“鬼脸罗刹”守护着状颊白痴的儿媳玲苓,她在等儿子龙生求药回来,这本来是毫无把握的事,因为“神农夫人”出现太行山只是一种传言,就算传言是实,偌大山区找一个隐匿潜居的人,也属大海捞针,但还是一线希望,她一向不信鬼神,但现在她不断念佛,希望菩萨保佑,但求得解药使玲苓复原。
呆呆地望着玲苓,她似乎也成了白痴。
“娘!”一声呼唤,儿子已出现眼前。
“你……回来了,怎么样?”
“皇天不负若心人,药求到了!”
“啊!”鬼脸罗刹喜极而双眼潮红。“谢天谢地谢菩萨,龙生,你辛苦了。”
“娘,孩儿一点也不累!”他上前抚了抚玲苓。“你就要复原了,玲苓,你就要好了,可怜的玲苓!”
玲苓对着他傻笑。
“龙生,你是怎么找到‘神农夫人’的?”
“说来话长,先看药灵不灵!”说完,掏出小瓷瓶,倒出仅有的一粒珍贵药丸,倒了杯温开水,服侍玲苓吞下,然后把她放平睡倒。
静候着等待变化。
这时刻,一分有一年长。
逐渐,玲苓木木然的眼珠有了光,转动着,然后她坐了起来,惊愕地张望,一脸茫然。
“我……我……”
“玲苓!”鬼脸罗刹一把将她搂住,泪水长淌而下。
“娘,龙哥,我……好像在做梦……”
“你是在做梦,一个很长的噩梦。”花间狐含泪带笑。“玲苓,你想想,在王屋客店冷无忌对你做了什么?”
“冷无忌……”玲苓苦苦思索了—阵,突地双睛一亮。“我想起来了,我在客店房中等你,小二送来一壶热茶,替我倒了一杯,我喝了,不久便感到一阵头晕目眩,我上了床,接着冷无忌出现,我发觉情况不对,想挣扎起已经力不从心,冷无忌得意地大笑,之后,我便什么都不知道了,我记得的只这些。”
“跟我所料的一样!”
“这到底……”
“冷无忌给你服下当初方一平对付司马茜的迷药。”
“啊!”玲苓目瞪口呆。
“玲苓,现在一切都过去了,我求到了解药。”
“怎么求到的?”
“好,现在我说求药的经过。”花间狐把太行山找“神农夫人”求解药的经过从头一一叙述……
说到紧张之处,玲苓紧抱“鬼脸罗刹”。
最后余述到韦烈甘为人质一节,“鬼脸罗刹”表现出无比地激动,而玲苓则是泪光晶莹。
“鬼脸罗刹”心里明白韦烈为什么这样做,而玲苓更深受感动,因为双方原本是水火不容的对手,感动之余是极度地困惑。
“韦烈为什么要这么做。”玲苓忍不住发问。
“我也不知道,当时又不便问他,他这样做一定有他的理由,我想……将来会明白的。”
花间狐只好如此回答,然后话题一转。“娘,您要去赴约?”
“鬼脸罗刹”沉默了许多。
“娘!”花间狐大为发急。“您不去,那韦烈怎么办?他是自愿做人质的,‘神农夫人’的个性……”
“龙生,你去!”
“娘,您……这是什么意嗯?我去……那不是等于多陪上一条命吗?当然,我不在乎生死,可是韦烈何辜?这不是太不公平吗?娘,我真不明白您如此做是什么原因,您不去……
对方难道不会找上门。”
玲苓起身下床,不知说什么好,只是发愣。
“她不会找上门,也不会杀韦烈。”鬼脸罗刹很平静地说。
“怎么会?”花间狐错愕莫名。
“等你上路时我会告诉你。”
“花间狐”深深吐了口气,脸上仍是茫然。
第五天,“神农夫人”的最后期限,单独在大厅里约见韦烈。
“韦烈,今天是你该提出答覆的最后期限。”
“在下知道。”韦烈已经打好了主意。
“这几天来,你跟谷兰每日相处,对她应该多少有些了解,你对她的看法如何?”神农夫人温和地说。
“很难得的女子,人品才艺都是第一流的。”
“你愿意答应这门亲事?”
“不能!”
“神农夫人”容色大变,这答覆大大出她意料之外。
“为何不能答应?”声调已变冷峻。
“夫人,在下丧偶才一年,一夜夫妻百世恩,夫妻有夫妻的义,心伤未愈,不适于谈喜事,请夫人体谅。”
“尽夫妻之义,一年已经足够,你这分明是遁辞。”
“夫人,这是不能勉强的。”韦烈保持冷静。
“你的意思是不喜欢谷兰?”神农夫人脸色很可怕。
“在下没这么说。”
“强辩,你忘了你在此的身分?”
“在下不敢忘,是人质。”
“如果蓝文瑛不履约,你知道是什么后果?”
“在下既然自愿留下,便不计较这些。”
就在此刻,谷兰突然传入声音。
“师父,龙生到。”
“她娘蓝文瑛呢?”
“没有,只龙生一个人。”
“好哇!”神农夫人怒冲冲地站起身来。“人呢?”
“在外面。”
“神农夫人”大步而出。
韦烈也起身跟了出去,心里在想:“师母为何不来,是怕吗?可是她叫师兄龙生来,难道不关心他的生死?莫非师母想到师兄弟联手足可对付‘神农夫人’,但这并非解决问题之道,而且师母也该想到对方是用药圣手,武功并不足恃,她为什么要如此做?自己又该如何应付?”心念之中,已经到了屋外空地。
双方已经面对面,谷兰站在一侧。
“花间狐”很镇定的样子,他何所恃令人猜不透。
韦烈停身在两丈之外,他不能轻率地插手,因为他的立场,是第三者。
谷兰望了韦烈一眼,脸上的表情很不自然。
韦烈只作没看到,两眼注定前方。
“龙生,你一个人来?”神农夫人声音森冷。
“是的。”花间狐意态从容。
“你娘竟然敢不来?”
“她不必来。”
“她准备牺牲儿子保自己的命?”
“没这么严重!”
“好,你就看看到底严不严重!”神农夫人前趋两步,右手扬了起来。
“夫人!”韦烈飘身上前。“暂请息怒,让这位朋友把话交代明白,他如此做必有他的理由,如果他娘有意规避,母子可远走高飞,何必要龙朋友自投罗网?”这几句话情在理中,再不讲理的人也非听不可。
“神农夫人”手放了下来,转回。
“韦烈,你逞能插手,这事你也有份?”
“当然,在下绝不逃避!”
“哼!”神农夫人重重地哼了一声,转回面。“好,现在你说,你凭恃的是什么?”
“没什么,只是一句话。”
“什么一句话?”
“夫人无妨问一下韦烈的出身。”
韦烈心头“咚”地一震,这是什么意思,难道要藉师父的名头压对方吗?不对,师母不会作这种事……
“神农夫人”倒是被这句莫名其妙的话弄得一愣。
“韦烈的出身与此事有何关联?”
“关联大了,夫人一听就明白。”
韦烈眉头皱紧,为什么要问自己的出身,难道双方之间的过节与师门有关?自己说出了师承就能化解干戈吗?五天前“神农夫人”曾问过自己的师承门户,被自己婉拒了,现在该不该说呢?心念之中,他望了“花间狐”一眼,当然,什么也望不出来,看“花间狐”的样子似乎非常笃定,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谷兰幽幽地道:“师父,您就问问嘛!”
“神农夫人”转向韦烈。
“韦烈,你说?”
“这……”韦烈迟疑了一下,看样子是非说不可,这是师母安排的,必有用意。“先师‘枯木老人’!”
“神农夫人”脸色剧变。
“你……你是‘木头人’的传人?”
“不错。”
“你刚才说……先师!”
“是的,他老人家业已辞世。”
“神农夫人”面孔扭曲,扭成的怪形僵化在脸上,那样子实在怕人,她为什么如此激动?
在场的全愕住了。
空气一下子沉寂下来。
许久,许久……
“他为什么会死?”神农夫人栗叫。
人,寿数到了,总会走上这条路的,谁也没接腔。
“我好恨!”神农夫人切齿。
她恨什么?这似乎牵扯到了儿女之情。
“韦烈,他怎么死的?”
“坐化!”
“葬在什么地方?”
韦烈这下可就不敢轻率出言了,如果仇怨是种因于师父,这女怪人要是去惊扰了遗蜕的话,自己可就百死莫赎了。
“为什么不说话?”
“夫人为何要问先师安息之地?”他反问。
“老身……要知道。”
“死者为大,不容惊扰。”
“你……在胡说什么?”
“韦兄!”花间狐开口:“告诉她!”
韦列又想了想。
“在王屋山一座峰头的石窟之中,也是他老人家幽凄了二十多年的地方,石窟已经封闭,没有任何记号。”韦烈只好实说了,但还是保留了部分。他没说出确切地点。
“他……竟然藏在王屋山中,老身……”下面的话没说出口。“韦烈,老身问你,为何要诡言欺骗老身?”
“在下没有。”
“那你说你跟他没任何关系?”
“事实是如此,在这一刻之前,是无关系可言,夫人可以问龙生,他知道吗?”韦烈振振有辞地说。
“你自己也不知道。”
“知道一点,是不久前师母相告的。”
“花间狐”望了韦烈一眼,要不是发生这件事,他根本不知道韦烈是他的师弟,也不知生父是谁。
“那你来不是巧合,是蓄意的?”神农夫人的确厉害,一点细情末节都不放过。
“是巧合,因为在下此来是为了搜找冷无忌,无意中发现了龙生,一念好奇跟了来,并不知道他来此的目的,他也不知道在下的身份。”
“神农夫人”举首向天。
空气又告沉寂。
韦烈心中不无忐忑,他不知道会起什么变化。
谷兰的眸光射向韦烈,但却是困惑的。
“你们滚!快滚!”神农夫人挥手厉叫。
这似乎就是结局,最好的收场。
韦烈与“花间狐”互望了一眼。
“告辞!”韦烈大礼不失地抱了抱拳。
“敬谢前辈宽宏大量,晚辈谢过!”花间狐也抱了抱拳。
两人转身奔向峰脚方向,为的是避开“散功草”。
“韦烈,你回来!”神农夫人大叫一声。
韦烈一震停身,莫非这女怪人又改变了主意?只好硬起头皮回到原地。
“夫人还有什么指教?”韦烈正视神农夫人”。
“方才在里边跟你谈的问题还没结果。”
“夫人要什么结果?”
“答应还是不答应,老身不喜欢模棱两可。”因为谷兰在旁边,所以“神农夫人”说话便十分含蓄。
“夫人,在下已经奉明目前不想谈这问题。”韦烈感到万分无奈,对方竟然不放过这问题。就事论事,谷兰的确是个好女孩,而“神农夫人”也是一番美意,可是这种问题能轻率答应吗?何况小青、小茜姐妹双双不幸,悲痛仍在心头,这问题自己连想都不会想。
“那以后呢?”神农夫人紧迫不放。
“以后是以后的事。”韦烈不顾失礼。
“好,你听着,老身一向言出不改,老身就等你的以后,如果你背信而另作别的打算,老身不会放过你。”
韦烈有些哭笑不得,没有诺言,何来背信?
“夫人说‘背信’二字不嫌太重了吗?”
“别跟老身哓舌,你心里明白。”
韦烈喘口气,他不想作无谓的争辩,故意转面向谷兰道:“谷姑娘,五天来蒙你殷切招待,在下十分感激,如果有机会再见,在下会酬这份人情。”
谷兰含情脉脉地道:“韦公子,我想……我们会再见的,到时我一定会领你的情。”这是话中有话。
韦烈顿时失悔自己这步棋下错了,本意是藉此打断“神农夫人”的话,不料弄巧成拙,谷兰把“人情”二字当成了男女之间的“情”,看来以后的麻烦大了。小茜之死,使他心里的影子幻灭,但却为另一个影子取代,那便是驼峰石屋的冷玉霜,虽然这影子很模糊,他没认真捕捉过,但终究一个影子。
“神农夫人”摆手道:“你可以走了!”
韦烈抱了抱拳,先朝“神农夫人”,然后转向谷兰,什么也没有说,转身起步,奔向尚在峰脚边等候的“花间狐”龙生,两人双双向外奔去。
出了谷,两人奔势缓一下来。
“我该……怎么称呼你?”龙生问。
“师母已经把一切告诉了你?”
“是的。”
“那我该称你师兄,你叫我师弟,名正言顺。”
“太好了!”龙生的喜悦发自内心,他怎么也估不到会有这么——个了不起的现成师弟,这实在是渊薮。
“师兄,关于师父他老人家的来路……”
“娘就是没告诉我这一点,说是还不到公开的时候,我正想问你,难道说你跟了先父这么多年竟不和他老人家的来路?”
“他老人家绝口没提。”韦烈苦笑。
“这倒是怪,不过……反正迟早会知道的旷师弟,我们这就出山回垣曲吗?”
“不,我要留下继续搜寻‘鬼算盘’!”
“那……我也留下。”
“师兄,你最好先回去,以免师母悬念,她老人家一定在急着知道你此行的结果。”韦烈很认真地说。
“花间狐”深深想了想,点头。
“好,我先回去。”
“对了,师兄,师母这着棋是根据什么下的?”
“娘没说,只叮嘱我照她的话说十有八九会改变情势。”话锋一顿又道:“如果她亲自来,很可能问题不能解决,反而演变成不可收拾之局。当然,我此来多少有些冒险的成分,因为‘神农夫人’生性古怪,心意难测,现在总算是风停雨住了。”
“很好的收场!”韦烈感慨地说。
“师弟,冷无忌真的骗走了你的‘宝镜?”“是真的,不然他当场就反驳了。他以司马茜的生命和毁你弟妹小青的墓为要挟,人没出面,也没拉明他是谁,只留字勒索,我不得已,只好照他的话做,是事后才从各种迹象判断出是他所为。”
“好,我先走一步赶回去,说不定这老邪又潜回垣曲一带,那边由我负责查探。”偏头想想又道:“我有个建议,我们之间的关系暂时保密,不公之江湖,仍各自维持以前的身分,办起事来会方便很多。”
“很好,我也正有此意。”
“那我们兄弟后会有期了!”
“师兄请便。”
“花间狐”展开身法,快速奔去。
韦烈摇头笑笑,天下的事可真难说,他最不齿的武林败类竟然是自己的师弟,如果当初一怒而杀了他,这笔帐该怎么算?其结果又是什么?
突地,他想到了“多事书生”王雨,王雨具有神通,自己又何必在太行山中苦苦搜查“鬼算盘”的踪迹,请王雨施展神通,找起人来不就方便多了。转念一想,又觉得不对,王雨既然具备神通,为什么不施展神通岂不手到擒来,而现在连他本人在内,都在盲目搜寻,看来此中必有文章,他是负责山外地区的,何不找到他把这问题弄明白?
心念之中,也朝山外奔去。
官道,由于位近山区,所以显得十分荒凉。
“多事书生”王雨和两名书僮正行走在这一段荒凉的官道上,一边是崇山峻岭,一边是半开发的村野,由于主仆三人的装扮太高贵,又没骑没乘,走在这种地段自然会引起过路者的注意与惊怪。
走着走着,王雨突然停了下来。
“公子,怎么啦?”立仁问。
“你看这里的景色多幽美!”王雨手指山边。
山边,林木苍翠,山泉倒挂,淙淙之声不绝于耳,一条羊肠小道顺涧而上,蜿蜒在林木中,极目上望,白云悠悠出没在山蚰之间,还加上虫鸣鸟叫的乐章。
“的确是一幅天然的图画!”立义附和着说。
“我们上去看看!”王雨兴致勃勃。
“公子,我们是在找人?”立仁说。
“人在那里?反正我们是瞎撞,碰上算数。”
“上去吧!”立义又附和。
于是,三人顺小道向上升登。
约莫两刻光景,到了峰头,只见山外有,山,谷里套谷,一片浑然雄伟,这座峰头只是最外缘的一个起点而已,环峰白云仍在头顶,看似很近,其实尚远,这小峰头和主峰被一条深涧涧隔断,茂密的林木掩盖,不知有多深。
三人站在涧边。
突地,一阵悠扬的琴声隔涧传来,音韵之美简直难以形容,如白云无心出岫,飘逸卷舒,又如春风拂柳,令人心怡神旷。不久,琴声一折,缠绵得像春蚕吐丝,柔蜿无尽,又若夜半私语,引人遐思。琴声再折,变为清泉过石,群鸟迎春,轻快中充满了愉悦。
王雨听得痴了。
“怪事,这种地方居然有人弹琴!”立仁幽幽地说。
“抚琴的必是高人雅士。”立义晃着头。
“是女人!”王雨接上口。
“公子怎知是女人?”立义问。
“你听不出这是凤求凰之曲?”
“哦!难怪这么感人!”
“公子,对面……林子里似有人家?”
“是一栋竹楼,楼里住的必是一位美女!”
“如果是无监嫫母呢?”立仁比较不那么温驯。
“光恁这高超的琴艺,纵是无监我也要会她一会,箫来!”
随说,随在涧边坐了下去。
立义从背囊里取出一支玉箫,双手递过。
王雨接过凑在嘴边试了试音,然后吹奏起来,吹的同一曲调,袅袅箫声配合着幽咽琴声,简直就是仙音。
立仁和立义也听得痴迷了。
琴声一断,箫声随止。
“我要去会会她!”王雨站起身来。“你俩在这边候着!”说完,一鹤冲天而起,然后如飞燕掠进绿波,踏着覆涧的树帽,轻盈地飘飞过去,投入了苍松翠竹之中。
浓绿里,果然是一座竹木搭建的楼房,回廊曲槛,精雕细筑,配上碧绿的窗纱,人已和大自然已融为一体。
“胜地幽居,仙境奇葩!”王雨赞叹了一声。
“什么人?”一个青衣少女出现楼栏。
“在下王雨,是被琴声召来的!”
“召来?谁召你了?你就是刚才吹箫之人?”
“不错,献丑了!”
“你来做什么?”
“想见见你家小姐。”
“咕!”少女掩了下口。“这里没有小姐。”
“那就见主人吧!”
“你好大胆,竟然敢闯了来。”
“琴音太美,情不自禁!”
青衣少女转身入内,不久又重现,向王雨招招手道:“我家主人破格见你,你上来。”
王雨登上扶梯,来到楼栏,青衣少女打起湘帘。
竹楼小厅,窗明几净,纤尘不染,壁上挂了数幅名家字画,桌椅全都是木面竹脚,别有一番雅致。
“多事书生王雨蒙主人破格延见,荣幸之至。”说完,步入厅中,这时才看到侧方有张凉榻,榻上有几,几上有琴,一个女人背影在几后,是背对门而坐,如云秀发直垂到腰际,穿的是宫装,榻侧高脚几上还燃着炉香。
“看座!”声音很脆,听不出多大年龄。
“请坐!”青衣少女扶了扶旁边座位。
“谢座!”王雨坐了下去。
满室氤氲,那炉香是极品沉香,沁鼻清神。
“你刚才自报多事书生?”
“是的。”
“来此多事,还是多事来此?”这话问得很妙。
“小号原多事,非为多事来!”回答得更妙。
“王公子箫艺不俗!”
“芳驾琴艺更佳。”
女的坐姿不改,缓缓磨转身来。
王雨差点惊叫出声,但他还是憋住了。对方竟然是个麻面女,一脸坑坑洞洞还加上雀斑,没眉毛,只两个眉骨突起,不是丑,简直是怪了。一个人如果没有眉毛,那脸相根本就不必形容了,何况还是个麻子。
王雨力持镇定,定睛望着对方,忽然莞尔一笑。
“王公子很失望?”
“在下乃是闻琴声而来,并非因人而至,有什么失望可言。”王雨的声音神色完全自然,一副泰然之色。
“刚才一笑为何?”
“芳驾自知,又何必故问。”
“哈哈哈……”笑声脆得如乳莺出谷,悦耳极了,如果她愿意一直笑下去,听的人绝对不会厌烦,等于是一种享受,可惜她很快就敛住了。王公子,你是个妙人,巴巴地到山中来,这是缘份吗?”
“如果芳驾相信‘缘’之字,这便是缘。”
“我相信,而且非常相信,既是缘来,岂可不志庆一番,姗姗,备酒!”
“是!”叫姗姗的青衣少女笑应一声,退了下去。
现面,四目相对,这女的一个怪脸,但一双眼睛却相当美,一种冶媚的美,足以令人心生悸动,如果配上两道柳叶黛眉,再加上平整的面庞,定然是个尤物,但在王雨的观念里,她已经是尤物了。
“王公子怎会到这荒僻的山区来?”
“寻幽觅胜,增长见闻。”
“寻到了吗?”
“所幸并未落空。”“说得好!”眸光闪了闪,像清风拂过湖面,令人心晨自生涟漪。
“听公子的口音似乎来自南方?”
“小地方,西蜀!”
“啊!天府之国,难怪如此倜傥!”
一阵响动,来着轻笑之声,四五名少女各捧食具酒莱,鱼贯而出,每一个的体态容貌都是一流的。很快就摆整好,少女们退了下去,只留下姗姗一人,笑向王雨道:“公子请入座!”
拉了拉客位的椅子。
女的起身下榻,这时才看出她那丰而不腴的身材,玲珑但稍许夸大的体态,不看脸,简直可以迷死人。
双方入座,姗姗斟上酒。
玉杯牙箸,金盘银匙,再配以精致的菜肴,清醇的酒香,使人几疑是琼宴御席。
“还没请教芳驾的称呼?”
“翠姬!”
“翠姬”两字入耳,王雨心头“砰!”然剧震。
“神女翠姬?”他脱口而出。
“咦!你居然也知道?”翠姬显然很意外。
“是……无意间听说的!”王雨勉强笑笑。
“神女翠姬”可以称为一代女妖,没人知道她确实的年纪,有人在四十年前见过她,隔了二十年再见时,她的丰采丝毫未变,行踪诡异,声名狼藉。她所找的对象都是当代顶尖的年轻貌美好手,缘尽即散,绝不留恋。
“你既然听过我的名号,那我不必再做戏了。”说完,背过脸一阵撕抓,再转过来,已经变成一个美艳绝化的尤物,冶媚之气逼人,看上去年纪绝不超过三十。
王雨目瞪口呆。
“你早已看出我是戴了面具的?”她媚笑着问。
“是的。”
“你是易容行家?”
“谈不上,略通门道而已。”
“来,我们开始庆祝万金难买的缘份!”
王雨在一阵激动之后又泰然下来。
美酒,不但香醇无比,而且入口生津,真的就像传说中的玉液琼浆。此物只应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尝!现在是醇酒、美人、佳肴、奇境一应俱全了。
王雨放量而饮,不知不觉进入了飘飘然之境。
姗姗又添了三次酒。
翠姬已经玉靥泛红,媚眼飞霞,散发出无比的诱惑。
“姗姗,要她们一舞助兴!”翠姬抬了抬手。
“是。”姗姗退到后面。
不久,后面响起了琵筝之声,和着云板节奏。紧接着,四只粉蝶翩舞而出,应着乐声,在座前旋飞起来。
弹的是霓裳羽衣之曲。
四只粉蝶既不着诸裳,也不穿羽衣,只披着一袭轻纱,实际上与裸体无异,诸般妙相毕陈。尤其四少女体态丰盈,臀波乳浪鼓荡在轻纱之间,不是蝶也不是人,是四团烈火在燃烧,可以烧溶铁铸的人,可以使冷血为之沸腾。
王雨先是惊愕,既而平静下来,他只是欣赏舞,并无一丝绮念,脸上的神奇静如止水,这是罕见的定力。
“王公子。如何?”翠姬漫声问。
“很好,旋律美,尤其接近自然。”
“你似乎毫不动心?”
“人体之美是大自然之一种,动心岂不杀了风景?”
“佩服,我头一次见到你这种年轻人。”
舞更急,如群莺乱舞,如百花摇颤,轻纱委地,变成了四个毫无掩饰的光洁胴体,霜肌雪肤,旋动之间令人目眩,说得难听些,是四个妖精在嬉舞。
王雨微笑着,脸色泰然。
“王公子,喝酒?”
“请!”
双方干了照杯,翠姬亲自为王雨斟上。
“王公子是海量!”
“不敢,略能耐酒力而已!”
“可是……我……已经不胜酒力了!”翠姬醉眼朦胧。“啊!好热!”她开始解衣,一件件褪落,最后只剩下一件亵衣,颤巍巍的双峰,挺立在冰肌玉肤里,幽幽体香比酒更能醉人,风情已赤裸裸呈现。
春色满竹楼。
乐声止,四少女捡起薄纱躬身退下。
王雨正视着眼前的火山。
“芳驾不输一朵盛放的牡丹!”
“你不热吗,何不也宽衣?”磁性的声音有极强的吸力,眸子、樱唇、粉颈、酥胸全在冒火,火焰在翻腾。
在这种情况之下而能不动心,白痴也办不到。
但王雨办到了,他连脸色都没变过。
“在下一向畏寒,不怕热!”
“你到底是什么人?”
“人,男人!”
“你不是!”
“那芳驾认为在下是什么?”
“没有血气的木头人!”
“哈哈哈哈,很妙!”王雨干了一杯。
翠姬呆了,呆呆地望着王雨,一条玉臂斜搁桌面,使躯体变成了半倾,一边的玉峰正好搁在桌沿。她为什么忽然发呆,但这姿势却更加地撩人,许久……
“你是有为而来?”
“什么意思?”
“你的反应超乎情理。”翠姬仍保持柔媚。
“芳驾的表现又在情理之中吗?”王雨冷静如恒。
姗姗转了出来。
“姗姗,拿那瓶牡丹露来,我跟王公子醉无休!”
“是!”姗姗以一种古怪的目光望了王雨一眼,到旁边竹柜之中取出了一只玉瓶,小心翼翼地打开,然后在各人杯里斟酒。顿时酒香四溢,沁人鼻孔,教人立感全身舒畅。
“王公子,这酒全是搜集牡丹花上的露水酿成,前后花了十年工夫,没有任何客人值得我开这瓶酒!”
“在下荣幸之至!”
“来,不干杯,慢慢品尝!”
“好,芳驾也正如这牡丹露,是要慢慢品!”
“这话……说得好极了!”翠姬笑了,仿佛春花怒放,骀荡的春风唤起了无边的春意,令人沉醉、沉醉。
牡丹露,香醇馥郁,酒中之酒,但又不像酒。
一杯已尽,又斟上了第二杯。
第二杯喝了一半……
王雨突然感觉翠姬的胴体在扩大,不断地放大,而自己却在缩小,最后,翠姬变成了一个硕大无比的巨型玉雕,把他包住,完全地包住,他意识到自己醉了,一个声音在心里大叫:
“你不能醉!”然而,他还是醉了,胸海已经失去了清明,他开始着急,这一醉后果不堪想象,但醉了就是醉了,事实是改变不了的。
“在下……告辞!”他站起身,但只一半又送了回去。
“王公子,你……还能飞渡涧谷吗?”
“这……”王雨哑口无言。
“既来之,则安之!”翠姬离座。“姗姗,快扶王公子来我房里休息。”
“不……这断乎不……”王雨连开口都乏力了。
姗姗上前扶起王雨,不是扶,是架,王雨的身材瘦小,跟姗姗差不了多少,手臂跨肩一架,很轻松地便架进了房中。
翠姬也跟进了房。
姗姗退出,关上了房门。
房间里传出吃吃地窃笑之声,由于这里的家具都是竹制的,所以也有竹床的“格吱!”
之声。
“啊!”翠姬突然惊叫了一声,然后又“哈!”地笑了一声,自语道:“怪不得我还以为他的定力超凡,原来是这样……太有意思了,哈哈哈……”最后是大笑,笑得站在外面厅里的姗姗一愣一愣。
到底是怎榉,没人知道。
可是,紧接着竹床又发出压挤晃动的声音。
|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