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女人神话在文学中起着重要作用。但它在日常生活的重要性如何?它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人们的习俗和行为?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明确阐述这个神话同现实的关系。
神话有各种各样。这种神话,也就是女人神话,使人类状态的不变方面——即把人类分为两个阶段的“分化”——得到升华,因而是静态神话。它把一种直接体验的,或根据经验概念化的现实,投进柏拉图的观念王国,用一种超时间的、不可改变的、必然的超越理念,来取代事实。价值、意义、认识和经验法则、这个理念是无可置疑的,因为它超出了已知范围:它具有绝对真理。于是。神话思想使唯一的、不变的永恒女性,同现实文人之分散的、偶然的、多样化的存在相对立。如果这一概念的定义同有血有肉的女人的行为发生矛盾,那么有错误的是后者:我们被告知的不是女性气毅是虚假的存在,而是有关女人不具备女性气质。面对这一神话,相反的经验事实是无能为力的。不过,它在某种意义上来源于经验。所以女人的确是和男人不一样的,这种相异性在欲望、拥抱和爱情中可以直接感受到。但是,真正的两性关系是具有相互性的关系,这样它才能产生名副其实的戏剧。由于性行为、爱情和友谊,以及替换它们的欺骗、仇恨和竞争,这种关系是都想成为主要者的有意识的人们之间的一场斗争,是彼此确认自由的自由人的相互承认,是从反感到参与的不明确转变。提出女人问题就是提出绝对他者问题,而绝对他者不具备相互性,对她做主体、做人的同类的所有体验都采取否定态度。
在现实中,女人当然具有各种面目,但是,围绕女人这个题目形成的每一种神话,都想in一院全地)概括她,都想成为唯一的。因而,就有一些相互不一致的神话存在,男人在女性观念显露出的不连贯性面前就犹豫徘徊。由于所有的女人都和这些原型的多数有关,而每一种原型都自以为拥有唯一的关于女人的真理,今天的男人在女伴面前也就再度感到惊讶,就像老诡辩家不明白人的肤色怎么会又有白色的又有黑色的时感到的惊讶那样。社会现象早就表明了向绝对的转变:正如智力不成熟的人认为,事物的关系是固定不变的,阶级关系、模式功能也容易是固定不变的。例如,以维护世袭财产为中心的父权社会必然暗示,不但存在着拥有和遗传财产的人们,也有拿走所有者的财产并让财产流通的男男女女。冒险家、骗子、小偷和投机者之类的男人,一般为群体所唾弃;而利用性简力的女人,却能够让年轻男人甚至家长分散他们的世袭财产,不受法律的制约。这些女人,有的在挪用她们受害者的财产,或用不正当手段取得遗产。这种角色被认为是邪恶的,扮演这种角色的女人被称为“坏女人”。但是,与此完全相反,在其他场合下,如在家和父亲、兄弟、丈夫或请人在一起时,她们实际上也可以成为守护神。对富豪进行“敲诈”的高级妓女,往往也是画家和作家的慷慨赞助人。在实际生活中,阿斯拒西鞋的次轰巴杜夫人的有歧义性约人格很容易得到理解。但是,如果把女人描绘成螳螂、曼德拉革和恶魔,那么发现女人还是缪斯、大母神和贝阿特丽丝,就会引起极大的混乱。
由于一级来说群体象征和社会模式是由相反的对废物来确定的,看来矛盾将是永恒女性的固有性质。神圣的母亲和残忍的继母相关,而天使般的少女则和邪恶的处女相关:所以人们有时会说母亲即生命,可是有时也会说母亲邓死亡;有时会说所有处女都是纯洁的精神,有时也会说所有处女都是献给居克的肉体。
显然,让社会或个人在两种对立的基本范畴之间做出选择的,并非是现实。在所有的时期,在每一种情况下,社会和个人都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做出抉择。社会和个人常常把自身所坚持的制度和价值,投入所选定的神话。所以要女人呆在家里的父权制,才确定她是感情的、内向的和内在的。实际上所有的生存者部既是内在的,也是超越的。当一种制度没有给生存者提供任何目标,或阻止地达到任何目标,或不讳地取得胜利时,他的超越性就会徒劳地陷入过去,就是说,重新陷入内在性。这便是父机制派给女人的命运,但这决不是一种天命,就像受奴役不是奴隶的天命那样。在奥古斯特·孔德那里,可以清楚看到这种神话的发展。把女人和利地主义相提并论,是为了以她的奉献来保障男人的绝对权利,这是在强迫女人服从一种绝对命令。
没有必要把神话和承认意义混为一谈。意义在客体中是内在的,通过生动的体验昭示于精神。而神话是一种超越的理念,完全不为精神所认识。米歇尔·莱里在《人的时代》空述他对女性器官的看法对,告诉我们的是有意义的事物,而不是精心炮制出来的神话。对女性身体的惊奇,对经血的厌恶,都来自对一种具体现实的淹没。揭示女性肉体的色情性质的体验,没有任何神秘之处;即使有人想通过与鲜花式水晶《比来描绘这种性质,也不于人的处境的极其神秘的事物,而这一神秘事物,在女人身上呈现出极其令人不安的形式。
但是,人们通常认为是神秘的那种东西,既不是有意识自我的主观孤独,也不是神秘的有机生命。神秘这个词的真正含义表现在交流方面:它并非是指一种完全沉默的、黑暗的和不存在的状态,而是在暗示一种断断续续的存在,这种存在使它本身变得暧昧不清。说女人是神秘的,并不是指她是沉默的,而是指她的语言是人们所不能理解的。她是存在的,却蒙在面纱之后;她存在于这些变幻莫测的外表之外。她究竟是什么人?是天使,还是魔鬼?是有灵感的人,还是演员?人们可能认为,这些问题是不可能找到答案的,或者更确切地说,可能认为,没有一个答案是合适的,因为具有根本上的歧义性是女人的特征。也许在她的心目中,她甚至对她自己也是极难确定的:她是一个司芬克斯。
实际上,她对判明自己是什么入会感到非常为难。但这并不是因为这个隐藏着的真实性实在是太含糊了,以至难以辨明,而是因为在这个领域根本就没有真实性。一个生存者,除了他扮演的角色什么也不是。可能不会超出现实,本质也不会先于存在:在纯粹的主观性那里,人什么也不是,应当根据他的行为对他进行评估。我们在谈到农妇时,可以说她是一个好劳动者,也可以说她是一个坏劳动者;在谈到女演员时,可以说她有天赋,也可以说她无天赋。但是,如果我们根据她的内在存在,她的内向自我来考察一个女人,我们关于她就绝对说不出什么,她不具备任何资格。所以,在恋爱或婚姻关系中,在女人是附庸者、他者的一切关系中,人们要根据她的内在性来对待她。值得注意的是,女同志、女同事和女同伙并无神秘色彩。相反,如果这个附属者是一个男性,如果一个年纪较大或较为富有的男人或女人,认为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在扮演次要的客体角色,那么这个小伙子就有了神秘性。这为我们揭示了女性神秘的基础,这个基础实际上是关系才得以不朽,在克尔悄郭尔看来,这种关系比积极占有更可取。在和一个活生生的神秘人物在一起的时候,男子仍是孓然一身——他单独和他的梦幻、他的希望、他的恐惧、他的爱情和他的虚荣心在一起。这种主观追求,可以从恶习一直通往神秘的极度兴奋,所以对许多人来说,这是一种比和人的真实关系更有诱惑力的体验。那么这种有利可图的幻觉的存在基础是什么呢?
在某种意义上,女人的确是神秘的,照梅特林克(Macer-linck)的看法,“如整个世界一般神秘”。每一个人只有对他自己才是主体;每一个人可以内在认识的只有他自己,单独一个人:根据这种观点,他者始终是神秘的。在男人看来,他所了解的那种自我——poursoi [自为]所具有的不透明度,在身为女性的他者身上更大。男人不可能通过任何共感作用,识破她的特殊体验:他们对女人性快感的性质、经期的不适以及分娩的痛苦一概不知,并为此受到了惩罚。实际上,双方都是神秘的:身为男性的他者,每一个男人自身也有一种存在,一种女人难以识破的内在自我;她对男性的性感觉同样是无知的。但是,根据我所说的普遍规律,男人用以思考世界的那些范畴,是根据他们的观点;作为绝对确立起来的;和在所有的地方一样,他们在这里也是误解了相互性。由于女人对男人是一种神秘,她才被认为在本质上是神秘的。
说实在的,由于她的处境,女人也很容易产生这种观点。她的生理特征就非常复杂,她忍受它时,如同在忍受外部的某种无聊事物。在她看来,她的身体不是她本人的清楚表现,她觉得在体内她自己是个陌生人。的确,那种在每一个人身上都把生理生活与心理生活联系在一起的纽带,或者更确切地说,那种在个人的偶然性与表现这一偶然性的自由精神之间存在的关系,是隐含会涉足神话。但是,说女人是肉体,说肉体是黑夜和死亡,或者说它是宇宙的光辉,这无异于抛弃地上的真理,飞向虚无的天空。因为男人对女人也是肉体,而女人不仅是发泄肉欲的对象,她的肉体对每一个人,在每一种体验中,也都有特殊的意义。女人也的确和男人一样,是一个植根于自然的人。她比男性更受物种的奴役,她的动物性更为明显。但是和男人一样,在她身上这些既定特征也是通过生存这个事实表现出来的,她也属于人类王国。把她比做自然完全是出于偏见。
几乎没有哪种神话比女人神话更有利于统治等级的了:它为一切特权辩护,甚至对它们的弊端也表示认可。男人没有必要自寻烦恼,去减轻已成为女人生理命运的痛苦和负担,因为这是“大自然有意安排的”。男人把它们作为进一步加深女性命运之神秘性的借口来加以利用,例如,他们拒绝给女人获得性快感的权利,让她的劳动有如役畜一般。
在所有这些神话中,没有一种神话比女性“神秘”这个神话,更牢固地树立在男性的心目之中。它带来的好处举不胜举。首先,它使所有的费解都轻易得到解释,“不理解”女人的男人,在以客观反抗取代主观精神之贫乏时是幸福的。他不是承认自己的无知,而是发现在他之外还有一种“神秘”:这的确是吹捧懒惰和虚荣的一种借口。一颗倍受爱情折磨的心,因此避免了许多失望:如果他的爱人是任性的,她说的话是愚蠢的,那么这种神秘有助于原谅这一切。最后,还多亏有了这种神秘性,那种消极实用的。
人们可以认为情感什么也不是。“在情感领域,”吉德写道,“真实与想像是分不清楚的。如果认为一个人在爱就足以说明他在爱,那么在这个人在爱的时候,对他说他爱的是他本人的一种想像,也就足以使他立刻爱得少一点。”只有通过行为才能在想像与真实之间做出鉴别。既然男人在这个世界上有特权地位,他就能够主动表明他的爱。他常常资助他所爱的女人,或至少常常帮助她。在和她结婚时,他给予她社会地位,向她赠送礼品。他的独立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使他有可能掌握主动权,去进行发明:M·德·诺普瓦刚同德·维尔帕丽西夫人分手,就昼夜兼程去看她。男人往往是忙碌的,而女人往往是懒散的:他给她时间,和她共同度过这段时间,而她接受了这种做法:这是为了快乐,为了感情,还是仅仅为了娱乐?她接受这些好处,是出于爱,还是出于自私?她是在爱她的丈夫,还是在爱她的婚姻?当然,连男人的证据也是暧昧不清的:送如此这般的礼物,是出于爱,还是出于怜悯?但是,尽管一个女人在正常情况下,从和一个男人的关系中得到了许多好处,可是对一个男人来说,只要他爱她,他同女人的关系就是有利可图的。所以,根据对他的态度的全部描述,人们几乎可以断定他的感情发展程度。
但是,女人却几乎无法听到她自己的心声。她将根据自己的心境,用各种不同的观点去观察她自己的情感。由于她被动地服从这些观点,各种解释的正确性相差无几。在一些极为罕见的情况下,她拥有经济与社会的特权地位。这时,神秘性发生了逆转,它表明,它并不属于这一个性别,而是属于另一个性别,属于当时的处境。对相当多的女人来说,超越的道路是封闭的:因为她们没有扮演任何角色,无法让自己成为任何一种人。她们隐隐地想知道自己可能成了什么人,可是这又会让她们提出自己是什么人的问题。提出这个问题是徒劳的。如果说男人无法发现女性的神秘本质,那完全是因为它不存在。女人处在世界的边缘,不可能通过这个世界对自己加以客观地确定,她的神秘性所隐藏的只不过是空虚。
而且,和一切被压迫者一样,女人故意掩饰她的客观真实性。奴隶、仆人和穷人,所有靠看主人眼色过日子的人,都懂得用永远不变的微笑或高深莫测的无动于衷来对待主人。他们的真实情感,他们的实际行为,都被小心地藏了起来。此外,女人从青少年时起,就学会了骗男人,搞阴谋和诡计多端。在谈到男人时,她脸上总是带着一副不自然的神情。她是谨慎的、虚伪的,她总是在做戏。
但是,神话思想所承认的女性神秘,有着更深远的意义。事实上,它直接隐含于绝对他者的神话之中。如果承认这个次要的有意识的人,也有明显的主观性,也能够进行C略协[我思],那么也就等于承认这个人实际上是主权的,能够重新变为主要者。为了使所有的相互性都完全成为不可能,必须使他者对自己也是一个他者,必须让他的主观性受他的他性影响。这种被异化为一种意识的意识,在其纯粹的内在存在中,将明显是一种神秘。鉴于它对于自己也会成为神秘这一情况,它在本质上将是神秘的。它将成为一种绝对的神秘。
同样正确的是,只要黑人和黄种人被绝对看成次要的他者,除了他们的掩饰所造成的秘密,在他们当中还有神秘存在。应当注意的是,美国公民虽然让普通的欧洲人深感困惑,可是他们并不被认为他是“神秘的”:人们会比较谦虚地说,他们不理解他。女人也并不总是“理解”男人的,但是并不存在男性神秘之类的事物。问题的关键在于,富有的美国及男人,是站在主人这一边的,而神秘则属于奴隶。
的确,我们只能沿着欺诈这条通幽小径,对神秘的大可置疑的真实性苦思冥想。犹如遥远的幻象,当人们想目不转睛地注视它时,它却消失了。在试图描绘“神秘的”女人时,文学总是失败的。作为一些奇怪的神秘人物,她们只能出现在小说的开始;而在结束对,她们放弃了自己的神秘之处,完全成了表里如一的透明人物,除非故事没有结局。例如,彼得·切尼(PeterC讪贝耶书中的主人公,始终对女人的高深莫测的任性感到惊讶:没有一个人能永远猜到她们将会如何行动,她们把所有猜测结果全都给推翻了。实际上,一旦把她们的行动动机向读者全盘托出,就会发现她们是些非常简单的人物:这个女人是一个好细,那个女人是一个小偷。不论小说的情节安排得多么巧妙,始终贯穿着一条主线。即使作者有天下所有的才华和想像力,它也不可能是别的样子。神秘只不过是一种幻象,当我们走近看它对,它使消失了。
我们现在会发现,在很大程度上,女人神话是用它对男人的有用性来解释的。女人神话是一种奢侈品。只有在男人对他所需要的东西不再感到迫切需要时,女人神话才能够出现;关系表现得越具体,这些关系的观念化成分就越少。古埃及的农夫,贝督因的农民、中世纪的工匠以及今天的工人,他们对工作和克服贫困的需要,都和他们的特殊公伴有关系。这些关系对她们来说是太明确了,以至用不着用征兆来装点,不论这些征兆是吉利的还是不吉利的。那些以有梦想闲暇为特征的时代和社会阶级,是那些树立了邪恶的或善良的女性形象的时代和阶级。但是,和奢侈一起出现的还有实用,这些梦想不可抗拒地受着利益的支配。毫无疑义,大多数神话都源于男人对他自己生存及对他周围世界的自发态度。但是,超出经验、面向超越的理念,被父权社会蓄意用来自我辩护。通过这些神话,父权社会以生动有力的方式,把它的法律和习俗强加于个人。正是在神话的形式下,群体命令(山e mp-m叮已rative)经过灌输,深入到每一个人的心中,通过宗教、传统、语言、寓言、歌谣和电影之类的中介,这些神话甚至渗透到受着物质现实的极严酷奴役的生存者心中。在这里,每一个人都能够找到对他单调体验的升华:在他受所爱女人的欺骗时,他称她是狂妄的子宫;在他为自己的性无能苦恼时,他称她是一个螳螂。还有一些人在妻子的陪伴中享受到乐趣:快瞧呀,她竟然是和谐、安宁和仁慈的大地!多数男人所具有的对永远讨价还价的爱好,对绝对合适的爱好,都通过神话得到了满足。连最微小的激动、最轻微的烦恼,也在反映超时间的理念。而这个理念,是一种对虚荣心非常愿意阿议奉承的幻觉。
女人神话,是虚假客观性设置的一个陷阱,而信奉现成评价的男人,一头扎进了这个陷阱。这里,我们又在和代替现成偶像对现实的体验,及代替这一体验所需要的自由判断打交道。女人神话用目不转睛地注视幻象,代替了同自主生存者的真正关系。“幻象!幻象!”拉福格大声喊道。“我们无法理解她们,所以应当杀死她们。或者,最好让她们平静下来,让她们受到教育,让她们放弃对珠宝的爱好,让她们成为我们真正平等的同志、我们的亲密朋友、世界上真正的伙伴,让她们穿着各异,让她们剪短头发,对她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恰恰相反,假如男人不再把女人装扮成一种象征,他什么也不会失去。梦想一旦变成正式的公众事务,变成陈词滥调,它们和活生生的现实相比,的确显得单调乏味。对真正的梦想者来说,对诗人来说,女人与其说是一个邋遢得出奇的婆娘,不如说是源源不断的泉水。极其真诚地对女人表示爱护的时代,不是封建的骑士时代,可也不是对女人大献殷勤的19世纪,而是男人把女人看做同类的那些时代,例如肥世纪。那时的女人似乎是真正浪漫的,《危险的私情》、《红与黑》和《永别了,武器》这类作品,就是这样充分表现的。拉克罗(h化k 侣)、司汤达和海明威笔下的女主人公,没有神秘性,可是她们因此仍然十分迷人。承认女人是一个人,并不是要对男人的体验进行任何改变:这不会让体验失去它的多样性、丰富性,或减弱它的强度,假如这种体验在两个主观之间发生的话。抛弃女人神话,并不是要完全破坏两性间的戏剧性关系,也不是要否定女性现实所确实向男人揭示出的意义,更不是要取消诗歌、爱情、冒险、幸福和梦想。这只是要行为、情感和激情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人
“女人不见了。这样的女人在哪里?今天的女人根本不是女人!”我们已经发现了这些神秘口号的含义。对男人来说,以及对于以男人目光看待事物的众多女人来说,母亲或情妇要做一个“真正的女人”,仅仅拥有女人身体或表现女性功能还是不够的。在性行为和母性中,女人作为主体,能够要求自主。但是,要做一个“真正的女人”,她就必须承认自己是他者。今天的男人表现出一种口是心非的态度,这使女人痛苦不堪。在整体上,他们愿意承认女人是自己的同类,是一个平等的人,但他们仍然让她做次要者。对她来说,这两种命运是不可比的。她在是做这种人还是做那种人之间犹豫不决,无所适从,因此失去了平衡。在男人身上,公众生活和私人生活之间并不存在着裂痕:他在行动和工作中越是证实他对世界的控制,就越是显得有男子汉的气魄。人的价值和生命的价值在他那里是结合在一起的。而女人的独立成功却和她的女性气质相矛盾,因为,要做一个“真正的女人”,就必须使自己成为客体,成为他者。
在这方面,男人的感受性和性冲动会完全有可能发生变更。现在,新的审美观念已经产生。如果说,时兴扁平的胸脯和狭小的臀部,即时兴男孩子的形体是昙花一现,那么以前几个世纪崇尚过于丰满的理想至少是一去不复返了。女性身体被要求必须是肉感的,但这个要求比较谨慎。它应当是苗条的,不发胖的;它必须是肌肉发达的、柔韧的、强健的,使人可以联想到超越;它不应当像终日不见阳光的温室里的花草那么苍白,而宁可如光着膀子在太阳下干活的工人那样晒得黝黑。女人的衣服在实用的同时没有必要让她显得无性感:相反,穿短裙倒是为了使她的双腿显出以前从未有过的性感。没有理由认为劳动会夺走女人的性魅力。认为女人既是一个社会的人,又是一个发泄肉欲的对象,这可能会引起人们的不安:在佩纳(ler)最近写的一系列作品中(1948年),我们发现,一位年轻男人撕毁了他的婚约,因为他受到美丽动人的市长夫人的诱惑,而她正打算主持他的婚礼。让女人既有某种“男人的地位”,又让男人感到称心如意,这长久以来是人们开下流玩笑的题目。但逐渐地,这种挖苦讽刺变得不那么犀利了,看来,一种新型的性爱正在产生——也许这会造成新的神话。
毫无疑义,让女人既承认她们的身份是一个自主的人,又承认她们的女人命运,在今天是十分困难的。这是造成失策和不安的根本原因,而这种失策和不安有时又让人们认为她们是“失去性别的人”。忍受无形的奴役,无疑比为解放而工作更舒适:就此而言,死气沉沉的女人比朝气蓬勃的女人更能顺应大地。无论从哪方面来看,重返过去都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值得向往的。应当寄予希望的是,男人能够从自身方面毫无保留地接受即将出现的那种处境。只有到那时,女人才可以无忧无虑地在那种处境中生活。那时,拉福格的这个祈祷将得到回答:“啊,年轻的女人们,你们到什么时候才能成为我们的兄弟,我们亲密无间、肝胆相照的兄弟?我们到什么时候才能真诚地握手?”那时,布勒东的“梅留辛,将不再受到男人给她带来的灾难的压迫,梅留辛将会得到解放……”将重新找到“她在人类中的位置”。那时,她将会变成一个完全的人,用蓝波信中的话来说,“那时,对女人的无限束缚就会嘎然而止,她将会在自身中并为自身而生活,而男人,尽管至今是可憎的,将会让她获得自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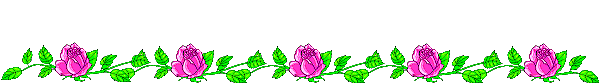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