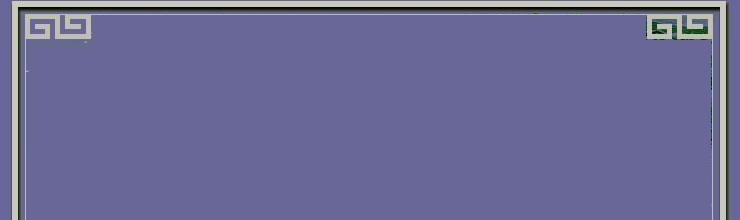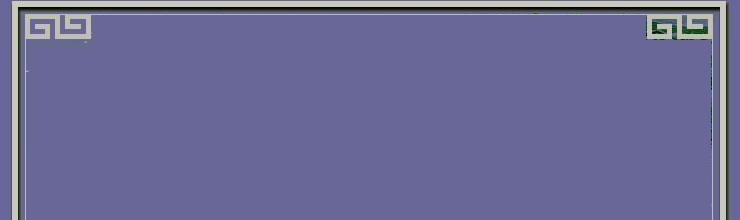|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234)
中图分类号:I51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634(2000)04-0074-(06)
摘 要:本文通过对奥涅金与达吉亚娜的“忧郁”的不同表现、性质的比较,分析了这两个人物所体现的不同社会、文化内涵,并从女性主义的视角揭示了达吉亚娜这个男权社会中的理想女性形象所反映出来的性别文化内涵。
关键词:奥涅金;达吉亚娜;忧郁;性别文化内涵
普希金在1823年春写下了《叶甫盖尼·奥涅金》最初的草稿,“他要通过俄国青年中的三个典型人物来展现当代文明俄国的广阔图景。这三个人物是:一个冷漠的否定一切的人物,一个热情的浪漫主义者和一个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少女”。①无疑,奥涅金和连斯基确实成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尤其是奥涅金,已被公认为“多余人”的鼻祖。赫尔岑说:“奥涅金是俄国人,只有在俄国才可能有;在俄国他是必不可少的,到处都可以遇到这类人……”② 诗人以奥涅金为例,对“多余人”的社会处境及身心感受进行了细致客观的描绘,对他们的处境抱以深深的理解和同情,从而表现出诗人强烈的社会批判态度。然而,“达吉亚娜不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而是作者塑造的理想形象”。③在小说中,达吉亚娜这一人物形象代表了普希金对俄罗斯文化及社会现实的出路的探索。她是浪漫主义艺术手法的产物,是普希金心目中的理想女性的投射。在她身上,反映了诗人的思想文化追求和审美理想,也体现了诗人的男权思想。
达吉亚娜的形象主要是在与奥涅金的形象相互辉映、相互衬托的过程中凸现出来的。同是出身贵族之家,奥涅金成长于繁华喧嚣的都市彼得堡,达吉亚娜则生长于幽静偏僻的村落。奥涅金在浮躁、喧哗的社交生活中无聊度日,而达吉亚娜的心灵则受到了静寂、神秘而辽阔的大自然的熏陶。奥涅金的家庭教师是一个敷衍了事的法国人,达吉亚娜则从奶妈那儿受到了民族传统文化的熏陶。两人都接受了来自西欧的先进文化和思想,奥涅金喜欢读亚当·斯密、拜伦的著作,而达吉亚娜则对感伤主义作家理查逊、卢梭的小说情有独钟。两人同为对现状不满的先进贵族青年,“忧郁”是他们共同的个性特征,但在“忧郁”的表现、性质中却又体现着性别的差异。首先,奥涅金的忧郁是男性的、不安分的,它透着空虚、浮躁和烦闷,像一座看似沉闷实则活跃的火山,总在寻找喷发的出口。在这股力量的驱使下,奥涅金无故杀死了好友连斯基,从而在良心的谴责下选择了四处游荡。达吉亚娜的忧郁则是一个女人的忧郁,它在压抑中透着宁静,像一条小河,满载着少女的心事和梦想,渴望流向一个未知的、幸福的海洋。奥涅金的忧郁是指向行动的,因此常意味着破坏力;而达吉亚娜的忧郁则是指向精神的,它预示着主人公精神的继续成长、发育。其次,奥涅金的忧郁是后天形成的,是作为一个社会个体的人在失落其价值、找不到出路后内心的压抑、躁动的表征,它反映了人与时代、社会的冲突,具有典型而深刻的社会意义。而达吉亚娜的忧郁是与生俱来的,它具有极少的社会性,仅仅是个人的幻想、渴望的情愫。“很久以来,柔情和苦痛一直在燃烧着她的想象,渴求那命中注定的食粮;很久以来,她年轻的胸中,一直深深地感到苦闷;心儿在盼望……那么一个人”。④显然,少女的忧郁的河流一直在渴望流向幸福的爱情。因此,当孤傲、狂妄、忧郁的奥涅金出现的时候,达吉亚娜就毫不犹豫地爱上了他。在写给奥涅金的情书里,达吉亚娜的内心感情暴露无疑,在仍未确知奥涅金对她的爱情之时,她就敢于大胆向他表白:“从此把命运向你托付”。她期待着奥涅金的爱,盼望他就是那个使她幸福且值得她终生依靠的人。
对于达吉亚娜,别林斯基说道:“达吉亚娜是一个特殊的造物,有着深刻的、善于爱的、热情的天性。爱情在她会是一生中最大的幸福,也会是最大的灾难,毫无任何调和的折衷可言。”⑤可以想象,如果达吉亚娜嫁给了一个她所向往的丈夫,那么她将会像《战争与和平》中的娜塔莎一样,完全把自己奉献给丈夫和孩子,并从中得到最大满足和享受。而在当时的俄罗斯社会,这种幸福也是女性可能得到的最大幸福了。达吉亚娜把自己的梦想托付给了奥涅金,但奥涅金是不可能给她这种幸福的,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在社会上找不到立足之处的“多余人”。他的浮躁的心境使他无法安于传统的、也是达吉亚娜所向往的家庭生活。因此,尽管他也被少女的纯洁感情深深打动,但他还是拒绝了达吉亚娜。如果说奥涅金的悲哀的本质在于找不到自己的存在,而不在于无法得到家庭的欢乐;那么,达吉亚娜的悲哀则在于爱上的是奥涅金,一个无法负担自己的命运、也不能负担她的命运的人。两相对照,便不难发现萦绕在两人心头的各自的愁结所在,也更能清楚地透视奥涅金和达吉亚娜这两个人物形象背后的社会内涵和文化内涵。
“如果说少女达吉亚娜从心灵到外在形态确实体现了某种现实可能性,那么,贵妇人达吉亚娜则更少某种现实因素,这是普希金的理想,是俄罗斯的灵魂”。⑥达吉亚娜在爱情受挫后,内心依然保存着对奥涅金的爱情,却身不由己被母亲带到了“未婚妻的集市”,成了一名贵妇人。她很快就适应了上流社会社交场中的角色,并以高贵、优雅的言谈举止博得了社交界的青睐和尊敬。尽管她对身处的浮华生活极其厌恶,内心依然渴望从前宁静、素朴的乡村生活,“情愿马上抛弃这些假面舞会的破衣裳;这些乌烟瘴气、奢华、纷乱,换一架书,换一座荒芜的花园,……”但由于她的高贵的精神,她的隐忍和自我牺牲的天性,她在上流社会保持了一个贞洁女人的体面形象。她的忧郁的河流默默地流向了道德。可想而知,如果达吉亚娜听从内心感情的召唤,接受了奥涅金的求爱,那么她就绝不会成为“俄罗斯的灵魂”,而是成为男性文化视野中面目可憎的“妖妇”了。
成为贵妇人后,达吉亚娜的本性虽未改变,依然纯洁、朴实,但她的形象却经历了一次蜕变。仔细分析达吉亚娜的生活,则会发现她在感情上忠于奥涅金,而在身体上和社会关系上忠于自己的丈夫。在她身上,灵与肉已彻底分离,“欲”已不复存在。她已不再是一个现实的女人,而是一个“女神”。正如《第二性》中所描绘的圣母形象:“基督之母的面部被光轮环绕。她是罪人夏娃的反面,她踩死了脚下的蛇;她是救世的调解者,而夏娃却是该罚入地狱的。”⑦此时的达吉亚娜,凭借其高贵的精神和隐忍的天性,已使爱情的痛苦和婚姻的无奈在道德中求得了平衡,她优雅的仪容举止无不显示出精神的超脱与在现实中的和谐,而这正是奥涅金所缺少和梦寐以求的。无怪乎在外漂泊了两年而终无所获的奥涅金一见到她就疯狂爱上了她。正如小说所说:“叶甫盖尼孩子般地爱上了达吉亚娜。”在内心的狂热激情的驱使下,他终于按捺不住地写信向她表白:“一切都已决定,一切随您处理,我决心一切都听天由命。”同是向对方表白自己的心迹,同是无条件地献身爱情,但达吉亚娜的爱情怀有对一个男子托付终生的希望,它的目的是得到对方的爱,进而过上幸福的家庭生活。而奥涅金的爱情是盲目而狂热的,它没有什么理智的引导,甚至也没有什么直接的目的,它是奥涅金自我救赎的一种冲动与需要,具有深刻的文化意蕴。在奥涅金心中,达吉亚娜是他获救的希望,是他痛苦灵魂的唯一避难所,他对她产生的是一种迷途的羔羊对“圣母”的依恋。而达吉亚娜则摆出一副道德训诫的架势,她称奥涅金的爱情为“令人羞辱的激情”,她甚至怀疑奥涅金狂热追求她的目的,尽管她仍然爱着奥涅金。此时的达吉亚娜,俨然成了道德的化身。
“我爱您(何必对您说谎?),但现在我已经嫁给了别人;我将要一辈子对他忠贞。”这是达吉亚娜最后的心迹表白,也是解读她形象的一把钥匙。别林斯基曾对此表白发问:“一辈子忠诚,——对谁?在什么事情上忠诚?对这样一种关系忠诚,这种关系是对感情和女性纯洁的亵渎,因为不为爱所尊重的那些关系,就是最大程度上的不道德的关系……”继而又指出达吉亚娜“服从另一种更高的律法——自己天性的律法,而她的天性——恰也是爱情和自我牺牲。”⑧然而,这种自我牺牲精神是违反人的本性的,它不可能是天生的,而只是父权制社会通过其文化传统长期以来对女性无形奴役的结果。父权制社会通过压抑女人的天性来维持社会的伦理与道德,从而维护其赖以存在的基础,这是自我牺牲精神的来源,它作为社会的文化代码在妇女身上代代相传。因此,自我牺牲对女性来说并非是幸福的天堂,而只是在父权制文化长期的扭曲下或主动或被迫牺牲自我的一种现实境遇。“自我牺牲精神并非是高尚的精神,它是一种死亡的表现。缺乏故事的生命,如同歌德笔下的玛甘泪的生命那样,实际上也是一种死亡的生命,一种生命中的死亡。‘祈祷纯洁’的理想,最终只能召唤天堂和地狱”。⑨归根结底,无论是自我牺牲,还是道德,都是男性强加于女性头上的律法。作为普希金理想的达吉亚娜实际上是被客体化了的,带有明显的男性修辞的印记。但是,“客体化的女性形象渗透着男作家对女性的心理反应和主观愿望,她们只是男性文化和生命体验的载体,而并不揭示女性的真面目。”⑩从这一点来说,达吉亚娜的形象是虚假的,作为一个活生生的女人,她只是一个相对于男人的虚假生存。但她的形象从本质上表明了女性文化的社会处境,因而又是无比真实的。
另一方面,在诗体小说中,达吉亚娜的形象还与其他女性形象形成了鲜明对照。首先反衬达吉亚娜形象的是上流社会的名媛贵妇们。在小说开头对奥涅金社交生活的描绘中,小说以讽刺、贬抑的手法对她们作了这样的描绘:“上流社会的这群女妖怪!他最先抛开的就是你们;说真的,在我们这个时代,高尚的谈吐真叫人烦闷;虽然,或许有一些才女也会谈点儿边沁或沙伊,但……一张面孔就够让你害上忧郁病。”她们是沾染了社交界浮华习气的世俗女人,与达吉亚娜的纯洁、高贵、自我牺牲的品质相比,她们虚伪、放荡却又故作高雅之态。奥涅金虽一度在她们中流连忘返,但最终又将其彻底抛开。
其次,小说还在达吉亚娜的身边设置了一个陪衬——奥尔加。与躲在高贵的精神世界中的达吉亚娜不同,奥尔加自小就沉溺于世俗的欢乐。她虽有美貌,但内心贫乏,思想平庸,也无憾人的道德力量和自我牺牲精神。而达吉亚娜虽然不美,却以其精神和道德上的灼灼光辉令妹妹黯然失色。而且,在诗体小说中,奥尔加还脱不了“轻浮”的恶名。连斯基的被杀,罪责虽不在她,但她在男权社会的眼里却脱不了“祸水”的干系。况且,连斯基尸骨未寒,她就另择佳婿,远走他乡了。其实,连斯基的死在诗体小说中既出于结构上的安排,又有其文化上的意义。小说借奥涅金之手杀死连斯基,不仅为奥涅金的出游提供了契机,更表明单纯浪漫主义在俄国现实中迟早会遭到失败的结局。让奥尔加在这场悲剧中成为引发事端的“红颜祸水”,只能说明父权社会对女性本身、特别是对女性肉体的敌视和恐惧。
再者,达吉亚娜的母亲拉林娜的形象也有其烘托意义。拉林娜年轻时也有过爱情,也爱读理查逊的书,然而被迫嫁给不爱的人后,她慢慢地从一个温雅的贵族小姐变成了俗不可耐的主妇,完全蜕化为宗法制父权社会的附庸,甚至还成了父权制代言人——“家长”,并把达吉亚娜引向了莫斯科这个“未婚妻的集市”。正如诗体小说中评论的那样:“老天爷把习惯赐给我们,让它来给幸福做个替身。”达吉亚娜的人生遭遇虽与母亲类似,结局却大相径庭,她凭其自我牺牲的天性,终于促成了自身道德的完善,却依然保持着精神的高贵。虽然小说对达吉亚娜不幸的现实处境的描述客观上透露出作者对女性命运的关注,但这并没有使作者放弃他的男权立场。因为小说对达吉亚娜的高贵的仪容和得体的言谈举止的赞赏远远超过了对她不幸的命运所抱的同情与遗憾。
上流社会的贵妇、奥尔加和拉林娜犹如众星捧月,从不同侧面衬托出达吉亚娜的“完美”。对已成为父权社会附庸的拉林娜,小说只对她的俗气作了嘲讽。而在上流社会的女人和奥尔加身上,却明显体现着“夏娃”形象模式的印记,她们反衬了达吉亚娜的“圣母”形象。这也恰恰反映了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生存困境,正如克里斯蒂娃指出的,“所谓女性,就是‘被父权制符号次序边缘化了的属性’。断言一切女性都是天赋的,和断言一切男性也都是天赋的,其目的正是为了使父权势力把一切‘女人’(不是女性)规定为符号次序和边缘人。正是这一地位,使男性文化时而贬低女人,把女人描写成恶魔与祸水,看作荒淫无度的娼妇和妖婆;时而拔高女人,把女人描写成高度纯洁的造物主,奉为天使和圣母。无论哪一种情况,都不符合女人的真正实质。”
另外,解读奥涅金与达吉亚娜的形象,还须注意诗人普希金在诗体小说中担任的角色。诗人在小说中以第一人称人物“我”的形象出现,并留下了大量的抒情、议论之笔。按照叙事学理论,它采用了“作者叙事情境”,叙述者外在于人物的世界,叙述者的世界存在于一个与小说人物世界不同的层面,叙述者采取的是外部聚焦。同时,由于小说独特的“诗体小说”的形式,小说又兼有“第一人称叙事情境”的某些特征,叙述者存在于虚构的小说世界中,叙述者是小说中的一个人物,人物的世界与叙述者的世界在一定程度上是统一的。因此,小说中的“我”在抒发感情、发表议论时是诗人自己,而在小说中出现时又带有了虚构的因素。但小说中的“我”在表达感情和对世界、故事和人物的看法时与诗人自己是完全一致的,诚如智量先生所言:“这个‘我’是原原本本的诗人自我。”B12因此,小说可看作以作者叙事情境为主,它直接表现了诗人的思想感情及内心世界。对奥涅金,诗人采用的是平视的视角。奥涅金在小说中是“我”的朋友,他有着进步的思想和不与世人同流合污的品格,他的思想和处境的痛苦就是“我”的痛苦。但从诗人自始至终对达吉亚娜的超凡脱俗的个性与品质的描绘中,我们却不难看出诗人对她的近乎仰视的喜爱甚至崇拜。她的确超出了一个作为人的女人的形象,而是带上了神话色彩。而对于与达吉亚娜形象形成鲜明对照的其他女性形象,诗人贬抑的态度是随处可见的。
如前所述,在达吉亚娜这个男性心中的理想形象中,渗透着浓重的宗法制父权意识。为什么普希金要塑造这样一个女性形象?归根结底,这与他所处的时代、他的思想和个人体验、他的审美倾向是分不开的。
《叶甫盖尼·奥涅金》写于1823年~1830年,它反映的是19世纪20年代俄国社会的现状,是“俄国生活的百科全书和一部最大程度上的人民性作品”。B13当时的社会孕育着矛盾和危机,西欧的先进文化和思想与宗法制俄国社会的冲突使普希金感受到思想的痛苦,奥涅金便是这种痛苦的表现和反映。因此,在诗体小说中,诗人作为奥涅金的朋友,“爱他身上的种种特点”。但在奥涅金身上是看不出社会的出路的,为了探索俄罗斯民族与文化的出路,普希金虚构了达吉亚娜这个形象。达吉亚娜代表的是吸收了西方文化的俄罗斯民族文化,她代表着俄罗斯民族文化发展的方向,因此她的精神最终达到了和谐的境地。她的富于自我牺牲的美德是俄罗斯民族文化的体现。然而,这种自我牺牲精神正是父权制的俄罗斯文化对女性的要求,它与父权制道德是密不可分的。正是在这个层面上,达吉亚娜作为“俄罗斯灵魂”的形象与她作为女人的身份是分不开的。
达吉亚娜身上也体现了普希金对女人的理想:她可以有爱情,但必须贞洁,求得道德上的圆满。这与当时的社会现状也密不可分:“当时俄国贵族妇女一方面是婚姻不自由,另一方面便是婚后生活的不幸,所以贵妇人的生活放荡也是比较常见的事。普希金在奥德萨时期曾经跟诺沃罗西亚总督夫人沃隆佐娃有过一段暧昧关系。这段风流韵事给他的心灵造成巨大创伤。他为怀念沃隆佐娃写下十几首诗,最后一段写于1830年,几乎跟达吉亚娜最后一次同奥涅金会面在同一时期。可见,作者是有感于民心不古而塑造出他所理想的贵族妇女形象来的。”B14这恰恰也体现了诗人的男权意识——男人可以随意地追逐女人,而女人则只能遵守妇道。对女人来说,这种双重道德标准是多么深重的父权制的压迫!在诗体小说第四章的别稿中,有一节诗句较明显地表露了普希金对女人的情感体验:“美妙、狡猾、柔弱的女性,在我生命的早年统治过我。”诗人在认清她们的“真面目”后,写下了以下断语:“她们是恶毒、神秘势力的造物,她们那沁人肺腑的视线,那笑容、语调,以及言谈——她们的一切都浸满毒液,都浸透凶恶险诈的变节……”B15不难看出,在诗人对女性恐惧、鄙视的态度中体现出浓重的男权意识。
另外,达吉亚娜的形象也表现了男性的审美理想。这种浸透着男权意识的审美趋向与女性的审美观是截然不同的。“女作家笔下,检验善与恶的尺度,不是贞和淫,甚至不是道德,而是情感:爱或不爱”。而在男作家那里,爱情由于道德的约束而出现了两极化倾向:善或恶。B16在对关于女性的“圣母—夏娃”或“贞女—淫妇”的二元对立形象的描绘中,显示了男权社会对女性的文化奴役。因为夏娃型的女性是男性欲望的对象,会令他们做出有悖社会秩序和道德的举动,令男性感到恐惧和厌恶,所以男性需要的是具有圣母属性——加强了的母性的女性。因此,在男权社会里,女性是应该适应男性的需要的,相对于男性,她是客体,是第二性,是被叙述和塑造的对象。达吉亚娜婚后的形象最终在男权社会中达到了完善,她是一个有利于男人的“圣母”形象。然而,她的圣母形象正是建立在她的自我牺牲精神之上的,它就是笼罩在圣母脸上的光晕。达吉亚娜身上忠实地体现出诗人,也是整个男权社会对女人的要求、想象和描述,“也许,再没有哪种角度比男性如何想象女性、如何塑造、虚构或描写女性更能体现性别关系之历史文化内涵了”。B17在男权社会里,“男性所自喻和认同的并不是女性的性别,而是封建文化为这一性别所规定的职能。这是一种神话性认同,它说明女性真实的性别内涵被剔出这一神话之外,除了形象和外壳之外,女性自身沉默并淹没于前符号、无符号的混沌之海”。B18
智量先生说过,“达吉亚娜是普希金在他所能达到的历史高度上为俄国人也为全人类树立的一种人生范例……”B19但如果我们仔细思考一下,则会发现这种人生范例不可能是属于男性的,它只是男性文化强加于女性头上的一种枷锁。更准确的表达应该是,达吉亚娜是代表男权文化的普希金为女性树立的一种人生范例,它是飘扬在男性心中的女性的旗帜。而真正女性的声音则被淹没在父权制“文明”的禁锢之下。正如吉尔伯特与古芭所言,文学中父权主义隐喻最终的矛盾在于作者同时创造及禁锢女性人物,在给予她们生命之同时将她们“杀死”。B20从达吉亚娜身上,我们目睹了男权社会强加于女性身上的文明枷锁,以及女性在男权文化中的生存困境。
注释:
①②列·格罗斯曼:《普希金传》,王士燮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10页、第412页。
③B14王士燮:《评达吉亚娜的形象》,《普希金创作评论集》,漓江出版社,1983年,第183页、第182页。
④B15《叶甫盖尼·奥涅金》,智量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96页、第387页,以下所引诗体小说的原文皆出自该译本,在此不一一注明出处。
⑤⑧B别林斯基:《论〈叶甫盖尼·奥涅金〉》,智量译,《外国文学名家论名家》,华东师大出版社,1985年,第193页、第219页、第221页。
⑥赵明:《个性的毁灭——论作为价值关系的奥涅金和达吉亚娜们》,《固原师专学报》1996年第1期,第50页。
⑦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陶铁柱译,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第199页。
⑨吉尔伯特和古芭:《阁楼上的疯女人》,转引自张来民《〈性/文本政治〉:西方女权主义批评的“信息金山”》,《河南大学学报》(哲社版)1989年第2期,第84页。
B10~B20.陈顺馨:《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20页、第6页。
B11转引自张来民《〈性/文本政治〉:西方女权主义批评的“信息金山 ”》,《河南大学学报》(哲社版)1989年第2期,第50页。
B12~B19智量:《论〈叶甫盖尼·奥涅金〉的形象体系和创作方法》,见《外国文学评论》1990年第3期,第92页,第8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