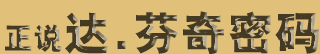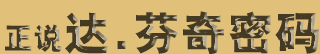|
想象的纪念碑
终于离开了圣叙尔皮斯教堂。我们可以喘口气了。与丹·布朗在一起散步从来就不轻松。下面让我们跟随兰登教授历险。他离开利兹饭店,穿过旺多姆广场,来到“正在盛开的茉莉花,从庄严肃穆的皇宫花园里散发出淡淡的清香”的黎塞留街(在那里,普通的巴黎人只能闻到汽车尾气)。在左侧的便道上,教授看到了“几枚铜徽章镶嵌在地上,排成了笔直的一行。每处徽章的直径有五英尺长,并突显出许多N和S的字母。N代表北,S代表南”。一百三十五块就这样撒过整个巴黎,以便“标示出巴黎本初子午线”。兰登,跟着丹·布朗,“曾从圣心大教堂出发,沿着这条线往北穿过塞纳河,最后来到古老的巴黎天文台。在那里,他发现了这条神圣的道路所具有的意义”(P?郾428—429)。神圣的道路所具有的意义?这一百三十五块铜徽章确实在巴黎留下痕迹——在1994年。它们被镶嵌到巴黎的地面上为了纪念科普之父弗朗索瓦·阿喇戈(1786—1853)!另外,他的名字也被镌刻在每一块铜牌上(对这一点,丹·布朗——确切说是兰登教授——为了他的秘密调查,却只字不提)。但是,作家在有一点上是有道理的:这些铜徽章与巴黎子午线有关,它标示出了这条线。天文学家阿喇戈是这条线的缔造者之一。直到1941年,这位学者的铜像仍然矗立在距阿喇戈大道不远的小广场上,但是它像巴黎的许多铜像一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熔掉了,只剩下了底座。于是一位荷兰艺术家让·迪拜(JeanDibbets)想出了一个主意,建立“想象的纪念碑”,将这些铜徽章镶嵌在地面上。巴黎人几乎都不知道的这条迪拜的路却是城市最宏大的纪念碑:它长达十七公里,穿过六个区,从毕加尔广场附近通过,到卢森堡公园、卢浮宫(有四个,其中一个在金字塔后面)、王宫。按照迪拜的想法,从一个铜徽章到另一个铜徽章漫步巴黎,“就会让人回忆起确定度量单位的早期的地图绘制者”。阿喇戈是这一史诗的其中一章。或者确切说,是他完成了这部史诗。
这一冒险活动始于路易十四时代的1669年,那时路易十四刚刚建立了科学院与天文台。当时科学家们希望揭开宇宙的秘密并绘制出地图。他们为大地测量学——“地球形态和尺度的科学”——奠定了基础。多亏了他们,我们才能在地理课上学到(或者试着学到)经线和纬线垂直相交于地球上的任意点。纬线是平行的线,单位是度,由赤道开始。所有经线经过两个极点形成围绕地球的大圈,也称子午圈。这些完全一样的圈的数量是无限的。地球上的每一个点都被某条经线穿过。但是为了能够给地球上所有的经线定位和编号,尤其为了海员的航行,必须抽象地选择出一条经线确定为本初子午线。在17世纪,我们斗胆说,是法国学者画出了最早的子午线。“他们的”子午线(被称作巴黎子午线)在近一个世纪里是海员、地理学家、旅游者等的“本初子午线”。直到1884年,靠着英国海军的重要影响,国际上用格林威治子午线取代了这条子午线。
此时,必须画出这条线。让-多米尼克·卡西尼,巴黎天文台的首任馆长——我们在前一章已经提过他的著名家族——于1671年致力于这项工作。在天文台三层的大厅里,他用一根铜线标示出了一个起点。这仅是一个开端,这支羽箭必须从南到北穿过法国,从敦刻尔克到皮尼昂!1781年,他的一个儿子最终完成了这项工作。法国大革命之后,根据这条经过修改和重测的子午线确定了长度单位:米。此后,“米”这个长度单位替换了图瓦兹①和法尺②(1799年确定,1米相当于地球子午线四分之一周长的一千万分之一)。
1806年,巴黎综合工科大学刚满二十岁的学生弗朗索瓦·阿喇戈,负责把“法国子午线”延长到巴利阿里群岛!这是一段类似于奥德赛的疯狂经历:他一度成了海盗的囚徒,被关押在阿尔及尔的贝伊①的监狱里,人们以为他死了。当他1809年回到法国的时候,他成为科学院终身秘书,后来担任了院长。他是坚定的共和派,1848年参加了法国大革命,成为部长,颁布了废除殖民地奴隶制度的法令。人们经常把他视为共济会会员,这是有争论的问题。然而,我们却知道他的兄弟埃蒂安在督政府时期加入了真理之友分会。
对一条子午线的东拉西扯
丹·布朗认为圣叙尔皮斯的铜线是巴黎子午线的一段,他犯了一个大错。它们不仅相差好几百米,而且我们知道,它们的功能并不完全一样。在神秘学圈子里,有些人把圣叙尔皮斯的铜线定义为“异端子午线”,并赋予它无数的含义;这些说法或许传到了丹·布朗的耳朵里。但是,他的“错误”却拥有小说的美妙之处,可以让他把故事情节的所有地点都放在同一条“圣线”上:巴黎子午线的确从卢浮宫穿过,圣叙尔皮斯却没有在巴黎子午线上;肯定有一条子午线穿过罗斯林礼拜堂,但那不是巴黎子午线!
最后一个侥幸的发现实在太棒了:丹·布朗说,Rosslyn源自Roslin,是礼拜堂所在的村庄的名字。而Roslin本身是源于Roseline(玫瑰线),或者法语中的RoseLigne。丹·布朗还说,这是从前的巴黎子午线——玫瑰线(lignedelaRose),抹大拉的马利亚后代(lignéedeMariedeMadeleine)的秘密名字(P?郾429)。所有的说法都圆上了!巴黎子午线直接把我们带到耶稣的婚姻和圣杯!只是——即使在神秘学的文学中,“玫瑰线”这种表达法也从来没有出现过。
我们再回到研究铜徽章的兰登教授这里。他的“调查”涉及几处地点。一个在法兰西歌剧院的一角,另一个在里沃利街(Rivoli),最后一个位于卢浮宫金字塔的后面。这个玻璃结构建筑是如此出名,今后几乎与《蒙娜丽莎》齐名,是美籍建筑师贝聿铭在密特朗执政时期的1989年建造的。丹·布朗强调,密特朗的外号是斯芬克斯,这点我们以后再说。玻璃的尖顶,映照着天空的颜色,它高达二十一米,而重量不到九十吨。这项艺术和建筑的顶尖之作耗资约一千五百万欧元。但是现在我们得跟上兰登教授,他在小说的最后几页直接朝着关键性秘密而去。他钻进金字塔,进入卢浮宫博物馆,走过通往一间“大厅”的长长通道。在那里,他迎头撞上了一个也是玻璃的倒金字塔。丹·布朗写道:“就在他的面前,倒立的金字塔闪着光芒,从上面垂下来——那是一个呈V字形的大得惊人的玻璃杯的轮廓。圣杯!……那是一个微型金字塔。只有3英尺高。……两者的顶部也几乎靠在了一起。圣杯在上,剑刃在下。”(P?郾431)兰登跪倒在地,他面前是圣杯,是抹大拉的马利亚,“被废掉的圣女的圣骨”!贴着它的微型复制品的尖顶朝下的倒金字塔并不是心醉神迷的教授的幻象。它建于1993年,属于大卢浮宫整修计划的第二阶段。它将白天的光线反射到商业走廊(“大厅”),被称作卢浮宫的阅兵场。
共济会的巴黎
丹·布朗不仅有想像力,他也懂得——我们已经看到了——出色地利用“轮回的历史学家们”,或者“神圣几何学”的专家的主题。例如,《圣血,圣杯》的作者们绘制了博学的图纸,把某座教堂或者某个清洁派的场所与法国的子午线联系到一起。但是,他们没有指出卢浮宫金字塔或者阿喇戈铜徽章。总体而言,可以引起丹·布朗兴趣的触及这个问题的著作非常少,也非常机密。它们阐述了一些模糊的,或者干脆是偏执狂的论点。比如,拉斐尔·奥利亚克(RaphaёlAurillac)的《共济会的巴黎指南》就把卢浮宫视为一个“异教的殿堂”。卢浮宫,记住这点,曾经是一个要塞,一处国王的居所,然后是科学院的驻地,在拿破仑一世时代被改为博物馆。可是,作者认为,拿破仑皇帝是一个共济会会员(这点并没有得到证实,尽管他的父亲和几个兄弟都是会员)。因此,“贝聿铭的金字塔最终完满地实现了自帝国时代就着手进行的事业”,因为“金字塔构成了共济会象征符号的一个主要的要素”。特别是这段话:“触到地面上的巴黎子午线的倒金字塔,似乎是启蒙路程的终点,过去的玫瑰十字军用一句格言谈论这件事情,即‘造访地球的内部,在矫正中你将找到隐藏的宝石’。”这就是《达·芬奇密码》所说的圣杯吗?
另外一位“共济会建筑”专家,多米尼克·斯特泽普方德(DominiqueStezepfandt)则做了几乎如出一辙的“分析”:“贝聿铭的金字塔和它的小妹妹倒金字塔向我们展示了交叉的圆规和角尺的图形,构成了所罗门之印。”这与《达·芬奇密码》完全一样,丹·布朗对我们解释说,据称在罗斯林礼拜堂出现的剑锋的倒V和圣餐杯的V也出现在两个金字塔上,构成了所罗门之印、大卫之星!……但是事情还没完。斯特泽普方德反对“按照一个秘术地理”排列的阿喇戈铜徽章的解释。对他来说,这条“共济会的轴线”是“魔鬼的脊梁”!丹·布朗是不是在阅读多米尼克·斯特泽普方德的有关论述时,得知迪拜看不见的纪念碑的?另外,后者还在他的著作里提到圣叙尔皮斯的日晷、雷恩城堡、墨洛温王族和郇山隐修会。
谁是多米尼克·斯特泽普方德?他的名字印在“事实与文献”丛书封面上。他是这套丛书惟一的作者,丛书的编辑是埃马纽埃尔·拉蒂耶。拉蒂耶是极右派记者,也是亨利·考斯通(HenryCoston)的弟子。考斯通是一个恶毒的排犹分子和患有强迫性神经官能症的人,他死于2001年,享年九十一岁。考斯通在战前创建了反犹青年组织,自1934年起就与纳粹的宣传组织建立了联系。他还是维希政府反犹记者组织的副主席。后来他逃到德国,1946年在奥地利被捕,被判处终身劳役,1951年被免除刑罚。在60年代,他成为否定主义①作品的编辑,写了多部有关“阴谋主义者”的作品(如《主导世界的金融家》、《匿名与漂泊的投资》、《执政的二百个家族》)。特别是邪恶的《化名大全》、《姓氏更迭大全》,没有其他任何的目的,我们能够猜到,就是追捕无论在哪的匿名的犹太人(考斯通主要使用占领时期建立的犹太人和共济会的名单)。他与拉蒂耶合作编写了其中一本字典。后者继承了考斯通的档案材料,继续从事他师父的工作。另外,他也是阴谋文学的专家。他还编辑了一份绝密文件,目的是揭露“为了个人私利损害法国利益者的身份”。
这里完全不是指责丹·布朗迎合拉蒂耶或者斯特泽普方德的论点,即使真是这样,这些论点也不会原封不动地直接转到他手里。这些思想在互联网上传播。它们可能,以多多少少被淡化了的方式,浸淫着其他作者的理论……我们已经分析了神秘学思想(或者伪神秘学思想)是如何偶然转化为最无中生有、最极端甚至疯狂的阐述。同样的一段历史可以被解释得完全相反。例如,布朗以前创作的小说《天使与魔鬼》提到了巴伐利亚的光明派①。这本小说里的人物,化身为学者的兰登教授解释说:“他们在欧洲变得越来越强悍,随后去攻占美国,美国许多领导人都是共济会会员,如乔治·华盛顿、本杰明·富兰克林……他们运用秘密的影响力建立银行、工厂,以便资助他们的终极目标:建立全球一统的国家,建立一个世俗的,以科学为基础的全球新秩序。”巴伐利亚的光明派是最荒谬的极右派阴谋家最喜欢的题材之一。想一想,他们代表了极端的阴谋——这是为了击垮天主教并且控制世界,渗入到所有其他的秘术团体(共济会、玫瑰十字会或者圣殿骑士团)内部的一个秘密团体!
弗朗索瓦·密特朗,斯芬克斯
当人们打算在某种秘传学的流沙中前行的时候,最好先弄清楚从哪里下脚。既然必须历尽艰辛,我们就再谈谈斯特泽普方德。我们还没有与他了断。我们还没有提及他是如何给他那部不朽的作品《弗朗索瓦·密特朗,全球的建筑大师》加上标题的!是的,他认为,这位前社会党总统任期内完成的大工程,Buren的柱子、巴士底歌剧院、卢浮宫金字塔、德芳斯凯旋门,都是一种异教占星术的“神殿”,这个异教聚集了从埃及到克尔特人的“接受奥义的人”,还包括玛雅人、圣殿骑士、玫瑰十字会成员、犹太人特别是共济会会员……弗朗索瓦·密特朗是一个反基督教和“世界主义”的阴谋集团的首脑。他在为一位必然是恶魔的大君主的降临做准备,而金字塔应该就是“御座”。
当然,丹·布朗和这些胡说八道离得很远。但是,他在书的最后着重指出,卢浮宫的金字塔,“它是20世纪80年代有‘斯芬克斯’之称的弗朗索瓦·密特朗构想并委托建造的;根据谣传,密特朗参与了秘密社团的内部活动”(P?郾429)。密特朗是“被授以奥义的人”?这样的谣言传了很久,特别是在极右派分子那里。他们提出的证据,例如,前总统经常去埃及的尼罗河。对他们而言,密特朗是魔鬼的化身,是法国大革命(“共济会的事业”、“圣殿骑士的复仇”)的继承者。但是,谣言和疑问超出了极端主义者的圈子。在索尼埃神父的爱好者中间,仅在1981年,就谣传他在大选前躲开所有人去了雷恩城堡,并坚持要参观贝朗热·索尼埃的产业!一些人很快就做出断言,他是去与某个强大的守护神签订一个秘密协定,尽管当时发表的所有照片都显示陪同他的还有大群的地方议员和大区的官员。十年之后,罗杰-帕特里斯·波拉(Roget-PatricePelat),卷入1990年政治献金案件的一个商人的名字和总统最亲密的一位朋友的名字出现在郇山隐修会大师的(假)名单里。极右派的刊物《Minute》为此捞了一把(刊物说这是“密特朗阴影下的一个秘密组织”,见该刊1993年10月13号)。这份假名单使皮埃尔·普朗塔尔受到警察的搜查,当年负责调查波拉案件的法官蒂耶利·让-皮埃尔签发了搜查令。普朗塔尔受到了严厉的训诫,因为不仅是列奥纳多·达·芬奇,弗朗索瓦·密特朗的密友也不是鬼魂隐修会的成员!相反,波拉参加了共济会,但这却不是什么秘密。
数不清的废话抛向了弗朗索瓦·密特朗。或许,也因为他一直——不管怎样——是一个复杂和神秘的人。斯芬克斯的外号就是因为他那几乎与《蒙娜丽莎》一样神秘的、尽人皆知的微笑。有关他喜好神秘事物,他的搅浑线索的艺术,他的“真实的谎言”,人们把话都说尽了。尽管他肯定是抵抗组织的成员,人们还是想发掘他的灰色区域,他与维希政府的一些人的联系。人们强调他对文学的爱好,他对星相学和神秘学的爱好(抽空去雷恩城堡的故事也许就是从这儿来的),他对死亡的迷恋,还有——因为他周围有不少共济会的人,人们有时就会问,他本人是不是也加入了共济会。他的朋友发誓说他没有加入。前外交部长罗兰·迪马,本人是共济会总会的成员,总是说“密特朗看不起共济会”,主要是因为他在主母会中接受的天主教教育。
六百六十六
但是,密特朗懂得玩弄象征符号。他有导演的天赋。我们想起荣军院的仪式。1981年5月21日,密特朗当选总统后的第十天,他拿着一朵玫瑰,只身进了荣军院,对着摄影机镜头,在社会党人让·饶勒斯①(JeanJaurès)、抵抗组织成员让·穆兰(JeanMoulin)、废除奴隶制之父维克托·舍尔歇②(VictorSchoelcher)的墓前鞠躬。对一些人来说,这个仪式更加证明了国家总统与共济会会员的联系(维克托·舍尔歇是真理之友分会的成员,让·穆兰尽管有块根深蒂固的招牌,但绝不是共济会成员);或者有人干脆说,他在墓前举行了一场秘密仪式!
总之,弗朗索瓦·密特朗令人仰慕,但是也引起对他的大工程政策的闲言碎语。最具有他个人风格而又独一无二的计划,要算纪念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的构思了。他建了一个大凯旋门,一百一十米高的巨大立方体,重达三十万吨。对于诽谤者来说,这个建筑已经成为他狂妄自大的证据。但是,引起世人最大争议的还是贝聿铭设计的金字塔。如今,这座金字塔被认为是无可争议的一个巨大成功。但是,在当年,人们不断嘲笑现代法老弗朗索瓦·密特朗的抱负。人们把未来主义的三角形看作“奶酪钟”或者“瘊子”(《达·芬奇密码》的贝祖·法希探长就用了这个称呼)。人们说弗朗索瓦·密特朗把自己看成古埃及的一个统治者,希望建造一座“坟墓”。尽管贝聿铭解释说,金字塔的功能首先是创造一个采光井为大卢浮宫的地下采光,也可以做成一个球形。但是所有这些辩解都没有用。象征符号的力量过于强大。
丹·布朗没有忍着不说,他写道:“在弗朗索瓦·密特朗总统明确要求下,这个金字塔正好由666块玻璃构成。……他们说666恰好是撒旦的代码。”(P?郾17)“凡是聪明的,可以算计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它的数目是六百六十六。”(《圣经·新约·启示录》ⅩⅢ,18)说密特朗要求金字塔必须秘密地带有撒旦的数字不仅虚假,而且荒诞。这个说法在《弗朗索瓦·密特朗,全球的建筑大师》一书中被充分论述过:“金字塔是献给一个统治者的,这个统治者是圣约翰的《启示录》选定的那只怪兽”,它“完全是由六这个数字构成的”。当然,斯特泽普方德指出,资料来源不同,玻璃的数量也不一致:在设计者的正式宣传册子上是六百七十二块菱形玻璃,几页之后又两次说是六百六十六块。另外一本手册说“六百零三块菱形玻璃和六十块三角形玻璃”,而另外一本又给出了一个新的怪兽的数字。最后斯特泽普方德说:这些矛盾的说法是为了把“被授以奥义的人”的注意力引向金字塔的撒旦的重要意义上!在一点上,他没有错:我们自己找到的数字也都不一样。1988年2月24号的《Télérama》周刊写道:“人们最终安装了六百六十六块菱形玻璃。”但是,十年之后,《解放报》说是“六百七十五块菱形玻璃,一百一十八块三角形玻璃”。而《共济会的巴黎指南》最终的结果是“七百九十三块菱形和三角形玻璃”。
最后,我们询问了卢浮宫博物馆的宣传部门,他们告诉了我们最终的数字,同时,他们也强调说这是一个“纯粹技术性的解答,与解释《达·芬奇密码》毫无关联”。(博物馆的领导部门不愿意听到谈论这本书,因为这是一本魔鬼的书。)“金字塔共有六百七十三块玻璃,六百零三块菱形的,七十块三角形的!”我们相信这个数字,我们拒绝爬上建筑去核实。至于为什么错误的数字在流传,这个问题还有待解决。或许,这又是一个让神秘爱好者们慢慢磨牙的东西。
-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