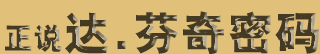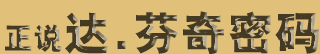|
虚假的剧作
塞拉斯(Silas),《达·芬奇密码》中的狂热的僧侣,以为在圣叙尔皮斯教堂找到了“谜的关键”。狮头、龙尾、羊身的吐火怪物。塞拉斯在这里丢掉了良心,杀死了一名修女。这座教堂的正立面以其列柱廊,那些柱子和双塔而像是一座剧场。这里一切都是虚假的。教堂是让·雅克·塞尔旺多尼的作品,一位18世纪初的建筑师、舞台布景师、剧团经理、杜伊勒利宫的成功的导演、声光表演——这可不是臆造——和“斜向透视法”的创始人。总之,这是一位幻象大师。这就是圣叙尔皮斯能够让人发疯的理由吗?传说它还隐藏着尚无人涉足的顶楼、巫术、魅影。丹·布朗把它当作郇山隐修会的象征性场所之一。教堂从某种意义上是这个修会的一个“隐蔽所”,由隐修会的桑德琳·比耶尔修女值守。丹·布朗确认说,教堂建在一幢“原先是为埃及女神伊希斯而修建(的古庙)”遗址上(P?郾79)。
圣叙尔皮斯,令人生畏的教堂,长久以来就令寻找“大秘密”的人们浮想联翩。或许是因为在其正儿八经的外表下,隐藏着一段不仅是秘密的,而且还充斥着流言蜚语和恐怖的历史。弃教的主教、撒旦式的作家、共济会的天文学家、崇拜最高主宰①(êtresuprême)的革命者都曾在这里出入。萨德侯爵本人也不例外。居然有那么多的事件,以至天主事工会的僧人塞拉斯想都不敢想……
让我们跟着这位患了白化病的僧侣。在夜里,他正准备敲厚重的教堂大门。他把车停在广场上,“惟一能见到的是圣叙尔皮斯教堂广场远处的一两个向夜游客们展示本钱的十几岁的妓女”(P?郾66)。这是没有肉体之欢的上帝战士的幻觉吗?在2000年,我们或许在圣叙尔皮斯广场的旅馆,或者有产者的家里见得到应召女郎,但是根本没有在马路上拉客的“生活腐败的女人”!在3个世纪前,当教堂正在建设中时,这地方属于“最腐朽的巴黎”。被教民们吓得目瞪口呆的神父说过他要与“邪恶的魔鬼”作斗争。塞拉斯会喜欢这些话的!这不是,他来到令人肃然起敬的教堂前。暮色降临,它甚至有些令人毛骨悚然。一般来说,巴黎人不喜欢圣叙尔皮斯这座“法国古典主义的杰作”。他们认为这种“虚伪的”①建筑风格过于冷冰冰的。塞拉斯现在打量着“教堂的两个钟楼像两个哨兵矗立在教堂长长的躯体上”,北边的那座搭着脚手架。多年来,圣叙尔皮斯教堂内部一直忍受着一种病痛:潮湿。
“大白于天下的秘密”
在大殿的科林斯式柱子的脚下,身材魁梧的塞拉斯显得十分渺小。圣叙尔皮斯是法国首都的第二大教堂(长119米,宽57米,高33米),与巴黎圣母院不相上下。当然,塞拉斯欣赏不到从大殿白色的天窗透过来的阳光,他是夜里来的。他不会知道,圣叙尔皮斯的建造者希望让教堂充满光明。他从来没有听说过17世纪下半叶诞生在法国的“唯灵论学派”。当时,他们的代表人物圣味增爵或者圣弗朗索瓦·德·塞拉斯不同意用中世纪样式的玻璃把教堂搞得昏昏暗暗,不愿意用图解的教义启发教徒。他们把希望寄托在教育上。这在当时是巨大的预言。博绪埃②(Bossuet)曾经在圣叙尔皮斯壮观的讲坛上布道。当时的神职人员希望把“神秘大白于天下”。把圣叙尔皮斯搞成了一块晦暗的宗教场所的丹·布朗知道这点吗?
要是没有找到丹·布朗描写的昔日异教崇拜的遗迹,塞拉斯就会在教堂里度过几个夜晚。“即便教堂建在一座供奉伊希斯的神殿遗址上,也不会对我有任何影响。”保罗·鲁马内(PaulRoumanet)——现在的堂区神父说。把教堂建在异教的圣所上是19世纪的神秘学转回来的主题之一——有种观点硬说Paris(巴黎)源于BarIsis(伊希斯)——但有时也是历史的实情(例如在墨西哥,一些教堂就使用了阿兹台克的奠基石)。至于说圣叙尔皮斯,历来“没有任何考古证据表明在教堂下面有一个异教的神殿”,鲁马内神父确信地说。
针对《达·芬奇密码》出版后成千上万的读者拥到圣叙尔皮斯来这种情况,鲁马内神父最终在圣器室附近的墙上张贴了一张告示,把“畅销小说的所有想象的影射”列了一张表。他也一直在有礼貌地回答各种各样的提问。他对一个游客说:“请看,塞拉斯打死修女的那个主祭坛上的蜡烛台非要三个男人才抬得起来!”另外,那可不像布朗所说的是“锻铁的”,而是金光闪闪的铜器,是法国最著名的金银匠(路易·伊兹台尔·舒瓦瑟拉)了不起的雕刻品。神父知道他无法说服“皈依者”,例如,这个游客就对他说:“反正,您是他们一伙的,您在保守大秘密!”游客也不同意神父的说法——玻璃上的字母P和S不是郇山隐修会的缩写,而是圣人彼得和叙尔皮斯,教堂的两位保护者。神父叹了一口气。他对此已经习惯了。早在这部畅销书出版之前,他就见到大量的“信徒”根据在圣叙尔皮斯教堂找到的“迹象”提出的最不可思议的问题。有的时候,保罗·鲁马内宁愿带着顽皮的微笑:“您瞧,我可以给您提供一个布朗没有说的新迹象:您想想,谁是圣叙尔皮斯。”
墨洛温时代的总主教叙尔皮斯
叙尔皮斯,公元570年生于贝里地区瓦当(Vatan)的一个高卢-罗马人家庭。很小的时候,他就想进修道院,但是,他的父母希望他做一个侍从。他经过许多挫折,直到四十八岁的时候才被授以教职。因此,他是受挫折而大器晚成的圣徒的楷模!他还是法国历史上第一位随军教士,曾在法兰克国王的军队服务。值得一提的是他还担任过达戈贝尔特一世和二世时代的布尔热地区的总主教。公元679年达戈贝尔特二世被谋杀。这又回到墨洛温王朝了!另外,您绝对想不到,圣叙尔皮斯死于1月17日,与索尼埃神父是同一天。
不管怎样,建造于12世纪的第一座圣叙尔皮斯教堂是以布尔热的总主教(他死后,变得非常有名)的名字命名的。现在圣叙尔皮斯教堂的地下室保存着这栋建筑的结实的柱子和基石,当时它被称作农田中的圣叙尔皮斯,因为,在中世纪,圣日耳曼德普勒还是一个小镇,在巴黎城外的塞纳河畔,周围是草场和菜地。大约五个世纪后,巴黎的发展突破了老城墙,与相邻新建的卢森堡宫相比,教堂就显得太小,太破旧了。堂区神父让-雅克·奥利耶(Jean-JacquesOlier),圣味增爵的同代人,也是他的朋友,自1646年开始了巨大的扩建工程。工程持续了大约一个半世纪,前后用了八名建筑师。公元1678年,工程在进行了约四十年后中断,因为堂区神父没有钱了。只能把新教堂的祭坛(惟一完成的部分)和老教堂(高和宽都比新教堂小二分之一)的大殿凑合着连到一起。1719年,新任神父让-巴蒂斯特·朗盖·德·塞尔吉(Jean-BaptisteLanguetdeCergy)为筹集资金组织了抽奖和收集银器活动。朗盖·德·塞尔吉是个出色的组织者,也是个对什么都充满好奇的人。正是因为他,我们才拥有了这个著名的圣叙尔皮斯天文日晷(在希腊语中是“指示器”的意思)。
“我在天上应该找什么……”
我们回到塞拉斯这里,他正在昏暗中审视这个日晷。他看着“一根光滑而又细长的铜条嵌在灰色的花岗岩地面中闪闪发光——这条金线斜穿教堂地板。这条线上标有刻度,就像一把尺”。直到“在那个角落,树立着一座碑,这让人感到意外。一个巨大的埃及方尖碑”(P?郾96)。铜条在方尖碑上垂直地向上。一个标准的日晷。这件东西放在一个教堂里,乍一看,的确很不适当。丹·布朗认为,这是“过去这里矗立着一座异教殿堂”(P?郾79)的补充证据。错了。或许是教堂里太暗了,以至于塞拉斯看不到方尖碑下面镌刻的铭文,它是以一句谜语开始的:“我在天上应该找什么,我在地上能够渴望什么,您是我心中的上帝,我永远希冀的天国。”然后,它很清楚地(尽管其中一些国王和大臣的名字在法国大革命时期被挖掉了)记述了日晷的来源和用处。
日晷是自上古以来最早用于天文学的器具,特别是在埃及(在埃及,使用方尖碑纪念早期的学者)。多亏这件仪器,托勒密(Ptolémée)才能够在2世纪确定地球是球形的。他手工制作的日晷可能只是用一根垂直的棍子放置在一个水平面上,影子的长度可以让人测量正午时太阳的高度以及它在不同季节的变化。圣叙尔皮斯的日晷则显得更精巧,更具戏剧性。它的构成正像丹·布朗所说,一根近四十米长的铜条从南面的耳堂开始,从祭坛的中心穿过,在北面的耳堂结束,以便爬上大理石的方尖碑。它还包括在南耳堂的一扇窗户右边高于地面二十五米处钻的一个孔。每天正午(巴黎时间)日光钻进这个孔,在铜条反应为一个点,在一年之中移动。这样,每年6月21日夏至的时候,太阳达到地平线的最高点,光点照到南耳堂地面上的一块大理石牌子上。12月21日冬至,当太阳最低的时候,光点就照到方尖碑上的铜条。在春分和秋分的时候,光点照到祭坛栏杆后面镶嵌在地面上的两块椭圆形铜牌上。
在天主教中,我们可以说,日晷可以用来确切确定复活节的时间,它应该是在春分后的第一个满月。另外,也正是这个理由,朗盖·德·塞尔吉神父向天文学家亨利·德·叙利(HenrideSully)和皮埃尔-夏尔·勒莫尼耶(Pierre-CharlesLemonnier)定作了这个日晷。勒莫尼耶在1743年完成了安装。他急着用这个日晷,因为日晷可以用在科学工作上。这个日晷在当时让科学院和巴黎天文台的所有学者着迷,他们希望精确确定地球转动的一些参数。就这样,来自意大利的法国著名的学者世家卡西尼(Cassini)——其父子都是巴黎天文台的台长——在近一百二十五年中,借助圣叙尔皮斯日晷确定了几乎与今天使用高科技手段的精度相当的度量单位。
方尖碑和圣水刷
总之,日晷为上帝和知识的荣耀而工作。塞拉斯并不知道。丹·布朗知道吗?他写道,方尖碑上部有一个“金球”,或许是为了加强物品的异教特征。但他忘记了说,在金球上,有一个十字架。科学与信仰并不总是水火不容。当然,哥白尼(Copornic)有关太阳系的著作曾在1616年被列为禁书;当然,伽利略不得不在1633年的宗教裁判所收回说过的话。但是一百年后,在启蒙时代和哲学家和学者的队伍临近的时候,他们的理论在教会里也少了许多有毒的意味。以至于他们的继任者——其中有些人,例如凯撒·卡西尼,参加了共济会——被允许将他们的仪器安放在教堂里,因为这些仪器需要大空间。圣叙尔皮斯教堂并不是惟一一座安装了日晷和铜条的教堂,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布尔热的大教堂、波兰的圣彼得教堂等等。再看看历史,宗教有时还可以得到科学的保护。如果说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圣叙尔皮斯的祭坛没有被拆毁,那是日晷的功劳。与此同时,铜条使得祭坛成为科学仪器不可分的一部分。
对其他部分,革命者就毫不留情了:小礼拜堂被拆毁,雕像被偷走,大钟被熔化,地下室的坟墓(那里埋葬着拉法耶特夫人和孟德斯鸠)被人亵渎。地下室里无数的尸骨散落在地上,人们说,圣儒斯特①(Saint-Just),国民公会的议员,曾在这里开会。圣叙尔皮斯教堂在大革命时期遭受劫难,也因大革命而扬名。1790年,共和派的记者卡米耶·德穆兰(CamilleDesmoulin)要求在这里举行婚礼。神父不愿意,人们就强迫他同意这件事。四年之后,德穆兰和他的妻子被他们的证婚人罗伯斯庇尔送上了断头台。1791年,还是这个神父拒绝在讲坛上宣誓遵守教士公民组织法。于是另一个“宣过誓的人”替换了他。从此,圣叙尔皮斯教堂变成了革命的平民演说家聚会的场所。他们就是在这里决定杀死被关押的所有拒绝“宣誓”的教士。当时有一百多人被处死。如今,在教堂里专门树起了一块牌子纪念这些“享受真福的殉教者”。
崇拜最高主宰
小说中,塞拉斯惊恐地在圣地看着方尖碑。如果他知道,在将近三十年的时间中,圣叙尔皮斯曾经是一座革命的殿堂,那又将如何?1793年,随着天主教的国教地位被废除,人们在这里敬奉理智女神(laRaison),然后敬奉最高主宰。在正门的三角楣上,我们依然可以辨认出似乎抹不掉的铭文“弗朗索瓦教民承认最高主宰和心魂永存”。后来,在1797年至1801年间,执政府把教堂出让给“有神博爱教信徒”,他们把教堂当作胜利女神(Victoire)的圣殿。这个教派把天主教和共济会的教义奇妙地混合在一起。
丹·布朗知道这段历史吗?然而它却给圣叙尔皮斯“受到共济会影响”的理论提供了素材。我们再说一些其他的场景。著名的管风琴木壳表现了一座古代神殿的正立面。这是让-弗朗索瓦·沙尔戈兰(Jean-Fran?觭oisChalgrin)(因为绘制了凯旋门的平面而名扬建筑史)在法国大革命前夜主持制作的。他是北极星的纯朴的心俱乐部会员。他还负责过两个钟楼的建造。较高的南楼上有一个三角楣,上面奇怪地镌刻了表示《旧约》的上帝希伯来文YHWH。在当时,一些人还把这座教堂称作“新所罗门圣殿”。因为法国大革命,沙尔戈兰建造的南塔没有最后完工,留下一个大窟窿,比北塔矮五米。它成了在卢森堡花园猎食的那些隼的窝。
这座教堂也激发了艺术家们的灵感。法国志怪和秘术作家于斯芒斯(Huysmans)把他的撒旦小说《那边》(1891年)里的敲钟人放在这里。丹·布朗没有提到他。相反,他详细说到维克多·雨果选择这家教堂结婚(P?郾79)。这点倒是与历史吻合。1882年10月12日,雨果在这里与阿黛尔·福歇(AdèleFoucher)举行了婚礼。这类小道消息肯定给丹·布朗的故事增加了调料,因为,他把大诗人打造成郇山隐修会的卡隆。丹·布朗还中规中矩地提到萨德侯爵和夏尔·波德莱尔在这里受洗,前者在1740年,后者在1821年。
雨果喜爱转动灵桌,萨德是共济会邪恶的侯爵,而波德莱尔则是受到秘术影响的《恶之花》的作者——因此,圣叙尔皮斯就理所当然地散发出魔鬼的气息。可是,在18世纪和19世纪,文学很自然地与秘术紧密相关。只要想一想歌德的《浮士德》、杰拉尔·德·纳瓦尔的《火焰姑娘》,当然还有维克多·雨果和他的《沉思集》、维利耶·德·利尔·阿达姆(Villiersdel′Isle-Adam)、E.T.A.霍夫曼或者爱伦·坡,这种关联就一清二楚了。此外还有巴尔扎克,借用他的话:“有两种历史:骗人的正史,还有神秘的历史。”
著名的修道院学生
丹·布朗在小说中悄悄说出一句颇有意味的话:“它的附属修道院见证过一段异教发展史,并且曾被作为许多秘密团体的地下集会场所。”(P?郾79)这是什么意思?“圣叙尔皮斯修道院”反正存在。这是由让-雅克·奥利耶于1646年创建的,他希望向神职人员教授教理和上帝之道。这个修道院最初设在圣叙尔皮斯广场(现在在巴黎近郊的Issy-les-Moulineaux),培养了无数的教士。他还将弟子派往全球各地:1791年他的学生到了美国(如今,在巴尔迪摩、旧金山、华盛顿都有圣叙尔皮斯修道院);随后教士们来到加拿大,在那里,他们参与了蒙特利尔的建设;在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各地,同样活跃着圣叙尔皮斯修道院教士们的身影。
教堂“因不太正统而闻名”?在19世纪,法国各地都接受了这座修道院的教学法和教材。布朗在此要影射什么?是影射在奥利耶“学派”学习过的名人,非常聪明的人?其中一个可能就是塔列朗①(Talleyrand),他在1769年十五岁的时候就进入修道院。与此同时,他却过着放荡的生活,同时拥有多个情妇。塔列朗在1788年被任命为Autun的主教。他在法国大革命时辞去教职,积极参加没收教会财产的工作,后来成为拿破仑的大臣,帝国里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人们送给他一个共济会成员的招牌。
大约半个世纪后,哲学家勒南(Renan)也可能是布朗试图影射的人物。勒南最初的人生目标是成为司铎,也在圣叙尔皮斯神学院学习哲学。后来他放弃了信仰,进入法兰西学院并出版了引起轩然大波的《基督的生平》。他没有把基督描写为圣子,而是把他看作一个“知名人物”(请注意,这也是《达·芬奇密码》中很有杀伤力的思想)。
在圣叙尔皮斯修道院的学生中,更具“非正统性的”人还有阿尔封斯·路易·贡斯当(AlphonseLouisConstant),笔名艾利法·莱维(éliphasLévi)的,被认为是法国最伟大的秘术学者之一,同时也是约瑟芬·佩拉当的老师。这个人我们在索尼埃神父和列奥纳多·达·芬奇那里已经见过了。在神学院学习后,艾利法·莱维于1833年成为圣叙尔皮斯的副祭职,后来因为引诱一个女学生,并发表社会主义和神秘学说倾向的言论而被清除出教会。他与所有的光明派人物都有交往,与共济会总部联系密切,还写了大量有关魔法的著作,如《绝密》、《大奥秘》。莱维于1848年成为革命战士,这使他受到斥责。他还是女权主义者,并收集和出版了弗萝尔·特里斯唐①(FloraTristan)的文章。他是“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代表人物。如果一定需要证据的话,就是秘术可以导致最激进的乌托邦思想,就像我们在皮埃尔·普朗塔尔身上看到的,走向最极端的极右主义道路。
但是丹·布朗影射的既不是塔列朗,也不是勒南,也不是艾利法·莱维。在他的书里,他留给我们一个带有使命色彩的线索:圣叙尔皮斯教堂的修女,塞拉斯的不幸的牺牲品。她叫比耶尔。桑德琳·比耶尔。与1891年的圣叙尔皮斯神学院院长同姓。历史几乎没有记述这位似乎一辈子过着平静生活的神父。但是,在杰拉尔·德·塞德和皮埃尔·普朗塔尔的传奇故事那里却有他。当时有秘密文献说,贝朗热·索尼埃在雷恩城堡教堂中发现了著名的羊皮纸文献后,可能访问了比耶尔神父。
雅各布与天使之战
关于圣叙尔皮斯还有最后一个线索有待提出。这条线索让雷恩城堡的热衷者们兴高采烈:人们在这座教堂中发现多个反写的N!反写的N?是的,它们出现在埃米尔·希尼奥尔(émileSignol)的两幅画中。画家的两次签名都用了反写的N。可是,在索尼埃神父的墓上,铭文上的N也是反写的!雷恩城堡的注释者们为此大费笔墨。他们在其他的宗教建筑中,在绘画作品里,在朝圣者刻在教堂墙壁上的铭文里寻找这些反写的N。这是简单的书写错误,还是伙计们、共济会成员、玫瑰十字会成员留下的痕迹?是重新审视基督教起源的那些“被授以奥义的人”理解的符号?是西尼亚的开头字母N——召开公会会议的那个尼西亚的所含的字母N(!)?
对于鲁马内神父来说,这些都是一堆废话。他说:“在十七、十八世纪,反写字母很流行。”生性诙谐的神父又指出了一个细节,它并不那么有名,但同样令喜欢秘术的人欣喜若狂。在希尼奥尔的一幅画中,彼拉多①(PoncePilate)的那句著名的话——“犹太人的纳撒勒国王耶稣”是用希伯来文从右到左写成的。这很正常。但是,画家还用希腊文和拉丁文写了这句话,也是从右向左写,这可不正常了。又得费一番脑筋想想这是为什么!
最后只剩下一个“好奇点”:教堂入口处的天使小礼拜堂。1855年和1861年,画家欧仁·德拉克洛瓦在生命的晚期创作了这两幅面对面的壁画。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人们称之为他的艺术誓约的《雅各布与天使之战》(作品的灵感来自记者和作家让-保罗·考夫曼的一部很有名的书),它表现了《创世记》中的一段场景:雅各布与天使的战斗。这个主题也常用在共济会分部,当作思考工作的图解。另一幅画没那么出名,是《被逐出圣殿的赫利奥多鲁斯》。根据马加比家族传记第二卷记载,公元170年左右,一个希腊国王把赫利奥多鲁斯派往耶路撒冷偷窃圣殿宝藏。结果他被一名“很可怕的骑士”抓获。鲁马内神父说:“耶路撒冷圣殿。这又该让《达·芬奇密码》读者惊喜了。”我们解释一下,有些人说欧仁·德拉克洛瓦是前神学院学员,是弃教的主教,人称“瘸子魔鬼”的塔利朗的一个私生子!这个在画家生前就开始流传的谣言,一直也没有平息过。现在该离开圣叙尔皮斯了。通过使用转换术,人们可以在这个教堂待上一辈子。
-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