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4期
解读施蛰存的历史小说《黄心大师》
作者:杨迎平
更多经典:点此访问——应天故事汇
一、纯文学大众化的典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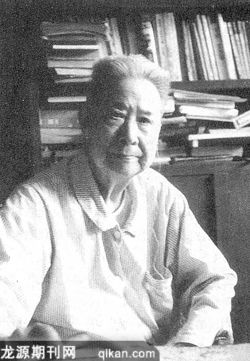
施蛰存于1937年6月1日在《文学杂志》第一卷二期上发表了他的最后一篇历史小说《黄心大师》。《黄心大师》与1932年1月由上海新中国书局出版的历史小说集《将军底头》里面的各篇都有很大的不同,小说集《将军底头》是施蛰存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运用于小说创作的实践,西方现代派的色彩更重。《黄心大师》虽然也运用了心理分析、潜意识、性心理等手法,但是,施蛰存在这里将这些手法与中国传统的写作手法相结合,从而创造了一个新的文体,这种文体正是纯文学大众化的实例。
施蛰存在《关于〈黄心大师〉》中说:“我不能不承认从前曾经爱好过欧化的白话文体,因为多数从事新文学的人似乎都感到纯粹中国式的白话文不容易表现描写的技巧。但因为近来一方面把西洋小说看得多了,觉得欧式小说中的一部分纯客观的描写方法,尤其是法国和俄国的写实派作品,有时竟未免使读者感觉到沉重和笨拙——可以说是一种智慧的笨拙;一方面又因为重读唐人传奇,宋人评话以至明清演义小说,从此中渐渐地觉得它们有一种特点,那就是与前后故事有谐和性的叙述的描写,易言之,即寓描写于叙述中的一种文体。中国小说中很少像西洋小说中那样的整段的客观的描写,但其对于读者的效果,却并不较逊于西洋小说,或者竟可以说,对于中国的读者,有时仍然比西洋小说的效果大。我们不能忽略了中国人欣赏文艺作品的传统习惯,到现在《水浒传》《红楼梦》始终比新文学小说拥有更广大的读者群……”这种情形给施蛰存带来一些困惑,也带来一些思考,怎样将国外的现代主义方法与中国的传统手法相结合,使它既是新潮的、现代的、先锋的,但又是中国的读者喜闻乐见、欣然接受的。施蛰存其实在这个时候就已经在尝试创造一个纯文学与通俗文学、先锋文学和大众文学相结合的道路,这个相结合的道路,中国现代作家从“五四”开始直至当前,可以说探讨、摸索了近一个世纪,但仍然收效甚微。我以为,施蛰存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将这种结合达到了一个高峰,迄今没有人能够超越。
《黄心大师》可算施蛰存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相融合、中西创作手法相结合的代表作,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主义小说。
施蛰存在《黄心大师》里排除了欧化的叙事和句法,将一个写性心理和潜意识的小说写得让中国的老百姓看得懂,将一个心理分析小说写成一个大众喜闻乐见的动人故事。施蛰存说:“因为我个人有这样的感觉,所以近一二年来,我曾有意地实验着想创造一种纯中国式的白话文。说是‘创造’,其实不免大言夸口,严格地说来,或者可以说是评话、传奇和演义诸种文体的融合。我希望用这种理想中的纯中国式的白话文来写新小说,一面排除旧小说中的俗套滥调,另一面也排除欧化的句法,或许这仍是‘旧瓶盛新酒’的方法,但这所谓旧瓶实在是用旧瓶的原料回炉重烧出来的一个新瓶。”①
施蛰存创作心理分析小说的初期,是不写故事的,“目的都只是要表现一种情绪,一种气氛,或一种人格。”②只是为了“发掘出一点人性”③,但在《黄心大师》里却注重了小说的故事性。在《黄心大师》之前,施蛰存用这种方法写过一篇《猎虎记》,在郑伯奇主编的《新小说》上刊登,当时有人写信给编者,说这篇小说是鸳鸯蝴蝶派的作品。而在《黄心大师》发表之后,许杰就担忧施蛰存恐怕仍有走回到评话演义小说的老路上去的危险。施蛰存说:“这两种批评,都是在我意料中的,我现在觉得,这关键是在于我所曾有意地尝试的这两篇小说都是采用一个故事(a tale)的形式,而中国小说却正是全体都是故事,从来不曾有过小说——短篇或长篇(a short story or a novel)。我若用纯中国式的白话文去写中国所没有的小说,这才看得出这文体尝试的成功或失败,如今却无意地写了两个故事,这在无论哪一个被中国式的文学欣赏传统习惯所魅惑着的新文学读者的眼里,确是容易忽略了作者在文体尝试方面的侧重,而把它看做无异于‘鸳鸯蝴蝶派’或‘回老路’的东西。无论是‘内容决定形式’或‘形式决定内容’,但决非‘内容即是形式’或‘形式即是内容’。”④施蛰存还固执地说:“我还要尝试这纯中国式的文体,无论是,也同时是,为‘文艺’,或者为‘大众’,我相信这条路如果走得通,未始不是一件有意思的工作。”⑤可以看出来,施蛰存是企图把为文艺和为大众这两者和谐地统一起来,其目的,是“把心理分析、意识流、蒙太奇等各种新兴的创作方法,纳入了现实主义轨道”⑥。
施蛰存自认为是“把心理分析、意识流、蒙太奇等各种新兴的创作方法,纳入了现实主义轨道”,而许杰所看出的却是神奇和古怪,许杰问:“究竟这位黄心大师,是神性的,还是人性的呢?是明白了一切因缘的,还是感到了恋爱的幻灭的苦闷呢?总之当时的人,没有一个能够发觉、能够理解,便是如今的作者,却仍旧是把握不住,不十分了解的。”许杰先生举例说,恼娘生下来做弥月时,一个女尼说:“阿弥陀佛,这位小姐是个有来历的人……只可惜了一念之差,不免到花花世界去走一遭。”恼娘出家时,妙住庵的老尼又说:“你的来意我早已知道,我已经预备了,叫她此刻就来。”许杰认为施蛰存相信因果之说,也格外的神奇、古怪。施蛰存说:“这是一个错误。这些话正是传说者嘴里的‘神奇’和‘古怪’,也是这个‘故事’的原形。我讲故事就说明这些‘神奇’和‘古怪’,但我的说明是在黄心大师本身的行动和思想上去表现,而并不直接做破除迷信的论文,因为在说故事的技巧上,这一部分,我可以不负责的。……恼娘在送季茶商远戍的时候,说了一句:‘不要愁,都是数。’这是整个故事中一个重大关键。一般人,自然连许杰先生也在内,把恼娘看做是个‘神性的’、‘明了孽数的’、‘晓得三生因果’的人物,可以说都由于这一句。我在写这一句的时候,曾经费了多时的斟酌。贤明的读者试替我想,我该不该用这模棱两可的句子?若恼娘不这样说,例如她号啕大哭,悲不自胜,以表示伉俪情深。或者把她写做悠然自得,绝不介意,以表示其幸灾乐祸,那么此时的恼娘的态度在整个故事的演进中是否自然?我说这是一个模棱两可的句子,是因为我正要表现在不了解恼娘者心目中,这句话是恼娘‘明了孽数’的铁证,而在恼娘自己却只是对季茶商说的一句并非由衷而发的,平常的安慰话。我们中国人不是大多数相信命运的吗?用一句话表现了两方面的观感,使他们并不觉察到矛盾,这下面才有故事出来。”⑦这正是施蛰存把心理分析、意识流、蒙太奇融入传统的故事之中,神奇、神秘,但又真实、自然、合理。
二、虚构和幻想的结晶
当施蛰存将心理分析与小说的故事性相融合时,将更突出了他创作的虚构和幻想的色彩,并且因虚构和幻想引出一段让施蛰存永久歉疚的故事。
1947年施蛰存写了一篇《一个永久的歉疚——对震华法师的忏悔》,讲了这段故事。1937年2月,施蛰存因读了明初时别人赠豫章尼黄心大师的一诗一词,不禁遐想,“颇欲知道这黄心大师的详细事迹”,但寻而不得,“但从诗词的辞气看来,从那词题下注的‘尝为官妓’这句话看来,也可约略揣测其人了。既无载籍可求,何妨借它来作现成题材,演写为我的小说。”施蛰存这“揣测”,这“演写”,就是虚构和幻想了。他用了两天的时间,以近乎宋人词话的文体写了小说《黄心大师》,登于这年6月的《文学杂志》上。施蛰存说:“至于这篇小说里的故事,百分之百是虚构的。我在篇中曾经提起过在一个藏书家那里看到了无名氏著的《比丘尼传》十二卷的明初抄本残帙,以及明人小说《洪都雅致》二册,并且也曾经引用了此二书中几段关于黄心尼记载,其实全出于伪造,正如莪相之诗于梅晴的古文尚书一样。一切都仅仅是为了写小说,从来没有人在小说里寻求信史的!”⑧恰恰就有人在他的小说里寻求信史,而且是一位虔诚地编纂比丘尼传记的法师,“于是我的荒诞无根的故事,却被采用为实录了。”⑨施蛰存知道此事时,已经是十年之后,他收到了将他的小说写进《续比丘尼传》的震华和尚的信:“阅读学生杂志,见有《黄心大师》一文,知先生亦有志于史学之研究。该文中之引言谓‘北平某藏书家庋有明抄本比丘尼传八卷’,当时见阅之下,恨不能乞为介绍借阅。余所编之《续比丘尼传》数卷,常抱憾未得将该书广作参考,迄今时隔九载,犹每为忆及。中国历史中以中国佛教史为最难研究,佛教史中以文献不足,比丘尼史更难着手。该藏书家所有明钞本藏之至今,完好无缺。不慧深恐古德幽光,永其沉埋。拟请先生代为转请该藏书家代为钞录惠寄。笔资多寡,当为负责汇奉。”施蛰存惶恐得不敢给这位病中的老和尚回信,他不想使这位老和尚失望,也不希望这虚构出来的明钞本比丘尼传被写进《续比丘尼传》,所以迟迟不敢回信。但却收到这位老和尚寄来的《续比丘尼传》六卷三册,在第二卷中,赫然有一篇南昌妙住庵尼黄心传,完全是依据了施蛰存的小说《黄心大师》写成的。施蛰存读了这篇文字,不知如何是好,本想到玉佛寺去拜访一下,也踌躇不敢,直到震华法师寂灭,才写这篇文章表达自己的一个永久的歉疚。“他永远没有知道那明钞本比丘尼传是根本没有的。他永远没有知道他的虔诚的著作里羼入了不可信的材料。让他安息在佛国里,确然永远怀着一个希望,但至少他无所失望。”⑩从这段故事里,我们再次了解到施蛰存写小说的虚构和幻想的特征,也了解了施蛰存小说的价值所在。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