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红楼梦》: 两性的和解(2)
|
大观园与警幻仙姑主持的太虚幻境相对应,一个是真实的人间,一个在虚幻的天上,而太虚幻境却是女儿们最终的归宿。因为大观园被物欲横流的世俗社会所包围,这片净土终将被玷污,乐园终将失去,贾宝玉(或作者)的“红楼梦”也注定要破灭。那些不符合成人社会准则的女孩将被清除,一个个女儿家的悲惨命运揭示了人世间的险恶。而身为当事人或见证人的贾宝玉又怎能熟视无睹、无动于衷呢?
大观园毁于姐妹们成年之际,这些花季少女最后是死的死、嫁的嫁,各奔东西。正如《红楼梦》第五回在太虚幻境中所预言的那样: 探春远嫁千里之外,与亲人骨肉分离;迎春婚后遭丈夫虐待,竟命丧黄泉;惜春削发为尼,独守青灯。史湘云介于宝钗与黛玉之间,虽嫁得如意郎君,却是好景不长。在姐妹之中,最悲惨的莫过于林黛玉,她真是为宝玉泪尽而亡。妙玉以其特殊的身份居住在大观园的边缘,她虽心性高洁,却不幸落入强盗之手。比较幸运的当数宝钗,她虽能与宝玉结为“金玉良缘”,但因黛玉之死而给他们的婚姻蒙上了抹不去的阴影,宝玉终于弃她而去。大观园原是姐妹们比诗论艺、施展才华、尽情享乐的舞台,到如今已是曲终人散,人去园空。难怪贾宝玉那样痛恨“婚嫁”,对世俗社会嫉恶如仇。到后来他也只能绝望地喊道: “这日子过不得了!我姊妹们都一个一个的散了!……为什么散的这么早呢?等我化了灰的时候再散也不迟。”贾宝玉幻想着与姐妹们长久地生活在大观园里,永不分离。如果不能一起活着,倒不如早些死了的好,姐妹们都散了,单单留下他一个,活着还有什么乐趣!
至于大观园以外,在贾府那些结过婚的女人身上都存在着世俗的印记。如: 王氏、邢氏、尤氏、赵姨娘、王熙风、尤二姐等等,她们与西门庆周围的女人相去不远,都不同程度地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内在联系。这些封建女性的特征主要表现为: 争强好胜、妒忌、贪婪、愚昧、盲目顺从等,其根本原因在于失去了女儿家纯真而美好的天性。
人类社会是适者生存的社会,在强大的世俗势力面前,贾宝玉显得势单力薄。贾宝玉不是革命者,也不是社会改革家,他只是一个偏离社会主流文化的无用文人,他根本无力动摇男权制封建社会的根基,因此他的抗争是软弱无力的。他只有哭泣、哀怨、气愤,他无力改变女性乃至自身的命运,因为他把自己的命运与女性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大观园注定要消亡,贾宝玉注定没有出路,最终只能怀着一腔怨恨遁入空门,远离尘世。看来,“两性的和解”这一理想目标还遥不可及,但是在贾宝玉身上我们却看到了一线希望。《红楼梦》通过描述贾宝玉的一生给予我们的最后一个启示就是从“自身”做起。
三、 男女之爱与性禁忌
男权制的历史经过了数千年的延续,已是根深蒂固。当社会逐步建立起男女不平等的原则时,女性价值的高低便取决于男性的态度。女性的功能主要是繁育后代,养育子女,其次是向男人提供快感,满足其色欲。在不平等的社会原则下,男性不把女性看做是与自己同等的人类,而看做是劣等人或非人类,她们是工具,是有用之物。如清代文人李渔在总结自己的性经验时,仍然认为: “女人如人参附子……”这是房中术“以人补人”论的延续。男人在纵欲的同时又要保全身体,于是,女人在满足男人的性快感的同时又成了男人养生的一剂补药。男人甚至幻想着能够因此而延年益寿。当平等的原则被打破之后,男人们是很少去考虑女人的感受和健康的。
作为社会主流文化的儒家思想,历来对“色情”二字极为敏感。孔孟礼教主张“好色而不淫”,宋明理学则认为“淫心尤恶”,而提出“诛心论”。贾宝玉显然既不符合孔孟礼教的准则,更不符合宋明理学的要求。因为贾宝玉接受的观念是“意淫——好色即淫”,他戒淫行,却不诛淫心。儒学发展的历史大致是一条“从节制到禁欲”的路线,《红楼梦》通过贾宝玉的成长历程同样实现了“从节制到禁欲”的目标,但二者却有着本质的区别,区别在于心理的与生理的之分。宋明理学的禁欲是“精神禁欲”,是对个体生命的窒息和戮杀;而《红楼梦》的禁欲是从生理上戒除“皮肤之淫”,是对个体生命的肯定。贾宝玉的“意淫”之法也因此而具有积极向上的意义和审美的价值,这是性冲动的升华。有一种观点甚至认为“意淫”是用思想和语言来进行的性活动,因而是一种极为高级的性活动方式。
道学家一方面用淫恶的罪名惩罚女性,另一方面又用贞洁的名誉来束缚女性,其实质仍然是维护男性的特权。而贾宝玉的“禁欲和意淫”一方面是自我保护,另一方面则是对女性的关爱。他实际上恢复了女性与男性平等的权利,甚至把女性看得高于自身。
以《金瓶梅》为代表的“色情文学”表面上看来是对宋明理学推行“精神禁欲”的挑战,但是,色情文学的出现只是违背了卫道士们“只许做不许说”的戒条。它在宣淫的同时并没有给予女性自由,并没有改变女性被歧视、受压迫的屈辱地位。而真正的反叛来自于《红楼梦》,因为它不仅抬高了女性的地位,而且肯定了女性的价值。贾宝玉在给予女性足够的尊重和同情之后,又把束缚男性的封建礼教和世俗功名等价值观念统统掷于脑后,于是真正惹恼了执政的皇权。《红楼梦》因此而与《金瓶梅》一起被列入淫书禁书。清代的道学家甚至认为《红楼梦》比《金瓶梅》更淫,如陈其元在《庸闲斋笔记》中写道: “淫书以《红楼梦》为最,盖描摹痴男女情性,其字面绝不露一淫字,令人目想神游,而意为之移,所谓大盗不操戈矛也。”《红楼梦》真正让道学家们感到一种恐惧,因为这与他们的主张相抵牾。
那么,在这样一种“万恶淫为首”的精神禁欲的阴影之下,男女两性生活的现状又是如何?
从古代性文化发展的历史来看,宋明理学之前并没有明确的禁欲主义思想,两性生活尚处于一种由古代延续下来的纯朴自然的状态。早期儒家的理想与社会实践只是把性限制在“发乎情,止乎礼”的范围,性的主要功能——生殖、快感、健康三者之间并不矛盾,而且在优生与养生的基础上产生了房中术。但是,随着封建礼教的加强,房中术被引入了魔道,由此派生的性原则就是贬斥爱情,并最终导致了“性”与“爱”的分离。夫妻生活变得有性无爱,只剩下生殖的义务,古老的性爱艺术堕落为荒诞的性巫术,由男欢女爱构成的闺中佳境已不复存在。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中,贾宝玉的言行无疑是背道而驰。
在关于男女恋爱这个问题上,心理学家告诉我们: 必须把“欲”和“爱”分别来看,“欲”只是生理的性冲动,而“爱”是性冲动和其他冲动之和。恋爱双方综合了性冲动和其他感情因素,它是一种相互吸引的情绪和自我屈服的感觉之和。有时,发展到极度的恋爱方式会成为一种完全忘我而利他的冲动,甚至于牺牲自我。总之,性冲动中占优势的成分有“自我”的或“利己”的,但在发展成恋爱的过程中,同时也转变为自觉的忘我和利他。在自然而正常的情形下,这种利他的成分,在性发育的最初阶段里就已经存在。甚至在动物界两性之间也存在着这种利他的理想成分,特别是在鸟类中间,如大雁会因丧偶而悲鸣,以至伤感到自我毁灭的境界。一般动物只在繁殖阶段出现短暂的发情期,但在孕育和哺育后代的过程中,雌雄之间建立了亲情,这种“亲子之情”便是单纯的性冲动在感情领域的扩大和延伸。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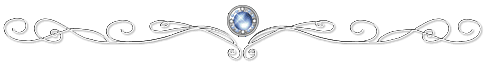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