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二十八 苑 召
|
写作《红楼梦》,是曹雪芹在西山时期的主要的志愿和事业。但是他是个大艺术家,他的生活是丰富多采的。他能演,能唱,能弹(琴),能写,能画,还能舞剑(注:曹家的家世,使他家的人都有具备能文能武的特长,这是因为康熙皇帝特别注重文武兼材的缘故,曹寅也是明白表示"读书射猎,自无两妨"的。--如果再往上推,那么他家本是魏武曹操之后,可以说从早就是主张"春夏读书,秋冬射猎"文武兼长的"世家"。)。这还只是我们确切知道的,其他的才能技艺定不止此。因此,他绝不是一个只在"案头"和"书堆"里生活的那种样式的文人学士,而是一位非常活泼富有生气、生趣的艺术家。来到西郊山村之后,在这些方面,都增加了新的生活感受和便利条件,使他得以更愉快地发挥和发展了他的杰出的艺术才能和见解。 朋友中间,则特别推重他的两方面的成就:诗,画。这一点,友人们简直是异口同声,不谋而合的,完全说明了他这两方面给人的印象的特殊强烈。 张宜泉说:
门外山川供绘画,堂前花鸟入吟讴。
敦敏则说:
题诗人去留僧舍,卖画钱来付酒家。
都是诗、画并举;其余的例子就不必一一开列。 只就这两个例子来说,张氏和敦氏各举事情的一面,着眼点不同,故此风趣各异。孤立地看,好像张宜泉的诗比较简单肤浅,而敦敏的就更为丰富深刻。其实也未必尽然。因为诗句还各有上下文在关联着,要说的"话眼"不是一回事,不能断章取义地来简单"评比"。这点留待下文略加分疏。但是为了我们这里叙述的方便,倒不妨先就敦敏的诗来分析一下看。 曹雪芹到达西郊山居以后,心情是舒畅痛快得很,可是生活也就越发窘困了,这是意中之事、必然之情。他到西山,也许多少总是有点像陶渊明的归隐的意味,尽管他们并不是同一类型的诗人或隐士。可是作为高士,虽然风流傲世,气节过人,还是必须有起码的物质生活才行。陶渊明躬耕以为计,那也得有土可耕;曹雪芹却并无可耕之土。朋友敦诚说他穷得以至于"日望西山餐暮霞"。这是诗人的慨叹和傲语而已,现实里的曹雪芹却不能真以"西山爽气"来维持生命,他是要吃饭的。 敦诚又说他:"满径蓬蒿老不华,举家食粥酒常赊。"这才是比较切近实际的一种生活写照(当然也不能按字死抠(注:按"举家食粥"系用颜真卿《乞米帖》的典故,故不能死看。《颜鲁公文集》卷十一《与李太保帖》:"拙于生事,举家食粥来已数月,今又罄竭,只益忧煎,……""食粥"本指南方人米食习俗,贫人米不足则不能蒸"干饭",只能以"稀饭"充饥;清人文集中此等食粥事例亦常见记叙,每言清寒之况一日两粥一饭过活。乾隆时代北方人,特别是满洲旗人,因嗜食面,则不一定以米为主食,穷人尤难得米食。(记满人米食面食之事的,《清朝野史大观》卷二有一则。)(张次溪先生见示冒效鲁先生题齐白石《红楼梦断图》诗有"啜汁"之语,其自注云:"喝豆汁以当茗饮兼果腹,北方窭人有此习惯。见京戏《鸿鸾禧》。"即不拘看"食粥"之例;其所解亦颇见心思。附记于此。)))。雪芹的酒,这时喝得更厉害了(笔者亲见过富家子弟、老来落魄、靠赊酒以"充饥"的人);他又是吃过"好东西"、嘴头儿馋的人(注:可看裕瑞《枣窗闲笔》:"又闻其(指雪芹)尝作戏语云:若有人欲快睹我书不难,唯日以南酒烧鸭享我,我即为之作书云。"此虽雪芹戏语,正见其落拓可哀。有人认为,这说明雪芹只吃不起鸭子,还吃得起别的。恐怕不能这样解释雪芹语意。),吃不对口,就更要以酒代食。况且当时文士生涯,公子习性,究竟不能和真正的村民野老相比,要求总是要高得多。那么,他这家计费用,到底从何而来呢? 敦诚的诗,就告诉了我们一个事实:卖画(注:按原句"卖画钱来付酒家"系用陆游"卖花得钱付酒家"旧句,易一"画"字。但此究当本诸实事。陆游诗句事,可看篇末附记。)。 当然,我们还不能认定曹雪芹就是完全靠卖画为活(当时他的画有多大销路?他的画能值多少钱?这都是重要问题),但是至少我们得以知道这是他的生活费用的来源之一。 他的画,和他的诗一样,是有家学的。他的祖父曹寅,自己工书能画,但常常称赞其胞弟曹宣(字子猷,号筠石、芷园;后因避康熙"玄"名嫌讳而改名"荃")的画法,自谦不如;而侄子曹颀又颇能"世其业",画梅花能作长干,许为多才。到雪芹这里,工诗善画,就不是什么值得讶异的事了。雪芹的画,不止一人见过(注:可看吴恩裕《有关曹雪芹八种》"考稗小记"。唯112页所记仅署"芹圃"二字款者尚须研究,盖同时江南另有画家名莘开,亦字芹圃,见《履园丛话》与《墨林今话》;又另一说字曰季张、号为芹圃的,归安人。故倘无"曹"姓或其他文字印记,尚难遽定。),又有人曾告诉我说现在还收藏着一幅。可惜都没有机会看到,不知道雪芹画法的家数、作风是怎样的,实在是遗憾的事。仅据张、敦等友人的诗句而推,可知雪芹擅画山水,也善画石。敦敏有《题芹圃画石》绝句一首,说: 傲骨如君世已奇!--嶙峋更见此支离。
醉余奋扫如椽笔,写出胸中磈礧时!
诗人把雪芹的画石,理解为是画家借石头的奇姿硬骨而抒写自己的傲世抗俗的性格和满腹的郁结愤慨,是非常有道理的。雪芹的画,想来也像他的诗,必不等闲而作,各有其用意。敦敏的诗便是很宝贵的证据。
这首诗还有另一面的可贵,就是它写出了雪芹的精神气度。我们好像看到了这样的情景:曹雪芹在痛饮之后,酒酣耳热,生气拂拂从十指出,他便解衣盘礴,濡毫舒纸,大笔挥洒,如兔起鹘落,如虎卧龙跳(tiāo),不一时,一幅惊人的杰作已然展现在眼前了。他一面雄睨高谈,当画得得意之际,则杂以狂呼大叫,声动四邻(注:如满洲诗人塞尔赫的《八艺咏》,说平郎中弼侯:"清影常书白练裙,折钗画沙屋漏痕,举觞狂叫惊四邻。"即其类也。),于是更倾数杯,浮以大白,而酒痕墨沈,谈风口沫,一时俱落于纸上…… 他大致就是这样地作画题诗的一位艺术家。这样的八旗人艺术家,在当时颇有例证(注:可参看周汝昌《红楼梦新证》增订本89页所引甘道渊、恒益亭等旗人行径事迹。按给这一类诗人、艺匠作出最好的概括描写的,当属郑板桥(他是最喜欢和八旗高人逸士交朋友的一位"怪人")的《音布》诗,其全篇云:"昔予老友音五哥,书法峭崛含阿那(nuo;阿那即婀娜);笔锋下插九地裂,精气上与云霄摩;陶颜铸柳近欧薛,排黄铄蔡凌颠坡;墨汁长倾四五斗,残豪(毫)可载数骆驼;时时作草恣怪变,江翻龙怒鱼腾梭。与予饮酒意静重,讨论人物无偏陂;众人皆言酒失大,予执不信嗔伪讹;大致萧萧足风范,细端琐碎宁为苛。乡里小儿暴得志,好论家世谈甲科;音生不顾辄嚏唾,至亲戚属相矛戈;逾老逾穷逾怫鬱,屡颠屡仆成蹉跎:革去秀才充骑卒,老兵健校相遮罗;--群呼先生拜于地,坌酒大肉排青莎;音生瞪目大欢笑,狂鲸一吸空千波;醉来索笔索纸墨,一挥百幅成江河!群争众夺若拱璧,无知反得珍爱多。昨遇老兵剧穷饿,颇以卖字温釜锅;谈及音生旧时事,顿足叹恨双涕沱!天与才人好花样,如此行状应不磨。嗟予作诗非写怨,前贤逝矣将如何!世上才华亦不尽,慎勿咤叱为么魔;此等自非公辅器,山林点缀云霞窝;泰岱嵩华自五岳,岂无别岭高嵯峨?大书卷帙告诸世,书罢茫茫发浩歌!"音布,字闻远,满洲人,死时也是"柳板棺材盖破祛,纸钱萧淡挂輀车"。直不啻为又一曹雪芹。此等写照,于理解曹雪芹之为人,最有印证价值,深可宝贵。(又如《天咫偶闻》所记的徐退,《墨林今话》所记的陈桓〔内务府人〕,皆可参看,今不繁引)。)。 和绘事有关的另外一点,还应该注意到张宜泉的那一首《题芹溪居士》诗。其全篇如下: 爱将笔墨逞风流,庐结西郊别样幽。
门外山川供绘画,堂前花鸟入吟讴。
羹调未羡青莲宠,苑召难忘(平声)立本羞。 借问古来谁得似?--野心应被白云留!(注:凡张宜泉诗皆见《春柳堂诗稿》。前后不一一备注。又所引诗第六句"立本"原刊本作"本立",系误倒。) 这首诗乍一看来不见得有什么大好处,而实际由浅入深,层层逼进,直到逼出最后结穴的主旨来为止:这是很会写诗的人的手法。诗意先从"笔墨"总纲而引起"诗""画"两大主题,然后派衍,分笔合写,双管齐下;中用唐代李白诗人和阎立本画家两人的故事作比:李白、阎立本,以他们的稀世的天才艺术成就,为皇帝、贵妃作"供奉""应制"等作品,或则暂得宠幸,旋遭迫害,或则未有"荣耀",先得耻辱(注:《旧唐书》卷七十七《阎立德传》附立本传:"太宗尝与侍臣学士泛舟于春苑,池中有异鸟,随波容与,太宗击赏,……召立本,令写焉。时阁外传呼'画师阎立本!'时已为主爵郎中,奔走流汗,俯伏池侧,手挥丹粉,瞻望座宾,不胜愧赧!退诫其子曰:'吾少好读书,……唯以丹青见知,躬厮役之务,辱莫大焉!汝宜深戒,勿习此末技。'"),总之,给封建统治者效劳服务的艺术家们,是不会有什么好出路好收局的。--而雪芹则不甘心去上这个当。 因此,有的研究者根据"苑召"的话,而疑心当时皇家画院曾来召聘曹雪芹,而为雪芹拒绝。 关于这点,当然还无法作出绝对肯定或否定的推断。张宜泉的诗,原是诗画二者平列并举的;一方面,我们既不能因有"羹调未羡青莲宠"的话而推断雪芹会有被引入宫廷作"应制诗人"的可能(当时也并无这样的制度或事例),好像就难以说惟独"苑召"一句却有所实指;而另一方面,诗家也可以因有一事,而配入一事,虚实互见,这种写法,也非罕例。如果事出无因,似乎张宜泉就不会单单想到这一层,并把它写为诗句的主要内容。我们也可以设想,当时皇子、王公们要招请画师墨客的风气很盛,有人曾想到雪芹,要荐引他去,则不无可能(注:诸皇子王公家的画师墨客、文士诗家的例子,可举先客于慎郡王府、后客于平郡王府的朱文震,客于宁郡王府数十年的汪苍霖(工诗善书,和敦敏、敦诚弟兄深交,有可能和曹雪芹熟识),客于康亲王府的袁古香,客于冰玉主人(怡亲王弘晓)府十余年的张尧峰(和明义有交谊)等人。此种人士中也包括八旗人,如礼亲王府延为记室的汪松,是佐领;在如意馆供奉的唐岱,是内务府人。唐岱,字静岩,满洲籍,工山水,为乾隆所赏识,著有《绘事发微》。),--由此也会辗转牵引而引起皇家如意馆的注意而加以招致。 不管怎样,反正雪芹像是坚决拒绝过这类的事情。这种拒绝,我想和敦敏题画石时所说的"傲骨",恐怕也可合看,大可消息。因此,张宜泉也赞叹雪芹的品格骨气,说:古来的李白和阎立本,在这一点上也比不起你;你为什么这样鄙弃富贵、视如敝屣,而甘愿在此山村受这等贫苦呢?--恐怕是山中的白云,适合你的野性狂情,故而贪恋不肯离去的吧(注:张宜泉诗末句本暗用《宋史》魏野传,野工诗,放达,后被征,拒不出仕,对使者说:"野心已被山中白云留住矣。"野,自称名也,但诗家往往活用原语,作泛义,可不拘看。)。 这正是曹雪芹的令人敬佩爱重的高贵品质的一面。 曹雪芹在山村中,穷得可以,食粥,卖画,已如上述。偶然好友敦氏兄弟从城里特意跑来看他,他也没有足够款待客人的能力,还要靠"司业青钱留客醉"--像唐代的郑广文先生一样,穷得无钱买酒,要靠苏司业"时时乞〔去声,借给〕酒钱"(注:杜甫《戏呈郑广文(度)兼呈苏司业(源明)》诗。唯敦诚原句以"司业"指谁,意见尚不一致。今只按杜诗原意解释。)。可见雪芹的生计,朋辈尽知,有的时亦加以接济。这也算是他的"收入"来源之一。 敦诚的诗,有两句也极堪注意:"阿谁肯与猪肝食?日望西山餐暮霞!"(注:餐霞本是道家修炼的典故,此处借写穷饿。)这也是写雪芹的贫况,但是诗中独用闵仲叔和安邑令的典(注:事见《后汉书·周黄徐姜申屠列传·序》。),必非泛泛无故之语。疑心此诗并非只是慨叹如今无有敬士济贫的地方官,而实是说该管的官府对雪芹还颇有凌逼之事(因为他是有罪抄家的人,还有被注意监视和被寻衅的可能),不过那语式极为婉蓄罢了(敦氏弟兄的诗大都如此;而涉及雪芹的诗,措词就更觉隐约含糊,看得出是有所避忌、深为谨慎的意思)。如系这样,那么雪芹的傲骨才更为突出,不为统治爪牙所屈伏,所以诗中才又有"步兵白眼向人斜"以及"燕市哭歌悲遇合""新愁旧恨知多少"等话语,可见内中包含的事故还很多,只是我们大都无法考见其委曲了。 我说疑有该管官吏,对雪芹犹加凌逼,是否有点穿凿附会呢?请读《庚辰本》石头记第二十一回,有一段朱笔眉批说: 赵香梗先生《秋树根偶谭》〔按此书名取自杜诗"读书秋树根"〕内,兖州少陵台,有子美词〔祠〕,为郡守毁为已词〔祠〕,先生叹子美生遭丧乱,奔走无家,孰料千百年后,数椽片瓦,犹遭贪吏之毒手,甚矣才人之厄也!固〔因〕改公《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数句,为少陵解嘲:"少陵遗像太守欺,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折克〔拆充〕非己祠。傍人有口呼不得,梦归来兮闻叹息;白日无光天地黑!安得旷宅千万官〔间〕,太守取之不尽生钦〔欢〕颜,--公祠免毁安如山!"■〔读〕之令人感慨悲愤,心常耿耿。壬午九月,因索书甚迫,姑志于此,非批《石头记》也,…… 试看这段异常突兀的话,因"索书甚迫",匆匆地记在这处本文与杜子美大诗人毫无关系的此回眉上,叹才人之厄,愤贪吏之毒,这是什么缘故?岂不正因现实中的雪芹这位才人之厄而发?我认为,这充分说明了我读敦氏诗句所生的疑惑,绝非无故。我还认为,这正说明,为了破坏雪芹写作《石头记》,该管的"上司"是用拆毁几椽破屋的手段来逼迫雪芹奔走无家的! 虽然如此,他却不是容易为贫困、艰难、种种欺凌逼迫所压倒的人,他依然是狂歌自得,孤标傲世,他的潇洒开朗的性格,挥霍谐谑的风度,一点也不因此而稍见减退。他看见气类相投、心里欢喜的人,便诗酒流连,推心置腹,谈笑风生。看见不入眼的那些俗物,却毫不客气,待以白眼,屏(bǐng)之三舍之外;得罪人,他是不顾也不怕的。敦诚说他"狂于阮步兵"!阮籍够狂了,他比阮籍还要加倍!他有辛酸之泪,却不流给人看,咽到肚里,入于笔下;他在人前最大的牢骚表现不过是"一醉■■白眼斜"而已。 他闲来时也喜欢行游散策,逐胜探奇。他住的那一带,名蓝古刹,固然很多,萧寺荒祠,也是不少,大大小小,遍布于林峦泉壑之间:诸如碧云寺、卧佛寺、观音阁、红门(普福庵)、黑门(广慧庵)、五华寺、普济寺、水塔寺、太和庵、圆通庵、天仙庵、广应寺、宏化寺、宏法寺、隆教寺、广泉寺、关圣庙……:仅在这香山、寿安山、聚宝山、普陀山、玉泉山一带,号称三百寺。这里面,有时住有名僧,如卧佛的青崖与莲筏,瓮山的无方等,也有不知名而隐于释道的高人大德,雪芹有时访访他们,作半日清话。雪芹是不信什么宗教迷信的(注:他对迷信是竭力讽刺嘲骂的,《红楼梦》中例证最多,可无待列举。),他把这些方外的谈侣,也不过看作畸人奇士,当然也可以谈谈哲理,但也有时只不过如敦诚所说,是"暇时阅两三贝叶,或与一二老宿相与啸傲于荒林古刹中,以少息世缘耳。"(注:《四松堂集·答养恬书》。)而且,他所到的败寺荒庵,也许根本并无僧道在内,他只是流连景色,凭吊残踪,因而兴感题诗,或如敦诚所云"题诗人去留僧舍〔一作壁〕",或如张宜泉所云"君诗曾未等闲吟,破刹今游寄兴深",在断碑颓壁之间,去领取"蝉鸣荒径遥相唤,蛩唱空厨近自寻"的风味。在那种地方,正是"寂寞西郊人到罕,有谁曳杖过烟林",只有雪芹一个,徘徊瞻眺,感兴无端。 此外雪芹最爱到的地方就是酒家。他平常日子赊了酒回家,或就地坐下喝个满意,攒到一个日期,卖了画,得些钱,再去结还账目。传说里提到,在卧佛寺东南佟峪村的关圣庙前,旧有小酒店(注:出樱桃沟、退谷的南口,走几步,便到佟峪村;此村位于健锐营的正白旗、镶黄旗北营子之间。与北沟村相去很近。从佟峪村再往东即可到四王府。四王府一带,旧日以产甜酱、小菜著称,下酒似不乏可口之物。至于此一小酒店,是否即为雪芹常到之处,只可聊备一说,以助想象。郑板桥赠保禄(满洲人,字雨村,笔帖式)诗云:"无方去后西山远,酒店春旗何处招?"无方,僧名,住瓮山(今颐和园一带),可见当时西郊的酒店青帘,也是一种风土特色。),雪芹就常到这里款斟慢饮,论古谈今。 以上就是我们所能窥见和想象的雪芹在西郊时期的生活梗概。 〔附记一则〕
盛如梓《庶斋老学丛谭》卷二记陆放翁云:"公集载,城南陈翁,以卖花为业,得钱悉供酒家。不能独饮,逢人辄强与共醉。一日,过其门访之,败屋一间,妻子饥寒,--此翁已大醉矣!殆隐者也。为赋诗一首:'君不见会稽城南卖花翁,以花为粮如蜜蜂;朝卖一株紫,暮卖一株红;屋破见青天,盎中米常空。卖花得钱付酒家,取酒尽时还卖花;春春花开岂有极,日日我醉终无涯;亦不知天子殿前宣白麻,亦不知相公门前筑堤沙;客来与语不能答,但见醉髮覆面白■■'"。汝昌按:敦敏赠雪芹诗:题诗人去留僧舍,卖画钱来付酒家。正用放翁诗中故事,以为雪芹写照,语语切合。敦氏弟兄诗,粗看平易,而含蕴深厚,未可为浅人道也。庚子上元后二日记。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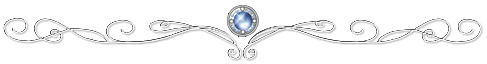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