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炸弹下的故事
作者:[英]杰妮·特纳
1940年至1941年的那场德军大规模空袭以后,又过了一段相对平静的时期,到了1944年的初春,伦敦又遭遇到一次敌方军力突然加倍的小规模空袭。两位女子坐在马里勒波路的一堆沙袋上喝茶。茶水有些发绿,可能用氯处理过;奶粉结成一团一团的;即便如此,两人像其他女人一样,照例争着要付钱。一个沙袋破了,泥土和些许残花败草露了出来。“‘大自然战胜了战争,’”两位新朋友中的一位“模仿播音员的声音说道,人们为无线电广播站撰稿时总会这么写——他们在被炮弹轰炸的区域发现了各种重未见过的野花、以前从未见过的鸟类,等等等等——没劲得要命。”似乎那些模糊褪色的老照片里的一张活了过来,开口说话了。
《守夜》是莎拉•沃特斯的第四部小说,这是她首次放弃了那“令人战栗的”、“戏仿的”、“维多利亚式的女同性恋”的主题,该主题曾在《轻舔丝绒》(1998年)(Tipping the Velvet),《吸引力》(1999)(Affinity),《指匠情挑》(2002)(Fingersmith)等作品中得到深入,并得到大众和评论界的一致好评。“令人战栗的”“戏仿的”“维多利亚式的女同性恋”都是沃特斯用来形容自己的术语——虽然总的来说并不都用得恰当——可以说这些词是既足够准确又有失偏颇。这些作品确实都是戏仿作品:一个同性恋理论家有可能会这样表现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一身朱迪丝•巴特勒式的装束(注:朱迪丝•巴特勒,著名哲学家,后结构主义、酷儿理论、女性主义者。研究对男女同性恋、双性恋等性身份的边缘群体。),还有福柯笔下的监狱和疯人院。(注:福柯,法国著名思想家,同性恋者。)这些作品也确实让人战栗,书里尽是些刚刚性觉醒的年轻女性,置身于一些女扮男装、乔装掩饰和撕破的绸内裤之类的场景中。但这些作品却没有这些标签令它们听上去的那么夸张,也没那么刻板。有一类作家打算从亨利•詹姆斯称为时代小说的“致命的低级”中牟取利益,沃特斯根本就不是他们中的一员。她的作品总是富于情感、 灵巧、精确。
沃特斯决定将她对历史方面的兴趣转移到别处是个勇敢之举,却也并不让人感到意外。那部精彩的《指匠情挑》当然把对十九世纪同性恋主题的戏仿发挥到了极致。故事是耸人听闻的情节剧:沃特斯记得在创作这部小说时,自己在书桌上摩擦双手,写到情节转折处还会着魔似地哈哈大笑。然而,从骨子里说,小说存在的目的并不单单是为了曲折的情节,而是为了一种噩梦般的、无尽的危机感:如迷宫一般无法走出的维多利亚时代女性的困境。然后,在小说倒数几页,出现了一桩不合情理的惊人事件——最最可恶的背叛与抛弃,这一揭示如同“漆黑夜空中划过的一道闪电一般尖锐而清晰”。这是她近期的小说中最有力、最创新的一刻,也是最沉痛悲伤的一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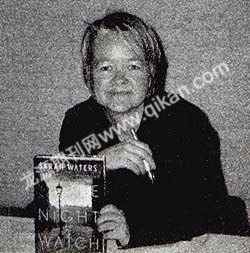
沃特斯的新作是用倒叙来讲述故事,分别以1947,1944和1941为时代背景,分成三部分。小说这样开头:“你现在已经成了这样一种人。”这个在责备自己的人物叫凯,她踽踽独行,观察着房东的访客,身上穿着一条灰色内裤和一件无领衬衫。她像个迷失的鬼魂一样游荡在那个肮脏灰暗的租来的房间里:出门前,她穿上休闲裤,套上男鞋,袖口处挂上银链。另一位书中人很喜欢观察她,当然只是出于好玩,叫她“巴克上校”: 说不定“她当过飞行员,或在空军妇女辅助队当过士官什么的。换句话说,她就是那种女人:在战斗中快乐地冲锋陷阵,然后潇洒地离开”。事实也正是如此,凯在战争中为伦敦辅助救护服务组织工作,从被压在地下的建筑中运出死者和伤员,她整夜驾驶一辆破旧的灰色小车,穿梭于破损不堪、硝烟弥漫的街道上;但这并不是她全部的故事。她就是《指匠情挑》中结尾处那个最后哀声痛哭的伤心恋人的翻版,只不过她身处在四十年代。
在小说的三个部分中,有四组主要人物。除了凯,还有海伦和朱莉娅,一对关系确定、生活安逸的女同性恋者,海伦是在婚姻介绍所工作的职员,朱丽娅是崭露头角的犯罪小说作家,最近刚把一部作品卖给英国广播公司。只不过, 朱莉娅的良好家世,让海伦倍感威胁,令她陷入疯狂的嫉妒;似乎“有个形容枯槁的小丑样的东西”被塞进了她的胸腔里。维芙是海伦的同事,性格温和,妩媚动人,“就在表面之下,隐藏着一层忧伤”,作者如此描述她。 她悲伤的起因之一似乎是雷吉,维芙的恋人,一位有妇之夫。“我已经为你忍耐了一整天了,维芙。”他们最后一次约会时雷吉这么说。她并不相信他的话,但为了让他高兴,还是把手伸到他裤子里。
维芙的弟弟,身材瘦弱、“长相古怪”的邓肯,在一家蜡烛厂有份奇特的工作:他的老友罗伯特•弗雷泽看到他在一个福利会性质的地方工作,那里专为伤残人士提供就业机会,感到难以置信。而且,邓肯已经搬去和一个他称为霍拉斯叔叔的上了年纪的人一同住,但那人并不是他的亲戚,“那个穿一身黑色套装的男人看上去精明能干,像个开殡仪馆的。那个小伙子耐心、严肃、英俊——在斯坦利•斯宾塞的画笔下……这是青春年少的象征。”但一个像邓肯这样的工人阶级的男孩起初怎么会认识念公学出身的弗雷泽呢?这却是沃特斯乐于在开场时就解开的为数不多的几个迷团之中的一个。他们几年前就认识了,那时他们是苦艾丛监狱的狱友。
对任何沃特斯笔下的人物来说,生活都不让人满意。每个人以不同的方式开始故事,活得都不容易,他们在焦躁、消沉中观察、等待着。生活条件是怪异、模糊、而又委曲求全的。人物之间的关系显得扭曲而反复无常,被隐藏着的阻碍打乱了平衡关系。当然,刚刚结束的战争引发了很多麻烦:单幢房子孤零零地矗立在那里,那是整幢房子里唯一保留下来的;小圆面包里不再加糖了,用糖精来代替;婚姻介绍所生意兴隆,复员的士兵都认不出他们的妻子了。然而,从某些方面来看,沃特斯的主人公在战争时期更快活些。“回想起来,真好玩。”某人说,“那时,有些事情更容易些。做事都有一套办法,是不是?另有他人替你做好了决定,告诉你那是最好的办法,你照办就是。”一部分是由于这个原因,你才失去了热情、目标和方向,才让这些人灵魂四处漂泊。
凯看来是个两次失去爱人的女子, 首先是在起初情况不明时失去了爱人——“同样的事发生在成千上万的人身上,他们和我们一样。谁没有失去亲友或财物呢?我走在伦敦的任何一条街道上,只要伸出手,就能碰到一个失去情人、孩子、朋友的男人或女人。”——战时的工作也很适合她。作者很漂亮地处理了小说中的一个次要主题,那就是,在没有年轻男子挡道的情况下,战争是怎样解放了像凯和她的好朋友米奇这类女性。她们可以留短发,可以穿着粗革皮鞋、打着领带“冲锋陷阵”,并受到每个和她们一起工作的人的尊重,只要胆子够大,会驾驶货车,她们的私生活如何无关紧要。接着,战争结束了,古老的秩序又恢复了。米奇在一家修车厂工作,在加油处做服务员,修车厂的前院是少数几个女人能穿长裤而不受指责的公共场所之一。“你知道战争已经结束了吗?”面包店里,有个男人嘲笑凯;她出门时,他肯定在她背后使了个什么眼色,其他顾客都笑了。“最好是厚起脸皮,”她想,可能这类事她时刻都会碰到。“昂起头,大摇大摆地走,以显得有个性,有骨气。不过,有时就是没力气去摆这个架势,有点累,如此而已。”
小说漫长的中心部分,发生在1944年初那场可怕的空袭期间。由于我们已经见识过了1947年,知道主人公们不会死于1944年;于是,在我们期待这些神秘的生物能更多地展示他们自己时,原先的紧张感就被一种奇特、悲哀的关注取而代之了。警笛声呼啸,爆炸声隆隆,海德公园的高射炮开始响起来;读者和凯、米奇一起,一头扎进了那训练严格、无私忘我的救护工作之中——“不是无所畏惧——只有傻瓜干这种工作时才会无所畏惧——而是清醒、警觉、充满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