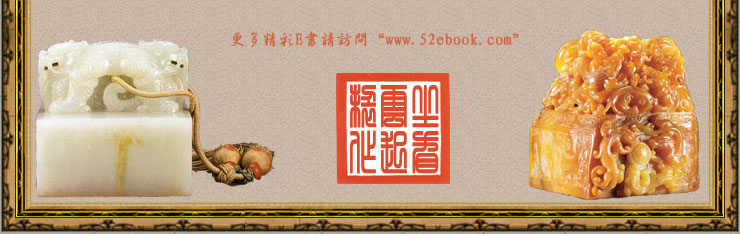发明“天人感应”大儒董仲舒,一万个也想不到信奉他的理论的人会中了魔似地追求符瑞。无论明主还是昏君,都愿见到上天赐予他祥瑞。没有祥瑞,刘秀应天命的谶言就少了说明力。只有“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的谶言还不够,他希望更多的祥瑞。--鬼话与符瑞,他都需要。
刘秀构成了历史上的一个独特的景观,作为最温和与最开明的皇帝,他又最迷信、最爱符瑞。谁要反对符瑞、谶言之类的,他肯定跟谁翻脸。在他的知识结构与意识形态里,灾异与符瑞是截然相反的东西。他经历了东汉末年的社会混乱,特别惧怕灾变;要彻底消除恐惧就得让符瑞屡现。
尽管他受益于谣,但谶谣并非全是吉祥之物,有的被称为“诗妖”、“谣妖”,正如服妖一样。所谓服妖就是穿奇装异服成流行时尚。人们猜测董卓进京,跟服妖有关。“灵帝好胡服、好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竟为之”,史称此为“服妖”。“其后董卓多拥胡兵,填塞街衢,虏掠宫掖,发掘园陵”--成了东汉初年人们一个禁忌式记忆。
【注7】《水浒传》中杨志求官,多少也是一个证明。
刘秀开辟了汉家第二帝国,企盼上天赐给他符瑞,让他用祥瑞的气象来营造帝国的政治环境。刘秀追求符瑞的另外一个动机,还在于让那些心怀异端如隗嚣者放弃谋求最高权力的打算。隗以为江山是可以轮流坐的,因为象刘邦那样的一介平民都能奋斗成皇帝,还有什么人还能呢。军事割据者隗嚣,最初起兵,也是打的恢复汉室的旗号。等刘秀基本上拥有了中原后,他又不肯服从刘,于是,隗刘间屡有试探性来往。隗嚣占据西州(今甘肃天水一带)时,自称西州上将军,以马援为将军,以班彪等人为宾客即参谋人员。班彪力劝他回归中原,两人就天命屡开过激烈的辩论。隗嚣以周制崩溃、战国出现为依据,认为江山轮流坐是天下大势。班彪反驳说,汉制与周制不同,周室是根小枝大,而汉承秦制是根大枝小,所以王莽只能危害中央,无法伤及基层;假冒刘氏的人也不少,所以汉室恢复有望。隗嚣说:“你说的周汉制度不同,我认可。至于那愚材利用刘氏之号以图兴汉,就没什么指望了。以前奏失帝位,帝位如鹿奔于荒原,大家共逐。谁会想到刘邦这么个平民能得到呢。那时百姓脑子恐怕连汉王朝的影子都没有!”班彪见口头论战说不服隗嚣,就用一篇文章回应隗,写道:
一般人只看见汉高祖是平民发迹,却不知其中有凭智慧力量得不到的东西。那就是命运!天子的尊位是不可妄处的,象韩信黥布一样勇猛、象项梁项羽一样强、象王莽一样因时而篡的人,最终不都丢了命吗?真正的英雄豪杰是通晓大义的,深谋远虑,知道神器有主,不要贪心得不到的东西。如此,荣华富贵可传给子孙,自己也可怡养天年。
隗嚣听不进他这一套去,仍自行其事。倒是后来的钱镠深谙此中道理,做起割据的主人来,名义上仍听命于中原的皇帝。
在刘秀统治的三十二年间,几乎征战不息;在无休止的战争中,无人向他呈现符瑞;等到战争基本平息,他也快到了生命的尽头。
建武三十年(公元55年),经过了水灾、日食、蝗灾等打击后,符瑞出现了。“是岁,陈留雨谷,形如稗实。”--天上降下一种谷粒,只是比正常的谷粒小,有如野谷子的粒。
这年离刘秀去世还有两年。这年,北匈奴也来进贡,表示认可汉家的威力秩序。
第二年,改了元,称建元中元(公元51年)。这一年,全国各地报告出现甘露,最初的发端是夏天的洛阳平地出了一眼泉水,泉水很甜且能治病;除了瞎子、瘸子治不好,其他有长年病的人一喝,病就好。于是,“各郡国频上甘露”。
正式的中兴征兆出现了。群臣引西汉宣帝时代每有瑞就改元的例子,建议让史官专门写一本符瑞集。刘秀心里好高兴,不过,表面上还很谦虚,没批准写专集的建议。但是,在甘泉涌出前的四个月前,他本人还专心志致地研究图谶之学呢!半年之后,他对图谶的兴趣再长,终于发生了桓谭的冲突事件。(见第六章)
他盼到了真眼所见的符瑞,也了却了他多年的心事。天下太平了,自己也该真正歇息了。
甘泉出现后不到一年,仅十个月后,这位伟大的中兴之主、卓越的政治家离开了人世。从此,第二帝国开始了秩序化的统治,直到桓灵时代灾异屡见,如服妖、谣妖之类。
从刘秀的一出生,他的名字便与符瑞联系起来。他出生的济阳县,生出了有九个穗子的谷子。古人称这种现象为“秀”。于是,他的父亲刘钦就给儿子取名为刘秀。
洛阳出了甘泉,给了他莫大的安慰,也给了他生命始点一个最好的注释。
与刘秀的幸运相比,其他喜欢符瑞的帝王却远没如此幸运。远的不说,看看刘秀之前的王莽就太清楚了。王莽为了求得符瑞,已经到了唆使他人造假的地步。
为了制造自己取代汉家的政治氛围,于平帝元始元年(公元1年),让益州刺史劝塞外的蛮夷即少数民族向汉朝献瑞。自称越裳氏的少数民族献给汉朝一只纯白雉【注8】。如何把这只白色的野鸡从四川的西部送到长安倒不是个大问题,问题是语言不通,要经过几道翻译。好比一个只会阿拉伯语的人和只会汉语的人交谈一样,必须找一个既会阿拉伯语又懂德语的人外加一个懂德语又懂英语的人和一个懂英语又懂汉语的人一样。两个人的交流,须经五个人来完成。
【注8】相传:帝尧唐陶氏五载,南夷有越裳氏,重译来朝,献神龟,盖千岁,方三尺余,背有科斗文,记开辟以来;尧命录之,谓之龟历。
翻译问题解决后,就是如何把纯白雉这符瑞表达为政治功迹的问题了。
王莽向太后告白:越裳衣不远万里,运来了纯白雉,歌颂我大汉政治清平,应当把纯白雉献于宗庙,用以祭祀。
王莽实权在握且那个时代特别重视符瑞,太后自然要采纳权臣的建议。于是,汉家的群臣开始为王莽铺设通往皇帝宝座的道路。大家建议说:“王莽功劳盛大,可比周公,应称其为安汉公。”太后自然又听从了建议,并吩咐专人办理加号事宜。王莽还在表演,假惺惺地四次推让,并装病不起床,说自己实在担不起这个荣誉。
伪装归伪装,秘密策划还得进行,他婉言示意公卿上书,让太后放弃监国的权力。太后由于年事已高,顺水推舟,说:“从今以后,有封爵的事告诉我一声就行了,其它政事一决于安汉公。”
这样,王莽的权力几乎与皇帝相等了。一个伪造的符瑞就能发挥如此之大的作用!一只绝对伟大的白色野鸡起了百万军队所起不了的作用。
王莽在奔向最高权力的道路上,不遗余力地追求符瑞,好让整个取代过程更有神性。
元始五年(公元5年)冬天,王莽毒杀了汉平帝,开始征立宣帝的玄孙。与平帝平辈的宣帝的曾孙都长大成人,王莽骗不了他们,他便以平辈不能继位为由选宣帝的玄孙。
明眼人一看,就知:这不是明摆着欺服人吗?
欺服人还要用神性来装扮。有人奏报,在浚井时挖出一块白色石头,上面有红字:“告安汉公莽为皇帝。”不过,这次造假有点太仓促了。已经冬天了,十二月了(腊月),长安周围的人谁会在大冬天淘井呢?这不妨事,王莽因这一块石头,顺理成章地成为“假皇帝”即代理皇帝。接下来的故事,就无须讲了,王莽从制造了纯白雉的符瑞后也等于把自己推上了不归路。
更有无耻者,在王莽的不归路上,助他一臂之力。初始元年(公元8年)冬十二月,哀章做成铜匮,呈献给王莽。哀章称是神赐给他的,让他到高庙里告诉刘邦的在天之灵:应该把帝祚转给王莽了。
王莽虽比不上后来刘秀的老练,但他的聪明劲作绝对在刘秀以上。艺高人胆大,胆大增技艺,一切全仗自己的精明而行。
“名应图谶”之说,也屡害人。《新唐书》所记董昌利用图谶夺取江山的造反活动,无疑是上了别人的当。
民间闲人(文士)山阴老人观察到位居高官的董昌有不满情绪,借机散布了一首自作的谣。谣曰:“欲识圣人姓,千里草青青;欲知天子名,日从日上生。”
“千里草青青”几乎任何有点历史知识人都知道是“董”字,因为东汉末关于董卓的童谣已经给此字定了格。“日从日上生”虽然不怎么规范(--应为“日从曰上生”),但牵强为“昌”字不为其过。更兼民间谑浪之语有称曰字为“短日”者。于是,这个关于圣主名字的谶言打动了怀有不满的高官董昌的心。
董昌是地方官(义胜节度使),以暴虐苛敛为已任,向朝廷的贡献位居各方之首。朝廷不断给他虚位以拢络他,加检校太尉(代理三军总司令),但该衔只表明正一品,无实权;同样,加给的同尚书名下平章事的头衔,也只是享受总理级待遇,而加封给的陇西郡王之爵也比真正的王爵差一等。他请求朝廷封他为越王,朝廷不答应。于是他大发牢骚,说:“我每年向朝廷进的贡已经不计其数,朝廷怎么还吝惜一个越王呢?”
看透了他心思的人,鼓动他说:“越王又算什么地位呢?不如称帝为好!”一时间,预言董昌代唐的谶谣到处都是,山阴老人的谣最精典。
终于,董昌于乾宁二年(公元895年)称帝,国号大越。
贸然称帝自然遭到讨伐,在一年多的拼杀后,他被擒获,全家三百口人全被杀害。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董昌贪吝无比,在城池遭到围困时,竟然还扣减士兵的粮食,并借战时紧急状态征敛民财。至城破时,光金帛杂货就有五百间房子的库存,仓库有粮三百万斛。
多亏他没当成皇帝。要是当成了,不知百姓该多受多少盘剥。
至于他悉心企求的越王封号,最后也落到了剿灭他的钱镠身上。
制造董昌应天命谶谣的山阴老人,毫无疑问是一个狡猾的政治分利者。他洞察到唐家天下不可能维持多久,故而鼓动董昌起来夺取天下。成功了,他会大发利市;不成功,只不过由董昌及其家族与承担后果而已。董昌是个志大财疏的军阀,完全称不上政治家。以他不顾民力之邀功论,就能看出他的刻毒;以唐室不赏而一怒翻脸,就能看出他的浅薄。他的败笔从赏给山阴老人百匹细绢就开始了。何以此论?看看他失败后留下的敌手“遗产”就知道了。
与董昌相比,钱镠却是个聪明的政治商人--投机家。起初,他追随董昌剿黄巢,起了家,任上节度使。后来,在董起事自立后,他以兵相威,劝董守住郡王之位、享人臣之极。最后,与自己最初的恩主划清界限,并一举消灭之。再后来,后梁封其为吴越王,终成一方霸主。他比董聪明,即不称帝,又过够了皇帝瘾。称吴越王时,其仪卫与天子一样,属官的建制也俨然一个朝廷。
比董昌聪明而有胆识,且取得了最大成功的当属朱元璋。尽管两人相隔年代久远,但利用谶言的手法大体一致。朱元璋在取得一定实力后,自己向社会散播了一首童谣:“塔儿黑,北人做主南人客;塔儿红,朱衣人做主人翁。”
“朱衣人”几乎直白地告诉人们,他朱元璋必定会取天下,成为天下的主人翁。
他的成功并不在于谶谣,而在于他的战略眼光,至少,他绝对不会犯董昌那样的低级的错误--在被围困时还要克扣士兵的口粮。
聪明的政治家嗜好符瑞,糊涂的政治家也乐此不疲,尤其把王朝导向败亡的君主,似乎更重视符瑞,除非他让灾变吓出了心理疾病而不敢奢求符瑞。
亡国之君赵佶在成为金国人的俘虏前过了二十多年的太平日子。当然,一直延续下来的文人党争还是没变,但对他的生活影响不大。他正式上任的第一天,就出了怪事儿:有一道赤色的云气横贯天空。右正言任伯雨给他写信说:“这是一种灾变,希望皇上您清平理政,用忠去奸,把灾异变成符瑞!”
在他执政的第七年冬天,有人报告:乾宁军(今河北青县)出现了黄河清的现象,从乾宁军往下,有八百里,清水时间保持了七天七夜。
宋徽宗闻报,大喜,下诏把乾宁军改为清州。报告的时间是大观元年(1107年)的十二月。所有接到报告的人犯了一个王莽式的常识性错误:腊月可是结冰的季节呀!既没人淘井去,河里也不会有流水。
但报喜总比报忧强,常识性的失误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因为黄河清这种现象太不易出现了,它是政治清明的表现呀!
既然黄河清的政治谎言被吹上了天,那么自然也就没人翻开史书查一下,黄河清实际上与政治清平并无直接关联。东汉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夏四月,黄河出现过真实的水清。但桓帝的败政没见过任何好转,反而愈加败坏。这年,二百多名文人遭到逮捕,历史有名的党锢之祸开始了。第二年(公元167年),他也在无奈中死去。如果他的死意味着清明政治的开始,那么黄河清还有意义,但继他而上的灵帝是个治德更加腐败、治能更加低下的家伙。
身为艺术家的皇帝赵佶似乎不太爱考证历史,更有趁势之人效法王莽时代哀章向最高当权者献礼,给生活在沉闷的无奈中的政治家们带来一个制造欢快的机会。
大观二年(1108年)春正月初一,赵佶在大庆殿举行接受八宝的仪礼,并大赦天下。为什么死水中会掀起微澜呢?原因是有人前几天献了宝,把黄河清的宣传效应又推向高潮。献宝的人进献了一枚六寸见方的龟纽玉印,上面的印文是“承天福、延万亿、永无极”。赵佶喜不胜收,下诏命此“宝”为镇国宝。马上又找了一名技术精湛的玉石匠,刻了六枚皇帝专用印章,六印章与秦为六宝玺数目一致。不过,赵佶的心气比秦始皇大,他要超过秦始皇。这六枚新印与民间进献的镇国宝并自己日常用的受命宝合在一起,称为“八宝”。
接下来的事情,似乎与黄河清与献宝印所代表的意义不大一样了。大观三年(1109年)夏天里(六月)太阳出了黑子。怎么办?用蔡京当挡箭牌吧!免他的官就是了。但这并没有完全消除灾兆,大观四年(1110)夏五月,慧星出现。他下令求直言,让天下人指出朝政的过失,并且在每一次拿蔡京当替罪羊,流放他出京城,到杭州去住。
符瑞的兴奋剂作用与星相的灾异示警让赵佶处于深深的两难境地。赵佶开始信道教,道教奇异的政治催眠功能让他很满足,他找到了神仙的感觉,让神职人员向天神请示,封自己为“教主道君黄帝”。就在得到册号的那一年即政和七年(公元1117年)的冬天,有一颗像月亮一样的星,向南运行。(按现在的观点应是外星飞船)--对于这个飞行物,没人言之为符瑞,也无人言之为灾变。因为没人能找到合理的本文来解释。但徽宗自有他的说法,他宣称:将有天神降临。
至于有否天神将临,历史无载。反过来,这倒说明赵佶已经陷入了谵妄状状态。
转过年来即重和元年(1118年)春正月,第九枚宝玺制成。制印的材料是于阗国(在今新疆和田县)进献的,玉长超过二尺,为前所未前。不过,这次他没举行盛大的庆典。
癫狂的状态,不久便被现实粉碎。
先是方腊起兵,后是妖气出气。
妖气确实很怪,几乎是死亡的代名词。神宗元丰末年,一个大如坐席的怪物出现在皇帝的寝宫之上,不几天神宗归了天。哲宗元符末年,这东西再现,哲宗亦死。赵佶的政和年间,它竟然白天出现。怪物周围被黑气笼罩。宣和三年(1121年),妖气再现。与妖气相配合,洛阳郊外出现了怪物。怪物像人形,但能四腿着地,所以又象狗,夜间,出来吃小孩子,后来竟然白天也为害不止。人称那东西为“黑汉”。“黑汉”在洛阳闹腾了两年,才渐至平息。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有坏人意然冒充黑汉干坏事。
乱了,天下大乱就要开始了,但节奏还是慢悠悠的。
政和七年(1125年)九月,一只狐狸爬上徽宗的床上,像个人儿似地端坐在那里。
也有这个月里,有一个卖菜的人像吃了迷幻药似地称自己是赵匡胤和赵琐的使者,在宣德门下大骂:“太祖、神宗派我来指示你们,现在改正错误还来得及!”卖菜人被促进开封府,一夜后醒来,他说:“我说什么了?啊?!我什么也没说呀…”
这一年的这一月,离靖康之变即赵佶赵桓父子成了金人俘虏的靖康二年(1127年)四月,还有一年七年月,不到两年。
黄河清在中国古代政治中有着深刻的含义,也是话语权争夺的一个焦点。关于东汉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的那次黄河清,虽然未引发大规模颂赞与庆祝,但是引来了强烈的反义表达。因为,那个时期的政治太败坏了,已经招致了底层知识分子的普遍反感。黄河清的现象发生在夏四月,到了秋七月就发生了逮捕李膺杜密的事件,党锢之祸进入了高峰期。此时平原人(今山东平原县)襄楷上书桓帝,指出自春秋以来,黄河从来就没清过,现在黄河清了不是好现象--完全的反义话语。他的信写道:
我听说皇天从不讲话,只以天象显示旨意。我发现作为五帝之坐的太微、天庭却有金、火罚星在其中扬光。在占卜上,表示天子凶险;又全部进入房星、心星,按占卜原理上讲是没有后代前代事业的象征。前年冬天,气候严寒,竹柏损伤枯萎。我从老师那里听说:“柏伤竹枯,不出三年,天子身当其冲。”今年春夏两季,霜雹、大雨、雷电接连不断,这是对臣下作威作福,用刑残酷苛刻的感应。真正的官员志在铲除奸邪,却将他们从远处逮捕加以拷问;三公为他们哀求,却遭严厉谴责。汉王朝建立以来,从没有象今天这样绝进谏、诛贤良、用苛刑的!自从春秋以来,黄河从没有澄清过。我认为,黄河是诸侯的位置。清澈,属于阳刚;浑浊,属于阴柔。黄河应当浑浊反而澄清,是阴柔要变阳刚,诸侯想做皇帝。只有京房《易传》说“黄河水清,天下太平”。如今天显变异,地现妖怪,人间发生瘟疫,三者同时出现,黄河反而澄清,就好像《春秋》中讲到的麒麟不应出现,孔子记下来,认为是灾异一样。希望陛下抽出时间召见,我将极尽全力详细陈述。
桓帝及朝中重臣自然不会接受如此强烈的反义刺激,反而指控襄楷违背儒经、诬蔑皇帝,交付司法部门予以处理。
到了宋徽宗时代,显然是忘了历史上曾经有过襄楷事件——与黄河清有关的政治案件!
当皇帝是个很无奈的事情。尽管像王莽、董昌、袁世凯那些人对此十分热衷,以致于搭上了性命,只不过是为追求一个轰轰烈烈的过程罢了。真地当长了,特别是太平时代的皇帝就十分乏味了。
人,都怕简单而重复的生活。
这个最朴简的道理对赵佶起作用,对赵佶之前的帝王也起作用。赵佶是个才华横溢的艺术家,无论如何他是坐不静、闲不住的,二十五个年头(对他的心理来说,想像得还要长)可怎么打发呢。十八岁(虚岁十九)就继了位,其间不折腾点事儿,哪受得了。所以,他要借道士来活跃气氛。在他掌握最高权力十三年后,他开始追求心灵的籍慰。这个时候,大宋王朝虽然也有些危机,但还不成其为大问题,并且与大宋为仇一百五十年的辽国国势衰微,走上了灭亡的不归路。
赵佶即位时,北宋经过神宗变法(虽然失败)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财政收入,加之哲宗时代十五年努力,国家财政已经大为好转。面对充实的国库,赵佶接受了蔡京“丰亨豫大”的财政政策,大肆开建国家消费性工程。虽然至即位的第六个年头儿即崇宁六年(公元1106年),赵佶有所反省,罢免了蔡京并停建全部工程,但过了十年,他的炫耀冲动再起。这次不仅要用财力来表现,而且还要用术士来烘托气氛,双管齐下。
政和六年(1116年)春正月,赐道士林灵素为“通真达灵先生”。林先生,何许人也?温州人士,年少出家为僧,因守不住摊子,经常挨师父打骂,一气之下改了信仰--转为道士。此时,赵佶所宠信的王老志死了,林灵素经人举荐顶坐了皇家牧师的职位。下个月,崇道的专门建筑落成,名曰上清宝篆宫。此宫设置奇特:外面挖了三丈深的环宫河,东面前一座景龙门桥,西面建一座天波门桥。桥的设计非常了得,下面通过船,而桥上的人几乎感觉不到--所有的船连成了一条长龙。这条环宫河,称为景龙外江。在环宫河外,还设立了称为鹤庄、鹿寨、文禽、孔雀的各个小型专门动物园,各种其它罕见兽类也有数千只。环绕此宫,还设有民俗村、野店、酒馆、妓院,一派繁华。【注9】
造这两座桥的代价实在不小,此前所作的两座称为天成、圣功的桥突然坍塌,算是一场实验吧!为造天成、圣功两桥,调集了大量的民工,究竟多少今已不可考。史称“两河之人愁困殆不聊生。”至少说明,农民的正常种地、收获受到了巨大影响。他做梦也想不到崇信道士及以前的大肆炫耀会同亡国联系起来。他很可能把自己想像成刘彻了。刘彻时代,也经常没事找事儿干,以避开可怕的简单重复。刘彻虽然受到了汉朝后人的严厉批判如夏侯胜反对给他加庙号(见第十章第2节),但到了班固的《汉书》成书后,汉武帝就全面伟大起来。班固称他:“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焉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
【注9】北宋亡国后,曾有匿名诗人作诗讽刺该工程,诗曰:“万炬银花锦绣围,景龙门外软红飞。凄凉但有云头月,曾照当年步辇归。”
对于符瑞的追求与人气的制造,赵佶确实有着与刘彻一样的风格。后世人百思不得其解,他赵佶为什么宠信童贯。殊不知童贯灭了方腊,又挂帅征辽,岂不是他的卫青么?
一句话:赵佶在政治风格上是处处临摹刘彻,力图制造一个宋代的“汉武故事”。
可是,刘彻的处境远比不上他赵佶。放下赵佶及其子钦宗赵桓被掳到金国去的后来结局不说,只说在位当皇帝这一点,刘彻在位五十四个年头儿,比他赵佶多一倍。并且从十五岁(虚岁十六)就被推到皇帝的位子,经历可怕的简单童年,他受得了吗?所以,今天来看刘彻当然地比后来的赵佶更需要符瑞、人气、炫耀,尤其以炫耀补充瑞气,势在必行。
在他统治的中期,沉闷的无奈压迫得他喘不过气来,尤其让术士栾大骗了一下子(差点把女儿许给栾大),很丢人。虽然杀了栾大,事件本身终是个不快的记忆。好在这时司马相如把临终的掏心窝子的话都说出来了:“皇上呀,上泰山封禅,可是个大好事呀!”刘彻动了心,问大臣儿宽此事如何,儿宽说:“好事呀!这可是帝王的盛大节日,能给以后万世带来样板。”刘彻非常高兴,自己参考儒学典籍,制定起规则来。他嫌儒生们帮不上忙,就免了他们一大批人的官,从此也不信任那些专家学者了。
兴心封禅,顺理又改了年号,明年就叫“元封”了!
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冬十月(以十月为一年开始),刘彻认为要效法古人先鼓动士兵出发,而后解散军,再行封禅。于是,从云台(今陕西淳化)出发经五原(今包头市)
登长城。登长城的队伍浩大,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十八万骑兵,打着旗子,形成了千里长的行军线。
刘彻想以这个气势给匈奴单于一下子震慑,没想到匈奴不买帐,还把使节给扣下了。
扣就扣了,封禅的事照样搞,并且在适当的时机再给外国人一个震慑。
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西方许多小国的使节都随汉朝的使者到汉朝来参观访问,刘彻大为高兴。从此,西方的使节来来往往,与汉朝热络起来。刘彻给他们演练了一次海上狩猎--捕鲸、捉鲨的行动,让西方许多小国的使节看完后还大行赏赐。外国人一下惊呆了:“汉朝太富了,富得让人不敢相信,怎么给这多东西?!”
仅有厚赏还是不够的,还要摆开盛大场面:有摔跤表演专场,同时还有演大戏的专场,动物游乐也上了场--各种罕见兽类大汇萃。参加表演的专业人员都有厚赏,设置酒池肉林,随便吃喝。打开长安的所有仓库,让外国人看看。西方小国的使节再次被惊呆了:“唉呀!不敢想像,不敢想像。汉朝竟然有这么丰饶的库存。恐怕我们今生今世也只能见这一回啦!” 刘彻得到了彻底的满足。让外国人发呆,要比天降符瑞好上百倍有余。
自此之后,中国帝王大多好奢侈,与武帝的成功炫耀的历史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符瑞虽然也常被提起,但总不如现实的炫耀更直接、有力地烘托瑞气。连隋炀帝那样的暴烈之人都相信这一点,其余及以后的大帝国的帝王还有谁不相信呢?只要时机成熟,终会有所表现。
杨广比刘彻幸运,他没那么压抑,也不求什么符瑞,信什么方术,只图现实的快乐。
刘彻等了半辈子才捞到一次炫耀的机会,而杨广在即位的第二年末就有消息说,突厥的启民可汗明年春天来朝见。杨广要搞一个浩大的欢迎场面,让启民可汗见识一下隋的强大、中国的富庶。
可是,此中困难也不小。他父亲文帝杨坚一向讲究节俭、清约,把各种杂舞杂乐全给开革了,乐户也全归入民间。为了征集到专业人才,杨广批准专门官员的呈请:把旧朝周、齐、梁、陈的乐家子弟全部列为乐户;并且,六品以下官员及百姓有音乐专长的,全部归入国家专门机构管理。于是,四方散乐全归京城洛阳,各种玩杂耍的也凑来了:海濑在路边池子来回穿越,带得满街是水;地面上各种龟、水人(不知为何物)、怪禽异兽随处行走。还有鲸鱼表演,人钻火圈,凡此等等。参加欢迎舞蹈的人都穿官方白给的锦绣彩衣。命令洛阳市及附近地区加班赶制,以致洛阳和长安的彩布都用完了,还完不了工。
杨广检视装备情况,大为高兴,兴致勃勃地说:“当时南朝齐国那么个偏安一隅小国儿,乐工曹妙达因精音律而封了王;我今天已经拥四海之内的天下,比他们可富强多了。你们乐工们听着:我给你们的富贵定会超过小小的齐国,努力干吧!”
一场上下同心的欢迎节目,在和谐的气氛中完成了。令人心醉的气氛,让主办者杨广享受到了成功的感觉。
他此时绝对想不到他会在十一年后灭亡。当政变者要杀他时,他还很坦然地问对方:“我有什么罪,值得你们要逼杀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