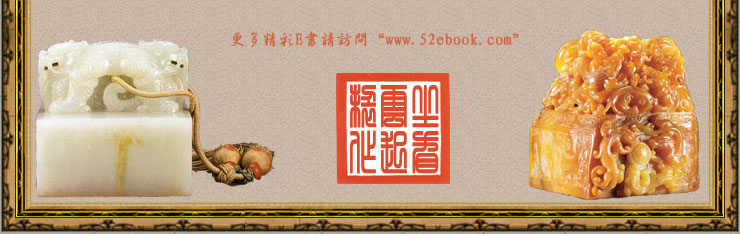国家将亡或将出现重大变故,总是鬼话迭出。这几乎成了亡国的一个必要条件。压抑的社会没有正常表达的途径,借助鬼怪说话便成了一种政治抗争与破坏的技巧。鬼话有时也是人话,那就是一经传出就遍地流行的谶谣。
再强大的镇制力量要想消灭鬼话几乎总是徒穷无益!秦朝强大无比,把天下的兵器都敛在一起,熔化后铸成金人(即铜像);法律也严苛无比,一帮戍卒如果不按时到达指定地点,就要统统被斩首。但是,一句鬼话就让给这个强大帝国下了病危通知,接下来便是死亡。
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秋七月,朝廷征发九百名贫苦百姓去戍渔阳(今北京密云),在大泽乡(今安徽宿县)集结。阳城(今河南登封)人陈胜、阳夏(今河南太康)人吴广在被征发的人当中。两素怀雄心,不愿生活在残暴的奴役之下。这次远戍渔阳,两个被选为屯长,负责集结与途中庶务。正值秋天,是多雨的季节。也是暴秦该亡,大雨冲毁了道路,也改变了戍卒们的命运。两人私下一合计:“造反吧!这么大的雨,道路冲毁了,按期不达就被处斩;造反大不了也是个死,一样的死为什么不干大事呢?”
陈胜对吴广说:咱们就借扶苏与项燕的名义吧。
扶苏与项燕早已作鬼了。一个是秦始皇的大儿子,因不满始皇暴政,遭贬黜,领兵在外;始皇一死,胡亥矫诏逼他自杀了。项燕是楚国名将,特别爱护士卒,深得人心。
陈胜因有政治雄心,比平常百姓关心时政,他知道扶苏自杀、项燕已死,而平常百姓却不知道扶苏自杀的事情,也更不关心项燕是死了还是在楚被秦灭后逃亡了。
第一步让鬼说话,图谋就序,用扶苏的正统性来打击胡亥继位的非法性,用项燕仁爱的资源来动员底层。两个本不相干的死人,被两位素怀雄心的“野心家”给盗版了。
第二步,要把鬼话做得有声有色。
给二人算卦的人知道他们的打算,也顺情说好话:“你们的事能成,但该问问鬼才好。”(--其实,这是一个暗示),陈吴二人便喜不自胜地问起鬼来。问鬼之后,付诸实践:用朱砂在帛上写上“陈胜王”三个字,并把它塞进人捕的鱼的肚子中。买鱼吃的人自然就见到了布帛,更是大为奇怪。吴广趁夜色到树林里的小庙中点上“鬼火”,学着狐狸的叫声,间或喊一声“大楚兴,陈胜王。”屯集在一起戍卒惊恐不已,加上日间从鱼腹中得到的有字帛书,便产生了群体效应,大家纷纷议论。
吴广故意用刺激性语挑逗押送他们的军官,说:“不行,跑了算啦!”岂知军官也心里有火,押送人员误了期也要受处分。借着酒劲,他用竹板子打吴广,吴广平时里特别爱护照顾大伙儿,大伙对军官的行为看不惯了。军官一看阵势不对,要拔剑,吴广上去抢过剑来,把军官杀了;陈胜也在同一时机杀了另一名军官。
鬼话转变成了现实的动员令,陈胜对大伙儿说:“现在是按期到不了啦,误期了,死路一条。就算到了不杀咱,戍卒的日子也不好过,十个有六七个要死。反了吧!闹它个大名鼎鼎!!王侯将相不是天生的,我们拼死一决,也会成为王侯将相的!!
大家一致同意:造反。
天下人受压抑已久,有陈吴这么一带头儿,各地野心家遍地野草般地出现了。这场造反结束了残暴且强大的秦朝的国运,让一个乡间无赖踏进了长安、坐上了皇帝宝座。
巨大的反差给历史留下了深刻的刺激;一个无赖尚能借机成为皇帝,那手握重兵或财产丰厚的人看准时机不也一样吗?
此后,大帝国的英雄们无一不在算计这样一个时机。东汉的刘秀一个口头宣称只想做皇室高级侍卫官(执金吾)的没落贵族,也成了皇帝,而在他之前赤眉的英雄们哪个不想一试身手呢?唐帝国的开国者李渊父子手握重兵,当然比刘秀来得方便;北宋开国者赵氏也易如反掌地利用了兵权夺位;大明开国皇帝起初的地位比陈吴二人还要低,不过一个要饭的穷和尚…
陈吴二人的鬼话打破了一个天命的神话,从此以后,中国人从本质再也不相信什么“天授”了。只有写刘邦历史的人(司马迁与班固)还编神话,说什么刘邦是赤帝之子。从刘邦以后多数人讲究以三种要素得天下了:天时、地利、人和,最后只简化为赤裸裸的武力了。五代的真正的野心家们从来就不讲什么天命,只讲究实力,于是丛林规则起作用的一场场政治资源争夺战,几乎每个重要环节上都一样。
从陈胜吴广之后,“让鬼说话”也成了野心家们的共同知识模式,不过是鬼话的表现方式更加精巧而已。
王莽篡汉以后,失去了当初的无形资产,再加上执政过于理想化,屡出重大战略失误。民间不满情绪在酝酿。无凤二年(公元15年),也就是王莽称帝的第九个年头,民间突然传说:“黄龙被摔死了!”
莫明其妙。黄龙指什么?谁又看见了?据说,这个谣传是针对王莽的,因为王莽自称黄帝之后。等赤眉【注5】之乱起后,“鬼话”变得明晰了。地皇三年(公元22年)夏四月,王莽派太师王匡、更始将军廉丹讨伐樊崇,十万精兵所过之处非抢既夺,政府军成了人民最痛恨的对象。那一年,关东地区(非今天的东北三省,而指陕西以东地区)由于上年发生了大饥荒,到来年春天发生了人吃人的事件。百姓明唱到:“宁逢赤眉,不逢太师,太师尚可,更始杀我”。--从黄龙摔死到这个歌谣盛传,经过七年的发酵过程。民间在制造“鬼话”的同时,也乐意传播奇异事件的发生,这成了对执政集团表示不满的一个手段。
王莽试图以代汉救时弊,无奈流弊源长,已经积重难返了。早在孝成帝时就发过类似黄龙摔死的谣言,建始三年(公元前30年)秋,长安下了四十天大雨,京师在老百姓都谣传发大水。在奔逃中自相践踏,年老体弱的人呼天喊地,长安城中一片混乱。大将军王凤决定:让太后和皇上及后宫的人们上船以避水,百姓后上城墙。左将军王商感到事情不对头,对皇上说:“自古以来,最暴虐的无道的王朝也被大水淹过城郭,今天怎么会出现大水一下子就来的事情呢?一定是有人在造谣。百姓要全登上城墙,会更加惊惧。”于是,成帝亲自下命令停止百姓登城。
【注5】此时樊怕自己的军人与王莽队伍分不清,将眉毛涂红,供自己人辩认,始称自号为“赤眉军”。
王商尽管虑事周全,他的话中也表露了自己的判断:我们的王朝虽然不算最残暴,但也不算好啦!
在这种不算好的状况下,大帝国慢悠悠地运转了十八年,怕灾变的心理不仅在百姓心理发酵,在皇帝心理也再发酵。他怕,怕得几乎神经过敏。这种神经过敏的重要促成因素也来源于意识形态的教育,自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理论写入意识形态文本后,天变就成了一种政治警告信号。元延元年(公元前12年)春,正月初一就出了日食;夏天(四月)在天上无雨响雷,某夜又出现了流星雨;秋天(七月),天上东井宿方位出现了慧星。成帝终于一改过去拒谏(对建议一概冷处理)的态度,广泛征求群臣的意见。当然,这也只是一种心理上的自我安慰,而绝无改革之意。随着这种安慰起了作用即缓解了成帝的抑郁症,他又对言论变得不耐烦了。很快就发生了朱云事件,多亏辛庆忌叩头流血才保住朱云的性命。
这一切的疲惫与反复给另一位野心家创造了上升的条件,王莽登台了。但很快,这个野心家不得不面对自己政策的后果--他大力推行谶纬之学,结果一首有史以来最长(到目前为止仍是)的谶谣针对它而来。卜者王况与另一位谋复汉室的名叫李焉的人制了一本谶书。书中说:“文帝发忿,居地下趣(亦作驱)军。北靠匈奴,南告越人。江中刘信,执敌拔怨,复续先古,四年当发军。江湖有盗,自称樊王,姓为刘氏,万人成行,不受赦令,欲动秦洛阳。十一年当相攻,太白扬光,岁入东井,其号当行。”
李焉的属吏在抄写过程感到事情重大,向王莽举报,王莽急忙逮捕李,办案的官吏们甚觉奇怪,私下传看谶书。谶书的主要内容也经这次逮捕更加迅速地传播开来。随后,王莽的卫将军王涉又经手下高级谋士造出一套新的“鬼话”:“星孛扫宫室,刘氏当复兴。”王涉以此鼓动国师公刘歆夺权,不幸事泄,二人被杀。“刘氏当兴”的理念是当时百姓与相当一部分权贵的共同心理,于是,“谐不谐,在赤眉;得不得,在河北。”以及“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的谶谣有了流行的基础。
随着历史的推进,“鬼话”的操作变得越来越简单,几乎用不着陈胜吴广那么麻烦了,又是往鱼肚子放帛书,又是找人算卦,又是点鬼火、学狐叫。东汉末年的黄巾军(前身为太平道教)干脆就一暗一明的一则谣和一句口号就是了。先散播不怕死的精神,称为:“发如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吏不必可畏,小民从来不可轻。”随后,在起事时高叫:“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
唐末“鬼话”的选择,又比东汉简单了,就一句:“金色蛤蟆争努眼,翻却曹州天下反。”元末红巾军的谶谣几乎就是唐末的“盗版”,至少也是一个改版:“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
“鬼话”最初是公开斗争的利器,陈胜吴广虽然在暗中操作,但最后的受益者还是自己,只半句“陈胜王”就足够了。至于“刘秀发兵捕不道”的后半句,更象一种公告--“看了吗?日后的天子是我刘秀。”张角的口号更明晰--“我来带领你们砸烂一个旧世界,就这么简单!”
历史的流变绝非如此简单和直白,“鬼话”也应时而变,由公开宣示变成了猝然而发的暗器。暗器不知发自何人,而打击的目标却异常地明确。
这种暗器,成了无权者的权力。
东汉桓灵统治的四十年,中国政治陷入了“文人-宦官-外戚”倾轧的怪圈。灵帝起初还有复振政治的打算,但终因国家积弊过深且自己治术低下,而没能达到所愿,反而更深地被卷入了文人集团与宦官集团的冲突中去。其实,早有人看透了他的命运,拒绝与他合作。延熹二年(公元59年),也是桓帝当政的第13个年头,外戚集团的首领梁冀被处死,百姓吹呼,一个清平的政治局面会出现。然而,他们高兴得太早了。除掉外戚强势集团后,宦官集团成为新的主流,一日有五名宦官被封为列侯。尚书令陈蕃也在体制内大造声势,为桓帝征召五位隐士。礼节之隆重,让旁观者眼热:称之为驷马安车的交通工具,是由四匹马牵引的,车轮子用蒲草裹起来,免于颠簸,礼物则是三黑二红的织帛--称为“玄纁”。但是,徐稚五位隐士没有一个人接受【注6】。
这对体制内开明派陈蕃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对桓帝更是一个打击。随后,在宦官集团的操纵下,桓帝把打击矛头指向了知识分子们。
灵帝的政治作为实在比桓帝更坏,除了延续了桓帝后期对知识分子的打击外,就是出卖官爵,以数钱为乐。最后,发展到连三公的位置也得花钱买了。此时,宦官与文人的斗争已经白热化;外戚领袖窦武与文人联手,欲除掉宦官,没想到宦官集团先发制人,一举消灭了两大集团。
窦氏外戚集团灭亡后,何氏外戚集团再起。何进为求政治缓和,团结体制内的力量去对付黄中军。但这触怒了宦官集团,一场血腥的斗争再起。这次血腥争斗,不会重复昨日的三角关系,一种强大的力量--军方介入。因为此时文人集团已经无力参与高层政治了,何进引入军方也势在必然。
中平六年(公元189年),灵帝统治的最后一年,董卓率领着浩浩荡荡的大军奔进首都洛阳。
董卓进京时是秋七月,灵帝死于夏四月。少帝刚刚继位三个月,实际上国家是以何进为最高领导人的。
外戚集团与军方实行了一场残酷无情的逮捕与屠杀,同时也让董卓变成了最高权力的实际掌控者。
这场政治悲剧的首席策划师是大名鼎鼎的袁绍。
袁绍劝何进一举消灭宦官集团,何进请示妹妹何太后,没得应允。于是袁绍再建议何进征召四方猛将进京,给何太后施加压力。应召而来的董卓显得很正义,他上书说道:宦官张让等人窃取恩信,扰乱天下。有俗语说:“止沸扬汤,不如釜底抽薪”捅破毒疮,总比五脏六腑受损要好。现我正挥师进军,以期扫除奸恶之人。
何太后见到董卓书信,大惊失色,不得不罢免了宦官们的职务。何进并不罢休,要求妹妹下令将宦官全部诛杀,事不机密,张让探知消息,先暗杀了何进。袁绍终于忍不住了,趁机捕杀宦官,无论长幼,见一个杀一个,拿下两千多颗人头。董卓也在混乱中赶到,将逃离皇宫的公卿与宗室人员接回皇宫。接下来,就是两个军事强人的冲突了。
董卓的第一手就是更换皇帝,废了少帝刘辩、立献帝刘协。董卓说:“天下之君,应该选贤,每每想到昏庸的灵帝,就让人咬牙。陈留王刘协看起来不错,大家议一下,看能否胜过刘辩呢?”
袁绍反对:“少帝虽然年幼,但没有恶行。你废嫡立庶,恐怕天下人要有意见!” “什么?你再说一遍!”董卓大怒,按住剑柄训斥袁绍:“你小子胆敢反对,天下的事不取决于我又取决于谁?”袁绍年轻气盛,一怒之下奔出殿堂,策马奔往冀州。董卓没空儿搭理袁绍,逼着何太后立诏废少帝、立献帝,而后又悄悄毒死了何太后。
历时四十余年的三边斗争,以军方的介入而终结,董卓成了政治巨无霸。
【注6】除此五人外,桓帝再征魏桓,魏亦推辞。初,其乡人劝行,魏问曰:“夫干禄求进,所以行其志也。今后宫千数,其可损乎?厩马万匹,其可减乎?左右权豪,其可去乎?”皆对曰:“不可。”乃慨然叹曰:“使桓生行死归,于诸子何有哉!”遂隐身不出。
董卓以军事实力支撑起的强权达到了中国历史至他那时的一个巅峰,在他之前没有一个军事人物能做得到。你袁绍不是跑了吗,跑了我也给你封官,给你封官就证明我掌握着核心权力。在袁绍逃掉之后的第三个月,董给了袁一个官衔--渤海郡太守。他也给曹操重新任命,任命曹为骁骑校尉。但是,精明的曹操预测到董必败的下场,不但不接受任命,反而走小路逃回家乡,准备招募军队,图谋天下。
面对他进入洛阳后,不到半年就兴起的反董军事联盟,董卓并不放在心上,但出于战略上的考虑,他打西迁都城,目标是长安。伍琼、周毖二人极力劝阻,结果要了伍周二人的脑袋。在周伍二人之前劝董卓的太尉黄琬、司徒杨彪已经被免职,一听说伍周被杀,黄杨二人赶紧给董卓叩头,赔礼道歉…
在董卓还没来得及品味自己胜利的果实时,千万只“暗器”就射向了他。
洛阳街头巷尾开始流传着一首董谣:“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
“千里草”为“董”字;“十日卜”为“卓”字;“何青青”则指草茂盛的样子,形容董卓兴起的暴烈之状;“不得生”则指董卓兴得快亡得快。此中别有意味的是,“千里草”该作成“草千里”,即字由上往下拆说,制谣者故以把草放在底下,映射董卓以下欺上。
果不其然,董卓从中平六年秋天进京到初平三年(公元192)夏天被杀,把持朝政还不到三年。若是他仍在河东郡驻军,不卷入进城的政变,肯定不会三年而亡。
制此谣言者,或许是被董卓残杀的何进的族人,诅咒他早日灭亡;或许是被他羞辱的袁氏,向天下散布董氏必亡的预言;或许是被董卓压制于朝廷的文人,发泄内心的不满。但无论是哪一方,都对董卓怀有不满,而这种不满已经是社会常态。人们,哪怕是最无权的阶层,也可以从几十年的政治变乱中总结出道理。这些道理就是打造暗器的基本材料,它经过高手加工以后,便有了无比的杀伤力。董卓可以暗地里处死何太后,但却没办法暗暗杀掉谣言的制造者;他也可以追补袁绍的官位,以弥补自己原来的过错,但他却永远无法向哪一个人施恩,要求取消童谣;他可以一怒之下杀了向他谏言的伍琼、周毖,但却无法一怒之下杀掉向他施放言论暗器的人。
几乎每一个欣赏这首童谣的人都成了他的敌人,但却无从知道面前的哪一个人欣赏这首童谣。
他知道明着的敌人在何处,但却永远无从找到暗处的敌人,哪怕他屠戮了整个洛阳城。
在一定意义上讲,无权者的这种暗器对有权者可能是一种提醒。只要是从中明了民意,及时更张,也许能得到的结果会好一些,可惜,历史上这样的掌权者几乎没有。
南宋宁宗时代(赵扩,1195-1224年在位),韩侂胄专权,政治败坏。韩除了继续北宋中后期以来的利用政治权势主导文人之争的恶劣政策之外,还善于将人品低劣的人引入权力体系。他任用的吏部尚书(相当于人事部长)许及之被人们称为“钻洞尚书”。
许任了两年吏部尚书,没在升上去,便抱着一线希望去拜见韩,希望能升为同知枢密院事(相当于副总理)。他见了韩,感恩涕零,称自己能有部长之职多亏韩太师的提拔;但,又说自己年老了,提拔得太慢,竟不顾自己年长,给韩跪下。韩见许如此卖身投靠,便提他的职务升了一级。此前有一次韩过生日,许去晚了,韩府大门关了。许急坏了,也是急中生智,见旁连供牲口出入的门没关,就顺势钻了进去。因此,时之讥之“钻洞尚书,屈膝执政。”
更为令人不齿的表演是一名姓赵(字从善)的地方官(临安知府)为从厅局级升为正部级竟然学狗叫,以博韩的欢心。
韩的生日时,百官争献奇珍异宝。赵从善最后一个到的,拿出了绝活,震惊了四座。他说:“愿献几许果核佐酒。”打开礼品盒一看,里而是用金子做成的葡萄架,上面缀了一百颗硕大的珍珠。往下的手腕更高了,他为满足韩的十位没有名号的侍妾的敛财欲望,给十个人每人送一项珠冠。于是,十个女人一齐在韩面前为赵求官。赵果被任命为工部尚书(相当于建设部长)。
有一次,韩与几位闲客逛山庄,对竹篱感叹说:“哎呀,这可真是一派农家风光,要是有鸡狗之乐更好了!”不一会儿,草木间果然有了狗叫声。韩一看,竟然是赵在学狗叫!人们当然瞧不起赵,因为他不仅有进士的学历,还有皇室的血缘背景--为宋太祖赵匡胤的八世孙。然而,学历与家世又管什么用呢!
【注7】现在是韩太师的天下,不求他,求谁去?
时人瞧不起许及之、赵从善,但更恨韩侂胄的猖狂。民间无法与之正面抗争,于是发出暗器。当时,首都大街上流行着一幅画儿,画面上是涨潮的情景,潮头与潮里又印满了小乌贼。卖画者说:“一钱一本儿啦!看呀,多好看--满潮都是贼!”
“潮”字乃朝廷之“朝”的谐因,“满朝都贼”用来讽刺、抨击韩相爷的内阁。
大街上有卖浆子的人,也奇怪地吆喝:“冷的吃一盏,冷的吃一盏!”
“冷”即“韩”字谐音“寒”的同义,“盏”即“斩”的谐音。实际是预言“韩相爷要吃一斩。”
临安府尹(首都市长)破译了“冷的吃一盏”的含义,不过他没有上报给韩相爷。只是抓住一个传谣者,就打一顿棍子,直到没人传谣为止。
不幸的是,预言非常准确。韩太师于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不顾国力不支的实情,贸然北伐,与金人开战。结果,屡战屡败,并导致了金兵大规模入侵。本来还可编安一隅的南宋,几乎面临崩溃。于是,一场政治谋杀不可避免。
开禧二年(1207年)冬十一月,礼部侍朗(相当文化部副部长)在征得皇帝的同意后,下令秘密处死韩太师。处死韩,也是战胜方--金国的要求;金国人的条件之是送韩太师的人头来。死了的韩太师也不得安宁了。于是,嘉定元年(1208年)三月,韩的棺材又被打开,人头被割下,装在木盒里。
当初,在割头一事上也有争议,但主和派的论断占了主流,他们说:“和议之事乃头等大事,金国人既然要人头,就得给。一个死了的奸臣的头,有什么可惜的!”这样,韩太师就残了,头颅在两淮地区示众后,送往金国。南宋用人头换了和平,换了土地,金国人见了人头后,归还了占领的南宋的陕、淮土地。
“冷的吃一盏”的暗器真地就射中了。一位腐败的高官,一场狂妄的战争,竞然让一句谶谣言中了结局。当然,要不是因为“满潮都是贼”的民忿,也不至于出现“冷的吃一盏”的预言。
民忿往往由预言中表现出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