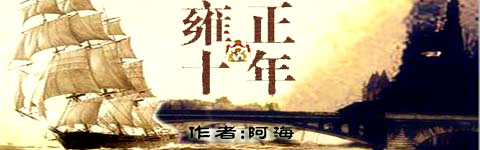洋人大班们在贸易镇上,摆足了大人的派头
蓝旗国的外洋船,今年到港已经甚晚,而双鹰国的外洋船,到港更晚。等他们的大班赶到广州城外的贸易镇,已是雍正十年的阳历九月十五日了。和法兰西、英咭利国的外洋船六七月份就到了广州相比,要差了二三个月之多。到了这个时候,洋货行的行商都知道,今年不会再有外洋船到了,因为信风季节已过。
九月份,正是贸易镇上最热闹的季节。外洋船俱各来到,所有的外洋大班都已经租下了夷馆,开始贸易。外洋大班一进货,就会从船上调来十数名军官和水手,看守夷馆的仓库。因此贸易镇上,金发碧眼的洋人着实不少:来港贸易的,有英咭利国、法兰西国、红毛国、蓝旗国、双鹰国和几条港脚船,总数有十七八条外洋船之多;以国别建夷馆,每个夷馆的洋人连大班加上军官水手,当在近二十人左右,这样加起来,整个贸易镇上,来往的洋人也有上百之数。
雍正十年,洋人在贸易镇上,相当自由。大班们出入可以坐轿子,派头倒有点像中国的官老爷。学术界向来认为洋人不许在广州坐轿,而雍正十年的情况,完全不同。坎贝尔记载:“这样,我们的轿子等在门口,我和其他的大班们一起去见海部。”官府虽然把洋人称为“夷”,比如“远夷”、“夷馆”等,这里的“夷”字,倒也没有歧视的意思。洋人大班去见官居二品的海关监督关部正堂兼监察御使,坐着轿子去不说,按例赐座奉茶。这在官场上,基本上是品级相当的官员才有的待遇。甚至洋人大班觐见结束,关部衙门鸣锣相送。这种排场,可谓礼遇有加。
洋人住在广州城外,一应事务,均由大班们自决,官府基本不加干预。只要不进城,既可以到处闲逛,也允许登高望远,抒发情怀。一直到乾隆雍正十年,洋人进城也不算一件难事,办法有两种,一种是洋人自己出面,向海关监督衙门申请一个批文,写明几个洋人要进城;二是广州城内有人发出邀请信,即可获得批准,进广州城内访客,这就好比是眼下的外国签证,通常分成旅游签证和访友签证两种。
外洋船的夷馆,在洋货行里面,却又有朝街的独立门户。贸易镇上的管理,想来也是很规范的,因为晚上闭门和早上开门都有一定的时辰;蓝旗国的大班规定,从船上调派军官和水手十二名,前来守卫夷馆,定期轮换。这样船上所有的人都可以领略广州的风情。如此一来,这夷馆也俨然很有规模:大门口有洋人把守,里面有夷馆买办派来的厨子、佣人甚至轿夫,大班们出入期间,自然也很有威势,这在普通的中国人眼中,根本就是所谓大人的派头。
既然是大人的派头,这些洋人大班就像煞是中国的大人们,对于平头百姓,引车卖浆之徒,多少要摆点臭架子,甚至公开欺负。比如蓝旗国外洋船回程的时候,得知领航的引水,同时也给法兰西国的外洋船领航,结果把这可怜的引水给关在蓝旗国的夷馆里好多天,免得他给法兰西国的外洋船先一步领航,走在蓝旗国外洋船的前面。这当然是毫无道理的事情,因为粤海关治下的引水不止一个人,这就好比要救一个死囚犯的命,却去把相关的刽子手给关了起来,多少有点好笑。
这无辜的引水莫名其妙地给关了起来,虽然没有受到虐待,吃喝供应一应俱有,却想破脑袋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等到蓝旗国的外洋船一切准备妥当,让他领航出关的时候,想必他也只好忍气吞声,自认了倒霉。否则和洋人大班这种大人级的人物争执起来,未必有什么好处。弄得不好,还要到衙门里吃一顿竹笋烧肉:衙门里的老爷动不动就用竹板子打屁股。
另一方面,这些洋人大班,交往的也都是些大人。一是大班之间,二是和行商之间,互相来往,当面客气得很,背后做些小动作。粤海关的官员、关部正堂、家人和书办,自然不便和洋人大班来往:一是官体,二是名声。但是和外洋贸易无关的官员和士绅,也有和洋人大班交上朋友,你来我往,十分热络的。雍正十年,坎贝尔至少有两位这样的朋友,一位是盐运使手下的盐场主,另一位居然是总督衙门的把总。前者八成算是士绅,后者却是现役军官。
这位盐场主是个住在广州城里的富翁。盐是国家专卖品,盐运使也算得上是高官,所以这个盐场主的地位当然也不低。坎贝尔等人和他熟悉以后,也走动得热络,先是这位盐场主写邀请信出来,请蓝旗国的四位大班一起进城吃饭,饭桌上遇到了一位总督衙门的把总,坎贝尔等人又邀请他们第二天到蓝旗国的夷馆吃饭,结果盐场主没有来,把总却如约而至。
盐场主不说,总督衙门的把总是现役军官,能够和洋人大班套交情,喝老酒,来往密切,可见雍正十年,贸易环境非常宽松,并没有把这中外之大防,当作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再者,中国官绅以己度人,对于洋人大班,也是以大人的身份,予以尊重和礼遇。这和日后乾隆朝晚期,处处限制外人的情形,可谓有天壤之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