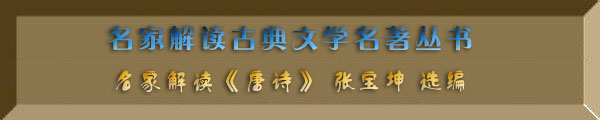邓绍基:从《即事》看杜甫拗律
|
|
暮春三月巫峡长,皛皛行云浮日光。雷声忽送千峰雨,花气浑如百和香。黄莺过水 翻回去,燕子衔泥湿不妨。飞阁卷帘图画里,虚无只少对潇湘。
这诗是杜甫居夔州(今四川奉节)时所作,诗体属七言拗律,旧时注释 家都称赞它“写景之妙”,清代的黄生说这首诗“可作暮春山居图看”。现 略谈我的粗浅看法。
第一句,“暮春三月巫峡长”。自四川奉节到湖北宜昌之间的长江两岸, 层峦叠嶂,无处不峡,其中最险者称“三峡”。晋代左思的《蜀都赋》中就 写道:“经三峡之峥嵘。”但历代关于三峡的名称的说法不一,在杜诗中也 有“三峡传何处”的发问句。现在习惯上把瞿唐峡、巫峡和西陵峡称为三峡。 在三峡中,巫峡数长,所谓“巴东三峡巫峡长”。暮春,春将过去。在唐代 以前,南北朝人写诗,不时表达惜春的感情,如“无令春色晚”,“处处春 心动,常惜光阴移”,“不愁花不飞,倒畏花飞尽”,等等。杜甫写“暮春 三月巫峡长”,把暮春和“巫峡长”联系起来,似乎峡中的暮春三月也较其 他地方的暮春三月为长,这就一反惜春的老调,有了新意。
第二句,“皛皛行云浮日光”。清代著名杜诗注家仇兆鳌解释道:“云浮日光而过,其色皛皛然,雷雨将作矣。”仇氏的意思是说诗人写这第二句 是为了引出写雷雨的第三句。清代另一位注家杨伦也作同样的理解。按照一 般的诗法观念,说七言律的第二句引出第三句,或者说第三句承应第二句, 原本无错。但对于大诗人的作品,却也不能一概地用诗法模式去套,从而作 出刻板的解释。前面说过,杜甫的这首《即事》诗是拗体七律,对拗体诗, 前人常从它的平仄、黏连等形式不合常规律诗的格律这点上作解释。现在我 大胆地提出一个看法,杜甫的拗体诗不仅在平仄形式上表现为“拗”,就是 在诗意的起承转合上也会表现出“拗”。由此我认为这首《即事》诗的第二 句未必即是起到引出第三句的作用,而且,“皛皛”是形容皎明之貌,陶渊 明诗句:“皛皛川上平。”杜甫写皎白的行云轻疾而过,并不是写阴云密布, 所以仇氏“雷雨将作矣”的见解未必正确。
我认为第二联的上句“雷声忽送千峰雨”是兀起之笔,也反映了当时当地忽睛忽雨的实际风光。而且,正是这一句,写出了壮丽场面。凡写暮春风 光,即使能够避免哀愁,却也不易写得壮丽。雷雨千峰,却正是一种壮丽的 场面。第二联的下句“花气浑如百和香”是由雨写花。如按老套,就会有雨 打花落,或者湿花垂枝之类。诗人摒却这些,却采用前人写雨后花更艳的意 境,李世民《咏雨》诗就写“花霑色更鲜”,虞世南也有“山花湿更燃”的 诗句。这里杜甫稍作变化,写雨后花气更浓。关于“百和香”,宋代著名杜 诗研究者赵次公引古诗云:“博山炉中百和香,郁金苏合及都梁”,说明“百 和香”是各种香物的混称。沈约《和刘雍州绘博山香炉》也云:“百和清夜 吐,兰烟四面充。”
第三联写莺燕:“黄莺过水翻回去,燕子衔泥湿不妨。”前人咏春诗中 常要出现莺燕,却又最易流入老套。杜甫由雷雨而捕捉住黄莺的一种特殊情 状,“黄莺过水”即“过水黄莺”,被雨水打湿了翅膀。仇兆鳌解释道:“莺畏雨,故翻回。”浦起龙《读杜心解》说:“翻回去,雨中栖止不定也。” 我想还是浦氏更有见地。不少杜诗中写黄莺都很可爱,这首诗中却写它的狼 狈形状。贴切吗?很贴切,娇弱的黄莺遇到雷雨,惊恐翻回,栖止不定,才 真符合它的“性格”哩!
燕子就不同,诗人写它冒雨劳作,“燕子衔泥”即“衔泥燕子”,浦起 龙说“湿,不指泥”,也很有见地,这里是写燕子身湿。如果仅仅理解为燕 子衔湿泥筑巢,那就流于一般了。或问:细雨蒙蒙,燕子衔泥是常见的,隆 隆雷雨中还有燕子飞翔吗?是的,诗人这里未必是实写,而是赋予想象。既 然他写过水黄莺的狼狈,必然要写衔泥燕子的豪壮。诗人必然会凭借石燕的 传说,《湘州记》:“零陵山有石燕,遇风雨即飞。”零陵燕作为一个壮勇 的形象,南北朝时人就有描写:“讵得零陵燕,随风时共舞。”(张正见《赋 新题梅林轻雨应教诗》)杜甫巧妙地把勤劳的衔泥燕和豪壮的迎风燕结合起 来描写,却也正切合这春雷千峰雨的环境,也就使这首《即事》诗的壮丽意 境再次升华起来。
尾联上一句“飞阁卷帘图画里”是总结即景风光,此时诗人客居夔州西 阁,“飞阁卷帘”当是实写。但结句荡得很远,一下子说到湖南,“虚无只 少对潇湘”。这看来似为突兀,其实也不奇怪,它使我们想起了阴铿的《度 青草湖》诗,其中写道:“洞庭春溜满,平湖锦帆张。源水桃花色,湘流杜 若香。穴去茅山近,江连巫峡长┅┅”青草湖即洞庭湖,这是描写“潇湘” 之诗,却联系到上游,出现“江连巫峡长”的句子。而杜甫此诗分明写峡中 光景,却纵笔飞思,一直写到下游。杜甫曾说他自己“颇学阴何苦用心”, 阴是阴铿,何是何逊。看来在杜甫写这首诗的时候,或许也是受到了阴铿《度 青草湖》诗的启发。“虚无”,如仇兆鳌所说,“空旷貌”。峡中图画是壮 丽的,山高水险,雷雨千峰,但还缺少一点什么,缺少浩茫广阔。潇湘洞庭, 正是浩阔所在。杜甫《长江》诗中就写道:“色借潇湘阔。”有的注家释为: “潇湘之阔,其色皆借资于此,以潇湘乃江水下流也。”为有长江之水,更 呈洞庭之阔;长江虽然壮丽,洞庭却为浩旷。诗人本极状峡中暮春景色,忽 然荡开作结,写它的不足——“虚无只少对潇湘”,这才真叫大家笔法。杜 诗读者知道,杜甫的《去蜀》诗中说:“五载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如何关 塞阻,转作潇湘游?”东下潇湘,是他早有的打算。他写《即事》诗时正滞 留峡中,这“虚无只少对潇湘”句正是他东下意念的自然流露。正如他在《暮 春》诗中写“卧病拥塞在峡中,潇湘洞庭虚映空”一样,所以这种荡开作结 更显得情景交融。
(选自《杜诗别解》,中华书局 1987 年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