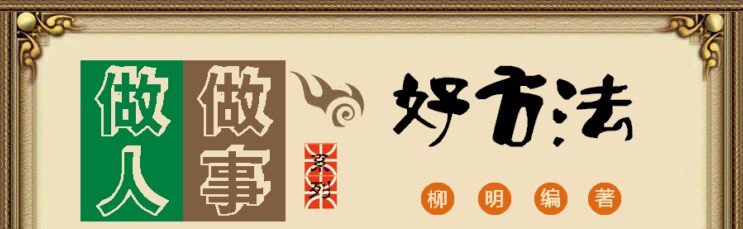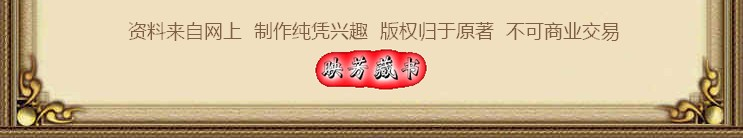在现实中生活,当然不能游离在群体之外,可是,如果你喜欢独来独往,也不必过分在意别人把你当成“孤家寡人”。如果你每天上下班需在途中乘车两个小时,你想利用这段时间看书、听外语、思索或仅仅闭目养神,那么就不必勉强自己去参与无聊的闲谈。心理学者研究后认为,在多感的青春年华中尤需充分体验孤独的乐趣。有某种才华的人,总会显露出孤独感。
闻名于世、陷入千百万观众和崇拜者的重重包围中的意大利电影明星索菲娅·罗兰居然也会感到孤独,而且还喜欢寂寞。她说:“在寂寞中,我正视自己的真实感情,正视真实的自己。我品尝新思想,修正旧错误。我在寂寞中犹如置身装有不失真的镜子的房屋里。”
这位艺术家认为,形单影只常给她以同自己灵魂坦率对话和真诚交往的绝好机会。孤寂是灵魂的过滤器,它使罗兰恢复了青春,也滋养了内心世界。所以她说:“我孤独时,我从不孤独。我和我的思维做伴,我和我的书本做伴。”
刘海粟大师主张,年轻人“精力正旺,正是做学问的好时光,一定要甘于寂寞。你集中一段时间闭门学习,不去赶热闹,社会上暂时不出现,没啥了不起,等你真正有成就,社会上永远记得你,你就永远不会冷清,不会寂寞了。这是我的经验之谈”,“对一个名人来说,热闹有时就是捧场,就是奉承。这对从事艺术创作是有害的。因为太热闹,脑子要发热,安静不下来”。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有根本的孤独感。大凡有根本孤独感的人,思想感情多为较深沉者。因为他们有独特的见解和独特的个性,不为当时社会和同时代人所容,在任何场合下他们都有与众不同的表现,故内心常有一种难以排遣的孤独。而其中的一些人,会让自己陶醉在科学、艺术和哲学创作中,他们能够感到实实在在的平安和满足。
比如司汤达活着时,声名并不显赫,但他预言要等到1880年左右才会有人欣赏他;贝多芬的许多作品更具有超越时空的性质,他自己也很清楚,他的几部钢琴奏鸣曲是为未来世纪的听众而创作的。少数天才人物,包括伟大政治家的身上,根本的孤独感几乎是一种不治之症,这种孤独感伴随着一种根本的惆怅和忧郁。企图抗衡和摆脱这种孤独感,便成了人类从事文化创造的一种最顽强的定力的内驱力。如,凡·高作画,既不为名,也不为利,他之所以要拼着一条性命去画,仅仅是为了排遣内心深处一种说不太清的根本的孤独感。
爱因斯坦的一生也患有根本的孤独症。在《我的世界观》一文中,他坦率地做了自我解剖:“我对社会正义和社会责任的强烈感觉,同我显然的对别人和社会直接接触的淡漠,两者总是形成古怪的对照。我实在是一个‘孤独的旅客’,我未曾全心全意地属于我的国家、我的家庭、我的朋友,甚至我最接近的亲人;在所有这些关系面前,我总是感觉到有一定距离并且需要保持孤独,而这种感受正与年俱增。”爱因斯坦终生对物理学、艺术和哲学的真挚的爱,全然是企图对这种孤独感的永恒摆脱和最勇敢的回击。
作为现代人都难免偶尔有孤独感。对于人类科学、文化创造来说,孤独感并不是一件坏事。也许,人才在教室、课堂上培养,天才则在孤独感中自己成长。因为孤独感会使人处于一种自我发现的紧迫状态。
孤独往往能带给我们大量的独处时间,供自己自由支配。大凡成功者都有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否则,幸运为什么独独喜欢降临到他们头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