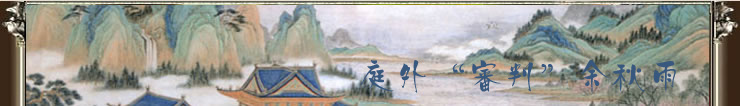 |
 |
|
看余秋雨告状谭大珩:略论余秋雨“告状”
|
 |
 |
|
网上消息传来,余秋雨教授果然在打“名誉”官司了:南告古远清于上海,北告肖夏林于北京,两处皆提出赔偿“名誉”费十万元。并且声明:要以他的“个案”,使“知识分子”懂得些“法治”云云,真是义形于色,好看极了。
诚然,余教授是曾有过美名的,比如“戏剧理论家”、甚至“散文大师”的称号。大约因为“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原因,曾几何时,一变而成了抹着“文化口红”的浪荡者。真是世事白云苍狗了。为什么有着这样的变化呢?也许余教授迄今仍认为对他围攻、批评的人,多是些妒忌、眼红的“小人”,因此,在痛定思痛之后,决心要洗去那些诬蔑之词,还其“冰清玉洁”之身,于是从文坛走向法庭了。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从我们这些普通读者的眼光来看,余教授之生平,其成功之处得力于天时地利,其失败之处却是失去了人和。天时地利是客观的条件,人和却是主观的因素。可以大胆地说一句:许多人之所以围攻、批评余教授,是他自己的态度造成的。当然,木秀于林,风必吹之。一个人有了点名气,一定会招来物议,这一点余教授应当明白。
也许余教授认为只有依靠法庭,才能恢复他的“美名”。我们却认为,一个作家的名誉是活在文坛上,有其作品和行为作证,无须向法庭讨“名誉”。向法庭讨“名誉”并不光彩,而且采取这种方式,更会失去“以和为贵”的精神。还有“告状”不一定能增长“名誉”,相反会暴露出自己品格之缺憾的。
那么,余教授“告状”,暴露了他什么缺憾呢?
一、少了点宽容。俗话说:“宰相肚里能撑船”。“夫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苏轼曾说:“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我想,余教授还达不到这样的境界,大约也不过和芸芸众生一样,涵养还差一点。一个作家,难免会受到各种各样的批评,好的坏的都会有,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所以在文艺圈内,我们提倡的是“百花齐放”,而不是舆论一律。在上世纪20十年代末,顾颉刚要状告鲁迅,说破坏了他的“名誉”,从武汉勒令要鲁迅在广州候审。然而鲁迅却对他嗤之以鼻!我们认为就算肖夏林有说过“余教授在深圳谈文化是为了一套豪华别墅”的话,也不必诉之法庭。因为这类事情,只需一则声明,便可大白于天下,何苦要请律师、上法庭呢?这不是“杀鸡用牛刀”吗?有什么话不能说清楚的呢?我们觉得余教授对当今文坛过于悲观,对知识分子的觉悟估计不足。余教授这样做,不管胜诉与否,首先是失去了“人和”,缺乏了“以和为贵”的精神。“冤家宜解不宜结”,余教授以为如何?
二、缺了点幽默。魏明伦先生正确地指出,余教授作品的缺点:“少了幽默”、缺了“滋味”。这一缺憾非同一般,因为它牵涉到做人的风格。在现代文学史上,被人诬蔑最多的恐怕是鲁迅先生了。当然,他亦有气愤之时,但他认为文艺批评的事,要通过文艺批评去解决,并且主张要“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使“敌人受伤或致死,而自己并无卑劣的行为”。他曾想编本“围剿集”,把论敌的言论一一收录,加以编排,以供后人借鉴。我想余教授是没有这样的胆识的,因为两人的心态截然不同。
说余教授的作品少了“幽默”、缺了“滋味”,也就是说余氏缺乏了文采。这是真的。纵观余教授的作品,《文化苦旅》还算文笔流畅,显示了他的才华,但作品思想苍老,屡有硬伤,而且一味正襟危坐,没有笑容。写到《山居笔记》,文学的意味已淡,偏多浮躁,指责对他批评的人为“小人”了。至于《霜冷长河》,只剩下些感喟和教训的文字,文学意味已茫茫不可见,真是冰冷长河了。肖夏林先生所写的《警惕余秋雨》,剖析余氏作品,中肯深刻、入木三分,难怪余教授恨之入骨,非寻漏子告他不可了。
三、欠了点冷静。余教授自视甚高,总是摆出院长、教授的架子,自以为是“大师”级学者了,因此遇事很不冷静,往往贻笑大方。比如,对他在“文革”时期的历史,许多与他共过事的人尚在,且有文章披露,然而他就是“千呼万唤不出来,犹抱琵琶严遮面”,对这段历史,讳莫如深。这就难怪人们对他的质问。余杰的一句:“余秋雨你为什么还不忏悔?”像惊雷一样震撼过他的心头。然而余教授却认为这个“黄毛小子”,乳臭未干,懂得什么叫“文革”呢?于是想在魏明伦先生处约见余杰,进行“教训”和私了。这是谁都知道的:余杰并不可欺。我们想,余教授是不敢告余杰的,余杰亦表示过不担心会成为被告。
余秋雨教授的《敬告全国读者》,实质是一篇“告全国人民书”,是典型的奇文。这是头脑发热到极点的文章,竟忘记了自己是何身份,而且借“盗版”之名,大骂了批评他的人,又一次激起了作家、批评家之愤火,终于形成了众怒难犯的局面。
至于到“千年庭院”去讲学,本是应某些电视台之约去做“文化明星”的,但偏要在朱、张讲学之处做“秀”。两湖文化你知多少?结果受到了不少有识之士的揶揄,“名誉”也将扫尽了。
还有蹩脚的《余秋雨的背影》,是别人为他写的一本“评传”,也是令人读来肉麻的书。它声声赞颂,并不能给余秋雨的“名誉”添彩,相反,却让人看到原来余的朋友之才华技巧是如此之低劣。稍有点冷静头脑的人,都不会写出这样的书。不知余教授对此书作如何感想,如果是默契的话,那么又证明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句话了。
总的来说,余教授从文坛走向法庭,说明了他走的是离开了文学的道路。依靠法庭去解决文艺批评之争,是不恰当的。一个作家如果只靠法庭去争“名誉”,那么,该人已走向末路了。
(《鲁迅世界》2003年4期)
|
|
 
本书由“啃书虫”免费制作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