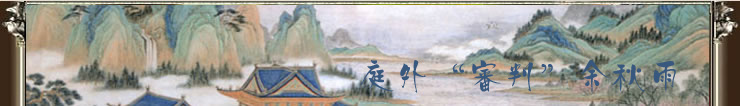 |
 |
|
看余秋雨告状修仰峰 余秋雨打官司的悲剧性解读
|
 |
 |
|
余秋雨状告《北京文学》编辑肖夏林侵犯名誉权一审败诉后,已向北京第二中院提出上诉。(9月14日《北京青年报》)单纯看这件事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它只是余秋雨众多官司中的一个。但如果从文学与市场的关系来看,则会发现其悲剧性的标本意义。
文学的魅力在于对社会和人性的深刻揭示,这一点决定了文学必须有相当的审美高度,与社会生活保持一定的距离。而实行市场经济后,我国文学及文学从业者迅速边缘化,社会地位与实际利益一落千丈。文学何去何从,一批感觉敏锐者(余秋雨就是杰出代表)迅速作出反应:主动融入市场,在创作过程中开始考虑市场需求,将产业意识引进文学领域。这对文学创作者们来说未必是坏事——借助市场,文学作品可以得到更为通畅便捷的传播,拥有更大范围的受众群体,也获得了更为丰厚的物质回报。欧美近现代众多知名作家的经历无不证明,市场化对文学并不完全是一剂毒药。在这个意义上,余秋雨迅速走红。
然而,市场化是把双刃剑,一旦涉入者驾驭市场的定力不足,市场的腐蚀能量就慢慢浮现——破坏涉入者的审美感觉不说,还将从根本上使文学作品逐渐沦为商品,文学创作逐渐褪色等同为流水线生产方便面的商业活动。这个时候,支配他们的不再是文学创作自有的原则,而是商业规律,其核心就是利用一切手段谋求利润最大化。从状告余杰、金文明到肖夏林,余秋雨为什么老打官司,其内在动力正在于碍了大众对其作品的美誉度以及眼球效应,有损于名义上为名誉权实则为增值空间的扩张。在这种博弈过程中,个人道德与品质如何不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尤其当余秋雨频频以文化活动家身份担任重大赛事评委或某城某地文化顾问时,他只是文学或文化商业化的一个符号,这个符号是中性的,与性别、道德、美感无关,它的价值指向很简单亦很明确:最大的利润空间。
余秋雨打官司作为一个研究标本的悲剧性,或者说文学过度市场化的悲剧性在此表露无遗:在余秋雨以市场为工具力图打通文学创作、传播的“任督二脉”时,他也自觉不自觉地成为市场驱使的工具;没完没了地打官司与论战也许并非余秋雨个人所愿,但一种莫名的力量又促使他必须这样做,因为“余秋雨”已不仅是文学名家,而是一种可以魔术般扩展的资本。资本与市场的贪婪本性决定了余秋雨笔墨官司的一而再而三,决定了每本新书出版前商业气息浓重的同一模式炒作。而这种市场与资本对人的异化,马克思、本雅明都有过大声疾呼。
最现实的问题是:面对市场的挑战与诱惑,余秋雨们何去何从?是在利润的石榴裙下沉沦,还是以此为炼狱期待灵魂的重构?这也许是“余秋雨打官司”悲剧性中蕴涵的积极意义——对文学中人如此,对志在全面奔小康的国人同样如此。
(中国青年报9月19日)
|
|
 
本书由“啃书虫”免费制作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