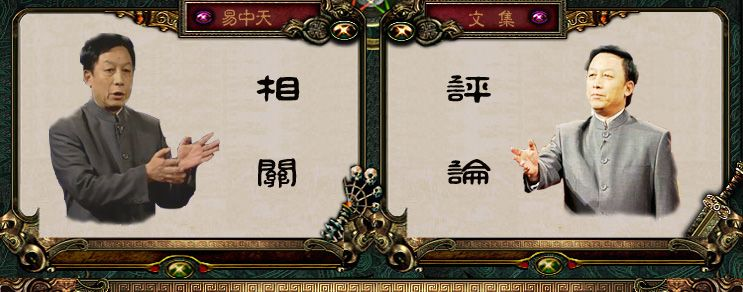 |
|
钢丝上的舞蹈
|
 |
|
——读易中天《破门而入:美学的问题和历史》
易中天这几年都在干啥?
关心易中天的读者难免要这样问。其实答案是明摆着的,大家心里也都清楚:他在写通俗读物。他写《闲话中国人》、《中国的男人与女人》、《读城记》、《品人录》等《随笔体学术著作》,写《书生意气》,写各种评论时事的杂文,甚至写小说。问题是对于他的这种选择,有人赞同,有人反对。赞同的人认为学术本来就应当走出象牙塔,走向大众,走向市场,因为学术本身就具有启蒙的性质,如果能够在启蒙的同时顺便赚点钱,何乐而不为?反对的人有两种,一种出于惋惜,一种出于嫉妒。惋惜者多半是些老学究,他们认为易中天本来是搞学问的,而且确实搞出不小的名堂,以他的才华,完全可望更进一步,出更多的成果,现在居然自愿“下海”,岂非自掉身价,甚至“自甘堕落”?嫉妒者多半是些无能之辈,他们和易中天一样,在高校也混了多年,做了大半辈子学问,可是名声不大不小,学问不高不低,出版著作也只好仰仗这个基金那个赞助,现在眼睁睁地看着易中天慢慢地如日中天,炙手可热,私下不免嘀咕:这厮原本水平和我也差不太多,何以运气就比我好?继而不免挑剔:易中天这个也写那个也写,出书如此神速,难道不会只管数量不管质量?不会滥竽充数?不会到了最后便没什么可写了?
其实不管是惋惜还是嫉妒,都是出于不了解,不了解就是无知。无知在于以为学术一定是艰难高深的,一定和通俗绝缘。他们忘了柏拉图的对话本来都是通俗读物,甚至公认最为艰难高深的康德也曾不遗余力地追求通俗。无知也在于以为通俗一定是很容易的。以为只要自己愿意放下架子,就必定通俗得起来,而且通俗得不比易中天差。易中天新著《破门而入》中引用的克罗齐的观点正好可以对付这种无知。克罗齐说,好些人都说他们有的是伟大的思想,只可惜表现不出来,但如果他们当真有伟大的思想,哪有表现不出来的?
什么是做学问?在我看来,做学问也就是将那些本来只是朦朦胧胧模模糊糊的东西用尽可能清晰的语言表达出来。比方说你隐约感觉着某个现象或某种观念或某些问题有些不对劲,有些奇怪,于是你分析这种不对劲的奇怪的感觉,使它浮到意识的表面上来,最终将它明确为某个问题,某种观点,固定在语言之中。这时你就是在做学问。所以“追求清晰”的需要乃是做学问的基本动力。那么什么是通俗呢?通俗当然可以有好几种解释,易中天的通俗正如《破门而入》的封面所书:“用通晓明白的语言,说深奥难懂的问题”。我想不通这种“通俗”与“学术”之间怎么可能存在冲突。我也想不通为什么将学术通俗化居然会被看作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难道不是只有“极高明”才能“道中庸”么?我以为,那些无法将自己的文章写得“通晓明白”一点的人,恰恰由于他本来就没有这个能力。
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只有表达得通俗易懂的学术才是好的。我只是说通俗易懂的学术著作很是有它存在的必要。这里不妨比较一下易中天的著作和他的朋友邓晓芒的著作。在中国目前的思想型或学者型的作家当中,我最爱邓晓芒、周国平和易中天三人,收集有他们的全部著作,一直是他们的热心读者。邓晓芒著作的学术水平有目共睹,而且显然也属于“通晓明白”的一类,但这只是由于超人的逻辑能力而导致的思维清晰,至于他的表达则无论如何也不能算是“通俗易懂”的。他的精神居于九天之上,高峰之颠。不过邓晓芒并不是那种“将思辨的城堡建造得高耸入云”的人,他也有一些自己认为是很“通俗”的作品。然而邓晓芒就算偶尔“将哲学从天上带到人间”,也还是带着从高空而来的刺骨的冰冷气息,我们必须将自身包裹得不畏寒冷,才能接近他的世界;必须提升自己的层次,才能和他进行对话。打个比方(只是打个比方,不算过分吧?):邓晓芒的表述有如耶和华或摩西,雷霆霹雳,振聋发聩;而易中天的表述有如耶稣或苏格拉底,和蔼可亲,平易近人。读邓晓芒的著作紧张,读易中天的著作轻松。人需要精神的紧张,才能实现重大的事业和严肃的目的。然而,整日价的紧张兮兮容易使人精神崩溃,这时候就需要调剂以精神的松弛。我们需要邓晓芒的紧张,也需要易中天的轻松。
现在还有一个疑问:易中天的书的确好读,好懂,有时甚至妙趣横生,但那会不会只不过轻松一回,过瘾一下,最后居然一无所获?或者它们会不会只有“调剂”的功能?产生这种疑问是可以理解的,谁都不愿意读书读到最后居然“白读”了。众所周知,追求通俗也不是没有危险。当一位作者把自己的主要精力集中于去寻找“深奥难懂的问题”的简单生动的表达时,往往会导致忽视了对问题本身的深入钻研;可能当他表述得很浅时,不知不觉把自己的思想弄得同样肤浅。这其实也是将学术通俗化的真正困难所在:你必须在“浅出”的同时做到真正的“深入”。但是易中天居然将这条钢丝走通了。不但走通了,而且走得有惊无险,履险如夷。《破门而入》可谓一场钢丝上的精彩舞蹈表演。
《破门而入》写得实在好。好到什么程度?我个人的意见,本书乃是易中天到目前为止写得最好的学术著作。比他的处女作《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好,比他的获奖作品《艺术人类学》好,也比他几年前尝试通俗地表达他的艺术理论的《人的确证》好。老实说,我也曾经为易中天担忧,他这样写来写去,会不会有一天没有东西写了?这样的例子也不是没有。比方说周国平。我读周国平著作的过程有如东郭子向庄子问道,感觉每况愈下。读《守望的距离》,激动;读《各自的朝圣路》,佩服;读《安静》,冷淡;读《自传》,失望。我觉得这部自传好比庄子抛出的最后一个回答,于是我的反应也只好是“东郭子不应”。当然这并不是周国平的过错,而是我对他期望过高的缘故。然而一位读者不应当对他向来信任的作家提出哪怕稍微高一点的要求吗?周国平越写越差,易中天越写越好。当我读到他的新著《艰难的一跃》和《破门而入》时,我更加坚定了以下的想法。人们可能不得不承认:余秋雨已经“王朝灭亡”(没有其他意思,也没有贬义,只是说他的高峰期已过),周国平已经“江郎才尽”,而易中天正是“方兴未艾”。照《艰难的一跃》和《破门而入》的势头发展下去,易中天有可能成为将来几年中拥有最多读者的学者作家。
还是谈谈《破门而入》吧。自从“美学热”在中国偃旗息鼓以来,就再也看不到几本关于美学的好书了。不过事情也许刚好相反,正因为没有什么有价值的建树,才导致了“美学热”的陡然降温。《破门而入——美学的问题和历史》的问世,在如今这种充斥着故作高深然而言之无物的读物的美学界,有如异军突起,破门而入,令人耳目一新。熟悉易中天或看过本书的人都知道,这部著作是有来历的,它的前身是邓晓芒和易中天合著的《黄与蓝的交响——中西美学比较论》。不过它并不是以往成果的简单复制,也不只是将以往成果加以“演讲体”的通俗化而已。当然“问题”并没有改变,“历史”可能也没有太大的不同,但是易中天加入了两种成分:十余年来的教学经验和独立思考。
先说教学经验。易中天绝对是个一流的导师,他的讲演向来是名闻遐迩极受欢迎的。他似乎将自己降得很低,低得甚至有些离谱,低到和你相当的水平,一开始你还以为他原来也没什么嘛,不过讲讲笑话编编故事而已,然而这不过是易中天耍的一个花招。这个花招苏格拉底用过,耶稣也用过,释迦牟尼和观音菩萨也用过。他们是渡什么人,现什么相。当你正在自我陶醉的时刻,易中天突然抛出了一个问题,于是你开始想问题、猜谜语,慢慢地觉得有点意思了,站在美学的门槛上了。可是易中天却在这个关键时刻带着你兜圈子,看风景,玩了一圈回来一看,原来谜语已经变了样,呈现出另一种气象。这时才发现易中天原来站得比你高。你已经被带到上面一层楼房。就这样问题不停地抛出,逻辑持续地延续,例子不断地闪现,你离地面越来越高,每一层都有一些意外的收获。于是你发现美学之路原来有章可循并且美不胜收。最后易中天把你带到顶楼,就像一个恶作剧的顽童,脸上挂着神秘的微笑,一把拉开幕布,将谜底揭露出来。你当场被弄得懵懵懂懂,因为以前谁也没有让你看到谜底是怎样打开的。下楼回家一想,美学有了崭新的面孔。就好像与苏格拉底辩论过的人,经过一场辩论,前后看世界的眼光发生了难以想象的变化。而且说来也怪,爬了这么高,居然一点不累。易中天将问题的分析、展开和解答结合在百来个十分巧妙的例子之中,既给你理智的启发,也给你情感的体验。随便举个例子,比方说关于“移情”的讲解。这个话题并不新鲜,自朱光潜先生首次介绍移情论以来,哪一本美学著作不曾出现这两个字眼?然而易中天不过轻描淡写地用了两三千字,点到为止,不落俗套,将它的现象、特征、原理和缺点一网打尽,而其中的几个例子用得多么恰到好处啊!
再说独立思考。从写作《艺术人类学》后,易中天这几年一直在经营艺术学。他认为艺术学是美学发展的现代阶段。也就是说,他的美学研究的侧重点转向艺术问题。立足于艺术的美学和立足于纯粹哲学的美学是有点不同的。于是,有些东西被省略了,有些东西被缩减了,有些东西被放大了,有些东西更被重视了——也就是说,相同的问题和相似的历史,现在被一种不同的目光重新加以审视。
比方说,对康德美学的解释几乎就是全新的。将康德美学讲得如此举重若轻,深入透辟,而且颇有新意,国内唯有易中天一人而已[1]!我想,如果以洞见的深度和思维的慎密作为衡量标准,那么邓晓芒研究康德美学的《冥河的摆渡者》有可能是当今中国美学界的最高水平(我以为邓晓芒能够同时在两条思维线路上正确而清晰地思维,而有些学者连按照一条逻辑线路有序地思考都办不到)。然而说来惭愧,我好歹也算是学美学的,这本书也只能是囫囵吞枣般地“啃”了下来。由于它过于艰深,甚至不屑于举例,它是邓晓芒的著作中对我帮助最少的一本。易中天的《破门而入》就不一样了。也许易中天理解康德和邓晓芒理解康德在原则上是一致的——毕竟他们曾经共同提出一种叫做“新实践美学”的理论,但是易中天的康德不是邓晓芒的康德。听易中天讲康德,你会觉得如顾恺之倒食甘蔗,渐入佳境;如陶渊明探桃花源,曲径通幽,豁然开朗。
我还想特别推荐一下书中作为附录的《中国古典美学史纲》。长期以来,我一直为李泽厚的《美的历程》后无来者而深感遗憾。正如作者在本书中的评价,目前流行的不少中国美学史其实根本不是“历史”,而是“历史资料”。真正的历史是有规律的,它的发展是有逻辑线索的。而且真正的美学史是要潜在地包含着作者本人的美学原理的。能够同时满足这两方面要求的,似乎只有李泽厚的《美的历程》。现在从这个短小的史纲中,似乎看到了某种希望。它是“史纲”,但是并非只有逻辑纲领,并不枯槁,其实还蛮丰满的,甚至也不缺少材料。这个史纲比起原来《黄与篮的交响》中对中国美学史的逻辑描述,显然更为整齐,更为全面,也更为生动。
终于到了对本书提点意见的时候了。我想假如我光是高唱颂歌,满口阿谀奉承,不但读者对我嗤之以鼻,作者本人也要不以为然。实际上,好书是不怕提意见的。我完全可以对柏拉图大师挑出一大堆毛病,但这根本不会伤害柏拉图的一根寒毛。我对《破门而入》的意见有三条。一是原则的,二是观点的,三是细节的。
原则是指对艺术的解释“艺术是人的确证”(关于艺术本质)。这个说法和“艺术是情感的对象化形式”(关于艺术作品)、“艺术是情感的传达”(关于艺术活动),是易中天对艺术的三个层次的界说。既然是对本质的解说,则必定是对艺术下定义;既然是下定义,则必定是对艺术的归类。黑格尔的定义“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其实应当颠倒为“美是感性显现的理念”,“理念”是个名词。易中天的定义好像不能颠倒为“艺术是确证的人”,而在“人的确证”中,“确证”也不好说是个名词,反倒有点像动词。因此这个说法只能是对解释艺术的人学立场的强调,而不能看作艺术的定义。
观点是指对“形式”概念的理解。易中天关于形式的解释很独特,好像是一种“泛形式”观,好像很多东西都是形式,但是形式的核心却没有指明。我想艺术作品必须有形式,是由于艺术作品必须有观众;所有的艺术作品都要有观众,因此所有的艺术作品都要有形式。没有形式,就不可能实现情感的传达。易中天曾在书中的一个旁注指出,戏剧与舞蹈的根本区别是戏剧必须有观众而舞蹈可以没有,我注意到邓晓芒在为《艺术人类学》写的序言中也肯定这一点。但是他们两人明明都强调,情感的传达是艺术活动的核心。所谓情感传达,首先当然是指艺术家(比方说舞蹈编导)把自己的情感传达给观众,既然如此,作为艺术的舞蹈怎么可以没有观众呢?以他们两人思维之严密,竟然会出现这个疏忽,确实有点奇怪。
细节是指比方说对朱光潜的评价。易中天对朱的《悲剧心理学》情有独钟,誉为朱最好的著作。但是我个人以为,朱最好的著作是《西方美学史》。朱光潜的功绩在于全面系统地介绍西方美学,“介绍”当然要客观、到位、准确。在《悲剧心理学》中,朱光潜的经验常常误导了逻辑,个人的知识常常歪曲了大家的学说,而《西方美学史》则基本上没有此弊。
最后我还要强调,《破门而入》是一部封面设计和版面设计都非常漂亮的书籍,为易中天所有著作之最。本书提供智慧的启迪、知识的传授、美感的体验,甚至暗中教导了一种做学问的方法,这么多优点集于一身,已是十分难能可贵,现在还将装帧设计得如此好看,使人不禁油然而生将它收入个人书架的冲动。
作者: 苔花如米学牡丹
回复:钢丝上的舞蹈——读易中天《破门而入:美学的问题和历史》
真是好贴子!谢谢苔花找出来分享!看健勇君这番感言后,我深有感触,也想说点什么。
记得读这本《破门而入》还是去年年底……
刚入大学,院系平台课里开着“文学概论”,虽说以前在家里书架上翻过几页这类书,当时也没有心情去琢磨--爸爸当年上大学的书,看着觉得挺生硬的……开课之后,耐着性子把《文概》啃将下去,可是经常看着看着就迷糊了,各种学说扑面而来不论缘由任意穿插好像我们这些初学者很熟悉这些理论似的,经常提到“审美”“美学”,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格罗塞,康德,“结构主义”,“形式主义”,“符号”……这些称呼倒是听着耳熟,可是具体的内容是什么呀,都有什么联系,为什么会在文学概论里经常提到“审美”“美学”呢……这门课开得我们很是疲惫,不到两个月换了三个先生,每个人都讲自自己的“研究成果”,虽然差不多都是名教授,大家听得也是兴味昂然,我却觉得有点像空中阁楼飘着,听完过后真正又有多大收获呢--一边听他们讲,一边自己啃书,拿着书单却不知从哪儿看起……真是一头雾水,郁闷至极。
恰好那段时间在图书馆淘易先生的书,经常在众人奇怪异样的眼光下抱着书痴痴地笑,引得旁人好奇我在看什么……当我顺着书目找到《破门而入》时(05年1月版),哈,确如健勇君所言--对比以前易先生出的书,这本书装帧设计简约大气,色调搭配时新抢眼却不落俗套,内页版面设计就更不待言,看着就相当舒服。最重要的是他恰好破门而入讲美学,这正是我最想了解的却又最找不到北的,真是救命了,呵呵。
迫不及待地进入“第一讲”,映入眼帘的第一句话就是“学术不是‘一夜情’,它是‘谈婚论嫁’”。天啦,为之叹服!也许就是从那一刻起,我感到了先生调侃背后的深意。顺读下去,简直是欲罢不能,边作笔记边看,不时产生共鸣会心而笑--尤其是先生对于中国传统教育的质疑和反思以及自己的切身想法--让我大受鼓舞备感理解深觉愉快!!!我印象中把这翻道理明摆出来还说得这么透彻的,第一所见是周国平先生的散文集中;而这一次,易先生是把一切(我心里懵懂着的东西)全道破了,真是受益匪浅岂不快哉!(其实,我当时正有点患得患失呢。)下面对于美学性质的阐释让我放了心,那个似乎很高很远的学问原来如此平实可感……时间过得好快,一讲细读下来闭馆的时间也到了……从那以后,每天穿梭于教室与图书馆之间,恨不得一有点时间就去跟着先生去“敲敲”美学的大门。正如易先生所说的那样,他是围绕问题讲历史、又是历史地讲问题,向后看去,在历史的线索中讲述着一个又一个问题,而又在问题地解决中,历史前进着。
当我匆匆忙忙囫囵吞枣地读到《破门而入》最后一页时,当我们文学概论讲完最后一节老师忙着作总结时,我看着一段时间的读书笔记,回想着一段时间一路小跑跌跌撞撞地跟着先生去梳理美学的问题与历史时,很久以前的迷雾已慢慢消逝,而我的思路渐渐清晰起来。当然我自知,这本书,其实只是先生引着我们走了一条捷径去接近去亲历一次美学发展史,若要深入恐怕还是要自己下功夫。这时候,我对先前觉得的文学概论里的深奥理论已不再感到费解(当然文概教材上有些话显然是纠缠不清的),甚至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审美就是情感的对象化过程,美感是对象化了的情感”“不通过传情的媒介,不通过情感的对象化,情感就不能得到传达或共鸣。因此不但传是审美的本质,而且审美是传情的唯一手段……”,“……艺术品的任务,主要是实现人与人之间情感的传达;审美对象的任务,主要是实现自己和自己情感的传达。”,“艺术是人的确证,美则是能确证人之为人的东西”……我想,文学作为一门艺术自然体现着艺术的特征,功能和本质,无怪乎他要说“文学是一种话语蕴籍的审美意识形态”,难怪文学的理论里处处谈审美,处处引用美学的“历史”与“问题”……
我是本书的受益者,的确如此。我的感受如上所说。而当我们在文学概论最后一堂课上同学的提问中,我也是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我的受益。很多同学“套”题不成,索性怒问--我们这学期文学理论都学了些什么啊?一阵心寒。我觉得同学确实很无奈,也很无助。先生们都在讲自己的成果,还换了三个人,各人的见识不同,喜好不同,弄得大家都像在听戏,评着谁“唱”得好,谁有风格,谁更前卫,是啊,很多先锋派艺术时新名词都介绍了进来,只是听个好玩么?!一位先生侃尼采侃了九节课,还不如找本《悲剧的诞生》花一下午看看周国平写的序呢。空中楼阁注定是一团幻影,我们不会是这种教法的受益者。我想,以后开这门课之前是不是可以先开一门美学入门课呢,或者至少该多读读美学方面的书。
周围同学深感焦虑之时,刚刚看到点眉目的我向他们力荐了这本书。一位自称彤心彤德的朋友立马进了图书馆,那是她第一次踏进那个阅览室,一向视那儿为禁地的她是闭馆时最后一个走出来的……她兴奋地向我描述看这本书时那个激动和愉快---我们都有这种感受,健勇君分析的很透彻:
“他似乎将自己降得很低,低得甚至有些离谱,低到和你相当的水平,一开始你还以为他原来也没什么嘛,不过讲讲笑话编编故事而已,然而这不过是易中天耍的一个花招……当你正在自我陶醉的时刻,易中天突然抛出了一个问题,于是你开始想问题、猜谜语……可是易中天却在这个关键时刻带着你兜圈子,看风景,玩了一圈回来一看,原来谜语已经变了样,呈现出另一种气象。这时才发现易中天原来站得比你高。你已经被带到上面一层楼房。就这样问题不停地抛出,逻辑持续地延续,例子不断地闪现,你离地面越来越高,每一层都有一些意外的收获。于是你发现美学之路原来有章可循并且美不胜收。最后易中天把你带到顶楼,就像一个恶作剧的顽童,脸上挂着神秘的微笑,一把拉开幕布,将谜底揭露出来。你当场被弄得懵懵懂懂,因为以前谁也没有让你看到谜底是怎样打开的。下楼回家一想,美学有了崭新的面孔。就好像与苏格拉底辩论过的人,经过一场辩论,前后看世界的眼光发生了难以想象的变化。而且说来也怪,爬了这么高,居然一点不累。易中天将问题的分析、展开和解答结合在百来个十分巧妙的例子之中,既给你理智的启发,也给你情感的体验……”
“回望射雕处,千里暮云平”。承着健勇君这段极其精准的分析,我想到了这句话,也许,不,读易先生这本书一定是这种感受。
作者: 影落明湖青黛光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