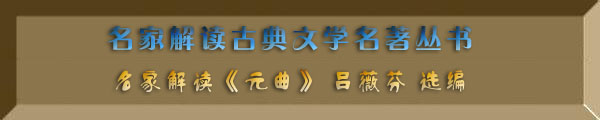周兆新:漫谈《汉宫秋》第四折
|
|
(一)
《汉宫秋》是元杂剧中一部不朽的名著,这部名著的重点在第四折。
如果单独看第四折,既没有引人入胜的矛盾冲突,又没有曲折复杂的戏 剧情节。它的登场人物也少得可怜:除了临近结尾的地方尚书五鹿充宗 出来讲几句话以外,基本上是汉元帝一个角色独唱;另外还有个小太监, 像个影子似地跟在他后面。然而这一折并不显得单调和沉闷,相反却具 有震撼人心的巨大力量。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强烈的效果?重要原因之 一,是前三折已经为第四折精采场面的出现作了充分的准备。因此,我 们必须把第四折与前面的戏联系起来进行分析。
《汉宫秋》第一折,主要是写王昭君因为不肯向毛延寿行贿,曾经 被点破图像,发入后宫,可是汉元帝在一次巡宫的时候,听到王昭君弹 琵琶的声音,发现她是一个容貌出众多才多艺的女子,对她产生了强烈 的爱情。这一折的气氛非常欢快,汉元帝与王昭君都沉浸在幸福之中。 试看汉元帝唱的[金盏儿]曲:
你便晨挑菜,夜看瓜,春种谷,夏浇麻,情取棘针门粉壁上除了差法。你向正阳门改 嫁的倒荣华。俺官职颇高如村社长,这宅院刚大似县官衙。谢天地,可怜穷女婿,再谁敢 欺负俺丈人家!
语言很诙谐,流露出一种按捺不住的洋洋得意的情绪。作者在第一折尽 力渲染汉元帝高兴的心情,显然是为了与末尾第四折形成鲜明的对照, 也就是先替剧本主人公设置一个顺境,以便于反衬后面的逆境。这是一 种先扬后抑、欲擒故纵的表现手法。汉元帝在第一折得到王昭君时越是 欣喜欲狂,到第四折失掉王昭君后悲哀的心情也会越重。
第二折和第三折写毛延寿把美人图献给了匈奴的呼韩邪单于,于是呼韩邪以武力威胁汉王朝,强迫汉王朝交出王昭君。汉元帝本来坚决不 肯让王昭君出塞,无奈五鹿充宗、石显等文武大臣都怯懦无能畏刀避箭, 没有人敢带兵前去抵抗匈奴。汉元帝费尽唇舌反反复复地责备他们,他 们仍然提不出任何使匈奴退兵的计策。最后汉元帝只好到灞陵桥为王昭 君饯行,眼巴巴地看着她被匈奴使者带走了。王昭君到边界上即投江自 尽。在这两折中,汉元帝面临着意想不到的灾祸,竭尽全力进行挣扎, 终于没能逃脱不幸的命运。他由欢乐的顶峰一步一步地跌入了痛苦的深 渊。尤其是汉元帝与王昭君的离别,乃是整个故事最大的转折点,也就 是逻辑上的高潮。在《汉宫秋》这个剧本中,逻辑上的高潮与感情上的 高潮并没有重叠在一起,因为汉元帝满腹的辛酸悲苦,在送别时还没来 得及尽情倾吐。但第三折逻辑上高潮的出现,已经造成了骨鞭在喉不吐 不快的形势,从而为后面再掀起一个抒发感情的高潮,创造了必要的条 件。
以上说明,前三折的戏,全部指向一个明确的目标,全是为第四折 积蓄力量。由于前三折铺垫得好,第四折才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形成 了一个特别激动人心的场面。
(二)
《汉宫秋》不仅描写了一场爱情悲剧,而且描写了一场政治悲剧。 汉元帝与王昭君既是一对情侣,又是两个政治人物。他们的爱情关系的 发展,始终与政治斗争交织在一起,始终与国家的命运密不可分。
历史上的汉元帝并没有宠幸过王昭君,他在位的时候汉王朝还比较强盛,而匈奴则趋于衰落。他派遣王昭君和亲也不是由于受到匈奴的逼 迫,而是为了巩固汉王朝与匈奴之间业已存在的友好关系。王昭君去匈 奴是自动请行的,她出嫁后曾经生儿育女,根本没有投江自尽。①然而马 致远创作《汉宫秋》的目的,并不是如实地反映西汉时代的状况,而是 利用历史题材曲折地表现自己生活的那个时代,寄托自己对于当代生活 的一些看法。作为一个失意的汉族知识分子,马致远亲身经历了元朝灭 宋的社会大变动,目睹了元朝政治的黑暗,很自然地会产生追怀故国的 情绪。他在创作《汉宫秋》的时候,对《西京杂记》中有关王昭君的传 说进行了大胆的改造,①虚构了汉元帝与王昭君的爱情悲剧,并且以此为 线索,把宋末元初的时代特征熔铸进历史题材中去。杂剧中汉朝与匈奴 的关系,不符合公元前一世纪的真实状况,但很像软弱无力的南宋王朝 与咄咄逼人的元王朝之间的关系。毛延寿、五鹿充宗和石显的艺术形象, 都与历史上的真人对不上号,②而是反映了南宋末年大批卖国求荣或贪生 怕死的文臣武将的丑恶面貌。王昭君已经不同于历史上那个担负着促进 民族友好的光荣使命的姑娘,而是一个在强敌压境时勇于自我牺牲的爱 国主义者。汉元帝也不像历史上那个太平天子,相反却很像一个亡国之 君。作者往往通过汉元帝的嘴,讲一些自己想说的话,在某种程度上把 他当成了自己的化身。从表面上看,《汉宫秋》第四折是写一个古代帝 王怀念他所钟爱的妃子。从实质上看,这一折乃是作者马致远借古人之 酒杯,浇自己之块垒,以隐晦和间接的方式,怀念一个消失了的时代, 哀悼一个灭亡了的国家。因此,这一折当中以汉元帝的名义抒发的思想 感情,与南宋灭亡以后大批遗民的思想感情非常接近。我们不妨看一下 第四折中咏唱孤雁的一支〔白鹤子〕曲:
多管是春秋高,觔力短;莫不是食水少,骨毛轻?待去后,愁江南网罗宽;待向前, 怕塞北雕弓硬。
再把这支曲子与南宋遗民梁吉士的《四禽言》诗比较一下:
行不得也哥哥,湖南湖北春水多。九嶷山前叫虞舜,奈 此乾坤无路何。行不得也哥哥!
(《宋遗民录·卷一》) 曲子和诗创作于同一个时代,都运用了托物寓意的表现手法,都是国破 家亡之后流落无依的人们的生动写照。由此可见,第四折的情节虽然极 其简单,但内容却异常深广,它概括了作者对于整整一个历史时代的深 切感受。当然,其中浓厚的绝望和感伤的情绪,也反映了马致远世界观 的消极方面,是远离群众斗争的封建知识分子找不到正确出路的一种表 现。
① 《汉书·匈奴传》:“竟宁元年,单于复入朝,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赐单于┅┅王昭君号宁胡阏氏,生一男伊屠智牙师,为右日逐王┅┅”《后汉书·南匈奴传》:“昭君字嫱, 南郡人也。初,元帝时以良家子选入掖庭。时呼韩邪来朝,帝敕以宫女五人赐之。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 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
① 《西京杂记》:“元帝后宫既多,不得常见,乃使画工图形,按图召幸之。宫人皆赂画工,多者十万, 小者亦不减五万,独王嫱不肯,遂不得见。匈奴入朝,求美人为阏氏,于是上按图,以昭君行。及去,召 见,貌为后宫第一,善应对,举止娴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帝重信于外国,故不复更人。乃案穷其事, 画工皆弃市,籍其家资巨万。画工有杜陵毛延寿┅┅。”
② 参看《汉书·佞幸传》。
(三)
第四折的构思非常巧妙。作者先让汉元帝做了一个梦,梦见王昭君 从匈奴逃回汉宫,但他还没有来得及与王昭君细诉衷肠,即被长空大雁 的叫声所惊醒。于是他徘徊于殿前,对着大雁,淋漓尽致地倾诉了自己 极度苦闷忧伤的感情。这种写法的优点,首先是为汉元帝思念王昭君提 供了一个典型环境。作者选择的时间是秋天的夜晚,地点是萧条冷落的 深宫。就在这个地方,当初百花盛开春意正浓的时候,汉元帝曾经踏着 皎洁的月光,遇见了仙女一般的王昭君。现在人事已非,只剩下一张美 人图悬挂在殿前,怎能不使汉元帝倍觉伤感?然而宫殿和美人图毕竟是 无声无息和静止不动的,作者别具匠心地引来一只失群的大雁,就借助 于乐队摹仿雁叫的音响效果,给静的环境增加了动的因素,从而渲染出 更加浓烈的秋天的气氛。深宫的荒凉,雁叫声的凄厉,与人物的精神状 态完全融会在一起,环境对人物起到了很好的衬托作用。白朴的《梧桐 雨》写唐玄宗在雨打梧桐的滴滴嗒嗒的声音中哀叹,莎士比亚的《李尔 王》写李尔王在风雨交加的大森林里行走,郭沫若的《屈原》写屈原在 东皇太一庙中向着雷电呼喊,曹禺的《胆剑篇》写勾践在会稽山中对着 胆和剑宣誓,与《汉宫秋》第四折都有异曲同工之妙。
其次,由于一只大雁突然惊破汉元帝的幽梦,使这一折极其简单的故事情节有了发展变化,郁积在汉元帝胸中的潮水般汹涌澎湃的感情, 也有了一个具体的发泄对象。例如汉元帝先是对大雁满怀怨恨,埋怨大 雁使他无法在梦中与王昭君团聚,继而又产生了种种揣测和联想:他想 到这只失群的雁像自己一样孤独和可怜,又想到大雁也许因年纪太老而 无力高飞,也许因缺乏食物而饥肠辘辘,也许正感到进退两难,找不到 一块安身之地。大雁的叫声像锥子一样刺痛了他的心,给他带来了无穷 的烦恼,他希望大雁快些飞走,使自己获得片刻的安宁,可是大雁偏偏 不肯离去┅┅就这样,作者让人物的歌唱与大雁的叫声互相穿插,互相 应和,用铺陈的手法,层层深入地揭示了人物的内心世界,并且替人物 设计了大幅度的形体动作,于是本来没有什么戏剧冲突的单纯抒情的场 面,凭空增添了不少戏剧性。
第三,大雁不只是构成典型环境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且同时起到了象征的作用。由于作者选择和安排得非常恰当,这只大雁已经由一只普 通的鸟,变成了一个具有高度概括性的艺术形象,变成了现实生活中某 种类型的不幸的人的象征。剧中写大雁的徘徊,大雁的哀鸣,都不仅仅 是对于实景的描绘,而是兼有象征的意味。《汉宫秋》在叙事和抒情的 基础上,适当地揉合进了一些象征的成分,这样就以含蓄委婉的方式, 表现了异常丰富的内容,并且发人深省,耐人寻味,给读者留下了广阔 的想象余地。
总之,《汉宫秋》第四折在艺术表现方面有许多独到之处,值得我 们很好地研究和借鉴。
(选自《元杂剧鉴赏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3 年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