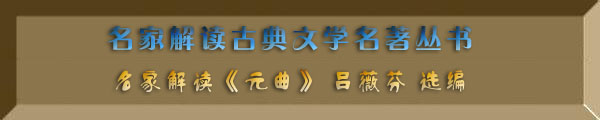宋常立:《汉宫秋》悲剧艺术二题
|
|
“悲剧艺术是一种特别艺术”(亚里士多德《诗学》)。悲剧美的 艺术力量,是任何别的艺术所难以替代的。马致远的杂剧《汉宫秋》是 写王昭君与汉元帝的爱情悲剧的。在所有以王昭君故事为题材的古典戏 剧中,《汉宫秋》被人称为“绝调”(焦循《剧说》),至今,仍以不 可抗拒的魅力,给我们以艺术的享受。
悲剧形象美的创造
自汉代以来,王昭君的悲剧故事代代相传,以昭君悲剧为题材的各 种形式的文艺作品,多不胜数。但是,在《汉宫秋》以前,没有一部作 品中的昭君形象能达到悲剧审美的要求,而马致远在《汉宫秋》的悲剧 创作中,做了开拓性的艺术创造,第一个创造出具有悲剧形象美的昭君 形象。总结一下马致远创造王昭君悲剧形象的艺术经验,对于我们认识 悲剧创作的艺术规律是有益的。
王昭君的形象是《汉宫秋》悲剧的灵魂。她是悲剧事件的心人物,作为主唱角色的一切唱调——汉元帝的内心活动,主要就是围绕着王昭 君而展开的。更为重要的是,王昭君还是《汉宫秋》中唯一的一个被剧 作家全面肯定的悲剧人物形象,有着强烈的悲剧美的感人力量,她使以 往任何同类题材作品中的昭君形象相形见绌。正是王昭君悲剧形象的 美,使《汉宫秋》获得了永久的魅力。
马致远对昭君形象是怎样构思与创新的?这只有在昭君故事历史发 展的比较中,才能看清。
昭君和亲出自汉朝,其事始见于《汉书》中的《元帝纪》和《匈奴 传》。但是,记载较详,并使昭君成为一个悲剧性人物的,是《后汉书·南 匈奴传》。据《后汉书》记载,昭君是以民间“良家子”的身份被选入 宫的,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待召掖庭的宫女。她“入宫数岁,不得见御, 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自请求行和亲,这一勇敢的带有反抗意味的行动,见出昭君是一个有个性、有见识的女子。这是王昭君最初作为 悲剧性人物出现时的本来面目,应该说,也是符合生活真实的面目,因 为她的命运不仅概括了广大被压迫被损害者的命运,而且从她的性格行 动当中,也体现出些那身处底层的人们要与命运搏斗的精神,而这正是 生活的底蕴。
这些见于正史显著地位中的记载,历代创造昭君故事的作者们,是 不会不知道的。但是,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未能正确地利用这一历 史素材,在写出昭君不幸命运的同时,使她富于反抗的性格放出光彩, 反而是用愈来愈浓重的宿命色彩,把她涂抹成一个只知一味悲苦啼哭的 薄命女了。
马致远却能独树旗帜,正确地把握昭君的悲剧性格,并使之达到艺 术真实与生活真实的统一。马致远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有其主客观的条 件在。
在元代,异族统治者的歧视和压迫政策,把一大批汉族知识分子抛 向了社会的最底层,科举无门、仕途堵塞,他们只好走向民间,将自己 的才华用于杂剧创作。这就使他们有更多的机会接近人民群众,在人民 群众的身上发现真、善、美,并将其表现于自己的作品之中。马致远正 是这样。时代的生活,斗争的实践,使他深刻地认识到,汉族统治集团 是无所指望的,只有普通的劳动人民才能充当反对异族侵凌,维护民族 尊严的真正英雄。从这种认识出发,马致远完全撇开了《琴操》把昭君 的出身写成“齐国王穰女”的做法,而把《汉宫秋》中维护民族尊严的 巾帼英雄王昭君的出身,从《汉书》、《后汉书》中的抽象的“良家子”, 进一步改为具体的“务农为业”、“家道贫穷”的“庄农人家”,并在《汉宫秋》中对这位农家女儿的爱国举动做了全面的肯定与赞颂,而对汉朝的满朝文武官员甚至汉元帝进行了批判与指责。 马致远对昭君出身的这种改造,为突出昭君悲剧性格的美,铺下了一块坚硬的基石。剧中,毛延寿所以要将昭君的美人图点上破绽,一是因为昭君“家道贫穷”,无钱贿赂,更重要的是昭君还“倚容貌出众, 全然不肯”。历代惋惜昭君不曾以重金买通画工的大有人在,如南朝梁 女诗人沈满愿的《昭君叹》:“早信丹青巧,重货洛阳师。千金买蝉鬓, 百万写娥眉。”李白《王昭君》:“生乏黄金枉图画,死留青冢使人嗟”┅┅。 马致远没有采取这种态度去写昭君,而是写一个普通的农家女儿王昭君 不仅被皇帝的使臣选做宫女,而且还要选为第一,对此唾手可得的荣华 富贵,昭君却无动于衷,鄙夷不屑。正是她这种傲岸的性格,惹恼了毛 延寿,招来了不幸的命运。从这里已经可以看出,马致远笔下的王昭君 已经不是一个任凭命运的风浪随意抛撒的“薄命女”了。
随着矛盾冲突的发展,马致远让昭君的这种性格的美在悲剧的结局 中得到了升华。
番使催索王昭君使悲剧的冲突达到高潮,矛盾的焦点集中到了昭君 身上。是否去和番?懦弱的汉元帝与屈辱的满朝文武大臣束手无策。而 王昭君却深明大义,在此民族危亡的紧迫时刻,“怕江山有失”,“为 国家大计”,毅然割舍了与汉元帝的爱情生活,挺身而出,“情愿和番”, 保全了国家的安宁。接着,她又为免遭异族统治者的玷污,维护民族尊 严,在番、汉交界处,纵身投入“黑龙江”,壮烈殉国。
这里,当时那种胡强汉弱、毛延寿卖国求荣、匈奴恃强要挟的形势, 与王昭君的性格之间构成了尖锐的冲突,并成为昭君悲剧发生的必然性 因素。王昭君的“和番”、“殉国”,虽然是迫于形势,还不能完全称 之为是“自愿”,但是,这个“形势”,却是国家的需要,民族的召唤。 响应这样的形势,正好表现了昭君无私、无畏、胸怀大局的美好品德, 表现了昭君对自己命运的掌握。马致远竭力在正义与非正义的矛盾冲突 中去刻画王昭君的悲剧形象,使昭君的悲剧形象充满了悲壮美与崇高 美。正是,“人格的伟大和刚强只有借矛盾对立的伟大和刚强才能衡量 出来”(黑格尔《美学》第一卷),“只有遭到反抗,才能显出力量”
(席勒《论悲剧题材产生快感的原因》)。 而以往的文艺作品描写昭君出塞,却总是写她含悲抱怨,哭哭啼啼,其归宿或是“杀身良不易,默默以苟生”(晋石崇《王昭君辞》),或 是愁苦憔悴地盼望“汉使却回凭寄语,黄金何日赎娥眉?”(白居易《王 昭君》),《琴操》虽然写的是昭君之死,但那也是在昭君到了单于那 里,过了一段“呜呼哀哉!忧心恻伤!”的生活以后,老单于死了,其 子要依照胡地风俗,“父死妻母”,昭君不堪忍受这种侮辱,“乃吞药 自杀”。这种种结局,表现了昭君对命运捉弄的无可奈何,虽然也是一 种悲,也能讨得人们一掬同情的泪水,但这种悲,却不是真正审美意义 上的悲。因为,作为审美范畴的悲剧应该是与崇高相联系的,而崇高只 有在矛盾的冲突与抗争中才能显现出来。马致远塑造的昭君形象是一个 爱国的昭君,抗争的昭君,这样的王昭君出现在当时的舞台上,怎能不 令人崇敬、动人心魂!
作为王昭君性格发展的组成部分,马致远还用大量篇幅写了王昭君与汉元帝的爱情生活。对这部分情节,历来评论,多持非议。认为这是 改变了《后汉书》所说“数岁”“积悲怨”的事实,调和了昭君与元帝 之间的矛盾,是全剧严重的局限。其实,这种描写仍然是出于剧作家对 昭君性格的统一构思。
试想,若据《后汉书》中“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的记载,去构造情节,那么即便是写昭君自请“求行”,也不难看出她有 着求出牢笼的个人动机。历代诗人词客所写昭君诗的主要内容,不就是 这种狭隘的个人“悲怨”吗?马致远所以要做新的艺术构思,写汉元帝 与王昭君有着深深的爱情,正是为了要保持《汉宫秋》中王昭君悲剧性 格的完整统一,使昭君的悲剧性格的美在结局上能够得到升华。而且马 致远笔下的昭君并没有因缠绵不尽令人陶醉的爱情而不能自拔,“为国 家大计”,昭君能断然抛弃这种爱情生活和荣华富贵去“情愿和番”, 以至为国捐躯。这比起因“积悲怨”而求行的昭君,不是显得更纯洁, 更崇高,因而更感人吗?
由上可见,马致远在整个王昭君悲剧形象的创造上,已经突破了历 代相沿的所谓“红颜女子多薄命”的命运主题。什么“专由妾薄命,误 使君恩轻”(薛道衡《昭君辞》),什么“薄命由骄虏,无情是画师”(沈佺期《王昭君》),什么“红颜胜人多薄命,莫怨东风当自嗟”(欧 阳修《明妃曲》)┅┅在马致远笔下,人们已经看不到这些跪拜在命运 面前的哭泣,而只有对命运的挑战与蔑视。促成昭君悲剧形成的直接原 因,已经不是令人神秘莫测的命运,也不是后来西方出现的“性格悲剧” 中所说的个人性格的缺陷与过失,而是由于王昭君性格中的美好因素与 社会丑恶势力之间的冲突造成的。
马致远能在创作实践上这样表现悲剧发生的必然性,这在世界悲剧 创作史上也有重要意义。因为,在创作实践上,西方直至 19 世纪才出现 了明确地把社会环境与个人性格之间的冲突作为悲剧成因的所谓的“社 会悲剧”。在理论上,只有到了马克思主义那里,才明确科学地指出, 悲剧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 的冲突”,强调了符合“历史的必然要求”的悲剧人物与扼杀“这个要 求”的社会环境之间的冲突是悲剧的成因。而处于 13 世纪的元代剧作家 马致远能在他的悲剧创作中已实践了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
那种认为,在我国悲剧创作史上,对王昭君悲剧的解释,“在古时 是完全归诸命运”(郭沫若《<王昭君>后记》)的观点,那种认为只 是到了郭老的悲剧《王昭君》,才“做了一件翻案文章”,剔除了王昭 君身上的命运因素”(吴功正《论郭沫若历史剧的悲剧艺术》,《新文 学论丛》1982 年第 2 期)的说法,是不确切的。马致远在王昭君悲剧形 象美的创造上所取得的成功与经验是应该肯定的。
悲剧气氛的创造
一般说来,悲剧气氛总是随着悲剧中所表现的对立双方的矛盾冲突 的不断激化,而逐渐从弱变强的。《汉宫秋》的情节发展到第二折末尾, 这种悲剧性的冲突可以说是基本完成了。这时,匈奴恃强要挟索要王昭 君成功,汉朝妥协,王昭君迫于形势请求和番,悲剧的局面已经形成。 悲剧气氛也已进入高潮,但是,这时还不是高潮的顶点。随着第三、四 折对汉元帝内心活动的展现,悲剧气氛才真正达到了浓重炽烈、震撼人 心的程度。从情节角度看,三、四两折并没有什么异峰突起的变化,昭 君的跳江作为双方冲突的最后结束,着墨并不多。这两折写的可以说是 汉元帝遭受到悲剧创伤的心灵的歌,它是如此富于变化地拨动着我们的 心弦:有时是衷肠的细诉,有时是悲剧的倾泻,有时是无言的啜泣,有 时是惨痛的呼号,有时如曲水流觞,百转千回,有时如江浪涛涛,一泻 千里┅┅。马致远用他的传神之笔,把汉元帝从内心深处流淌出来的情 感波澜逼真、感人地抒发尽净。这跌宕有致的悲剧情调,不断地激起观 众的情感高潮,使观众沉浸在悲剧的情感潮流中。
作者是凭借着怎样的艺术处理和艺术手段达到了如此强烈感人的悲 剧效果的呢?
主要是,作者能依据人物思想感情活动的节奏,大胆巧妙地安排剧 情,并在表现汉元帝内心活动时,娴熟地交替使用了直接抒情和间接抒 情的手段,特别是运用了幻觉、错觉、梦境等非写实的艺术手法渲染、 强化悲剧气氛,从而使《汉宫秋》产生出巨大的艺术魅力。
当然,这并非马致远的独创,元杂剧中不乏其他优秀范例。例如《窦 娥冤》,关汉卿在第二折的末尾,已将窦娥的经历、遭遇,交待清楚, 悲剧冲突也已基本完成,窦娥的悲剧已成不可逆转的必然之势。但是, 为了表现窦娥的愤怒与觉醒,作者又以第三折整整一折的篇幅,让窦娥 酣畅淋漓地倾诉满腔悲愤。从情节角度看,这一折只表现窦娥的“明正典刑”,与前折的情节容量相比,显得单薄而不均衡。作者所以要这样 安排情节,正是出于表达剧中人思想感情活动的需要。《梧桐雨》第四 折的处理也是出自同一艺术原则。但方法特点有所不同。《窦娥冤》是 把悲剧冲突的发展中人物思想感情活动翻滚最剧烈的关键点——窦娥走 上法场——放大展开。《梧桐雨》则是让唐明皇在悲剧冲突完全结束后, 做痛定思痛的悲剧性抒情。
《汉宫秋》综合运用了上述两剧各自不同的方法特点,收到了独特 的悲剧效果。作者先在第二折中充分细腻地去刻画汉元帝灞桥送别时的 心理活动,因为悲剧冲突只有发展到送别这个时刻,只有汉元帝眼见昭 君即将离去的时刻,悲痛的感情才真正达到了沸腾的顶点。其后,作者 又用全部第四折的篇幅,在悲剧冲突结束后,让汉元帝做痛定思痛的抒 怀。
从情节发展的角度看,第三折主要写离别,到第四折情节简直可以 说就停顿了。这两折情节发展的容量比起前两折少多了,似乎显得不均 衡。但汉元帝的悲痛感情此时却如决堤的潮水,奔腾而出,涨满这两折 的内在感情活动的容量,使悲剧情调在这里大大加重了分量,使这两折 成为浓化悲剧效果的重头戏。
《汉宫秋》的悲剧冲突、戏剧纠葛,并不是十分简单,交待几笔就可以的。这里,王昭君与毛延寿之间、汉元帝与王昭君之间、匈奴与汉 朝之间、汉元帝与满朝文武之间┅┅,各个矛盾侧面相互交织、感应, 构成了比较复杂的情节。然而作者敢于将上述种种冲突的叙述压在大致 两折的篇幅内,而用长达两折的篇幅让汉元帝做悲剧性的抒情,这如果 没有深厚的艺术功力,是难以驾驭成功的。因为这两折的内容概括地说, 基本就是离怨别恨。如果是平庸作手,用这样长的篇幅表现这单一的内 容,很容易搞得平板枯燥,重复乏味。但是马致远却能得心应手地运用 各种抒情手段,把剧中人物感情的复杂细微的变化,传达得惟妙惟肖。
第三折写灞桥送别。在这生离死别、情意缠绵的时刻,汉元帝的情感活动是复杂的,也是有变化的。如何精确逼真地把它们表达出来? 我们看到,作者先在汉元帝来到灞桥之后的一段时间内,集中地运用了[新水令]、[驻马听]、[步步骄]、[落梅风]、[殿前欢]、[雁儿落]、[得胜令]、[川拔棹]八支曲子,让汉元帝做直接抒情:吐诉离别的哀伤, 倾泻相思的苦痛,追忆昔日的欢娱,嗟怨自己的无能┅┅,凄情幽韵仿 佛扑面而来。
接着,昭君开始分手上路了,“怎禁他临去也回头望”,汉元帝的 心碎了,视线模糊了,留下的只是弥漫的风雪与悲壮的鼓声。这时,作 者用[梅花酒]、[收江南]两支曲子为我们展现出一幅汉元帝返咸阳的情 境:
[梅花酒]┅┅他他他,伤心辞汉主;我我我,携手上河梁。他部从入穷荒,我鸾舆返 咸阳。返咸阳,过宫墙,过宫墙,绕回廊;绕回廊,近椒房;近椒房,月昏黄;月昏黄, 夜生凉,夜生凉,泣寒螀;泣寒螀,绿纱窗;绿纱窗,不思量!
[收江南]呀!不思量除是铁心肠!铁心肠也愁泪滴千行。美人图今夜挂昭阳,我那里 供养,便是我高烧银烛照红妆。
王国维赞赏这两支曲子是“写景之工者”。然而,工则工矣,它却并非 实景,而是幻景。这是剧作家在采用幻觉的形式作间接抒情。
这里所以采用这种非写实的艺术手法,并不是剧作家挖空心思的别 出心裁,而是由剧中人物在规定情境中的感受逻辑来决定的。角色的这 种感受逻辑实际上也正是生活逻辑的反映。
汉元帝的幻觉是出现在与昭君分手诀别的刹那间。这时,生活发展 的逻辑应该是,离恨未已,相思又继,人去则楼空,睹物就必定会伤怀。 这种生活中事物发展的逻辑决定了剧中人物的感受逻辑。昭君起程之际 的“临去秋波”,激起了汉元帝极度的悲哀,他已经无暇顾及周围的一 切,一味地沉沦于“人去楼空”的想象之中。
这移步换形的景物描写,把汉元帝即将返回咸阳宫时的神态,把那 种来到昭阳殿孤对美人图相思之情状,有形有色地表现出来了。由这些 景物所创造的深邃朦胧、惨淡凄凉的咸阳宫殿的阴冷气氛,强化了汉元 帝与昭君诀别之际的离思别恨,使此时悲剧情绪的感染力达到了饱和状 态。
随着剧情的发展,昭君走远了。如何让已经达到高潮顶点的悲剧感 情再生波澜?
幻景消失,作者在一段写实性的抒情独白之后,又写汉元帝的错觉, “┅┅唱道伫立多时,徘徊半晌,猛听得塞雁南翔,呀呀的声嘹亮,却 原来满目牛羊,是兀那载离恨的毡车半坡里响”。错觉与幻觉不同。幻 觉是把未曾存在过的事物的形象做了知觉,错觉则是对眼前实有的某种 对象或现象所产生的一种错误的知觉,但二者都是人在特殊的甚至有时 是失常的心理状态下产生的。形神凄怆的汉元帝对昭君思念之极,在凝 神呆想之中,错把北去毡车的声音,当做是大雁南归,传来了昭君的音 信。透过这幅错觉景象,人们看到的是,由对昭君依依不舍的惜别之情 引起的汉元帝心灵的又一次震颤。
在第四折高潮的余波中,作者在汉元帝独处冷宫的境域中又穿插了一梦境:汉元帝与王昭君在梦中相会了。汉元帝的梦是他心理欲望的形 象化的反映,是镂骨铭心的相思之情发展到极致的一种结果,是汉元帝 情波中的又一个波峰。作者就是这样,在运用直抒胸臆的艺术手段的同 时,又创造性地运用幻景、错觉、梦境这些非写实的艺术手法做间接抒 情。时而让汉元帝悲恸欲绝的情思直接回响在观众的耳际,时而又将汉 元帝丢魂失魄的神志呈现于观众的眼前。在这种笔墨的变化中,作者把 汉元帝感情波澜的起落,表现得纤细精确、情态毕露,把悲剧气氛渲染 得一层浓于一层。
1983 年 1 月稿
1985 年 7 月定稿
(选自《中国古代戏曲论集》, 中国展望出版社 1986 年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