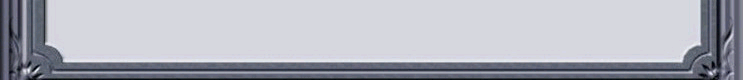第八章 余韵茫然
1.有“汉奸”嫌疑吗?
张爱玲孤芳自赏,本来朋友就不多,知心更少,与胡兰成恋爱后,她更沉湎于两个人的狭小天地,除了炎樱、苏青来往外,其他人多不相通问。
胡兰成为讨好她,在报刊上招摇,吹嘘,对张爱玲的身世与两人的关系大加渲染,对傅雷等人的善意批评横加指责,反唇相讥,信口开河,颇令时人侧目。连爱玲的舅舅也对她与汉奸混在一起大为不满。张爱玲的一位朋友女作家潘柳黛看不惯写了一篇文章,把胡兰成与张爱玲挖苦了一番。
潘柳黛原来与苏青、张爱玲关系都不错,接触一段时间后她对张爱玲与别人格格不入的孤僻有点看不惯。潘柳黛说,张爱玲在待人处世的方法上虽不合于中国人习惯,但是却颇合乎外国人脾气。比方与人约会,如果她和你约定的是下午三点钟到她家里来,不巧你若时间没有把握准确,两点三刻就到了的话,那么即使她来为你应门,还是照样会把脸一板,对你说:“张爱玲小姐现在不会客。”然后把门嘭地一声关上,就请你暂时尝尝闭门羹的滋味。万一你迟到了,三点一刻才去呢,那她更会振振有词地告诉你:“张爱玲小姐已经出去了。”她的时间观念比飞机开航还要准确的,不能早一点,也不能晚一点,早晚都不会被她通融。潘柳黛和苏青上次去拜访张爱玲,张爱玲的盛装打扮就弄得她们俩很尴尬。苏青倒没什么意见,但潘柳黛心里很不高兴,从此就不常去了。
潘柳黛看到了胡兰成写的《论张爱玲》,文中除把张爱玲的作品形容为“横看成岭侧成峰”之外,更对张爱玲的身世与“贵族血液”极尽能事地吹嘘一番。潘柳黛对胡兰成这神魂颠倒的文章感到肉麻,一时心血来潮,以戏谑的口吻,就发表了一篇《论胡兰成论张爱玲》,出于“幽他一默”的态度,把胡兰成与张爱玲大大调侃一顿。这篇文章,先“肉麻地”把稳坐“政论家第一把交椅”的胡兰成捧场几句,接着故意断章取义地问胡兰成对张爱玲的赞美“横看成岭侧成峰”,是什么时候横看的?什么时候侧看的?这还不算,最后把张爱玲的“贵族血液”挖苦得更厉害了。潘柳黛举了一个例子,胡兰成说张爱玲有“贵族血液”,因为她的父亲讨的老婆是李鸿章的外孙女,她是李鸿章的重外孙女——其实这点关系就好像太平洋里淹死一只鸡,上海人吃黄浦江的自来水,便自说自话是“喝鸡汤”的距离一样,八竿子打不着的一点亲戚关系。如果以之来证明身世,根本没有什么道理,但如果以之当生意眼,便不妨标榜一番。以上海人脑筋之灵,行见不久的将来,“贵族”
二字必可不胫而走,连餐馆里也不免会有“贵族豆腐”、“贵族排骨面”之类出现。最后并以“正是:请看论人者,人亦论其人”作结。
这篇玩笑文章发表不久,作家陈蝶衣主持的大中华咖啡馆改组卖上海点心,果然便以“潘柳黛女士”笔下的“贵族排骨面”上市。胡兰成与张爱玲便对潘柳黛敬而远之,断绝了往来。
1945年8月10日,日本投降前几天,张爱玲与日本女明星李香兰、日本军人松本、川喜多以及汪伪政府的陈彬、金雄白的“纳凉晚会”,在《杂志》15卷5期登了出来。在此前后,日本控制的报纸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
的作家名单中,赫然列上“张爱玲”的名字。张爱玲心头一惊,赶忙写信辞去,然而白纸黑字再也没办法灭掉。
几天之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汪精卫汉奸政府随之覆灭。国民政府回到南京后,对这些汪伪汉奸严行通缉正法,陈公博、梁鸿志等先后全被处决。他们手下的一些大小娄罗,有的被枪毙,有的被判刑,有的像胡兰成隐姓埋名逃走。“纳凉晚会”上的金雄白、陈彬这些“文化汉奸”,忙忙如漏网之鱼,急急如丧家之犬,早已逃之夭夭。
张爱玲对政治从来都是漠不关心的,以前她发表文章的阵地《杂志》、《古今》、《苦竹》这些文化汉奸办的刊物纷纷停刊了,苏青主编的《天地》也被停掉了。张爱玲自信自己与政治没有关系,便泰然地保持沉默。
但是背后的各种议论纷纷而来。张爱玲在沦陷区汉奸办的刊物上发表文章,文化汉奸捧她,大出风头。她与汉奸胡兰成的恋爱,成为人们议论的话柄。还有人拿出报纸,“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上列有她的名字。因此,她被人暗中列入有“文化汉奸”嫌疑的名单上。
她的朋友苏青更受到指责,有人说“敌人投降了,苏青大哭三天三夜”,还有人说苏青的文章是“性的诱惑”等等谩骂丑诋。苏青向来是泼辣的,她说:“是的,我在上海沦陷期间卖过文,但那是我‘适逢其时’,亦‘不得已’耳,不是故意选定的这个黄道吉期才动笔的。我没有高喊打倒什么帝国主义,那是我怕进宪兵队受苦刑,而且即使无甚危险,我也向来不大高兴喊口号的。我以为我的问题不在卖文不卖文,而在于所卖的文是否危害民国的。
否则正如米商也卖过米,黄包车夫也拉过任何客人一般,假如国家不否认我们在沦陷区的人民也尚有苟延残喘的权利的话,我就是如此苟延残喘下来了,心中并无愧作。“她又说:”在这里我还要郑重声明:当时我是绝对没有想到内地去过,因为我在内地也是一个可靠的亲友都没有的。假如我赶时髦地进去了,结果仍旧卖文,而且我所能写的文章还是关于社会人生家庭妇女这么一套的,抗战意识也参加不进去,正如我在上海投稿也始终未歌颂过什么大东亚一般。“苏青这种亮烈难犯的脾气使她能继续写稿谋生。大报答应请她编副刊,条件是更换个笔名,她还不干。小报倒乐意她用真名,也肯出高稿酬,虽然把她的文章放在”木匠强奸幼女“之类的新闻下面,未免心痛,但为了在米珠薪桂的社会中谋生,她也顾不得这些了。
张爱玲没有苏青的豁达与泼辣,但她比苏青世故一些,她谢拒大报小报的“盛意”,沉默了一年多。从1945年8月至1946年全年,她没有发表任何作品,但仍不能免除人们各种议论。到1947年,她出版《传奇(增订本)》时,仿照苏青的先例,在书前写了一个《有几句话要同读者说》:我自己从来没想到需要辩白,但最近一年来常常被人议论到,似乎被列为文化汉奸之一,自己也弄得莫名其妙。我所写的文章从来没有涉及政治,也没有拿过任何津贴。
想想看我唯一的嫌疑要末就是所谓“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第三届曾叫我参加,报上登出的名单内有我;虽然我写了辞函去,(那封信我还记得,因为很短,仅只是:“承聘为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代表,谨辞。张爱玲谨上。”)报上仍旧没有把名字去掉。
至于还有许多无稽的谩骂,甚而涉及我的私生活,可以辩驳之点本来非常多。而且即使有这种事实,也还牵涉不到我是否有汉奸嫌疑的问题;何况私人的事本来用不着向大众剖白,除了对自己的家长之外仿佛我没有解释的义务。所以一直缄默着。
她是一个职业文人,没有工作,只能靠稿费来养活自己,没有地方发表文章,她的生计便要发生问题,她只好重新振作起来,整理整理思绪,再写些东西。
2.华丽不再有缘
这时的张爱玲,正一步步地远离源远流长的贵族身系,从她华丽世族的感情世界走入现实,看看这吵杂、脏乱、纷坛而又实实在在的生活。
张爱玲拎着网袋,在菜场上转来转去买些豆腐、甜面酱、黄芽菜,张看着这陌生的世界:穿着艳丽而又肮脏衣服的小孩子,青翠醒目补丁连缀的长袍的男人,咧着大嘴扯着高嗓吆喝的小贩,沿街磕头化缘的黑布袍道士,肉店铺里生着麻黄眼睛用上海话骂小姑劣迹的女人,穿着破羊皮袄戴戒指染指甲口镶金牙的老娼妓,夜幕将沉店家无线电里咿咿呀呀的申曲……她处在这样的环境下,想着古戏唱本里“谯楼初鼓定天下”,看着由汉唐一路传下来的中国,万家灯火,在更鼓声中渐渐静了下来,很在感触她把她的感情写成诗:
我的路
走在我自己的国土。
乱纷纷都是自己人,补了又补,连了又连的,补丁的彩云的人民。
我的人民,我的青春,我真高兴晒着太阳去买回来沉重累赘的一日三餐。
谯楼初鼓定天下,安民心,嘈嘈的烦冤的人声下沉。
沉到底。……
中国,到底。
这就是张爱玲眼中的中国。纷纷扰扰的人们为着生命的一日三餐奔波,在这毫无色彩的尘世中寻求生趣,中国人的本色与理想全是这样。
她就生活在这样下沉的中国的日夜里。
1946年初,张爱玲以前的一个作家朋友龚之方,筹办了一个山河图书公司,出版一个通俗性文艺刊物《大家》。龚之方虽与张爱玲接触不多,但一直很喜欢她的文章,对她的孤芳自赏落落寡合也很同情。办刊之初,没有一批写稿的人,便想到要拉张爱玲的作品,张爱玲此时正愁着自己的文章无处发表,旧时的刊物纷纷关闭,新的刊物人又不熟悉,况且有时还要忌讳她的名声,像苏青遭遇那想要求换笔名也未可知,她也是不愿这样,这时她也就乐于为《大家》写文章。《华丽缘》就是发表在《大家》上的。《华丽缘》是一篇散文,她在题目下说:“这个题目译成白话是‘一个行头考究的爱情故事’。”写她一次在浙江乡下看的一出绍兴戏的戏里戏外。这个江南的农村是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这里的人不像是花得起娱乐费的,然而一年到头难得的一次娱乐,也要做出满不在乎的样子,演起绍兴戏。而且还要表现出眼界很高的样子,年轻人学着城里流行的时髦的打扮,评价着:“今年这班子行头是好的!——班子呢是普通的班子。”
戏子也是乡下式的戏子,但戏台上都是色彩华丽的装扮,乡气而世俗的华丽。戏是中国传统式的故事,秀才小生一边读书赶考,一边表兄妹偷情,被老夫人发现,把小生送回读书,路上庙里遇惊艳,又是一番缠绵,卖身投靠女家……下面大概是以后金榜题名,奉旨完婚,自会一路取过来的。
她听不懂内容,只是看看红红黄黄的颜色,听着慢悠悠的腔调,那种腔调对心慌意乱的现代人是一粒定心丸。然而,张爱玲却注意“那绣着‘乐治剧团’横额的三幅大红幔子后,露出祠堂里原有的陈设,里面黑洞洞地,却供着孙中山遗像,两边挂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对联。那两句话在这意想不到的地方看到,分外眼明。我从来没知道是这样伟大的话。
隔着台前的黄龙似地扭着的两个人,我望着那幅对联,虽然我是连感慨的资格都没有的,还是一阵心酸,眼泪都要掉下来了“。
他们是漠然的、没有什么理想的。他们的生活是很朴素的,男人几乎一律穿着旧蓝布罩袍,老太太灰格子布料里隐隐夹着一点点红线,便会觉刺眼,骂道:“把我当小孩子呀?”但是他们也会背地里有偷情,也有离异的事件。
他们生活没有色彩,但内心却向往,所以,“如此鲜明简单的‘淫戏’,而他们坐在那里像个教会学校的恳亲会”。在看戏里寄托着“华丽”人生的奢望。
戏里的行头是华丽的,但戏外的行头却是灰暗无色彩的,灰暗的人、灰暗的生活。“每个人都是几何学上的一个‘点’——只有地位,没有长度、宽度与厚度。整个的集会全是一点一点,虚线构成的图画;而我,虽然也和别人一样地在厚棉袍外面罩着蓝布长衫,却是没有地位,只有长度、阔度与厚度的一大块,所以我非常窘,一路跌跌冲冲,踉踉跄跄地走了出去”。
张爱玲依然是张爱玲,她在这个社会上,要保持她的个性与自我,有自己的“长度宽度与厚度”的棱角,但却没有地位,她不愿这样,不愿这种无色彩无光芒的生活,入乡却随不了俗,虽出了戏院,但现实仍是如此,她还得耐下性子看生活中的戏。
张爱玲把她的视线逐渐转向下层,不仅是写的内容,戏路也在变。她为了迎合《大家》这个通俗性刊物,因为这家杂志的两个主要人物龚之方与唐大郎(云旌)都是鸳鸯蝴蝶派式的文人,这个刊物也主要是给一般读者看的言情性文学刊物。
虽然文章还依旧文采斐然,但这时的张爱玲,心里已经落寞颓唐多了,没有以前《传奇》、《流言》时代的欢乐了。她已感到自己与这个时代之间的距离在越来越大,感受着时代的压迫,一种恐怖不安感袭上心头。
1947年11月《传奇》(增订本)由龚之方、唐大郎那个空挂招牌的上海山河图书公司出版,增收《留情》、《鸿鸾禧》、《红玫瑰与白玫瑰》、《等》、《桂花蒸:阿小悲秋》等小说。这是山河图书公司出版的唯一的一本小说。她又换了一个封面,已经没有《传奇》初版再版时的亮丽的颜色,换成另一种表现她这时候心境的图画:封面是请炎樱设计的。借用了晚清的一张时装仕女图,画着个女人幽幽地在那里弄骨牌,旁边坐着奶妈,抱着孩子,仿佛是晚饭后家常的一幕。可是栏杆外,很突兀地,有个比例不对的人形,像鬼魂出现似的,那是现代人,非常好奇地孜孜往里窥视。如果这画面有使人感到不安的地方,那也正是我希望造成的气氛。突兀、不安、尴尬的画面是她的内心的真实感觉。面对着这个陌生的社会与时代,她有点不安,担心自己适应不了现代的一切。她更恐惧的是,就连现在这样的环境恐怕也不会长久,“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
3.中国的好莱坞传人
面对这样的生活,她徒唤奈何。
既然大雅的纯文艺来不成,她就大俗,俗也俗得彻底,俗要俗得雅致,做到雅俗共赏,通俗而不庸俗,这是张爱玲的追求。张爱玲操起她另一个拿手好戏,为上海文华影片公司编写电影剧本。
上海文华影片公司创办于1946年9月,是由民族资本家吴性栽独资办的。吴性栽也是一个老电影家,从事电影事业数十年,但影片上从不署名,他不爱名,只专注于他的事业。著名的电影导演桑弧(李培林)、黄佐临都是文华公司的台柱。龚之方也加入该公司。龚之方与桑弧知道张爱玲以前曾自编话剧剧本《倾城之恋》很轰动,他们经柯灵介绍到她的住处迈克公寓拜访,恳请张爱玲为他们编电影剧本。张爱玲起初有些犹豫,经他两人的怂恿,立即决定说:“好,我写。”然后几天时间,她翻看了杂志上的一些剧本,琢磨一下,就动笔写了起来,很快地完成了她第一个电影剧本《不了情》交到了文华公司。她写惯了贵族式情调的小说,那是给有文化知识的人看的小说,她的标着“传奇”名字的小说并没有多少传奇故事,而是刻意对环境与情调,人物的心理、性格的细腻地刻画,尽管这些大都是写爱情的,但那是“高等的调情”,没有鸳鸯蝴蝶派式的曲折离奇扣人心弦的情节。她清楚地知道沦陷区里有闲阶级文人办的纯文艺刊物时代已告结束,现在面对的是一般的百姓,生活在生命线边缘为衣食忙碌的下里巴人,这正是她作品的买主,她的作品应该适合他们的需要。
然而张爱玲却没有这种生活阅历,她的生活环境限制了她创作的领域。
于是,她走电影剧本的创作路子。这样还是她熟悉的环境与人物,通过电影的方式“卖”给普通大众这个“最可爱的雇主”。
但电影毕竟不同于小说。因为小说可以有少数人看,电影这东西可不是能给二三知己相互传观的。因此,她得研究一般观众的心理。她说。她对观众的心理没有一点把握,因为中国的观众最难应付的一点并不是低级趣味或理解力差,而是他们太习惯于传奇故事,如果没有曲折离奇可歌可泣的故事情节,不能打动读者的同情心或满足他们对传奇戏的欲愿,那么这“可爱的雇主”也未必肯买账的。她不得不稍稍迁就迁就读者(观众)的口味,根据好莱坞电影的一般手法,有限度地布置一个起伏波动的情节,有悬念、有巧合、有噱头,吸引读者的注意力和兴趣。张爱玲为上海文华电影公司写了两个剧本,《不了情》和《太太万岁》,一度还把自己的小说《金锁记》改编成为电影剧本。《不了情》是一个爱情悲剧。写的是一位躲避家庭阴影到上海谋生的少女虞家茵与她所做家教的男主人夏宗豫之间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巧合促成了两人的相遇相识相爱,但这爱却是一个没有结局的“不了情”。1947年4月中旬,文华公司这部处女作被搬上银幕,由桑弧导演,陈燕燕、刘琼等主演。剧本与演员都是高水平的,因此,一公演便产生轰动效应,获得一致好评,被称为“胜利以后国产电影最适合观众理想之巨片。”(1947年4月6日上海《申报》评语)然而电影替代不了小说,小说中的语言的韵味,意象的安排,心理的暗示在电影中不能充分发挥,张爱玲又把它改写成小说《多少恨》发表在《大家》上,作为她的小说向通俗文学过渡的标志。
她在这篇小说开头的短序中说:“我对于通俗小说一直有一种难言的爱好;那些不用多加解释的人物,他们的悲欢离合。如果说是太浅薄,不够深入,那么,浮雕也一样是艺术呀。但我觉得实在很难写,这一篇恐怕是我能力所及的最接近通俗小说的了,因此我是这样的恋恋于这故事——”
这篇小说的女主人公虞家茵,“她独自一人的时候,小而秀的眼睛里便露出一种执著的悲苦的神气,为什么眼睛里有这样多悲哀呢?她能够经过多少事呢?可是悲哀会来的,会来的”。
她在电影院门口退掉多余的一张票,被一个中年男人要走了,这个男人“年轻的时候不知是不是有点横眉竖目像舞台的文天祥,经过社会的折磨,蒙上了一重风尘之色,反倒看上去顺眼得多”。虞家茵后来做了一家的家庭教师,为那家的小孩买生日礼物时,恰巧又碰上了在电影院遇到过的这个男人,他也在买礼物,更巧的是他也到了她要去的那家,这个中年男子便是她做家教的男主人夏宗豫,一个公司的经理。
夏宗豫的家布置得很精致,但是冷冷清清,好像没有人住。他的太太是一个没有知识的乡下人,年轻时由父母包办成婚,婚后生一女儿,夫妻不和,太太一人长期住在乡下。见到了虞家茵,他从荒漠的感情里萌生了爱意,他的女儿小蛮,把两个人拉到了一起,他到虞家茵的住处去,看她的房间虽然狭小,又摆着书架橱子,火炉锅里还烧着饭,觉得“她这地方才像是有人诚心诚意地过日子的,不像他的家,等于小孩子玩的红绿积木搭成的房子,一点人气也没有”。他们之间产生了一丝温暖的感情,但当他与虞家茵坐在一起玩牌,看看前途如何,翻开牌,是“下下”,书上面写着“莫欢喜,总成空,喜乐喜乐,暗中摸索,水月镜花,空中楼阁”,两人都受了震动,沉默了。一个不祥的征兆。
这个不祥的征兆应验了。虞家茵的父亲来到了上海。虞老先生自小就是一个挥霍钱财的浪荡阔少,一辈子吃喝嫖赌,没有正经职业的无赖,他娶了家茵母亲,生下家茵后,与妻子离婚,又娶了一个妓女,现在又抛下了这个女人一人来上海,骗走家茵手中一点点积攒下来的钱,转眼之间他挥霍一空之后又来了。他还缠着女儿不放,看到女儿在夏家做家教,他便摸了去,仿佛女儿已是夏家的人了似的,向佣人招摇撞骗。看见客厅没有人,“他马上手忙脚乱起来,开了香烟筒子就捞了把香烟塞到衣袋里”。他让夏宗豫在公司里为自己谋个职。可是不久把自己薪水挥霍完后,又将公款也装进自己的衣袋。
虞老先生自从到了公司,便以未来的丈人“老长辈”自居,不断厚着老脸再来夏家要钱。这次,夏太太得到佣人告诉的消息后从乡下回来了。他不为自己女儿的处境担忧,反而极力要女儿做夏家的姨太太。他一方面对夏宗豫道:“我的女儿她跟你的感情这么好,她还争什么名分呢?
你夏先生这样的身份,来个三妻四妾又算什么呢?“严宗豫转过身来瞪眼看着他,一时都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虞老先生又道:”你不必跟你太太闹,就叫我的女儿过门去好了!大家和和气气,你的心也安了。……“
夏宗豫冷冷地喝住了他的胡言乱语后,第二天,他又到夏太太处,对夏太太说:“夏太太,我今天来就是这个意思。我知道您大贤大德,不是那种不能容人的。您是明白人,气量大,你们夏先生要是娶个妾,您要是身子有点儿不舒服,不正好有个人伺候您——哪儿能说什么离婚的话?真是你让我的小女进来,她还能争什么名分么?”
这就是虞老先生的嘴脸,为了自己要骗钱,竟能狠心到出卖女儿,他的作人哲学是“顶要紧的是抓住几个钱”。他幽灵般地出现在虞家茵周围,一个可怖的阴影,遮挡了女儿对爱的美好憧憬,虞家茵忍受不了了,她不忍心与宗豫的感情沾上这重永远抹不去的阴影,不忍心使宗豫的女儿恨爸爸,像她恨自己的爸爸一样,她选择了“走”这条路,违背自己的感情,离开了上海。
“水月镜花,空中楼阁”……又是一个“美丽而苍凉的手势”,没有结局的结局。
虽然是张爱玲最通俗的小说,也还要表现她的一贯的风格。
《不了情》轰动以后,桑弧请张爱玲接着再写一部,他构思了一个喜剧腹稿讲给张爱玲参考,张爱玲因为确有了第一次的经验,手也熟了,又一气呵成写了《太太万岁》交给桑弧。
《太太万岁》是一部爱情喜剧。女主角陈思珍(蒋天流饰)是一个上海普通人家的太太。她一结婚便由少女一跃而为“中年人”,跳掉了“少妇”
这一人生幸福阶段。她是一个尽职的太太,在一个半大不小的家庭中周旋。
家里上有老,下有小,还有一个终日感到“怀才不遇”郁郁寡欢的丈夫唐志远。陈思珍在家里忙忙碌碌,既要哄住婆婆不为儿子操心,又借娘家的钱支持丈夫的事业,还要拿出自己的私房钱来安抚家中的佣人,她在家中是能干的女人,安于朴素的生活,一家老小都夸她能干;出了门又会穿上“雨衣肩胛”的春大衣,手挽玻璃皮包,打扮得粉白脂红。她面面周到,替丈夫吹嘘,替婆家争气,替娘家撑场面,替考试不及格的儿子遮羞。可是在她资助下丈夫时来运转,为自己的才华鼓舞,桃花运也随之而来,移情别恋,爱上了一个交际花。陈思珍在婆婆、娘家面前撒得圆圆的谎,一个个露出破绽,谁都不领情,谁都说她不好,丈夫知道自己的发财机会原来是太太一手造成的,“大丈夫”的自尊心受到伤害,也向她大发脾气。她被弄得里外不是人。但这个家被丈夫弄垮之际,又是她这个能干的太太,挺身出来收拾残局,吓退了交际花施咪咪(上官云珠饰)的敲诈勒索,保全了这个家,使丈夫回心转意。她也就又恢复了自己原来的生活与地位。
这个喜剧充满了误会与巧合,添了一些噱头和笑话,这是张爱玲为了照顾电影的特点而做的妥协。但是,这只是在这本来平淡无奇的大情节中添入的小情节,添出戏来,虽然弄得几个演员忙得团团转,但这个故事还基本上保持她平时的作风。她的目的是“冀图用技巧来代替传奇,逐渐冲淡观众对于传奇戏的无厌的欲望”。环境是上海的小弄堂七十二家房客式的环境,气息是当时最熟悉的生活气息,人也是普普通通的小市民太太。她的生活情形里有一种不幸的趋势,使人变得狭窄,小气,庸俗,以致于社会上的人一提起“太太”两个字往往都带有点嘲笑的意味。中国人对太太们似乎没有过多的期望,除贞操外也很少要求。而有许多不“称职”的太太也就安然度过了一生。而那些尽职的太太,如同这出戏里的陈思珍,在一个半大不小的家庭里周旋着,处处委屈自己,顾全大局,虽然也煞费苦心,但和旧时代的节妇列女贤妻良母那种残酷的牺牲精神比较起来,就成了小巫见大巫了。陈思珍毕竟不是《列女传》上的人物,她比她们少些圣贤气、英雄气,因此看上去要平易近人得多。然而她却实在是更不近人情的。没有环境的压力,凭什么她要这样克己呢?这种心理很费解。如果说她有任何伟大之处,这伟大倒在于她是自动的,我们不能把她算作一个旧制度下的牺牲者。
然而,这就是陈思珍这种人更可悲之处。一个少女一结婚立刻变成了中年人,应该有幸福的“少妇”阶段的生活她没有享受到,就进入了中年,具有中年人的气质了。她的悲哀也不是完全没有安慰的,她有一个快乐的“结局”,但她最后重新获得的“快乐”结局并不是什么快乐,只不过重回到以前那种没有自我人格的生活中罢了。所谓的“哀乐中年”,大概那意思就是她们的欢乐里永远夹杂着一丝辛酸。这就是所谓的“浮世的悲欢”。这就是她们所能得到的安慰。
女人的可悲不是时代,不是制度,造成她们的悲剧是她们自己,是她们自己心甘情愿。陈思珍用她那圆滑的处世技巧费神的心机使周围的人们的生活圆滑化,使自己的生命悄无声息地逝去。
女性自我的主体意识哪去了?
如果说《金锁记》中的曹七巧、《花调》里的郑太太、《心经》里的许太太、《桂花蒸:阿小悲秋》中的阿小的生活是“浮世的悲哀”,那么,陈思珍的生活就是“浮世的悲欢”。“浮世的悲欢”更可悲,因而有一种“苍茫变幻”的感觉。
这没有传奇色彩的琐碎平凡的生活照样能感动人。本来,如果从追求传奇效果上讲,张爱玲可以给女主人公一个“死亡”的结局:“死亡使一切都平等”。“但是为什么要等到死呢?生命本身不也使一切人都平等么?”看来,还是坚持自己的原则的。
这部影片同《不了情》一样,由桑弧导演,选的演员像蒋天流、上官云珠、石挥、程之等都是一流的演员,所以该片比起《不了情》更为成功,轰动一时。
4.山雨欲来
《太太万岁》从1947年12月14日起在上海的皇后、金城、金部、国际四大影院同时放映,引起很大的轰动。整整两周,各影院场场爆满,上海各报竞相报道演出盛况,称之为“巨片降临”、“万众瞻目”、“精彩绝伦,回味无穷”,甚至被推为“本年度银坛压卷之作”。观众们对这部电影予以一浪高一浪的喝彩。张爱玲《<太太万岁>题记》12月3日在洪深主编的《大公报。戏剧与电影》周刊上发表时,洪深在“编后记”中就说:“好久没有读到像《<太太万岁>题记》那样的小品了。我等不及地想看这个‘注定要被遗忘的泪与笑’的Idyll如何搬上银幕。张女士也是《不了情》影剧的编者;她还写有厚厚的一册小说集,即名《传奇》!但是我在忧虑,她将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优秀的HighComedy(高级喜剧)作家中的一人。”
张爱玲果然不负High Comedy的称誉,《太太万岁》成为当时最卖座的电影。这种都市浪漫喜剧是一个尝试,有点好莱坞神经喜剧(Screwball Comedy)的影响,在中国确是首次出现。
然而就在观众如痴如狂地喝彩的时候,评论界一场极“左”的批判浪潮无情地向张爱玲袭来。甚至影片还没放映,有的左派批评家就开始着手对影片的抨击了。《太太万岁》上演前两天,一位署名胡珂的《抒愤》已在《时代日报。新生》上骂起张爱玲与洪深:……寂寞的文坛上,我们突然听到歇斯底里的绝叫,原来有人在敌伪时期的行尸走肉上闻到High Comedy的芳香!跟这样的神奇的嗅觉比起来,那爱吃臭野鸡的西洋食客,那爱闻臭小脚的东亚病夫,又算得什么呢?
把张爱玲比作“敌伪时期的行尸走肉”,并指责洪深:“难道我们有光荣历史的艺园竟荒芜到如此地步,只有这样的HighComedy才是值得剧坛前辈疯狂喝彩的奇花吗?”只是恶毒的人身攻击。这篇文章把本来属于文艺争论的内容变成了政治攻击,为张爱玲蒙上一层可怖的阴影。
另一位王戎是在看过电影后骂的,他说:“在中国这块被凌辱了千百年的土地上,到处都是脓疱,到处都是疖疤,一个艺术工作者,是不是就玩弄、欣赏、描写、反映这些脓疱和疖疤呢?这是不应该的。而张爱玲却是如此的写出了《太太万岁》。”“鼓励观众继续沉溺在小市民的愚昧麻木无知的可怜生活里。”鲁迅的《阿Q正传》、《孔乙己》不也是这样以喜剧的方式描写社会的“脓疱和疖疤”的吗?可是这篇文章的作者却没想到,而指责张爱玲不该这样写。
还有一位名叫沙易的人,“钦佩”张爱玲的天才,“像《太太万岁》这样没有‘故事性’的故事,而居然能编成一个电影剧本,诚令人感到惊奇”,但笔锋一转,又说“电影最要紧的是主题,如果作者仅凭着聪明的技巧,赚取小市民的眼泪,它的最终的目的——艺术价值,是一定非常低下的”。
一时间,上海的《大公报》、《新民晚报》、《中央日报》连篇累牍地攻击起这部电影剧本。从比较客观的立场评论的不是没有,但在这强大的攻势面前,却被掩没了。
这是一场很有政治背景的批评,张爱玲在沦陷期间的身份使她受到执政当局的注意,她的作品被当做毒素对待。柯灵为她的《传奇》(增订本)问世在自己主编的《文汇报》副刊上登一条短讯都受到当局的警告,可见政治上对张爱玲施加的压力或警告。洪深为发表《<太太万岁>题记》可能同样受到政治的压力,要不然,为什么这样一个杰出的戏剧大师,也很快在报上登文检讨呢?1948年1月7日,在《大公报。戏剧与电影》上登了两篇文章。
一篇是署名“辛薤”的《我们不乞求,也不施舍廉价的怜悯——一个太太看<太太万岁>》,提出更为明显的政治性攻击:“时代是在‘方生未死之间’,反动的火焰正图烧灭新生的种子,袖手旁观的人儿是麻木无情呢还是别有用心?”另一篇是洪深自己写的《恕我不愿领受这番盛情——一个丈夫对于<太太万岁>的回答》,对发表张爱玲的《题记》公开认错,好像自己是受了张爱玲“蒙骗”似的,对《太太万岁》全面批判,与他一个月前的观点截然相反。可见这场争论不是一般的文艺争论。
张爱玲被这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打得晕头转向。文华影片公司原计划筹拍的《金锁记》剧本已编成,导演与主演已内定,也被迫停止了。
《大家》杂志只出了三期就停刊了,写电影剧本也不可能了。时代的压力太太,张爱玲放下手中的笔,再次沉默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