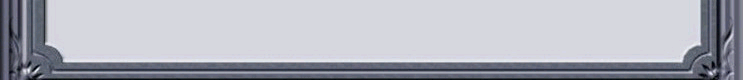第五章 世象的临摹(绘画篇)
——张爱玲《〈传奇〉再版的话》
对张爱玲略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她画得一手好画,对张爱玲稍有兴趣的人无不对她的画印象深刻。但是张爱玲画画究竟学自何时,抑或不学自会;学自何师,抑或无师自通,迄今尚无人明确告诉我们答案,好在张爱玲的作品里以及别人的回忆文章中有点滴或片段的透露。
张爱玲在《私语》里写道,8岁时,随父亲从天津回到上海。不久母亲从国外归来,把父亲送到医院去戒毒,他们“搬到一所花园洋房里,有狗,有花,有童话书,家里陡然添了许多蕴藉华美的亲戚朋友”。张爱玲快乐极了,“在狼皮褥子上滚来滚去”,她还“写信给天津的一个玩伴,描写我们的新屋,写了三张信纸,还画了图样”。
※※※
她在《天才梦》里也写道:
八岁那年,我尝试过一篇类似乌托邦的小说,题名《快乐村》。快乐村人是一好战的高原民族,因征服苗人有功,蒙中国皇帝特许,免征赋税,并予自治权。所以快乐村是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大家庭,自耕自织,保存着部落时代的活泼文化。
我特地将半打练习簿缝在一起,预期一本洋洋大作,然而不久我就对这伟大的题材失去了兴趣。现在我仍旧保存着我所绘的插画多帧,介绍这种理想社会的服务、建筑、室内装修,包括图书馆、“演武厅”、巧克力店、屋顶花园。
都是8岁。
成年后的张爱玲公布了她9岁时为向《新闻报》附刊投稿写给编辑的一封信,其中写道:“……我常常喜欢画画子,可是不像你们报上那天登的孙中山的儿子那一流的画子,是娃娃古装的人,喜欢填颜色……”在《对照记》里,张爱玲对她小时候的一张相片做这样的诠释:
“面团团的,我自己都不认识了。但是不是我又是谁呢?……我记得的那件衣服是淡蓝色薄绸,印着一蓬蓬白雾。T字形白绸领,穿着有点傻头傻脑的,我并不怎么喜欢,只感到亲切。随又记起那天我非常高兴,看见我母亲替这张照片着色。一张小书桌迎亮搁在装着玻璃窗的狭窄的小洋台上,北国的阴天下午,仍旧相当幽暗。我站在旁边看着,杂乱的桌面上有黑铁水彩画颜料盒,细瘦的黑铁管毛笔,一杯水。她把我的嘴唇画成薄薄的红唇,衣服也改填最鲜艳的蓝绿色。”
那时她的家在天津时期,她是两岁的时候从上海搬到北方去的,而母亲是在她三四岁的时候出国的。据此可以说,张爱玲习画的兴趣来自母亲。换句话说,母亲是她绘画的第一位老师,而时期就在她3岁左右。她8岁回到上海,不久母亲自国外归来,那时期母亲还对女儿画画不时指导:“我母亲还告诉我画图的背景最得避忌红色,背景看上去应当有相当的距离,红的背景总觉得近在眼前……”
张爱玲的母亲有心将女儿往洋式淑女方面培养,而如张爱玲在《银宫就学记》里所说:“西洋美术在中国始终是有钱人消闲的玩艺儿。”鼓励女儿习画当然就再自然不过了。
后来以写作赢得大名声的张爱玲,谁能想到,最初获取的稿费,却不是来自她的“字”,而是她的画:“生平第一次赚钱,是在中学时代,画了一张漫画投到英文《大美晚报》上,报馆里给了我五块钱,我立刻去买了一支小号的丹琪唇膏。我母亲怪我不把那张钞票留着做个纪念……”
中学时期的张爱玲,对绘画的兴趣有增无减。她的中学老师回忆道:“她在教室里总是坐在末一排,不听讲,手里的铅笔则不停地在纸上划着,仿佛是很用心地记笔记的样子,可是实在她在画教师的速写样。”弟弟则回忆姐姐道:“还有一次寒假,她仿照当时报纸副刊的形式,自己裁纸和写作,编写了一张以我家的一些杂事作内容的副刊,还配上了一些插图。”而且当时张爱玲的画技已经相当娴熟,她发表在圣玛丽亚校刊《凤藻》上的插图可资佐证。
四十年代初,在香港大学求学的张爱玲,在战争的刺激下,画了不少画,大多是市井图:有斗鸡眼突出得像两只水龙头、脾气暴躁的二房东太太,有头颈如同电吹风的少奶奶,还有蹲着的露出红丝袜的尽头与吊袜带的病妓……
小说是变形的人生。张爱玲自小又生在一个不健康的家庭里,世象人情在她的心目中多是阴暗的、变态的。不知是不是这个原因,“生来是一个写小说的人”的张爱玲走了一条漫画的道路。
张爱玲画漫画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社会环境的诱导。当时的上海,商品社会的一些特征已经较为明显,文化舶来品并不罕见,除了漫画书、卡通影片外,常以漫画为表现形式的广告影画更是随见于报刊媒体、商店橱窗。而张爱玲对它们,除了具有一般女孩通常的兴趣外,还多一道艺术的眼光,这使得她的观感与心得也较之他人多一些。在她的小说与散文里,就不时提及漫画。
※※※
《茉莉香片》中,聂传庆在公共汽车上邂逅了班上的女同学言丹朱。张爱玲这样描绘言丹朱:
“大约是刚洗了头发,还没干,正中挑了一条路子,电烫的发梢不很鬈了,直直地披了下来,像美国漫画里的红印度小孩。”
《花凋》中对郑川嫦父亲的描写:
“郑先生长得像广告画上喝乐口福抽香烟的标准上海青年绅士,圆脸,眉目开展,嘴角向上兜兜着,穿上短裤子就变了吃婴儿药片的小男孩,加上两撇八字须就代表了即时进补的老太爷,胡子一白就可以权充圣诞老人。”
《桂花蒸·阿小悲秋》对广告画的描写:“墙上用窄银框子镶着洋酒的广告,暗影里横着个红头发白身子,长大得可惊的裸体美女,题着‘一城里最好的’。……这美女一手撑在看不见的家具上,姿势不大舒服,硬硬地支拄着一身骨骼,那是冰棒似的,上面凝冻着冰肌。她斜着身子,显出尖翘翘的圆大乳房,夸张的细腰,股部窄窄的;赤着脚但竭力踮着脚尖仿佛踏在高跟鞋上。短而方的‘孩儿面’,一双棕色大眼睛愣愣地望着画外的人,不乐也不淫,好像小孩子穿了新衣拍照,甚至于也没有自傲的意思;她把精致的乳房大腿蓬头发全副披挂齐整,如同时装模特儿把店里的衣服穿给顾客看。”
《创世纪》里潆珠站在橱窗前:“忽然发现,橱窗里彩纸络住的一张广告,是花柳圣药的广告,剪出一个女人,笑嘻嘻穿着游泳衣。”
《中国的日夜》写一个挑担卖桔子的人:“完全像SAPAJOU漫画里的中国人。外国人画出的中国人总是乐天的,狡猾可爱的苦哈哈,使人乐于给他骗两个钱去的。”
《续集·自序》:“记得一幅漫画以青草地来譬喻嘉宝……”
在张爱玲其他一些作品中,虽然言未及漫画二字,但她的描写手法实际上是漫画的,比如小说《留情》中对米晶尧的描写:“米先生除了戴眼镜这一项,整个地像个婴孩,小鼻子小眼睛的,仿佛不大能决定他是不是应当要哭。身上穿的西装,倒是腰板笔直,就像打了包的婴孩,也是直挺挺的。敦凤向米先生很快地睃了一眼,旋过头去。他连头带脸光光的,很齐整,像个三号配给面粉制的高桩馒头,郑重托在衬衫领上。”《连环套》中对米耳的描写:“米耳先生哈哈大笑起来,架着鼻子的黄胡子向上一耸一耸,差点儿把鼻子掀到脑后去了。从此也就忘了翻白眼,和颜悦色的向梅腊妮道……”
散文《公寓生活记趣》中那一对有着同样木渣渣的黄脸与木渣渣的黄膝盖的看门巡警,富于想象力的从高楼的窗户向下张望而可能晕倒的蚊子,以及不时要发怒的肝火旺的热水管道,乃至通篇都无不是漫画的笔调。
除了行文及字里行间运用画笔的笔法,张爱玲还时而直接在文字作品中自绘插图。她的散文集《流言》中就收了不少插图,大多是港战时的作品。有人奇怪她何以将许多不同类型的人画在一张纸上,其实原因很简单,战争环境下难以从容备纸,不过这样倒又参差地构成别有趣味的组画了。
张爱玲在上海的一个综合性英文月刊《二十世纪》上发表的《中国人的生活与时尚》,配了她手绘的12幅插图。
此外,张爱玲在她陆续发表的作品里,也都可以不时见到她画的插图。如短篇小说《心经》、《琉璃瓦》、《年青的时候》,中篇小说《金锁记》、《红玫瑰与白玫瑰》等;散文集《流言》不仅内有她的插图,连封面用图都是她绘制的;苏青办的杂志《天地》,自第11期至14期的封面也是张爱玲设计的,画面上方以几片云代表天,以一尊佛或是肥硕的唐代仕女的仰姿侧面头像代表峦(大地),以与刊名契合。(图92)
张爱玲与苏青还经常搞一搞图文“双璧”。《天地》第七八期合刊《生育问题特辑》中,苏青写了一篇《救救孩子!》,文首即配有张爱玲画的一帧画:一个两岁左右的小胖囡,一边一只羊角辫支楞着,一脸担惊受怕的表情,一只小手扒在栏杆上,上嘴唇也搁在栏杆上,非常勾人怜悯之心。《天地》的副刊《小天地》的创刊号上,有苏青的连载《女像陈列所》,也有张爱玲配的插图。
※※※
八百年前,大诗人陆游教人如何学作诗,说“功夫在诗外。”这句话流传至今,被人们广泛引用。也有人据其意作无休止类推:功夫在画外,功夫在字外……但少有例外,所有的“功夫”几乎都是单指学习者,而不指赏析者、评论者。除了喜欢画画,张爱玲也喜欢读画,而她的读法与人不同。她的观点每每红杏出墙,挂着画的墙,她的眼光在画外。她的眼光不是艺术专业的,而是社会学的。
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里写道:“Michelangelo的一个未完工的石像,题名‘黎明’的,只是一个粗糙的人形,面目都不清楚,却正是大气磅礴的,象征一个将要到的新时代。倘若现在也有那样的作品,自然是使人神往的,可是没有,也不能有,因为人们还不能挣脱时代的梦魇。”
Michelangelo即米开朗基罗,16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三杰之一,杰出的画家、雕塑家,也是卓越的建筑师和诗人。米开朗基罗有件雕塑作品,名字一般汉译为“晨”,也有译为“黎明”的,但它是一件已经完成的作品,面目是清楚的,故而与张爱玲所说的有差异。胡兰成在《今生今世·民国女子》里提到他与张爱玲说此画的情景:“我与她同看西洋画册子,拉斐尔与达文西的作品,她只一页一页的翻翻过,翻到米开朗基罗雕刻的人像‘黎明’,她停了细看一回,她道:‘这很大气,是未完工的。’”似乎可以作为张爱玲所指确为米开朗基罗的“黎明”的佐证,其实未必,因为胡兰成的印象可能来自于读《自己的文章》,而不是当初与张爱玲共读的画。
米开朗基罗的确有几件雕刻作品,是未完工的,人形粗糙,面目也不清楚,也可谓大气磅礴,可惜没有命名。
张爱玲在《忘不了的画》的开头,花了不少笔墨在说一幅画,因为那幅画是在所有给她留下深刻印象的画中唯一的一幅名画,这幅画她看得很细:
有些图画是我永远忘不了的,其中只有一张是名画,果庚的《永远不再》。一个夏威夷女人裸体躺在沙发上,静静听着门外的一男一女一路说着话走过去。门外的玫瑰红的夕照里的春天,雾一般地往上喷,有升华的感觉,而对于这健壮的,至多不过三十来岁的女人,一切都完了。女人的脸大而粗俗,单眼皮,她一手托腮,把眼睛推上去,成了吊梢眼,也有一种横泼的风情,在上海的小家妇女中时常可以看到的,于我们颇为熟悉。身子是木头的金棕色。棕黑的沙发,却画得像古铜,沙发套子上现出青白的小花,罗甸样地半透明。嵌在暗铜背景里的户外天气则是彩色玻璃,蓝天,红蓝的树,情侣,石栏干上站着童话里的稚拙的大鸟。玻璃,铜,与木,三种不同的质地似乎包括了人手扪得到的世界的全部,而这是切实的,像这女人。想必她曾经结结实实恋爱过,现在呢,“永远不再了”。虽然她睡的是文明的沙发,枕的是柠檬黄花布的荷叶边枕头,这里面有一种最原始的悲怆。不像在我们的社会里,年纪大一点的女人,如果与情爱无缘了还要想到爱,一定要碰到无数小小的不如意,龌龊的刺恼,把自尊心弄得千疮百孔,她这里的却是没有一点渣滓的悲哀,因为明净,是心平气和的,那木木的棕黄脸上还带着点不相干的微笑。仿佛有面镜子把户外的阳光迷离地反映到脸上来,一晃一晃。
“果庚”就是我们现在通译的“高更”,法国画家,后期印象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艺术对后来法国的象征派和野兽派有较大影响。1889年,万国博览会在巴黎开幕,这使高更非常兴奋,他对殖民馆中展示的各种生活方式充满了兴趣,他被异国风情深深迷住了。他对朋友称自己对那些异国那乡的“未知世界”充满了“可怕渴望”。他对他的画家朋友贝尔纳说起该年冬天的计划,说他想到越南和中国海南岛之间的北部湾去居住。
后来高更不断改变计划,最终他去了南太平洋上的法国殖民地塔希提岛。他说:“在这土著人的天堂里,追寻到了我心中的太阳,实现了我的艺术梦想。”他创作了不少以岛上风土人情为题材或背景的作品,《永远不再》就是其中一幅佳作。
※※※
高更的研究家、法国博物馆名誉馆长弗朗索索瓦丝·加香评论道:“这幅画真正画出了高更理想中的原始美女。她的肉体代表他自觉快要走到尽头的生命。”
画中与画外死亡的气息,高更在写给友人蒙弗雷的信中也表露无遗:“我正努力完成一幅画,好跟其他画一起寄去,但不知还有没有时间……我试着通过裸体来暗示久远以前的某种野蛮奢华。我特意让沉重和悲哀的色彩弥漫整幅画面。”他又写道:“《永远不再》这个画名,指的不是爱伦·坡的乌鸦,而是负责看守的恶魔之鸟。”
埃德加·爱伦·坡是19世纪美国最著名的诗人之一,被誉为唯美主义的先驱,桂冠还有科幻小说及侦探推理小说的鼻祖、短篇小说理论的创立者等。爱伦·坡在构思《乌鸦》时,创作的意图就十分明确。他认为,死亡是悲哀的主题的极点,而当死亡与美结合得最紧密的时候最富诗意,美女之死无疑是天下最富诗意的主题,而最适合讲这个主题的人就是一个痛失佳人的多情男子。于是《乌鸦》就以叙事诗的形式,以第一人称来叙述事情的经过,同时抒发内心的感情。而与那位多情男子的对话者,就是一只乌鸦。
那是一个凄凉的深夜,寂寥的“我”想用读书转移失去心爱的姑娘莱诺的痛苦,可是那些枯燥的图书却使“我”昏昏欲睡。隐约间,传来一阵叩门声,“我”打开门,门外除了黑暗什么也没有。声音又好像从窗棂传来,“我”打开窗户,一只乌鸦飞了进来,停在房门上方一尊帕拉斯雕像的上面。“我”猜想乌鸦的来历,询问它的名字,乌鸦却答非所问地叫一声:“Nevermore”;“我”向乌鸦诉说内心的苦闷,希望上帝送来解忧良药,或是灵魂能在遥远的仙境与美丽的莱诺拥抱,乌鸦一律只一句:“Nevermore”;“我”恼羞成怒,要赶乌鸦出门,可乌鸦动也不动,仍只机械地
高更画的原名为“Nevermore”,张爱玲译为或她所见的译本译为“永远不再”,其实这个单词与“永远不再”并不完全对应。它在不同的语境下,语意可有一定的差别。在《乌鸦》的诗里,乌鸦的话,除了可译作“永远不再”外,有时还可译作“永不再现”、“永无指望”、“永不可能”等。
高更的《永远不再》,主旨与意趣都与爱伦·坡的《乌鸦》太相近,而且画面的窗台上竟也站着一只鸟,难怪人们对此画与彼诗产生联想。尽管高更说他的“恶魔之鸟”不是“乌鸦”,客观上显然难以完全否认掉彼此的联系,爱伦·坡诗中的“我”也是称乌鸦为恶魔的。
再从爱伦·坡作诗与高更作画当时各自所处的境况来看,前者夫妻关系不睦,家庭因生活拮据而反复搬迁,妻子患肺病而缺钱医治;后者则先是生病付不起住院费,继而爱女阿林以20岁的妙龄死于肺炎(据说高更此画即为纪念死去的女儿阿林而作),半年后他在一座山丘上服下大量砒霜自杀,却因呕吐而未死成。由此看来,两人创作该诗画时阴郁灰黯的心情是相近的,主题相仿也就不奇怪了。
张爱玲对《永远不再》的诠释明显打着“张氏风格”的印记,那么细致、具体、真实,并且与上海的妇女相结合,但是否脱离了高更的主题和含意,却又难说。因为《永远不再》原是高更为纪念他死去的女儿阿林而作,他的本意在“伤”逝去的生命,张爱玲理解的“伤”则是逝去的爱情,虽然相同的都是“伤逝”。
高更在写给蒙弗雷的信中说该画名叫“永远不再·啊·塔希提”,而今日一般的画册上都写着画名为“永远不再”。画名不同的原因也许是高更改变了主意,也许是画册的版本问题。张爱玲看到的画册应是“永远不再”。
关于塔希提,张爱玲在《谈看书》一文中提及,她把它译作“塔喜提”。她读到人种学家瑟格斯所著的《泡丽尼夏的岛屿文化》一书,夏威夷、塔希提等群岛统称泡丽尼夏。书中说岛上的居民来自华南(广州、海南岛一带),因为汉族在黄河流域势力膨胀,较落后的民族被迫南迁。虽然夏威夷人究竟是来自亚洲还是西太平洋尚难断定,但夏威夷人的祖先是华侨的可能性引起了张爱玲的兴趣——高更笔下的那位横卧着的塔希提模特儿,是华侨的后裔也并非完全不可能,上海小家妇女吊梢眼的“横泼的风情”也似乎有源可寻了。
※※※
高更在1889年年底画了一幅自画像,题为“戏笔的自画像”。他用象征天国的红色作背景,把自己的身体涂成明亮的柠檬黄,他的表情带着嘲讽,头上则悬着一道黄色的常见于圣母圣子头上的光环,以此把自己比做圣人。他右手的食指与中指间,夹着一条常见于僧侣手上的小蛇,如此似又把自己比做先知。(见图29)
这使人想起张爱玲1937年发表在圣玛丽亚校刊《凤藻》上的插图。画中所有的人物头脸用的是相片,身子是画的。这就像是命题作文——须根据已固定了的长相及表情来设计姿态和动作。看它们的搭配的确饶有情趣,同时也显示出作者巧妙的构思,以及灵巧的画笔。这些都是张爱玲的同学们,而她自己也在其中。虽然不在正中处,所处却也是重要位置。而那个位置——画面的左上角——似乎是张爱玲偏爱的地方,她的另一幅同学合影,她也是站在那个位置的。当然这也可以理解为只因在这幅画中,张爱玲所充当的角色与她的同学们不同。关键是,她用浓黑的英文为自己织就了一圈花环,写着:“PROPHECIESofaFORTUNETELLER”,意为“一个算命者的预言”,预言她的同学们的未来。
由此似乎表明张爱玲与高更有相近的自视与自诩。
胡兰成在《今生今世》里提到他曾从池田那里借了日本的浮世绘与张爱玲同看。张爱玲在《忘不了的画》中谈到日本的浮世绘:
日本美女画中有著名的《青楼十二时》,画出艺妓每天二十四个钟点内的生活。这里的画家的态度很难得到我们的了解,那倍异的尊重与郑重。中国的确也有苏小妹、董小宛之流,从粉头群里跳出来,自处甚高,但是在中国这是个性的突出,而在日本就成了一种制度——在日本,什么都会成为一种制度的。艺妓是循规蹈矩训练出来的大众情人,最轻飘的小动作里也有传统习惯的重量,没有半点游移。《青楼十二时》里我只记得丑时的一张,深宵的女人换上家用的木屐,一只手捉住胸前的轻花衣服,防它滑下肩来,一只手握着一炷香,香头飘出细细的烟。有丫头蹲在一边伺候着,画得比她小许多。她立在那里,像是太高,低垂的颈子太细,太长,还没踏到木屐上的小白脚又小得不适合,然而她确实知道她是被爱着的,虽然那时候只有她一个人在那里。因为心定,夜显得更静了,也更悠久。
浮世绘(ukiyoe)是始自17世纪中叶,在日本流行了200多年的一个画种,从它诞生于市井艺术家之手就表明它的旨趣是入世的、世俗的。单看它字面上的意思也相去不远,描绘的是浮生世象。浮世绘在手法上分为水印木版画与画家手绘两种,从画风中可以看出它所受中国唐代以来工笔兼小写意的仕女画、中国风俗画的影响,但浮世绘的题材内容形象又是典型的日本风格。可能正是这个原因,至少是原因之一,浮世绘不仅在盛行的当时深受人们喜爱,而且在衰亡之后直到现在,致使它衰亡的地域之外的人们对它的喜爱逾数世纪而热情不减,世界各大博物馆对浮世绘作品多有收藏。
浮世绘多以现实生活中的美人、艺伎、妓女、儿童、风景、花鸟、虫草及动植物等为题材,其中以美人和艺伎为浮世绘两大主题。被称作浮世绘“中兴始祖”、“一代宗师”的浮世绘画家喜多川歌(麻吕)(UtamaroKitagawa1754-1806)就以擅长美人肖像著称,他在多彩版画、画本、手绘画方面留下了许多杰作,《青楼十二时》就是其中之一。
《青楼十二时》共有12幅,每个时辰(两个小时)一幅,如张爱玲所说,“画出艺妓每天二十四个钟点内的生活。”
显然张爱玲是赏画过后凭印象撰文的,所以不免记忆有错。说是丑时没错,女子换木屐以及小白脚小得不适合;“一只手握着一柱香,香头飘出细细的烟”;“女人似乎个子太高、颈子太细太长”大多没错,错的是人物的另一只手,并没有“捉住胸前的轻花衣服,防它滑下肩来”,而是捏着几张手纸;她的身旁,也没“有丫头蹲在一边伺候着”。
※※※
画中人物那样的宽衣大袖,想来无论是瘦削或圆润的美人肩,都会撑挂不住的,一不留神就要滑下肩来,于是用手去“捉”。可这是张爱玲的想象。丑时正要如厕的这位女子的衣襟虽然不算平整,却也没有将要滑落的迹象。《青楼十二时》里,12幅图中,并没有防止衣裳滑下肩头的画面,倒是有两幅露肩像,一张是“辰时”,一张是“巳时”。前者画的是女子正在起床,刚从被窝里钻出来,侧起身子时,半边衣襟敞开,不仅露出肩头,酥胸也半露了。后者画的是晚起的女子正由丫头侍候着洗漱,右手忙着用手巾擦脸,不意左肩的衣衫滑下。
《青楼十二时》里,除了“巳时”的这一幅外,还有“子时”、“未时”、“酉时”、“戌时”、“亥时”等,都是“有丫头蹲在一边伺候着”的,而且画家显然为了使人物主次分明、身份分明,丫头一般都画得小一些、矮一些,要么或蹲或跪屈着身体。
综合衣裳溜肩与丫头侍候的画面,看来还是“巳时”最接近张爱玲与“丑时”弄混的画。
由《青楼十二时》,张爱玲觉得日本画家是把“妓女来理想化了”,其原因,她认为“是日本人对于训练的重视,而艺妓,因为训练得格外彻底,所以格外接近女性的美善的标准”。否则很难理解日本小说家谷崎润一郎在《神与人之间》里为什么以艺妓来代表圣洁的圣母。
张爱玲的诠释却没有得到日本学者的认同。张爱玲觉得费解的,日本学者却认为道理很简单,池上贞子说:那位艺妓之所以被作为圣母,是因为她“虽然原来出身艺妓,却恪守妇德十分圣洁”的缘故。张爱玲在此纯粹是想得过深,这才影响了自己的判断。她若用自己在那半年前写的《洋人看京戏及其他》一文中对京剧《玉堂春》中妓女的理解,来理解《神与人之间》中的艺妓,就没有问题了,她写道:
“《玉堂春》代表中国流行着的无数的关于有德性的妓女的故事。良善的妓女是多数人的理想夫人。既然她仗着她的容貌来谋生,可见她一定是美的,美之外又加上了道德。”
《玉堂春》在京剧史上地位不同寻常,它不仅是京剧旦角的开蒙戏,也是中国戏曲中流传最广的剧目之一。故事见于冯梦龙编订的《警世通言》卷24《玉堂春落难逢夫》,《情史》卷2中亦有此事。剧情为:
明朝名妓苏三(艺名玉堂春)与前吏部尚书之子王金龙春风一度,动了真情。王金龙将钱财挥用尽后,被老鸨赶出妓院。老鸨把苏三骗卖给山西富商沈燕林作妾。沈妻皮氏好妒,用姘夫赵昂买的毒药下在挂面里,想要毒死苏三,不料却毒死了沈燕林,即与赵昂合谋嫁祸苏三。苏三被押官府,屈打成招,被解到省府太原再审,在大堂上巧遇时已做了八府巡按的王金龙。于是案情大白,皮氏与赵昂被斩,苏三冤曲得伸,有情人终结连理。
苏三的“良善”或者说“道德”,表现在当王公子最初在妓院挥霍无度时,她就曾劝他银子不要“混花”;当王公子千金散尽时,苏三也并未脸色随之而变,而与他仍旧恩爱不改,后更以私房钱赠予落魄潦倒的王公子,鼓励他发奋读书,这才救了对方也救了自己。
张爱玲在《忘不了的画》里又谈到另一幅根据民间故事创作的日本画《山姥与金太郎》:
……我也比较喜欢日本画里的《山姥与金太郎》,大约是民间传说,不清楚两人是否母子关系,金太郎也许是个英雄,被山灵抚养大的。山姥披着一头乱蓬蓬的黑发,丰肥的长脸,眼睛是妖淫的,又带着点潇潇的笑,像是想得很远很远;她把头低着,头发横飞出去,就像有狂风把漫山遍野的树木吹得往一边倒。也许因为倾侧的姿势,她的乳在颈项底下就开始了,长长地下垂,是所谓“口袋奶”,蟹壳脸的小孩金太郎偎在她胸脯上,圆睁怪眼,有时候也顽皮地用手去捻她的乳头,而她只是不介意地潇潇笑着,一手执着描了花的博浪鼓逗着他,眼色里说不出是诱惑,是卑贱,是涵容笼罩,而胸前的黄黑的小孩子强凶霸道之外,又有大智慧在生长中。这里有母子,也有男女的基本关系。因为只有一男一女,没人在旁看戏,所以是正大的,觉得一种开天辟地之初的气魄。
※※※
“太郎”在日语里是“男孩”的意思。因为日本是一个弹丸岛国,人民又渴望强大,所以无论是文学作品还是民间故事,以小胜大的主题不少,“太郎”出现的频率也就较高。金太郎是日本的民间故事《金太郎》中的主人公,据吉林大学于长敏于1996年在日本土浦市阿见中学所做的一项调查,由100名该校中学生写出自己最喜欢的5个日本民间故事,结果金太郎名列第四。因此说金太郎的故事家喻户晓应不为虚。可是奇怪的是我国国内出版的几种日本民间故事集,不约而同地都只有一个“桃太郎”的故事,而未见金太郎的故事;张爱玲对金太郎的来历居然也不清楚,所以才有“大约是民间传说”之猜。而她是与胡兰成同看这画的,胡兰成也可以向借画给他的日本人池田询问,看来对此都不很清楚。
关于金太郎的身世,有的说他生于一个山民家中,有的说他母亲本是天皇的侍女,因与一名侍卫产生了私情,后来在山中生下了他。若抠起字眼来,也可以说第二种说法与第一种并不矛盾,因为生于山民之家也不一定就代表他是山民之后。
金太郎孩提时就力大无比。故事之一是他把黑熊高高举起来又重重摔下,被他打败了的黑熊从此俯首贴耳听命于他,每天把他砍下的柴禾驮到他家里去;故事之二是有一次山林着火,金太郎无处可逃,竟把一棵参天巨树推倒,搭在两个悬崖之间,使他和他的母亲可以从上面走到安全的对岸去。
金太郎力大无穷的“神性”的来源,也有两种说法。一是他从小与野兽生活在一起。可以设想,假如他与长臂猿一同练习攀缘,自然臂力是可以过人的;而假如他与羚羊为伍,跑跳一定是无人能及的。二是张爱玲所说,是山灵(山姥)抚养的结果。
综合来看,金太郎有两位母亲,一是生身的母亲,一是养育他的母亲(山姥)。而在所有的画作里,画的都是他与养母在一起的情景。按弗洛伊德的理论,母亲在给儿子喂奶的过程中,是有性的意味交流的,何况养母养子。所以张爱玲说:“这里有母子,也有男女的基本关系。”她真的是目光敏锐,连画中的暧昧与微妙意味都读得出来。她又觉得山姥与金太郎有“一种开天辟地之初的气魄”,而果真金太郎后来当上了源赖光的武士,取名坂田公时,成为源赖光打天下的四大金刚之一。
胡兰成在《今生今世·民国女子》中写道:“我从池田处借来日本的版画、浮世绘,及塞尚的画册,她看了喜欢。”而日本的版画是也包括浮世绘的。浮世绘中,也不只一位画家一幅作品以金太郎为题材,所以张爱玲见到的那幅《山姥与金太郎》很可能也是浮世绘作品。
浮世绘画家葛饰北斋画有《金太郎与野兽》,喜多川歌(麻吕)画的金太郎则有多幅,可是没有一幅完全符合张爱玲所描绘的画面。最接近的一幅,虽然有“金太郎偎在她胸脯上,圆睁怪眼,有时候也顽皮地用手去捻她的乳头”,也可以说金太郎有“强凶霸道之外,又有大智慧在生长中”的表情,但是没有山姥“不介意地潇潇笑着,一手执着描了花的博浪鼓逗着他”,眼色里也似乎没有诸如“诱惑,卑贱,涵容笼罩”,而只有专注与享受,乳房也不是所谓长长地下垂的“口袋”,而是坚挺鼓胀的浑圆。尽管如此,我们由此已经差不多可以感受到张爱玲所描绘的画中人物的神情了。
张爱玲之所以喜欢《山姥与金太郎》,是因为她觉得此画面中的母与子神情自然,真实地存在于天伦之中。而欧洲诸国的圣母画则不然,张爱玲觉得画外总有一圈看客,使得圣母对圣子所有的动作表情都成了表演:“有时候他身上覆了轻纱,母亲揭开纱,像是卖弄地揭开了贵重礼物的盒盖。有时候她也逗着他玩,或是温柔地凝视着怀中的他,可是旁边总仿佛有无数眼睁睁的看戏的。”而圣母之所以做戏,张爱玲认为除了“当众”的缘故外,还与圣母平凡的出身有关:她因平凡而被推为皇后,所以不禁要保持平凡,于是要做戏了。
显然张爱玲对“浮世绘”这个词颇有感觉,六十年代她将《十八春》改写时,在取名“半生缘”之前,曾考虑用“浮世绘”作题名,后因觉得不大切题而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