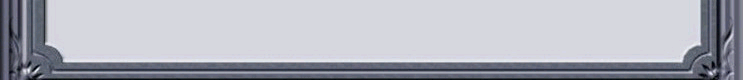第十一章 《传奇》世界(上)
或许我们首先应该将这段表述看做对《传奇》的大背景或曰大环境的把握。姚先生的家、川嫦的房间等等,作为故事展开的具体环境单个地看,并没有什么超出特定地点、场所的意义,然而当它们与《倾城之恋》中的白公馆、《金锁记》中的姜公馆、《茉莉香片》中的传庆家、《留情》中杨太太的府第等,由于一种内在的相似性,在读者的心目中相互重叠,发生关联,构成一个独特的“世界”时,每一个具体环境就在作者统一的命意下获得了超越自身的新的意义。一个场景如果重复出现,它就有可能变为一种象征。上面所举各篇小说中的具体环境当然不是同一个,然而它们有内在的相似性--都是没落的旧式家庭。更重要的是,它们有同样灰暗的色调,同样腐烂的、令人窒息的气味--又使人们可以将它们当做同一个来看待。这是衰落的中国封建文化的缩影,也可以说,一种衰落中的文化构成了《传奇》世界的总背景。
文化是一个宽广的概念,它包括了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日常习俗、道德规范等等,而文化的衰落往往表现在这一切在到来的时代面前显得不合时宜。囿于过时的生活方式,抱着陈旧信念的人们不能应付现实,不是失败,就是陷于可笑的境地。《传奇》增订本印行时张对封面设计所做的说明证明她对自己要表现的是什么有着极清醒的意识:“(封面)借用了晚清的一张时装仕女图,画着个女人幽幽地在那里弄骨牌。旁边坐着奶妈,抱着孩子,仿佛是晚饭后家常的一幕,可是栏杆外,很突兀地,有个比例不对的人形,像鬼魂出现似的,那是现代人,非常好奇地孜孜往里窥视。如果这个画面里有使人感到不安的地方,那也正是我希望造成的气氛。”那个尺寸大于古装人几倍的现代人的身形在画面上造成一种压迫感,室内原有的宁静、和谐全被打破了,然而画中人并不觉察到身后的情形,兀自专注于骨牌的世界,这正是对《传奇》中人物的极好写照。他们固然已失去了那种静谧的文化氛围,现代生活的冲击使他们的神经一再地被骚扰,然而他们对时代作出的反应、他们与时代的关系实质上却正如古装人之于身后的现代人。他们忘却了时代,也被时代忘却,整个地封闭在旧的生活方式中,始终背向着时代盲目地挣扎,不知道生活中发生波动震荡的真正原因,现代人的出现因此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梦魇。这些败落之家从一开始起就已经处在一种无可挽回的颓势中,根本不可能出现“兰桂齐芳”的转机,又因为外界的重大变化始终呈现在这些旧式人物的主观感受之中,小说中没有一个像《家》中的觉慧、《雷雨》中的周冲那样代表着新的生活方式的内视点,甚至也没有像觉新、曾文清(《北京人》)那样虽无力挣脱旧文化影响,却能够反省旧的生活方式的人物,《传奇》的世界更显示出它无望和封闭的性质。
在一些现代小说的理论中,背景变成了“气氛”或“情调”。在《传奇》中,代表旧文化的旧的生活方式的式微正是通过笼罩于全书的颓丧气氛和情调得到说明的。这种情调和气氛见于室内的陈设、人物的服饰、日常生活的细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总之,是环绕着主人公的一切。这一切将一种文化、一种生活方式立体化、具象化,人物是融于这气氛中的一部分,而在这褪色的背景的衬映下,人物的悲剧命运更见得分明。
要说明主人公的命运与其背景之间的关系,《茉莉香片》是一个极好的例子。聂传庆的背景就是他的父亲、他的家。他的父亲是个遗少型的人物,他的家弥漫着鸦片的烟香。尽管这个家只是故事中的一个场景,但是他的家、他的父亲却是他苦恼的真正根源。小说直接展示的是传庆的变态心理,而他的心理变态、他的性格,却是那个家一手造成的。他是病态的、毫无生气的生活方式结出的一枚苦涩的果实。
他家是一座大宅。他们初从上海搬来的时候,满园子的花木,没两三年的功夫,枯的枯,死的死,砍掉的砍掉,太阳光晒着,满眼的荒凉。一个打杂的,在草地上拖翻了一张藤椅子,把一壶滚水浇上去,杀臭虫。
(言丹珠有一次想去传庆家打网球)传庆笑道:“我们的网球场,很少有机会腾出来打网球,多半是晾满衣服,天暖的时候,他们在那里煮鸦片烟。”
这就是传庆的家,他的笑中该有酸楚的恨恨不已的内容。《传奇》中没有新与旧的正面冲突,没有对败落过程的交待,张爱玲习惯于用具体的物象传达出来的一种情调、气氛来说明一切,生活上的腐朽通过它的结果呈现出来:聂传庆的耳朵有些聋,那是他父亲加于他的肉体的伤害,他的内心受到的不断的折磨更为严重,那也是他的家庭施予他的。他因此憎恨父亲,憎恨家,希望在言子夜教授身上寻找到理想的父亲形象。当这个企求幻灭之后,他又在言丹珠身上寻找寄托,对丹珠施暴前一段狂热的表白吐露出他的心声:“丹珠,如果你同别人相爱着,对于他你不过是一个爱人。可是对于我,你不单是一个爱人,你是一个创造者,一个父亲、母亲,一个新的环境、新的天地,你是过去与未来,你是神。”可见言子夜父女在他是另一种生活方式的象征,而他的不幸来自他与家、与父亲之间的宿命的关系。这种关系不单使他得不到父爱,而且使他在生活的其他方面也看不到希望。
然而“他爸爸并不是有意想把他训练成这样一个人,现在他爸爸见了他,只感到愤怒与无可奈何,私下里又有点怕”。真正的罪魁为谁?只能是他父亲代表的那种生活方式。父子间关系的紧张、他对父亲的厌憎、父亲对他的恐惧,都由那种特定的生活方式铸成。他父亲本是没落文化的殉葬品,现在又成了罩在他头上的阴影。
这种生活对他的毒化更表现在,他即使对环境不满,充满憎恶之情,也无力摆脱它。正像父亲对他无可奈何一样,他也怀着厌恶、恐惧,无可奈何地不断在自己身上发现父亲的影子。他已经没有力量改变自己,只有在言子夜差一点成为自己父亲的幻想中找点安慰,或者绝望地向外界的力量呼吁--甚至这种对于生活的态度,也是过去的生活交给他的。他成了一个废人,对丹珠的施暴实质上不过是一种自戕的行为。小说以四个字作结:“他跑不了。”--那就是说,他抹不掉自己的背景。丹珠的出现将不断向他提示这个背景的存在,而变态心理的折磨注定要延续下去,这就是他真正的宿命。
聂传庆在《传奇》中是一个特殊的例子,在更多的情况下,张爱玲关心的是旧文化、旧生活方式没落背景下那些青年妇女的命运。《花凋》中的川嫦、《金锁记》中的姜长安、《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和宝络、《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孟烟鹂、《红鸾禧》中的邱玉清、《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等等,这些人在过去都是所谓“大家闺秀”,如今随着她们的家庭、门第的贬值,她们的身价也一落千丈。她们的不幸在于,在社会的眼中她们已成了一批陈旧过时的货色,然而她们的家长仍抱着陈旧过时的信念,希望找到门当户对的人家,结一门体面的婚姻。她们的全部教养都来自旧的文化、旧的生活方式,这些教养皆是为出嫁做准备的,生活的唯一出路在于婚姻,按照旧的信条,她们又只能“待字闺中”,出去交际被认为是有损身份。这样的矜持在过去是大家风范的证据,现在却乏人赞赏,反使她们婚姻的机会更少,于是嫁不出去的危机成了她们的一个噩梦。
新时代中旧式女子陷入婚姻困境,这在凌淑华的小说里曾经得到表现,鲁迅有过甚高评价的《绣枕》,就非常出色地描绘了一个为旧式婚姻观念牺牲了的女子的悲哀。“五四”以后的小说,大多以包办婚姻的不幸揭露旧礼教、旧道德的罪恶,凌淑华放过了这一主题,她以旧式女子处境的尴尬来说明旧派人物的落伍。在这个意义上,张爱玲有相似之处。不过《传奇》小说中的女子大体上生活在稍后一些的时期,旧的一套的不合时宜显得更加触目,这些人物以及她们的家长,已经多少迁就了现实,张爱玲也比凌淑华更加曲折多面地展示她们面临的困境。
白流苏离婚后住在娘家,那个已离了婚的丈夫的死使她在娘家的日子一下变得复杂微妙了。找到一桩安全的婚姻是她摆脱烦难的唯一出路。徐太太点明了这个真相:“找事都是假的,还是找个人是真的。”这对《传奇》中的绝大多数女子都适用。她们的一切教育都是为出嫁做准备,难怪婚姻动机构成了生活中的一个主旋律。白流苏的自忖可以说是对她们所受教育的一种说明:“除了人之外,她没有旁的兴趣,她所有的一点学识,凭着这点本领,她能够做一个贤惠的媳妇、一个细心的母亲。”这是进入另一个大家庭,周旋于叔嫂公婆之间的必备条件,除此之外,流苏一无所能:“我又没念过两句书,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我能干什么?”她还会女红--她在故事中出现的第一个镜头,便是坐着在绣一双拖鞋。凭着旧式教育给她的这一切,她能找到一个好人家么?白流苏也知道这一切如今不时兴了,所以她向徐太太抱怨:“……像我们这样的家庭,哪儿肯放我们出去交际……依仗着家里人,他们根本不赞成……”愈是如此,与那些新派女子比起来就愈是缺少竞争的能力。白流苏最后总算有了一个圆满的收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将她与范柳原联系在一起的最初的契机恰恰是“妇德、妇言、妇容、妇功”以外的东西--她会跳舞。原是为宝络去相亲,范柳原看上的偏是流苏。四奶奶回来之后愤愤地道:“我们诗礼人家,不准学跳舞的--像你三妈,像我,都是大户人家的小姐。活过这半辈子,什么世面没见过,我们就不会跳!”宝络不会跳舞,她应该是更标准的大家闺秀,按照四奶奶的信条,理想的人选怎么也该是她,可范柳原偏偏对她无兴趣。在这场无意识的角逐中,“残花败柳”的流苏出人意料地占了上风。流苏还有更大的罪过,她离过婚,这也是四奶奶看她不起的理由。但是四奶奶的矜持清高有什么用呢?--只见得迂腐可笑。当小说临近结尾时,四奶奶居然也闹着要同四爷离婚了。
《传奇》中的其他女子与白流苏相比,情形大有改观。“养在深闺人未识”显然是不行了,旧家庭也要维新,孟烟鹂、邱玉清、郑川嫦,以至七巧治下的姜长安,都有机会进学堂,然而生活方式未变,观念信条一仍其旧,断文识字代替女红手工,西体中用,最后的目标依然是一桩靠得住的婚姻。所以外面的学校倒在其次,“郑川嫦可以说一下地就进了‘新娘学校’”。为门第所限,郑家的女儿不能当女店员、女打字员,只能做“女结婚员”,出去做事等于宣布放弃淑女的身份,这身份食之无味,弃之可惜。要保住这身份,婚姻对她们才成为迫切的课题,而又是真正的难题。
但是真正因此陷入绝境的情形并不多见,只是在《金锁记》中的姜长安身上我们看到一出彻头彻尾的悲剧。长安与《绣枕》中的那位小姐又有不同,她生活在较晚一些的时候,受到社会气氛的熏染,多少已经取了较为主动的姿态,是她的家庭,是七巧的诡计更直接地夺去了她可能的婚姻。除她而外,婚姻问题经常导向了喜剧和闹剧。一种生活方式腐朽没落到这种程度,以致那些原本带着悲剧意味的人物已经失去了悲剧的美,只能上演可笑的滑稽戏了。然而滑稽可笑中透露的恰好又正是大家闺秀们的式微。
《倾城之恋》中三奶奶、四奶奶听说有范柳原这么一个婚姻的机会,连忙争抢着要让女儿挤上前去,而那天晚上,惨遭淘汰的金枝、金蝉急不可待地等着相亲的人们的音信,一副十足的猴急相倒是披露出败落之家的小姐们在婚姻中饥不择食、慌不择路的心态,那种未必为个中人清楚地意识到的恐惧心理,也许是这一流人中存在着的“集体无意识”。
在《红鸾禧》中,邱玉清得到一桩令她心满意足的婚姻,但是在她的一团高兴中我们看到的却是相反的内容。邱玉清小心翼翼地掩饰自己的兴奋,“坐在石鼓上,身子向前倾,一手托着腮,抑郁地看着她的两个女傧相,玉清小心地不使她自己露出高兴的神气--为了出嫁而欢欣鼓舞,仿佛坐实了她是个老处女似的”。要掩饰是她的门第要求于她的风仪,作者的讥讽却把这种掩饰变成了哈哈镜,更显出她的兴奋不一般。她要去的姜家是新起的暴发户,按照旧的眼光,邱玉清的出嫁不是高攀,而是俯就,这样一桩看来是委屈了她的婚姻居然也让她如此兴奋不已,唯有在对这一团高兴的掩饰中才勉强地证明着身份的高贵,一团喜气中显出的,岂不正是旧式淑女的末路?难怪在新派的二乔四美的想象中,玉清已经成了“银幕上最后映出的雪白耀眼的‘完’字,而她们是精彩的下期佳片预告”。旧式淑女的形象的确在历史的银幕上渐渐地黯淡下去,她们或是像姜长安一样,谱一曲哀歌,留下一个“苍凉的手势”,或者是在向现实让步,因勉强跟趟而显得可笑。
《传奇》中的大多数人都受到旧的文化背景的制约,张爱玲也最善于塑造在这个背景制约下的人物。有些次要人物往往只有短暂的登场机会,而张爱玲往往只借助一些细节,寥寥数语就能将人物的性格气质呈现出来。例如《金锁记》中的姜季泽,第一次登场时作者让他“一路打着哈欠进来”,仅仅着重写他“水汪汪的眼睛里永远透着三分不耐烦”的神态,写他倒骑了椅子将女人们剥了孝敬老母的核桃仁一个一个拈来吃的动作,便活灵活现画出了一个败家的阔少形象。《花凋》中郑先生的名士派头加遗少派头则从他给家里安排的日常生活秩序中体现出来:
说不上来郑家是穷还是阔。呼奴使婢的一大家子人,住了一幢洋房,床只有两只,小姐们每晚抱了铺盖到客室里打地铺,客室里稀稀朗朗的几件家具也是借来的,只有架无线电是自己置的,留声机屉子里有最新的流行唱片。他们不断地吃零食,全家坐了汽车看电影去。孩子蛀了牙没钱补,在学校里买不起钢笔头,佣人们因工资欠得过多,不得不做下去。下人在厨房里开一桌饭,全弄堂的底下人都来分享,八仙桌四周的长板凳上挤满人。
《传奇》中人物与特定的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张爱玲经常是在写人的时候,也就在写一种生活。上面所举的遗少是《传奇》中再一出现的人物,其他如较常出现的太太、姨奶奶、丫环、小姐,也都是与旧式生活联系在一起的人物,随身带着旧式生活的气氛。他们都是传统的中国人。当张爱玲把自己的笔探向一些与这种生活、与旧的文化背景间的关系疏远以至于无的人物时,她的笔往往失去了写前一类人物时所具有的从容自如,乔其乔和范柳原即是明显的例子。这两个人物在各自的故事中都是所谓男主人公,出现的机会也不少,但作者始终不能从正面把握住他们,她想让他们作为立体的形象活着,但她始终不能进入他们的内心世界,当她希望在浪子的特点以外从他们身上找到一点更为结实的东西以丰富人物形象时,人物形象反而模糊了--他们始终是影影绰绰的影子。
这并非因为作者是个女作家,男性形象对她是个难题,我们看到,即使是作为故事头号人物出现的男性形象,只要他在旧文化的背景下出现,只要他在某种程度上负荷着所谓传统的分量,张爱玲的笔能立时就显得沉稳有力、不浮不乱。只要将佟振保、米尧晶与乔其乔、范柳原作一比较,就可以证明上面的判断。佟、米二人是在旧式生活边缘上行走的人,尽管喝过洋墨水,骨子里依然是旧式的中国人。米先生与淳于敦凤的结合可说是更彻底地把自己带回到旧式生活中去,而佟振保关于女人的观念正烙着旧文化的印记,“一个是圣洁的妻,一个是热烈的情妇--普通人向来是这样把节烈分开来讲的”。发生在振保身上的悲喜剧不用说与这观念有着必然联系,而佟、米二人都是按照中国式的逻辑对外部做出反应,也就是说,他们思想意识中的背景是旧文化的某些观念,这正是张爱玲能准确描写他们的心理,使他们的性格生动、丰满的原因。
熟悉旧的生活方式,谙晓旧式人物的习性,擅长描写没落的文化背景下的人物的悲喜剧,这本身就说明了张爱玲与传统文化之间深刻的联系。她是没落世家的后裔,故对旧式生活的腐朽没落等有着真切的体验与清醒的意识,正如鲁迅所说,这些情形,“非同阶级是不能深知的,加以袭击,撕其面具,当比不熟悉此中情形者更加有力”。《传奇》中形形色色的病态人物凑集在一起,反映着他们身后的生活方式、文化背景的病态,张爱玲准确地把握了她的人物封闭于其中的那种生活的颓丧、没落的特征。
为了强调这一特征,她甚至有意识地造成一些人物外观上的对比,如《红鸾禧》中二乔四美的丰满结实衬出玉清的瘦削,《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王娇蕊的丰腴衬出孟烟鹂的苍白,《茉莉香片》中言丹珠的活力、朝气衬出聂传庆的干瘪萎靡。前者当然不是什么新人形象,但是张爱玲似乎意在说明,与那种旧式的生活靠得越近,就越难以避免染上它所特有的一股死气。在《金锁记》中,张爱玲更借了童世舫的意识活动来揭示旧式生活的特质:“……卷着云头的花梨炕,冰凉的黄藤芯子,柚子的寒香……姨奶奶添了孩子。这就是他所怀念的古中国……他的幽闲贞静的中国闺秀是抽鸦片的!他坐了起来,双手托着头,感到了难堪的落寞。”童世舫的古中国梦的失落部分也是张爱玲对旧文化、旧的生活方式的失望。《传奇》因此成为展现旧式生活奄奄一息、行将就木的一卷褪色的画卷。聂传庆跑不了,《传奇》世界中的大多数人也都跑不了,因为他们按照老的时钟生活,“他们唱歌唱走了板,跟不上生命的胡琴”,为旧的生活方式封闭着,而这旧的一切正在走下坡路,他们如同坐在就要坠落山崖的闷罐子车内,谁也不得脱身,只能像川嫦临死前感觉到的那样,“硕大无朋的自身和这腐烂美丽的世界,两个尸身背对背拴在一起,你坠着我,我坠着你,往下沉”。《传奇》中的人物与旧文化、旧的生活方式,正是这种“你坠着我,我坠着你”的关系。
尽管张爱玲在小说中反映了旧文化的衰落,反映了旧的生活方式的崩溃,这一切对于她却不过是舞台上的布景,她的最高命意不是鞭挞和批判,而是在这布景下上演普遍的、永恒的人生悲喜剧。亨利·菲尔丁向读者介绍他的作品说:“这里替读者准备下的食品不是别的,乃是人性。”张爱玲备下的也是这样一道菜,在张爱玲看来,她的布景--那个新旧交替中的时代,那种没落的文化--恰好使人性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说《传奇》是“开向沪、港洋场社会的窗口”,只能是我们基于现实主义标准对它做出的价值判断,假如《传奇》可以称为一个窗口,那么张爱玲希望通过这窗口张看到的便是永恒的人生,普遍的人性。她当然也这样希望她的读者。
在《传奇》中,普遍的人性凝定在普通人的身上。《传奇》初版扉页上有作者这样的题词:“书名叫传奇,目的是在传奇里面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这里的普通人绝非社会学、经济学意义上的划分--按照贫与富的标准,几亿中国百姓眼中的白流苏、葛薇龙、佟振保之流,当然不那么普通--而是与英雄、超人相对的概念。毋宁说这里的“普通”是一种品格气质、精神思想上的定义。普通人没有脱俗的理想,没有过人的理性,没有超人的毅力,没有超凡的美德,他们只不过按照世俗的要求,按照自己的常识处世行事,好与坏都被性格的平庸限制着,干不出惊人的事件,只配领略平淡无奇的生活,唯其普通,体现在这些人身上的人性在张爱玲看来才更带有普遍的意味。至于把普通人与传奇联系在一起,则是她希望在普通人身上咀嚼出浓稠的人生况味,而又将奇归于不奇,滤去人们一厢情愿掺和在巧合事件中的浪漫成分。
《传奇》全部小说的写作不过经历了一年半的时间,然而即使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小说的外观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大致说来,这种变化的趋向是“绚烂归于平淡”--小说中“奇”的因素减少以至消失。在写作时间较早的那些小说中,张爱玲注意制造出“奇”的效果,《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奇”来自薇龙面对的新奇的环境,《沉香屑:第二炉香》中的“奇”来自奇特的事件,《心经》中的“奇”来自恋父情结,《茉莉香片》中的“奇”来自聂传庆的变态心理,《金锁记》中的“奇”来自七巧的乖戾的性格,《倾城之恋》中的“奇”来自突转的结局。《留情》、《红鸾禧》、《红玫瑰与白玫瑰》、《等》、《桂花蒸阿小悲秋》等小说写作时间靠后,作者已经放弃了曲折故事情节的经营,小说中的其人其事、其情其境都不再包含任何“奇”的成分,作者的风格转向了平实。然而不论在奇异中,还是在平凡里,张爱玲的目光始终专注于人性,在故事中发现着人性的规定。
《传奇》中展现的人生是书中不同人物的一份又一份的失败记录。故事开始时,主人公经常处于一个人生转折的当口,通过一段具体的人生故事,主人公在生活中的位置发生了变化,或是毁灭或是落到一个比原先更不堪的境地。有的时候,作者只是截取人生的一个或几个片段,人物的实际处境也许没有变化,但他们的内心感受已经与前大不相同。在记录这个过程的同时,作者似乎更注意人物的内心经历,当故事结束时,主人公原先对生活的信念以及自我感觉已经得到调整。从一种特定的对生活的意识到这种意识的被否定或被动摇,这是一个内在的圆周运动。在《传奇》中,这一运动注定地表现为一个下坠的过程:原先生活构想的幻灭、精神的萎缩、自信的丧失--这是作者为人物安排的认识必然(也就是人生真谛)的路径。通过自己的失败,他们认识到现实的肮脏、复杂、不可理喻。
《年轻的时候》中的潘汝良原本爱幻想,愿意戴着玫瑰色的眼镜看世界。沁西亚在他眼中是仙女,一连串实际接触后,他的梦一点点褪色,渐渐发现她不过是一个平平常常的女孩子,而且从她的婚姻,从她的重病中看见了人生的悲哀,于是他在这个女孩子的身上获得了启示,调整了对现实的意识,故事这样开始:“潘汝良读书,有个坏脾气,手里捏着铅笔,不肯闲着,老是在书头上画小人。”结尾是“汝良从此不在书头上画小人了,他的书现在总是很干净”。这说明他的幻想已经对现实作出了让步。
潘汝良对人生的体察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从旁观者的角色来进行的,《传奇》中的大多数人物是通过自身的遭际更深刻地洞察了现实的严酷与人生的悲剧性。《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并不像汝良那样浪漫,但她有自己的标准,有维护人格完整的自信,尽管她知道梁宅不合于她的标准,却抱有出污泥而不染的幻想。她的态度很现实,可是计划着好好把书念完,这仍然不失为她的一种理想。这个不算过分的期望在结尾时被彻底否定了--“她已经没有天长地久的计划”。这中间是她一点一点地发现对生活的预期与生活的真相之间的距离,而后一步一步地在现实面前退缩。由想念书到想嫁人,由想找一个理想伴侣到抓住乔其乔这个可能的机会,由想结婚到情愿只做情人,由情人到发现乔其乔的不忠之后仍然嫁给他,直至死了心为梁太太弄人,为乔其乔弄钱,这就是薇龙失败的历程。这里的每一次让步在过去都是不可想象的,当司徒协的出现逼着她向乔其乔的追求认输时,她已经觉得自己作出了重大牺牲,因为她感觉到乔其乔的不诚实,“也许乔其乔的追求她不过是一时高兴;也许他对任何女孩子都是这样的”。此时薇龙仍然有自信,有幻想,有希望:“的确,在过去,乔其乔不肯好好地做人,他的人生观太消极……幸而他现在还年轻,只要他的妻子爱他,他什么事不能做?”然而事实很快告诉她,这样的在她看来已经是缩小了的愿望依然是过分的。乔其乔不给她当好妻子的机会,只要她做情妇。“这和薇龙原本的期望相差太远了,她仿佛一连向后猛跌了十来丈远。”不幸的是,这还不是最后的一步,现实一定要把她的所有自信,把她的幻想剔除得干干净净才肯罢休。不愿意有一天变成梁夫人那样的人,这是薇龙的信念,是她的人格标准,最后的结果却是这一天来得那么快,她的情形甚至比梁夫人更糟。小说最后乔其乔、薇龙逛湾仔是惨淡的一幕,薇龙意识到自己的命运实质上跟妓女差不多:“怎么没有分别呢?她们是不得已,我是自愿的。”她在黑暗中伤心抽泣,然而也认命了。
张爱玲并不希望用这样一则故事来控诉社会,假如其中有社会批判因素的话,那也是它的副主题。张爱玲首先想在这险恶的环境,肮脏、复杂、不可理喻的现实背景之下展示人的脆弱、幻想的脆弱。她承认、接受这个现实。在她看来,现实原本就是如此,而这个现实是难以抗拒的,人只有节节败退,所以她无可奈何地哀叹:“总之,生命是残酷的。看到我们缩小又缩小的怯怯的愿望,我总觉得有无限的惨伤。”
的确,人的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是张爱玲小说的潜在主题。《传奇》中没有人对命运的胜利、理想对现实的凯旋,人的自信结果往往被证明不过是自负,受到现实无情的嘲讽。《心经》中的许小寒起初乐观自信,她以为能够把握住父亲,而把握父亲在她就是把握了自己。她骄傲,因为她能支配龚海立,可以捉弄波兰,广而言之,她自以为是现实,是周围环境的主人。故事的发展却证明她不过是现实的牺牲品,父亲的弃她而去摧毁了她良好的自我感觉,她哆嗦着预感到她已经“管不得自己了”。
《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佟振保“下定决心要创造一个‘对’的世界随身带着,在那袖珍世界里,他是绝对的主人。”事与愿违,他在生活中遇到的是一连串的“不对”。他总是想证明自己的主动,结果无往而不被证明他总是被动的,故事中出现的几个女人反复地向他提示,他做不了自己的主人。巴黎的第一次嫖妓在他是难堪的经验,“嫖,不怕嫖得下流、随便、肮脏黯败”。他的难堪在于他控制不了局面,不是他在导演,相反,他仿佛是被拉来客串一出不相干的戏。在与玫瑰的关系中,佟振保获得了做主人的自信,虽然这种自信以背地里的懊悔作代价,然而回国后王娇蕊的出现很快又把他从主人的位置上颠下来。当他们第一次接吻时,王娇蕊过于娴熟的姿态与他的发狠、他的自证自疑恰成对照。不由自主、失去控制的不是娇蕊,而是他,不论他怎样企图说服自己,也改变不了这样的事实,两人关系中这样的局面并不是他的初衷。在交谈中小心翼翼,躲到公寓外面回避与娇蕊的接触才是振保想做自己与环境的主人的有意识的努力,可是这种努力注定是徒劳。与孟烟鹂的结婚是振保做绝对的主人的又一次尝试,这个尝试显然又告失败,裁缝与烟鹂的通奸使他发现自己亲手铸造的世界依然又充满了“不对”,《红玫瑰与白玫瑰》于是成了一则主人公想做自己与环境的主人而不可得的故事。故事结尾回到了小说的开头,这是现在的佟振保--他“改过自新,又变了个好人”。一声长叹表示他的认命:大约不再愚妄地想创造一个“对”的世界,不再想做绝对的主人了。
假如说在佟振保的失败中除了对人以为可以主宰自己的愚妄的讥讽之外,也含着对佟振保陈腐观念、褊狭视野的嘲弄,那么《倾城之恋》的故事则是命运对人的自主意识的更彻底的否定。《倾城之恋》是《传奇》中唯一以大团圆结局收场的小说。白流苏如履薄冰地跨过了一段危险的情妇生涯,终于如愿以偿,得到了一桩她所向往的安全可靠的婚姻:范柳原不仅同她结婚,而且真正把她当做自家人--名正言顺的妻子--来对待。在旧小说中,在鸳蝴派作家的笔下,这可说是尽善尽美的结局--有情人终成眷属,不是吗?但是这样的处理与张爱玲对人生的理解背道而驰,她在表面的圆满之下发现了更深刻的不圆满。她要做的不是把结婚推向一个喜庆的高潮,而是冲淡轻松的气氛,让可能出现的高潮跌落下来。白流苏得到了想要的一切,与故事开始时的处境相反,她成了白公馆中人人羡慕的对象。“然而流苏还是有点惆怅”,这样的结局是她的爱对范柳原的征服吗?是她凭自己的魅力、手腕挣来的吗?正是在这里,一桩姻缘证明的不是人生的美满,反倒暴露出人生更大的缺憾。白流苏有过自己的努力,她声称能管得住自己,结果证明她管不住,她成了范柳原的情妇。成全了她的不是她的奋斗,而是凌驾于个人意志之上的命运,白、范结合证明的不是人对命运的主宰,而是命运对人的随意摆布。在这不可抗拒的命运的衬映之下,个人的努力简直可怜,范柳原在调情阶段对白流苏说:“……生死与离别,都是大事,不由我们支配的,比起外界的力量,我们人是多么小,多么小!可是我们偏要说,我永远和你在一起,我们一生一世都别离开,好像我们自己做得了主似的!”白流苏不相信,她以为那是花花公子油滑的遁词--在范柳原,那的确是遁词,然而这里面却包含着张爱玲理解的生命的真实。最后白流苏相信了:“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这正是使她惆怅的原因--一桩可靠的婚姻向她晓谕了更广大的人生的不可靠。在这种不可靠的面前,人比在婚姻中更显得无能为力。《倾城之恋》因此成为一个“苍凉的故事”。
《传奇》中的人物登场时,都在不同程度上抱着掌握自己命运的信念,以为自己的处境可以通过个人的努力得到改善,当故事的帷幕徐徐落下时,他们的信念全部夭折,不得不承认现实与环境的力量,这就是《传奇》中画出的一个又一个圆周。表现在外部的活动上,便是明知挣扎无益,便不挣扎了;执著也是徒然,便舍弃了--他们都是小人物,没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这样的圆周运动同时揭示了人的盲目与无知,那些人物抱有的信念与人生真相之间的巨大反差就是证明。人的盲目无知还反映在人物对现实的错觉中。《沉香屑:第二炉香》中的罗杰·安白登教授开着汽车,春风得意,“他深信绝对不会出乱子,他有一种安全的感觉”。其实他的身边危机四伏,充满不安。张爱玲有意识地强调他的安全感,用以与后面接踵而至的打击形成对比,教授很快就在追愫细的路上感受到“一片怔忡的庞大而不彻底的宁静”。安全感变成了恐怖感,他最后就在这恐怖感中自杀。这个结局冷酷地嘲弄了他在登场时的感觉。在《花凋》的结尾,张爱玲安排了一个同样强烈的对比。母亲替重病中的郑川嫦买了一双鞋:
她从被窝里伸出一只脚来踏在鞋里重新试一试,道:这种皮看上去倒很牢,总可以穿两三年呢。
她死在三星期后。
赫然的两个“三”将人对命运的盲目反衬得触目惊心,川嫦话中的“两三年”不过是随口出之,“她死在三星期后”并没有什么必然的道理,这样的排比倒是更清楚地显露了作者的用意,她要以此来宣示人生与人性的必然。
人的渺小、人的无知映照出现实的不可抗拒。现实在《传奇》中被赋予了多重的含意,在《花凋》中它是自然法则,在《沉香屑:第一炉香》中它是险恶的环境,在《倾城之恋》中它是重大的事变……但是张爱玲并不把现实看做外在于人的存在,人就是这样冷酷的肮脏复杂的不可理喻的现实的一部分。或者说,现实不仅是外部世界的真实,也是人性的真实,导致人物失败与挫折的不但是外来的苦难,更是人的与生俱来的情欲。外部世界诚然是不可理喻的,人是可以理喻的吗?葛薇龙“明明知道乔其乔不过是个极普通的浪子,没有什么可怕,可怕的是他引起的她那不可理喻的蛮暴的热情”。佟振保的周围不存在什么外部的压力,可是他的情欲一再地拖着他往下沉,他抵挡不住异性的诱惑实质上是抵挡不住自己情欲的诱惑,几个女人的出现不过充当了他的情欲的测度计。
在《金锁记》中,人物的情欲更是燃烧到可以点着火的程度,畸形的婚姻在姜家为七巧安排了一个特殊的位置,这个位置给了她觊觎黄金的机会,剥夺了她正常的情欲的满足。黄金欲膨胀得越大,恋爱欲也就被压抑得越厉害,然而压抑并不能使恋爱欲熄灭,越是压抑得厉害,情欲越是要通过反常的方式寻求出路,恋爱欲的得不到满足导致她对金钱的疯狂追求。起初她用黄金之梦来抵挡情欲之火,结果当情欲变相地借金钱之欲显形时,她丧失了人性。七巧与姜季泽的两次相遇是小说中最富于戏剧性的场面,平淡的对话下面激烈的内心搏斗,使它们充满一触即发的紧张。在第一个场面中,七巧“颤声说话”,“脸庞的下半部抖得像嘴里含着滚烫的蜡油,用尖细的声音逼出话来”,那些对僵尸一样的丈夫的刻骨怨愤的台词以及她对季泽由爱得不到手而生出的嫉恨,照彻她内心如焚的情欲。但是为了黄金之梦,她不得不按捺住情欲,她不敢明目张胆地追求季泽,只能恨恨地“低声道:‘我就不懂,我什么地方不如人?我有什么地方不好……’”在第二个场面中,七巧已经因为黄金的缘故,用捉迷藏式的浮薄的调笑包裹着内心的情欲过了十年,她终于听到季泽叫她“七巧”了:
季泽立在她跟前,两手合在她扇子上,他也老了十年了。然而两人究竟还是那两个人啊!他难道是哄她的吗?他想她的钱?仅仅这一念便使她暴怒起来了……
她甘心地把最后一个满足爱情的希望吹肥皂泡似地吹破了。为了黄金,过去她只能在双关的调逗语言中咀嚼一点爱情变味的渣子,现在她又用黄金欲制服最后一点爱情,对季泽的渴望是七巧人性的表征,泯灭了这点爱,她便彻底地套上了黄金的枷锁,变成地道的疯子。不幸她还是人母,是婆婆,她的疯狂不仅使自己走向毁灭,而且将身边的人拉来做陪葬。“三十年来她戴着黄金的枷锁,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她知道周围的人恨毒了她”,但是她无法控制她自己,只能让疯狂拖着她往绝路上走。疯狂来自黄金欲,而黄金欲变成盲目的破坏力量,又是爱情不得满足的直接结果。她要报复,报复她为黄金付出的代价,不顾一切,不择对象,情欲就是这样盲目地支配着人。
七巧是《传奇》中唯一的英雄,谁也没有像她这样在失望与绝望中仍然不停止最后的挣扎,情欲的力量在任何人身上都没有像在七巧身上那样具有如此巨大的破坏性。然而其他人也同样为情欲支配着,尽管情欲并不总是表现得那么强烈。情欲的本质在于它的非理性,而非理性经常与下意识联系在一起。许多论者都注意到《传奇》对非理性与潜意识的表现,这种表现正是通过对人的情欲的盲目性的展示来进行的,或者说,张爱玲对情欲的力量的渲染正是对人的非理性、人的潜意识的强调。在那些篇幅较长、对人物命运做了正面交待的小说中,盲目的情欲始终是导致悲剧的一个重要因素。葛薇龙、佟振保、白流苏、许小寒等人起初之所以有那种掌握自己命运的幻想与自信,是因为他们潜在的生存欲望欺骗了他们,生存欲望改变了现实的形貌,使他们一厢情愿地对待世界,对待自己。就连在《花凋》这篇人物命运与情欲力量并没有直接关联的小说中,张爱玲也不失时机地表现人的情欲的盲目,正是想活下去的顽强欲望使川嫦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她以为还能活很久。
人逃脱不了情欲的支配,这就是张爱玲发现的人性的规定。她经常以情欲,以非理性来解释人物的失败与挫折,这使《传奇》与旧小说,与鸳蝴派小说严格地区分开来。旧小说用因果报应的迷信来说明一切,而造成悲剧的原因在鸳蝴派小说中不是一个坏到极点的恶人,便是偶然的巧合。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按照叔本华的观念,将悲剧分为三种,第一种是“由恶之人,极其所有之能力以交媾之者”,第二种是“由于盲目之命运者”,第三种是“由于剧中人物之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者,非必有蛇蝎之性质与意外之变故也”。在王国维看来,第三种悲剧展示了一种必然:“但由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彼等明知其害,交施之,而交受之,各加以力,而各不任其咎……彼示人生最大之不幸,非例外之事,而人生之所固有故也,若前二种之悲剧,吾人对蛇蝎之人物,与盲目之命运,未尝不悚然战栗,然以其罕见之故,犹悻吾生之可以免,而不必求息肩之地也。但在第三种则见此非常之势力,足以破坏人生之福祉者,无时而不可坠于吾前,且此等惨酷之行,不但时时可受诸己,而或可以加诸人,躬丁其酷,而无不平之可鸣,此可谓天下至惨也。”假如说旧小说、鸳蝴派小说所写悲剧属于前两种的话,张爱玲在《传奇》中希望表现的就是第三种悲剧--无时不在,无所不在,而又无不平之可鸣的“至惨”悲剧,而“不得不然”的人物之位置则是不同人物的情欲交互作用的结果。每个人都有情欲,悲剧的因素不仅存在于外界的威胁,更在于人的本性之中,因此悲剧不是人们可能会遇到的偶然,而是人人必将面临的必然。情欲与生命相始终,悲剧因此无休无止,不断袭来,一步一步将人引入更加悲惨的境地。人之不幸,诚如老子所说:“吾所以有大患者,唯吾有身。”不幸是注定的、与生俱来的,《传奇》中故而弥漫着宿命的气息。
人生是残酷的,人性的真相是可怕的。一般的人没有勇气面对这幅可怕的图景,假如偶然的机缘使人们从一己的欲望里与偏见中跳出来瞥见这幅图景,对生命的本相有所了悟,他们也不可能长久地停留在这一点上--生命的可怕与恐怖是一般人的意识难以负荷的,人们只有回到纷扰的现实去,埋头于眼前的琐事之中,借助习惯的力量忘却生命的恐怖。对于张爱玲,人生的悲剧是永恒的、无涯的,因此往远看,朝透里想,万事皆悲,看看眼前,看看周围,人才感到还有可为,还能找到一点快乐。她的人物都在眼前的欢乐中寻找着避难所。葛薇龙在湾仔看到的是“无边的荒凉,无边的恐怖”,“她的未来也是如此--不能想,想起来只有无边的恐怖,她没有天长地久的计划,只有在这眼前的琐碎的小东西里,她的畏缩不宁的心能够得到暂时的休息”。
张爱玲在《传奇》中多次通过人物突出了人的不敢想、不能想,以说明直面人生给人带来的重压。这种意识并不是人物自觉意识到的,《桂花蒸阿小悲秋》中的女佣人阿小只是在一个偶然的场合里突然朦胧地感觉到一阵恐怖和悲哀。她自己也未必能解说得清,因为没有什么具体的、直接的原因,她只是为她自己突如其来的疯狂的自由所惊惧,“心里模糊地觉得不行,不行!”四周无人的清静吓住了她,自由吓住了她,通常她的时间都是由喧闹忙碌来填满的,她总是有事情可做,总是在人丛中,有具体的琐事可谈,现在她是一个人,她有时间思想了!她马上感到了空虚,感到荒凉,一个个忙碌的日子是容易对付的,而阿小此刻面对的是混沌的人生的重压,她要把孩子领回来,有孩子在身边,她就不再“自由”,不再有无边际的胡思乱想的机会--她的思绪找到了具体实在的寄托。小说结束时,阿小已经完全恢复了平静,她打听楼上的新娘夜里如何寻死觅活地打闹,抱怨别人将瓜壳果皮乱扔,脑子里不再留下空隙--一旦回到日常习惯的轨道上,她便有了一种安全感。《封锁》中电车车厢里的一群人偶然暂时地脱离了日常习惯的轨道,一时无事可做,看见一个人在看用来包着包子的报纸,马上群起效仿,“看报的看报,没有报的看发票,看章程,看名片,任何印刷物都没有的人,就看街上的市招,他们不能不填满这可怕的空虚,不然,他们的脑子会活动起来,思想是一件痛苦的事”。
人性是盲目的,人生因盲目而残酷。在《传奇》中,这一切表现为现实的肮脏、复杂、不可理喻,假如不是被情欲或是虚荣心所欺瞒,人对现实的了解实质上仅限于这一点:生活即痛苦,人生即是永恒的悲剧,这就是人所能达到的最高的,也是真正的认识。对于张爱玲,认识人生就是认识人生的悲剧性,但是,获得这种认识,既不给人带来安慰,也无助于现实处境的改变,相反,它将人置于幻灭、空虚的重压之下。《传奇》中的故事因此成了没有多少亮色的无望的彻头彻尾的悲剧。《琉璃瓦》、《红鸾禧》等几幕短小的喜剧只是这个悲剧的补充。张爱玲曾经这样议论《金瓶梅》、《红楼梦》:“只有在物质的细节上,它得到欢悦……仔仔细细开出整桌的菜单,毫无倦意,不为什么,就因为喜欢--细节往往是和美畅快、引人入胜的,而主题永远悲观,一切对于人生的笼统观察都指向虚无。”在某种意义上,这倒也适用于对《传奇》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