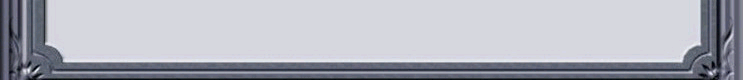第八章 卖洋文,谈中国人
但她正年轻,年轻人的伤口是容易愈合的。她不是学成归来,但也说不上是铩羽而归,天高地广,前面的路也正长。回上海的途中,她也许正是这样的心境,在轮船上,她已经同炎樱谈论着上海的繁华摩登,想象着将要成就的一番事业,如同一切刚刚迈出校门的年轻人一样,怀着即将踏入社会的莫名的兴奋。她有过许多梦想,但在她的日程表上,那都是大学毕业以后的事,现在大幕提前拉开,她也一样地跃跃欲试,何况这舞台是她感到亲切而又刺激的上海。
那时的上海非香港可比,它是国际性的大都市,是东方的巴黎。在香港人的心目中,上海滩霓虹灯闪烁,大高楼林立,好似一个繁华梦,一如今日上海人心目中的香港。而香港弹丸之地,不过是英国治下的边陲小城。张爱玲九岁来到上海时就对这里的摩登、洋派喜之不胜,其后十年寒窗,一墙之隔,她无暇尽情领略这都市风光,一方面也不免习而相忘。在香港呆了三年,有了一番比较,隔着时空的距离,对大上海的记忆分外诱人,也分外明晰。不仅是一家挨一家的店铺,不仅是各种各样的时髦,这里更有她感到亲切的上海人。香港人是犯冲、刺激、不调和、不平衡的,上海人则世故、聪明(即便是小聪明)、有根底、有他们的一套完整和谐。有这份世故、这份聪明的人才能懂得她张爱玲,张爱玲愿意把他们设想成她的读者。
回到上海,张爱玲同她姑姑住在一起,那是静安寺赫德路192号一幢公寓的6楼65室。以后她很长时间都是和姑姑一同生活。自从出了张家的门,张爱玲几乎就和张家的人断了来往。她一个人住在外面,小时候与她一同嬉戏的弟弟几次去看她,她也显得很是冷漠张的弟弟张子静在张走红后的那段时间里写过一篇《我的姊姊张爱玲》,想是当时张已成新闻人物,编辑向他约的稿。文中除记琐事之外,当然要突出张的才。他在张面前显然感到自卑,至于张对他冷漠,除了因其不争气看不起他以及对张家人无好感之外,也是她的性情所致。,尽管她在《私语》、《童言无忌》等文中提到这个弟弟时颇有做姐姐的一份亲切。她与母亲的关系也相当疏远,唯独与这位姑姑还算亲近。她姑姑虽是张家人,与嫂嫂的关系却比同她的亲哥哥的关系好。姑嫂二人曾一同出洋留学,张爱玲母亲离婚后两人有很长时间住在一处做伴,张爱玲有一次挨父亲打骂离家出走,也是这位姑姑出面去说情,结果说情不成,张的父亲反出手打了她。张爱玲戏称“她对我们张家的人没有多少好感——对我比较好些,但也是我自动沾附上来,拿我无可奈何的缘故”。
这位姑姑走的是职业妇女的路,似乎一直在外国人的机构里做事,有一个时期还做过电台的播音。她一直未嫁,是个“单身贵族”。张的姑姑一直没有离开祖国大陆,独身数十年后,却在晚年放弃了独身生活。80年代张在祖国大陆再度走红,提到她的文章多起来,《新民晚报》上曾有文章也顺便谈到读者于她散文中熟悉了的这位姑姑的暮年婚姻。老姑娘的身份看来并没有影响到她的性情,使之变得孤僻、冷漠。从《流言》中对她的描述推想,她的脾气要比张的母亲好得多,随和、平易、不乏幽默感。张爱玲与她有近十年的时间里朝夕相伴,而两人相处得甚为融洽,有一种亲切的戏谑的气氛。张常常“押着”她读自己的作品,又喜向她“嘀嘀咕咕”地“唠叨”家常话,她也是张遇事可以与之商量,帮着拿主张的唯一一位“家里人”。
张爱玲称她姑姑是“轻度知识分子”,“说话有一种清平的机智见识”,在她的散文中姑姑是出现频度最高的人物之一,而且每出现必出以亲切的、会心而笑的笔调。姑姑和炎樱似乎组成了张日常世界中轻松愉快那个部分。她在《姑姑语录》等文中流露出的欣赏之意,一望而知。对姑姑的欣赏恐怕也包含了对姑姑选择的生活方式的欣赏,那种生活方式的要点是,自己挣钱自己花,自己管自己,自由自在,住在公寓里,清清静静,没有牵牵绊绊的人事纠缠。总之是一种清爽、利落的生活。当然,要做到自食其力,才有这一份开心和理直气壮。
张爱玲一直渴望做一个自食其力的人,后来她直白地说过:“用别人的钱,即使是父母的遗产,也不如用自己赚来的钱来得自由自在,良心上非常痛快。”并不是每一个生在高门大户里的人都会生出这样的念头,但是张爱玲的以往的遭际、眼下的处境、她的敏感、她的心性,都使她对这条道矢志不移。如今学生时代已告一段落,她当然不愿向家里伸手,再去看人眼色,再去品尝她已尝够了的寄人篱下的滋味——该是她自己养活自己的时候了。靠什么谋生呢?也许她可以在教会学校里当一名教师,像《封锁》中的翠远;也许她可以到某个机构里做个职员,像她的姑姑;也许她面对的可能性比我们所能想象的要多得多。但是她后来成了那样一位杰出的作家,那样一个传奇性的人物,以致其他的种种可能性似乎统统没有存在过——就好像命里注定只能选择作家的饭碗。不管怎么说,张爱玲决定用笔来谋她的衣食,她开始卖文了。
她最初卖的是洋文。头一个对她大加赏识、为她戴上“天才”冠冕的是一位洋人。
1941年10月,上海出现了一份英文月刊,刊名《二十世纪》(The XXth Century)。主编克劳斯·梅奈特(Klaus Mehnert)是德国人,当过驻苏联记者,在美国的大学里教过历史,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来到上海。上海是当时尚存的最后一个国际性大都市,还没有被交战国任何一方完全控制,敌对情绪也不像别处那样严重,梅奈特便想借这夹缝中的真空地带来实现他的新闻自由,对时事战局作公正客观的分析报道。虽然如此,《二十世纪》却是一份“软硬兼施”的综合性杂志,时事报道之外,也有小品、风光旅游、书评影评之类。它的主要对象是羁留亚洲的西方人,尤以上海外国租界为重点。它的作者亦是五湖四海,创刊号各文章的撰稿人便分属八个国家。
1942年年底,梅奈特从来稿中发现了一个陌生的名字Eileen Chang,她送来的是一篇万字长文,题为Chinese Life and Fashions(《中国人的生活和时装》),并配有十二幅作者本人所绘的发型、服饰插图。此文行文流畅典雅,从容自如,有英国小品文的风致,不仅见出对中国人生活和服装的独到见识,而且见出不凡的英文造诣,加上简洁有趣的插图,真是图文并茂。梅奈特一见之下大为惊喜,很快将其刊登在1943年1月出版的《二十世纪》第4卷第1期上,并在编者例言中向读者郑重推荐,誉作者为“极有前途的青年天才”。这个“天才”就是张爱玲,而此文就是后来收入《流言》的《更衣记》的底本。
张迷读张爱玲的散文,读到《中国人的宗教》,起首一句是“这篇东西本是写给外国人看的”,没了下梢,细心的人不免就有几分疑惑,收进《流言》以前,此文是登在《天地》月刊上的,难道洋人会去读这中文杂志?答案就在《二十世纪》,事实上《流言》上的好些文章最初都是以英文形式在这里发表的。
张爱玲对文字有特殊的爱好,也有过人的感受力,对方块字如此,对蟹行文字也是一样,《天才梦》中说到她对色彩浓重、音韵铿锵的字眼的喜爱,“珠灰”、“黄昏”、“婉妙”之外,她也举出splendour、melancholy这样的英文词汇。
上中学,教会学校对英文的重视当然更在中文之上,校刊《凤藻》既登中文,也登英文的习作,张爱玲的英文习作Sketches of Some Shepherds(《牧羊者素描》)、My Great Expectations(《心愿》)就登在上面。港大三年,张爱玲苦修英文。为了让英文写得地道纯熟,狠狠心三年没用中文写东西,甚至通信用的也是英文。留过洋的姑姑对她的英文功底很是佩服,说她“无论是什么英文书,她能拿起来就看,即使是一本物理或化学”。物理、化学张爱玲不喜欢,她是揣摩里面的为文之道。过人的悟性加上刻苦的砥砺,成就了张爱玲一手漂亮的英文。她姑姑的评价是,她的英文“好过中文”。迷张的人听了此话当然不会怀疑她姑姑对她英文评价过高,但却不免要为《传奇》、《流言》中那花团锦簇的文字抱屈。
不管怎么说,此时英文张爱玲正用得顺手,而单从“卖文”的角度讲,英文杂志的稿费自然比中文杂志高得多。《中国人的生活和时装》发表后颇受好评,这信息自会通过梅奈特反馈到张爱玲那里,而梅奈特也肯定要向她约稿,于是张爱玲一鼓作气,又为《二十世纪》写了好几篇文章。写得最多的是影评。1943年底的5月号上登了她的Wife, Vamp, Child(《妻子,荡妇,孩童》,即《借银灯》),评的是《梅娘曲》和《桃李争春》,自此开始到1943年底,几乎每一期《二十世纪》上都有张爱玲的影评文字:6月份题为The Opium War(《鸦片战争》),评的是《万世流芳》。7月份的一篇没有题目,仅在On the Screen(影评)栏下评了《秋之歌》、《浮云遮月》两部影片。
8、9月份《二十世纪》出的是合刊,张以Mother and Daughtersinlaw(《婆婆和媳妇》)为题评了《自由魂》、《两代女性》、《母亲》等三部片子。10月份的一篇又是无题,评的是李丽华、严俊、王丹凤主演的《万紫千红》和刘琼自编自导自演的《回春曲》。10月的影评题为China Educating the Family(《中国的家庭教育》),这就是后来收入《流言》的《银宫就学记》。
张爱玲的影评本身就是上好的小品文字,不过梅奈特更推崇的还是那些大块的文章。1943年6月,张爱玲发表Still Alive(直译是“依然活着”,中文本更名为《洋人看京戏及其它》),梅奈特在编者按中指出,元月份的张文“备受称赞”,而张爱玲的过人之处在于“她不同于她的中国同胞,她从不对中国的事物安之若素;她对她的同胞怀有的深邃好奇心使她有能力向外国人阐释中国人”。这年12月,张爱玲又在《二十世纪》发表Demons and Fairies(直译为“神仙鬼怪”,中文本即《中国人的宗教》),在刊于《二十世纪》的文章中,该文最长,它也是张爱玲“向外国人阐释中国人”的最具雄心的尝试。因为题目太大,处理起来似乎不像《中国人的生活与服装》那样举重若轻,但仍是一样轻灵的风格,而且时而淡言微中。梅奈特在编者按中又加推荐:“作者神游三界,妙想联翩,她无意解开宗教或伦理的疑窦,但却以她独有的妙悟的方式,成功地向我们解说了中国人的种种心态。”
《神仙鬼怪》是张爱玲在《二十世纪》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此后她的英文写作便暂时告一段落,直到1952年离开祖国大陆。所以她卖洋文只卖了一年。不过读者万勿以为她在这段时间里专卖洋文,事实上到1943年底她已用中文发表了好几篇重要的小说。像现在这样从张爱玲的创作时间表上把她的英文作品提前集中起来,除了其他的便利之外,还因为它们隐然有一个共同的主题——中国人。谈京戏实际上是要“用洋人看京戏的眼光来看看中国的一切”,说的是已成为思想背景的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原题“依然活着”就出自文中这样一句话:“只有在中国,历史(历史在这里是笼统地代表着公众的回忆)仍于日常生活中维持着活跃的演出。”评电影,下力最多的,也还是评中国人,《借银灯》里声明说“我看的不是电影而是电影里的中国人”。谈时装,配上十二幅插图,似乎要做“专论”了,但是她之感兴趣,还是因为衣中有人,呼之欲出,她不能不联系到中国人的生活、中国人的心理、中国人的趣味。
大体上讲,张爱玲走的还是林语堂的路线,用轻松而饶有风趣的文字向外国人介绍中国文化、中国人的生活。这一半也是为刊物的性质所决定,《二十世纪》的对象是租界的外国人,对于身边这个纷攘、神秘、滑稽的国度自有了解的兴趣,但是他们并非汉学家,了解也是以初级教科书的程度为限,若诉之以纯文艺,会有多少读者就十分可疑,所以《二十世纪》像大多数西文杂志一样,不愿给诗歌、小说之类留下一席之地。梅奈特推崇张爱玲的天才,却不道她“生来就是写小说的”,亦无缘得见她这方面的才华——张爱玲这一时期的小说都是用中文写的。
正是世界大战战况正烈的年头,中国的行情似乎又看涨了——不是在租界,是在中国的那些西方盟国。世界大战改变了世界原有的格局,中国这个素来被欺侮的弱国忽然间成了反轴心国列强的盟友,贫富强弱的悬殊暂时被搁置到一边,大有同仇敌忾、共赴胜利的气象。英、美诸国的民众渴望了解盟友的情况,介绍中国的文字一时间多了起来。林语堂在美国标榜中国的哲学,萧乾、叶君健在英国或报道中国的战况,或描摹中国乡间百姓的苦难和他们的勤劳善良,加上这之前赛珍珠那部颇为流行的《大地》,西方的传媒多少在改变着西方人心目中原有的那个滑稽可笑的中国人形象,而战时的气氛似乎也使西方人乐于接受现在这个正面的中国人形象。在国内,日本人的侵略使国人的爱国主义情绪空前高涨,“五四”时期对传统文化的激烈抨击至此全然偃旗息鼓,代之而起的是对中国人传统美德、中国文化优异面的肯定和褒扬。可是上海租界的特殊地位却使它于国内外的一片大气候中保持了它的特殊,而这特殊正好容许张爱玲以一种在别处不允许有的从容超脱的态度品评中国人、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她笔下浮现的国人形象虽不可直指为“丑陋的中国人”,但轻松调侃的语气见出这里面更多的是批评针砭,这是无可怀疑的。
《洋人看京戏及其它》由京戏的热闹说到中国人生活的拥挤,落脚在中国人因缺少私生活带来的毛病:“就因为缺少私生活,中国人的个性里有一点粗俗。‘无事不可对人言’,说不得的便是为非作歹。中国人老是诧异,外国人喜欢守那么些不必要的秘密。不守秘密的结果,最幽微亲切的感觉也得向那群不可少的旁观者自卫地解释一下。这养成了找寻借口的习惯。自己对自己也爱用借口来搪塞,因此中国人是不大明了他自己的为人的。”
《更衣记》写到古中国服饰上繁复无谓的点缀,转而讥刺中国有闲阶级的趣味:“这样聚集了无数小小的有趣之点,这样不停地另生枝节,放恣,不讲理,在不相干的事物上浪费了精力,正是中国有闲阶级的一贯态度。唯有世界上最清闲的国家里最闲的人,方才能够领略到这细节的妙处。制造一百种相仿而不犯重的图案,固然需要艺术与时间;欣赏它,也同样地烦难。”
《银宫就学记》原名《中国的家庭教育》,谈的是两部“富有教育意味的电影”,道出的却是中国式教育的荒唐。《渔家女》的男主人公是个时代青年,也是时代青年习惯并喜爱的那种形象,张爱玲则张见了他骨子里的“中国人的脾气”:男主人公声称他不喜受过教育的女人,但却情不自禁地要教渔家女认字。“他不能抵抗这诱惑。以往的中国学者有过这样一个普遍的嗜好:教姨太太读书。其实教太太也未尝不可,如果太太生得美丽,但是这一类风流蕴藉的勾当往往要到暮年的时候,退休以后,才有这个闲心,收个‘红袖添香’的女弟子以娱晚景,太太显然是不合格了。”男主人公不过是借了编导“稀有的恬静风格”提前(年纪轻轻)温习中国多少代读书人的桃色梦。“‘渔家女’的恋人乐意教她书,所以‘渔家女’之受教育完全是为了她先生的享受。”一石二鸟,夹枪带棒,中国读书人的恶习被抖搂出来示众,那位编导也被挖苦得惨了。
《中国人的宗教》谈的是中国人的信仰,结果发现的却是中国人并无真正的信仰,有的只是怀疑主义:
就因为对一切都怀疑,中国文学里弥漫着大的悲哀。只有在物质的细节上,它得到欢悦——因此《金瓶梅》、《红楼梦》仔仔细细开出整桌的菜单,毫无倦意,不为什么,就因为喜欢——细节往往是和美畅快、引人入胜的,而主题永远悲观。一切对于人生的笼统观察都指向虚无。
世界各国的人都有类似的感觉,中国人与众不同的地方是:这“虚空的空虚,一切都是虚空”的感觉总像个新发现,并且就停留在这阶段。一个个中国人看见花落水流,于是迎风洒泪,对月长吁,感到生命之暂,但是他们就到这里为止,不往前想了。
受过教育的中国人认为人一年年地活下去,并不走到哪里去;人类一代一代下去,也并不走到哪里去。不管有没有意义,反正是活着。我们怎样处置自己,并没多大关系,但是活得好一点是快乐的,所以为了自己的享受,还是守规矩的好……不论在艺术里还是人生里,最难得的就是知道什么时候应当歇手。中国人最引以自傲的就是这种约束的美。
因为“六合之外,存而不论”,中国人的世界终成为一个拥挤的人的世界,“在古中国,一切肯定的善都是从人的关系里得来”,“五四”大潮一来,中国人崇信的这些基本关系都被动摇,“中国人像西方人一样变得局促多疑了。而这对于中国人是分外痛苦的,因为他们除了人的关系之外没有别的信仰”。
这种信仰使中国人注定要把维护和谐的人际关系当做表现人之“性本善”的唯一舞台,“一切反社会的,自私的本能都不算本能。这样武断的分类,倒很有效,因为谁都不愿你说他反常”。
“然而要把自己去适合过高的人性标准,究竟麻烦,因此中国人时常抱怨‘做人难’。‘做’字是创造、模拟、扮演,里面有吃力的感觉。”
……
这些文章中颇多可圈可点的妙语,在在反映出张爱玲对中国人的生活的洞见,而由一个二十出头的青年女子道来,自然要让梅奈特啧啧称奇。然而张爱玲的过人之处并非她对中国文化作了如何了不得的探本的分析,而在于她以其慧质灵心从日常生活的幽微处张见了现代中国人身上蠢动着的那个传统中国人的形象;她的材料不是儒、释、道的哲学,而是大众文化,中国人日常的行为方式。
能有如此的洞见,张爱玲的本钱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她的家庭背景,一是她受的西式教育。她的身世使她谙熟古老中国的生活方式,她对传统文学艺术的喜爱使她的举证左右逢源;她受的西方式教育则使她有了另一个支点,跳到圈外,借洋人的眼光对中国人的生活做一番反省。两个方面缺一不可,没有前者,就没有她鲜灵、生动、活泼的感觉——租界的洋人读罢或者但觉有趣,熟知张爱玲的人读了却要悟到里面非个中人不能道的奇特感受;没有后者,张爱玲或者会像她的大多数同胞一样,对中国的一切习而相忘、浑然不觉——至少她要在很大程度上失去她现在保有的那重有利的旁观者身份。除了梅奈特说到张外来者的旁观眼光之外,沦陷时期颇为活跃的一位散文作家周班公对张的小说、散文都有类似的印象,称张的笔法虽在模仿《红楼梦》、《金瓶梅》,他仍模糊地觉得“这是一位从西方来的旅客,观察并且描写着她喜爱的中国”,并说这一点使他想起赛珍珠。见《〈传奇〉集评茶会记》,载《杂志》,1944年9月号。
或许就是这重身份让她的这组谈论中国人的文字掺进了更多惊异好奇的成分——这里更多的是对中国人生活的不失好奇心的张看,而不是价值的评判。虽然挑出了中国人的不少毛病,有挖苦,有针砭,但是见不到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沉痛,也没有曹禺、巴金“吾与汝偕亡”式的愤怒,重要的是了解、知道、懂得——好奇心总是导向“知”的。
然而并非单单是好奇心的满足。或者说,对于张爱玲,好奇心当中自有严肃的因子。从给洋人看的《依然活着》到给国人看的《洋人看京戏及其它》,大堆的反语当中就冒出了一段箴言式的劝导性文字:“多数中国人爱中国而不知道他们所爱的究竟是一些什么东西。无条件的爱是可钦佩的——唯一的危险就是:迟早理想要撞着了现实,每每使他们倒抽一口凉气,把心渐渐冷了。我们不幸生活于中国人中间,比不得华侨,可以一辈子隔着适当的距离崇拜着神圣的祖国。那么,索性看个仔细罢……有了惊讶与眩异,才有明了,才有靠得住的爱。”仔细地看了,她就不能不看到中国人的种种毛病。几十年后与人谈起鲁迅,她最推崇的便是鲁迅对中国人性格中的阴暗面和劣根性的暴露,而在她看来,后来的中国作家在提高民族自信心的旗帜下,走的都是“文过饰非”的路子,没有批判,只有褒扬。水晶:《蝉——夜访张爱玲》。
那么,有了惊异,有了明了,有了对中国人劣根性的清醒意识之后,她还有“靠得住的爱”吗?或者“爱”这个字眼还过于简单,她没有指向未来的中国梦,没有“改造国民性”抱负,有的是“了解的同情,同情的了解”,有的是复杂的爱恨情结,剪不断、理还乱的难以明言的依恋。
仿佛是要为这情结,为这依恋做注脚,1947年《传奇》增订本问世之际,张爱玲写下了一篇《中国的日夜》。这是她买菜路上采下的一个个不相干的镜头——又一回“道路以目”。穿了打补丁棉袍的小孩、抱着胳膊闲看景致的小贩、敲着竹筒沿街化缘的道士、向亲戚絮絮数落小姑的女老板……最寻常的中国城市的街景,最寻常的中国人,最寻常的中国生活的节奏,她的内心却有异样的悸动,陌生、震惊,然而没有厌倦憎恶,有的是异样的亲切:“我真快乐我是走在中国的太阳底下。我也喜欢觉得手脚都是年轻有力气的。而这一切都是连在一起的,不知为什么。快乐的时候,无线电的声音、街上的颜色,仿佛我也都有份;即使忧愁沉淀下去了也是中国的泥沙。总之,到底是中国。”
张爱玲写作向来斟词酌句、惨淡经营,这一次,不相干的街景却让她以令她自己都感到吃惊的速度写下了一首看似更不相干的诗:
中国的日夜
我的路,
走在我自己的国土。
乱纷纷都是自己人;
补了又补,连了又连的,
补钉的彩云的人民。
我的人民,
我的青春,
我真高兴晒着太阳去买回来,
沉重累赘的一日三餐。
谯楼初鼓定天下;
安民心,
嘈嘈的烦冤的人声下沉。
沉到底……
中国,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