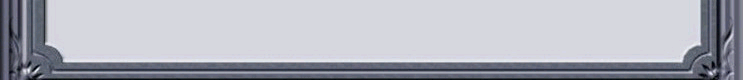第六章 港战中的印象
香港是英国人的殖民地,香港的抗战是英国人的抗战。开战的消息在这里并没有像在内地那样激起高涨的民族情绪。张爱玲是个冷眼的旁观和体验者,像她周围的大多数人一样,映现在她眼中的战争不是它的政治色彩、民族色彩,而是它的灾难性质。在这个意义上,战争如同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
英军的一座要塞挨着港大,日军的飞机来轰炸,她和同学们都躲到宿舍最下层黑漆漆的箱子间里,听着外面机关枪响着如同雨打残荷,有说不出的惶恐和恍惚。几天禁闭过后,港大停止了办公,有地方可去的同学都走了,张爱玲随了一大帮同学到防空总部去报名,领了证章参加守城工作。此举是出于不得已,她倒不是要做志愿者:学校已关门大吉,离开学校她便无处可去,吃住都无着落。可是领了证章也不见得就得了保险,战事期间到处都乱作一团,像她这样的防空团员只能分到米和黄豆,没有油,也无燃料。张爱玲原本不善自理,更未对付过这种日子,也许是无从措手,也许是懒得动手,她接连两天什么都没吃,“飘飘然去上工”。
她对饥饿的体验毕竟是肤浅的、次要的,更重要的是她体验到了人生的安稳是何其脆弱。在灾难的背景下,所有的一切都失去了确定性。她回忆围城中的感受时这样描述道:“……什么都是模糊,瑟缩,靠不住。回不了家,等回去了,家也许已经不存在了。房子可以毁掉,钱转眼可以成废纸,人可以死,自己更是朝不保暮……无牵无挂的空虚与绝望……”——仍然是一种不安全感,只是它现在已不仅仅是建立在纯粹个人遭际的基础上,而获得了更广阔的视景。同时,由于战争带来的破坏与一己环境中的不和谐相比更是无从捉摸、无从控制的,因此不安全感也就来得分外强烈。就在这样的感受中,张爱玲升腾起自己关于个人命运的玄思:社会、历史的运作有如天道无亲,个人是渺小而微不足道的,他被拨弄于不可知力量的股掌之间,根本无从掌握自己的命运,自觉的努力、追求“注定了要被打翻的吧”?面对一己人生的沉浮变幻,人唯有茫然、惘然。
这样的想法后来成为她下意识的一部分背景,往明确里说,也可以讲是她对人生的稳定把握的一部分。战争、社会性的运动等等非个人的人类行为在她皆表现为惘惘的威胁,无情地侵入个人的世界,不由分说地将个人裹挟而去。此后张爱玲还将通过自己的经历、见闻和感受一再向自己印证这样的认知。比如,1949年以后到她离开祖国大陆这段时间里她的所见所闻所感,就肯定再次对她证明了惊天动地的变革面前,个人世界的安稳是如何难以守护。所以她的小说尽管大多不是社会性的,然而超出那些沉醉于封闭世界的浑然不觉的人物的视界之外,读者总能隐约意识到故事后面是一个风雨飘摇的世界。不管后来她如何深化和丰富她的认知,她的这种忧患意识首先是在港战中获得的,在《倾城之恋》的结尾,她借着对白流苏命运的议论,将她在港战中的感受直白地表达出来。
可以让她对个人命运产生惶惑、迷惘之感的一个具体事件是佛朗士教授的死——这是港战期间对她触动较大的一件事。佛朗士同其他英国人一样被征入伍,张爱玲还记得开战以前,每逢志愿兵操演,这位豁达幽默的教授总会带几分调侃拖长了腔调通知他的学生:“下礼拜一不能同你们见面了,孩子们,我要去练武功。”开战后的一个黄昏,佛朗士回到兵营里去,一边走一边思索着什么问题,没听见哨兵的吆喝,哨兵便开了枪。令她感叹的还不是佛朗士死在自己人的枪下,决无“求仁得仁”的壮烈,而是这位有几分玩世的教授其实对保卫殖民地并无多少热情,他之入伍亦无多少“志愿”的成分,不过是无可无不可的随波逐流,不欲有异于众而已,谁知竟莫名其妙送了命。换了坚定的历史唯物论者,或许会以必然、偶然、不可免的牺牲之类来解释此事,但是对于张爱玲,理论是从来没有说服力的,她不能不感到人类行为的荒诞、不可理喻,也不能不从佛朗士的命运去怀疑世上是否真有所谓因果的法则。不知是出于有心还是无意,她述及此事时用了“枪杀”一词(“我们得到了佛朗士教授被枪杀的消息”),或许她觉得这个字眼犹能传达出某种荒诞感,以及这意外事件中包含的人生讽刺?无论如何,此事给她印象之深是显而易见的。她颇有几分动情地感慨道:“想不到‘练武功’竟送了他的命——一个好先生,一个好人。人类的浪费……”除了对胡适之,我们还很少看到她对谁有这样的追念之情。
但是张爱玲在更多的时候当然仍是保持着她冷眼旁观的一贯作风,她将冷静而挑剔的眼光投向周围的人,同时也投向自己,于众人的种种反应与行为中张看着人性。她发现了人性的盲目和偏执,人人都缩在自己封闭的壳里,对现实的处境浑然不觉:“我们对于战争所抱的态度,可以打个比喻,是像一个人坐在硬板凳上打瞌睡,虽然不舒服,而且没完没结地抱怨着,到底还是睡着了。能够不理会的,我们一概不理会。出生入死,沉浮于最富色彩的经验中,我们还是我们,一尘不染,维持着素日的生活典型。”她的同学因战时没有相应的时装而犯愁;飞机在天上扔炸弹,门洞子里躲空袭的人在无谓地争闲气,谁都振振有词;一个受轻伤的年轻人因暂时成了众人注意的中心而洋洋得意;空袭警报刚刚解除,人们又“不顾命地轧电车,唯恐赶不上,牺牲了一张电车票”……落在她眼中的这一切都让她相信战争并不带来真正的震荡,人们一边本能地惶恐着、惊怕着,一边对情势的严重性毫无意识,虚荣心、贪小利、自我中心等这些世态剧中最常出现也最易受到嘲讽的内容在战争的灾难背景下仍然若无其事地继续搬演着。
张爱玲亦是她平日的疏离态度。她经历的最惊险的一幕是有一次飞机扔炸弹,轰然一声似乎就掼在头顶上,她将防空员的铁帽子罩住了脸,黑了好一阵才知自己没有被炸死。她是防空员,但那身份与她似是不相干的,她称自己是个“不尽职的人”,她还是在局外。防空员驻扎在冯平山图书馆,张爱玲在这里找到一部《醒世姻缘》,“马上得其所哉,一连几天看得抬不起头来”。图书馆房顶上架着高射机枪,成了日军的轰炸目标,炸弹一颗颗轰然落下,越落越近,她只想着:“至少等我看完了吧。”还有一部《官场现形记》,她大约也是在这里发现的,这书也能让她读得如醉如痴,浑然忘我。虽然外面战火纷飞,围城中的大部分时间她还是能在躲空袭的人群中找到一个角落,埋头读她的《官场现形记》。她那时已经因用功过度患了深度近视,光线不充足,书上的字又印得极小,她还是“在炮火下”把书读完了。一边读,她一面担心的还是“能够不能够容我看完”,倒不担心她的眼睛——“一个炸弹下来,还要眼睛做什么呢?”然则若是炸死了,读书又有何用呢?这个她却没自问,读书在她已成一种本能行为,以后她去当看护,也还是躲在一边看书。
十八天的围城过去,香港落入日本人之手,应该说是沦陷了,可是香港原本是殖民地,战事的平息好似灾难的过去,人们反倒沉浸在莫名的兴奋、狂喜之中。——“我们暂时可活下去了,怎不叫人欢喜得发狂呢?”张爱玲还记得和她的同学一道满街寻找冰淇淋和唇膏,挨个闯进每一家店里打探是否吃得上冰淇淋,得知有一家第二天可能有卖,这些平日养尊处优的大小姐次日居然步行十多里路去饱这点口福。而且她们天天带了莫名的兴奋到城里逛街。她后来称她就是在这段时间里“学会了怎样以买东西当做一件消遣”。在街上逛着,她看见这里那里触目皆是小吃摊,三教九流的人,包括衣冠楚楚的体面人都改行做了饼师。有时她们立在街头的小摊上吃滚油煎的萝卜饼,尺来远脚底下就躺着穷人青紫的尸首,就这也不能打消她们的兴致。
一面没在狂喜的人群里,一面她却也有众醉独醒的冷眼观照:“香港重新发现了‘吃’的喜悦。真奇怪,一件最自然、最基本的功能,突然得到过分的注意,在情感的光强烈的照射下,竟变成下流的、反常的……宿舍里的男女学生整天谈讲的无非是吃。”一个重大的事件过去,在人们的意识中竟没有留下什么痕迹,没有反省,没有对人生的真正了悟,有的只是动物式的本能的庆幸,一种延续生命的可能,一个重新吃东西的机会,生存的最起码条件一下变得有如上天赐福,带来令人难以置信的巨大满足,这不能不使她感到人性的盲目和人的可怜可笑。
她的一位叫苏雷珈的同学倒是因为战争变得话也多了,人也干练了。苏雷珈来自马来半岛的偏僻小镇,原先受的是修道院式的教育,她学的是医科,无知到会向人打听被解剖的尸体是否穿衣服,校内传为笑谈。用张爱玲的话说,她是“天真得可耻”。虽然她不大可能是《沉香屑:第一炉香》中愫细的原型,我们仍可以从小说开始时带了夸张神秘表情向“我”讲述“秽亵”故事的那个女孩身上瞥见她的影子。开战后苏雷珈念念不忘她的时装,炸弹就在宿舍的隔壁爆炸,舍监在催促众人下山,她仍力排众议将衣服收拾了一大箱冒了炮火运下山。箱子里的衣服在她当临时看护时给了她“空前的自信”,她因此得了男看护的注意,自信地与男看护们混在一起,她胆子大了,能吃苦,能担风险,也会开玩笑了。张爱玲的冷眼引导她去发现苏雷珈的转变其实是虚荣心的作用,她还是她。她叙述此事固然有戏谑之意,里面却有真实的心理观察。
与大多数学生的漠然、空虚相比,有位叫乔纳生的同学可以称得上是有为的青年了。他曾经加入志愿军上阵打过仗,停战后众人庆幸狂欢,唯独他充满鄙夷和愤恨,他鄙夷的不是周围人对战争的漠然,愤恨的不是未能打赢这场战争,而是计较原先许给他们这些志愿兵的特别优待条件没有兑现。打仗时他受命与另一学生出壕去将受伤的英国兵抬进来,他对此事耿耿于怀:“我们两条命不抵他们一条。”张爱玲揶揄地称乔纳生“有三分像诗人拜伦”,出生入死,他仍然是他素来的自我中心,生活在自己的幻想里,“投笔从戎之际大约以为战争是基督教青年会所组织的九龙远足旅行”,战争实质上丝毫没有让他对现实有所认识。
然而战争毕竟是战争。港大的学生开战之初大都乐得欢蹦乱跳,因为平白免去了一场大考。战争中吃够了苦头,他们多少改掉了不切实际的作风,用张爱玲的话说,是“比较知道轻重了”。只是这由务虚到务实的转变令她悚然,更让她感到人的空虚。困在学校里的学生无事可做,成天就是买菜、烧菜、调情,无聊地在玻璃窗上涂满“家,甜蜜的家”的字样,或者是进入更直接的“男女”。这是否就是人现出的本相?张爱玲不禁要怀疑人是否真有所谓“进步”:“去掉一切浮文,剩下的仿佛只有饮食男女这两项。人类的文明努力要想跳出单纯的兽性生活的圈子,几千年来的努力竟是枉费精神么?事实是如此。”这种怀疑态度成为张爱玲张看人生、考察人性的又一个稳定的视角,她总是能够发现现代人的机智、装饰后面的空虚,逼使她的人物露出原始人的本相。
不过最令张爱玲感到不耐的,还是乔纳生式的“热血青年”。在她看来,他们慷慨激昂的调子空洞苍白,而且可笑,因为与真实的人生毫不相干。内地的青年在抗战爆发之初对未来充满幻想,相信战火将给民族带来生机,人亦将成为崭新的人。张爱玲执著于她的所闻所见,同时也受她独特的视角的指引,对“炮火的洗礼”云云唯有不屑和鄙夷。相比而言,她看到人们在现实面前退缩、屈服,却表现出更多的宽容和同情,因为以她的观点,那毕竟是对真实人生的某种趋近。
香港战事中,许多人受不了无牵无挂的空虚绝望,急于抓住一点实在的东西,没结婚的人都赶着结婚了。报纸上挤满了结婚广告,张的同学中提早结婚的也有。她在防空总部的办公室里曾遇到过一对准备领结婚证的男女,她揣度那男的“在平日也许并不是一个‘善眉善眼’的人”,他或者是个范柳原式玩世不恭的浪荡子,可是现在到这里来借汽车,一等几个小时,却是不时地与新娘子默默对视着,眼里满是恋恋不舍之情。朝不保夕的环境教他学会了怜取眼前人,珍惜到手的东西。这一幕给张爱玲极深的印象,或者她由此得了创作《倾城之恋》的灵感也未可知。至少我们可以说,她替白流苏、范柳原安排下那样一种结局时,脑子里一定想着那些匆匆结婚的人们,尤其是那对男女。放弃人生的其他许多重要的内容,退缩到个人生活的封闭小天地,固然令她感到莫名的悲哀,另一面她也有理解的同情,范柳原态度的转变在她看来乃是“艰苦的环境中应有的自觉”。假如说“自动地限制自己的活动范围,到底是青年的悲剧”,那这悲剧中也贮满她乐于寻觅的人生的苍凉意味,而张爱玲写《倾城之恋》也正是要传达出这种意味。
香港沦陷后,张爱玲倒又同她的许多同学一起,到“大学堂临时医院”去当看护。与她去做防空员一样,她做看护也还是出于不得已——张爱玲从未对社会服务表现出什么热情。这医院利用的就是港大的校舍,环境原是她所熟悉的,现在住满病人,对她成了一个陌生的、从未接触过的世界。她的病房里住的大都是战事中中了流弹的苦力,或是战乱中趁火打劫抢东西被击伤逮捕的人,断胳膊断腿,沉默、烦躁地躺在那里。脏乱的环境、污浊的空气、流血流脓的伤口、奇臭的烂蚀症、残损的肢体、麻木的面孔、痛苦扭曲的表情,这一切与张爱玲熟悉的充满布尔乔亚气息的世界相去实在太远,仿佛是现实的肮脏的某种呈现,逼着她注视。虽然她在另一场合说及中国人的生活时曾说“脏与乱与忧伤之中,到处会发现珍贵的东西,使人高兴一上午,一天,一生一世”,她在病房里却全无这样的宽宏和从容品味的心绪,她只有一种近乎本能的不自在、憎恶、恶心。
布尔乔亚的世界里如果有痛苦,那也绝不是这样穷形尽相的、赤裸的痛苦——她受不了这种痛苦。病房里有一个尻骨上得了烂蚀症的患者,痛得受不了,常常整夜整夜地大声呻唤,张爱玲没有同情,唯有厌恶,“因为他在那里受磨难”——生命应当是华美的,是尽情的享受,不该有这样的惨厉。她时常上夜班,那个病人的呻唤成了她的一种折磨。她给我们记下了某天夜里的情形,那时她的同伴都昏昏欲睡,唯她一个醒着,去厨房烧牛奶:
……我把牛奶倒进去,铜锅坐在蓝色的煤气火焰中,像一尊铜佛坐在青莲花上,澄静、光丽。但是那拖长腔的“姑娘啊!姑娘啊”追到厨房里来了。小小的厨房只点一支白蜡烛,我看守着将沸的牛奶,心里发慌发怒,像被猎的兽。
这一幕极准确地传达出张爱玲自己的形象,她于脏与乱之中仍能为自己布置起一个“澄静、光丽”的封闭小世界,她亦拼命地闭上眼睛拒绝、抵挡外面的肮脏现实,而那个现实如同病人悠长、痛苦的叫声,执拗地挤进她的世界,侵入她的意识,令她心烦意乱。
对肮脏现实厌恶、惧怕的情绪驱走了与现实保持一定距离时可能会有的同情心,她称她自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没良心的看护”。对于病人的要求,能不理会的她尽量不理会,烂蚀症病人不停叫唤着,直要到病房里的其他人都醒了,看不过去帮着一起喊,她才烦恼万分地出现。屏风后面是她的避难所,大部分时间她躲在那里看书,用书挡开外面发生的一切。她的同伴也和她一样冷漠。如果说有不同,那就是她有更多的恼恨,不光是恨那个病人,因为她一边逃避着责任,一边也在通过同伴和自己的行为、态度究诘着人性。那个病人的死使她们如释重负,同时我们又看到她以怎样的并不超脱的语气叙述她们的反应:
这人死的那天我们大家都欢欣鼓舞。是天快亮的时候,我们将他的后事交给有经验的职业看护,自己缩到厨房里去。我的同伴用椰子油烘了一炉小面包,味道颇像中国酒酿饼。鸡在叫,又是一个冻白的早晨。我们这些自私的人若无其事地活下去了。
尖刻的讽刺后面是压抑了的悲哀。在这里,她和同伴的态度皆成为一种人性的证明,向她证明着人的孤独与自私,其中包含着人生的讽刺。张爱玲的冷嘲并无多少自责之意,她无意于道德上的判断,假如人的本性就是自私的,假如人生来就是孤独的,自责又有何用?对于她,问题的关键不是道德原则的重申,而是人性的真相必须接受。战争的特殊环境使得这真相骤然地以某种较平时更为触目的形式暴露在人们面前。在《烬余录》的结尾,我们看到张爱玲带着难以明言的复杂情绪接受她所发现的真相:
时代的车轰轰地往前开。我们坐在车上,经过的也许不过是几条熟悉的街衢,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惊心动魄。就可惜我们只顾忙着在一瞥即逝的橱窗里找寻我们自己的影子——我们只看见自己的脸,苍白、渺小;我们的自私与空虚、我们恬不知耻的愚蠢——谁都像我们一样,然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孤独的。
张爱玲在香港战事中感受到的一切,全都浓缩在这儿了。
一个作家最好的早期训练是什么?海明威回答说:“不愉快的童年。”乔治·曾林浦敦:《海明威访问记》,见《海明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76页。这肯定不是绝对真理。假如可以将“童年”的时限大大放宽,或者干脆改作“早年”,那此话对张爱玲至少是适用的。不愉快的经历使她早熟,使她养成内省的倾向,早熟、内省使她能够从自身的经历中提取更多的东西,所以她有一段并不算坎坷复杂的经历,却拥有一份并不简单肤浅的人生经验。对于不觉者,再丰富的阅历亦无用处,张爱玲的早熟早慧则使她有可能将有限的阅历转化为深度的人性体验,直至借此构筑成一个虽然狭小却相当深邃、完整的经验世界。她早年的经验之所以特别值得注意,并且可以当做一个自足的世界来对待、把握,不仅因为这是她创作《传奇》的灵感源泉,更因她以此为依托,已经形成了稳定的人生观,其后的发展并未溢出这个基本的框架;同时她亦由此形成了张看人生的独特视角,在后来的写作生涯中一直没有离开过这个视角,纵使她求助于其他的经验,纵使她后来延展、扩大了自己的视景。
张爱玲的小说世界与她的经历,准确点说是与她的经验世界关系密切。这里所谓经验指的是个人经历中一些富有典型意味的事件里所凝聚的作家对于生活的主观感受;是事件对当事人的影响或者说是经历中已经为主观感受渗透、溶解了的部分。张爱玲不是那种天马行空、更多凭恃想象力的作家,她恋恋于事实的人生味——所谓“事实的金石声”。对于她,“生活空气的浸润感染”尤其重要,有了鲜活的感觉她才能自信地复活人生的原汁原味,而这感觉当然最好是向她的经验去寻找。另一方面,她的生活天地狭小,阅历并不丰富,所以她对自己的经验格外珍惜,力求使其涓滴不漏地转化到虚构世界中去。在她的小说创作中,尤其是在《传奇》里,她无疑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她早年所经验到的一切,尽管它们在小说中出现时已经被高度地艺术化了。
细读张爱玲的小说,我们经常会发现她的生活经历与小说世界、她的个人经验与人物的感受之间的奇妙对应。没落的贵族之家是她小说中最常见的场景,不论我们将“场景”理解成环境、气氛,还是情调——张的“场景”通常具有三者打成一片的浑然一体的效果。我们在《金锁记》、《花凋》、《留情》、《倾城之恋》、《茉莉香片》、未完成的《创世纪》,乃至以女佣为主角的《小艾》中一再发现了它。在她小说中另一频频出现的场景是香港,而如前面说过的那样,她在香港的经历正是她经验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她常常喜欢将这两个场景组合到一起,把她的两段生活放到一处来处理。她的人物大多在生活中是有其原型的,除去《茉莉香片》中传庆及其父母有她家人的影子之外,她小说中的许多其他人物也往往取自她熟悉或是有过接触的人,比如《连环套》中的霓喜及女婿,其原型麦唐纳太太、潘那矶先生她都见过。《〈张看〉自序》。而据她自己后来所言,范柳原和《留情》中的米尧晶也有所本。水晶:《蝉——夜访张爱玲》。张爱玲在同水晶的谈话中称《传奇》里的故事和人物,“差不多都‘各有其本’”。谈到《红玫瑰与白玫瑰》时她说明男主人公和白玫瑰她都见到过,红玫瑰则只是听到过。虽然张爱玲创造人物的习惯做法是“杂取多人为一人”,她却喜欢从某个特定的原型开始,因为特定的原型(哪怕只见过一面也好)可以帮助她比较容易地找到她所需要的感觉,使她的想象有一个给她踏实感的凭附。
她笔下人物的许多感受经常来自她本人的具体经验,她也乐于将自己的感受寄植于不同人物的身上,借助人物对各自所处特定情境的反应表现出来。《沉香屑:第一炉香》中,葛薇龙作为一个穷亲戚的许多心理活动都传达出张爱玲在香港读书期间的感受。《十八春》中顾曼桢在禁闭中的恐怖感与张在父亲家被关禁闭时的感受显然也存在着某种对应,白流苏在意识到自己在那个没落之家必然的悲剧命运后发出的“这屋子里可住不得了!住不得了”的恍惚的自语,更无疑是她出走前在父亲家一段亲身体验在虚构世界的回声。张爱玲甚至也愿意让一些与她相去甚远的人物分享自己的人生体验。比如《金锁记》中七巧在姜季泽离去后对因与果的困惑反映了张爱玲对人生遭际复杂性的感慨,《留情》中米尧晶“对于这个世界他的爱不是爱而是痛惜”的叹谓是张对人生忧患意识的流露。
如此这般“拆碎七宝楼台”,将艺术还原为材料,当然是煞风景的事情。事实上张爱玲决不肯像郁达夫一类的作家,径直把文学当做传记来作,亦不肯以简单的方式来处理她的自我形象。她的种种人生体验于她是共时性的存在,是相互渗透重叠的完整“世界”,旧式家庭与香港两个场景的嫁接,将自己的情绪、感受寄植到不同类型的人物身上都是明证。找出张爱玲的生活与创作之间某些可以指认的关系并非要做索引,虽然它也许可以提供某些轶闻轶事的趣味,其真正的意义却是应该帮助我们感知她的经验世界与小说世界之间的整体的对应。英国名小说家格雷厄姆·格林有言:“一种占支配地位的经验赋予一书架的小说以一种体系上的统一性。”所谓“经验世界”可说是占支配地位的经验的总和。这是张爱玲意识的深层结构,或者说是下意识的一部分背景,不论她在某篇小说中直接描绘的是哪一个部分,作为一个整体,它们都在她想象力的深处蠢动,当虚构世界完成时,便化为弥漫其中的空气,不一定看得见,摸得着,但却无时不在,无所不在。而一个优秀作家的真正考验,当然是看他能否将个人性的经验真正地艺术化,升华为具有普遍性的东西。
不过在走入她创造的世界以前,我们最好还是先来看看张爱玲早年的另一种训练——写作基本功的训练,也追踪一下她回到上海后一举成名的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