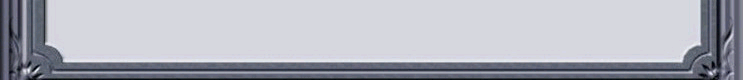第四章 “赤裸裸地站在天底下”
她在床上“倾全力”听着大门的每一次开关,巡警抽出锈涩门闩的咕滋咖滋声、大门打开时的呛啷啷的巨响、通向大门的那条煤屑路上有人走过时沙子发出的吱吱声,声声入耳,甚至梦中也听到这些声音。一等到可以扶着墙行走,她便设法从保姆口中套出了两个巡警的换班时间,又伏在窗上用望远镜张望门外马路上有无行人,而后挨着墙一步步摸到铁门边,拨出门闩,闪身出去——她成功了。多年后她回想起当时的情景,仍然有一种抑制不住的喜悦流露笔端:“……当真立在人行道上了!没有风,只是阴历年左近的寂寂的冷,街灯下只看见一片寒灰,但是多么可亲的世界呵!我在街沿急急走着,每一脚踏在地上都是一个响亮的吻。”
她比照着小说悬想出的那些更带惊险味道的计划最后一个也没有用上,不过她的出逃仍然无疑是她一生中最富冒险色彩的经历之一。更重要的是。她在她成长中的关键时刻永远地告别了那个家、那种扼杀青春的生活方式。也许就是这短短的几分钟、短短的几步路,已经彻底地改变了她的命运。
那个家、那种生活会把人变成什么样,她的弟弟是个极好的例子。他小时是秀美可爱的,然而在死气沉沉的家庭生活中,在父亲的喜怒无常、继母的虐待下渐渐销蚀了意志,变得萎靡不振。逃学,忤逆,没志气。关于弟弟的一件小事张爱玲一直铭然在心,那是她偶尔有一次回家碰上的:
……在饭桌上,为了一点小事,我父亲打了他一个嘴巴子。我大大地一震,把饭碗挡住了脸,眼泪往下直淌。我后母笑了起来道:“咦,你哭什么?又不是说你!你瞧,他没哭,你倒哭了!”我丢下碗冲到隔壁的浴室里去,闩上了门,无声地抽噎着,我立在镜子面前,看着眼泪滔滔流下来,像电影里的特写。我咬着牙说:“我要报仇。有一天我要报仇。”
浴室的玻璃窗临着阳台,啪的一声,一只皮球蹦到玻璃上,又弹回去了。他已经忘记了那回事了。这一类的事,他是惯了的。我没有再哭,只感到一阵寒冷的悲哀。
她弟弟已经麻木了,在环境中昏睡下去,她却不能。她的多少带些戏剧性的姿态也许同她看巴金《灭亡》一类小说引起的愤激情绪不无关系。张爱玲虽然对“新文艺腔”的作品素来抱有反感,中学时受学校里的空气影响,一度也曾以读新文学为荣,《童言无忌》中记她见弟弟租了许多连环画来看,便觉不上品,“认为他的口胃大有纠正的必要”,其时她就正读着巴金的《流亡》和穆时英的《南北极》。也许我们应该承认她自小要强,与她弟弟原本就是两种性格,以此推断,她即使仍在家里继续待下去,她也未必就会变得像她弟弟那样。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讲,环境的力量也是可怕的,这种生活显然已经改变了她的性情。她小时候并不缺少一般儿童的健康、活泼,可是像我们在后面将会看到的那样,她上中学时已经变得郁郁寡欢,而且给人萎靡不振的印象。
上面引的这个片段同时也很能说明张爱玲敏感内省的气质和她的早熟。在她“寒冷的悲哀”中沉淀着难以明言的寂寞与孤独感。这几乎是与自我意识俱来的对生活与环境的重大感受。随着年龄的增大,这种感受越发强烈。孤独与寂寞将自尊心琢磨得愈加灵敏纤细,而愈是如此,她就愈是不能放过来自外部的对于心灵的哪怕是极小的伤害;将种种被伤害的感受作了放大的处理之后,她更加意识到环境的不可靠、不安全。张爱玲敏感内省的气质与冷漠的家庭气氛对心灵的窒息,这二者之间相互生发的矛盾运动构成了张爱玲性格成长中的恶性循环。其结果,过分敏感的气质发展为多疑、善疑的倾向,它使得张逐渐习惯于不是以信任的眼光,而是以审慎怀疑的态度注视周围的人与事。反映到创作中,则是一种相当冷静而挑剔的眼光成为张爱玲对人物心理洞察力的主要标志,在这种眼光的照射下,人物言行背后隐秘的心态和动机暴露得格外真切。同时,这种眼光也多少解释了张爱玲在小说散文中描写、议论虚构或真实的人物时,何以笔调往往由俏皮入于尖刻。
她逃到母亲家中,由母亲供给生活与教育费用,她甚至能从母亲的神情态度中觉察到她(母亲)“一直在怀疑我是否值得这些牺牲”。她跨出父亲家大门的那一步果如保姆所料,使她永远回不了那个家了,后母把她的一切东西分着送了人,只当她死了。这并不让她恐惧或是难过,因为她根本没打算回去。问题是,在母亲这里她能得到她所要的一切吗?我们在《私语》中看到的是,逃离父亲那个家带来的短暂兴奋过后,她又被一种新的不安所俘虏,对于她,母亲的家很快就“不复是柔和的了”。她的内省倾向,她的过度敏感都妨碍她毫无顾虑地走入这个她仰慕已久的,对于她应该是明亮、亲切的所在——在母亲家中她不像一个受尽委屈,终于回到温暖母爱中的女儿,倒像是来到贾府中的那个“步步留心,处处在意”的林黛玉。
但是也像林黛玉的情形一样,她的谨慎怀疑除了性格的关系之外,也不是没有缘故的。她曾说她“一直是用一种罗曼蒂克的爱来爱着我母亲的”,与母亲很少有接触的机会使她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能将这种爱维持不坠。她还记得有两次母亲领她出去,穿过马路时偶尔拉住她的手,她便感到“一种生疏的刺激性”。一旦朝夕相处,转入真实具体的关系,母亲在她心目中的“辽远而神秘”便开始掉彩褪色。她的母亲现在也是在窘境中——大家闺秀而想走职业女性的路总不免有失落感,而她的出现无疑增加了她的母亲的负担,所以她才感到母亲是作出了牺牲。她是在窘境中学习做淑女,而要像她那些家境优裕的同学那样做淑女,保证之一应该是充足的零花钱。她三天两天向母亲伸手要钱,却使母亲渐渐地不耐烦了。小时候她站在父亲的烟炕前面要钱买钢笔或交学费之类,父亲躺在烟炕上吸鸦片,她久久地得不到回话,这是经常出现的一幕;她在母亲那里没有受到这样的“冷遇”,母亲的不耐烦却让她尝到了另一种“琐屑的难堪”,正因琐屑,这是难于启齿又一言难尽的,张爱玲在回忆中不欲提起,只是读者仍可感觉到她言下的委屈。她在私下里不可能没有抱怨,然而她是一个在不和谐的家庭中长大、富于内省倾向的人,不可能像许多受宠的小姐那样理直气壮地加责于母亲,相反,在不满的同时她又要“为自己的忘恩负义磨难着”,这只能将她同母亲的关系拖入一种更别扭、更不自然的状态。
张爱玲的姑姑曾笑说她“不知从哪里来的一身俗骨”,又分析她的父母纵有缺点,都还不俗,即不把钱当回事。可是她母亲对她的不耐烦有很大一部分就是因钱而起的,或许正因为对自己向父母讨钱时感到的那份羞辱难堪有着过于分明的记忆,张爱玲后来一再挑战式地特意宣称她对金钱的直率立场。她还在谈到对母亲的爱一点点销蚀时写出下面这样一行警句:“能够爱一个人爱到问他拿零用钱的程度,那是严格的试验。”假如这真是试验,那她已经证明了,她母亲对她的爱不可能是无条件的。
当然她同母亲之间的隔阂不可能光是因为零用钱。母亲一去七八年,这段时间正是张爱玲性格成长中最重要的时刻,也是可塑性最大的时期,而且母女二人天各一方,过的是全然不同的两种生活,当她归来时,她在女儿心目中诚然还是——至少暂时还是——那个“辽远而神秘”的形象,但女儿已经不是她记忆中的女儿了。《天才梦》中说:“我母亲从法国回来,将她睽隔多年的女儿研究了一下。‘我懊悔从前小心看护你的伤寒症,’她告诉我,‘我宁愿看你死,不愿看你活着使你自己处处受痛苦。’”熟知张爱玲在父亲家里的不幸遭遇的人容易将她母亲的话理解成对她的处境的同情和担忧,实际上看看上下文便可了然,这里的“痛苦”是指张对生活的不能适应。这段文字并非纪实,带有戏谑色彩,但它多少暗示了她母亲的失望,因为女儿没有如她期望的那样成为一个淑女。
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张爱玲在学校里接受的虽然是淑女式的教育,但是因为后母虐待她,父亲则以他的性情,即使在脾气好的时候也不会关心到她的这个方面,她的淑女式的训练在母亲走后事实上已经完全中断了。相反,因为心境不好,她除了读书用功之外,在生活上懒懒散散,打不起精神。这是她母亲不愿看到的,而当两人朝夕相处地在一起之后,张爱玲身上的这一面更加暴露无遗。以她的敏感,张爱玲不可能意识不到母亲的失望,以她原先对母亲一贯的仰慕艳羡之情,她当然想让母亲满意,甚至暗中非常希冀得到母亲的赞许,但是她力不从心。张爱玲在她母亲面前无疑有某种心理上的劣势,她母亲虽然不是什么成功的人物,但是她几度出洋,而留学深造正是她自己的目标,另一方面,她母亲是“西洋化的美妇人”,似乎也善于社交场中的酬酢。以“所有的女人都是同行”的观点,以她的敏感早熟,则她在母亲与自己的对比中感到某种压抑是很自然的。
她母亲似乎只能接受一个够得上淑女标准的女儿,她给女儿两年的时间学习“适应环境”——这是学做淑女的另一种说法。张爱玲要接受的基本训练包括“煮饭、用肥皂粉洗衣、练习行路的姿势、看人眼色、点灯后记得拉上窗帘、照镜子研究面部神态,如果没有幽默天才,千万别说笑话”等等。换句话说,所有这一切都正是她不能让母亲满意的地方。几年前当她从母亲那里接受这方面的最初的教导时,她有说不出的好奇和兴奋,这些年来她的心智已朝着另一方向发展,她的世界几乎已经缩小到她的内心,外部世界她简直无从应付。她的学习过程是她的“惊人的愚笨”让母亲感到惊奇和不满的连缀。更糟糕的是,因为得不到母亲的任何鼓励和嘉许,她不断地意识到母亲一再流露出的失望、怀疑和不耐烦,这使她感到紧张和慌恐,就像一个在考场上使尽浑身解数仍然屡战屡败的小学生登上考场一样。对于学做淑女,她再也没有幼时那种跃跃欲试的劲头和游戏的心境。她只是一次又一次地想到,“我不该拖累了她们(指母亲和姑姑)”,并且更加意识到自己的无能:
……在父亲家孤独惯了,骤然想学做人,而且是在窘境中做“淑女”,非常感到困难……常常我一个人在公寓屋顶的阳台上转来转去,西班牙式的白墙在蓝天上割出断然的条与块。仰脸向着当头的烈日,我觉得我是赤裸裸地站在天底下了,被裁判着像一切惶惑的未成年的人,困于过度的自夸与自鄙。
……逃离父亲那个家带来的短暂兴奋过去之后,她很快又被一处新的不安所俘虏。她要同激进青年划清界限,多次表示她的出逃“没有一点慷慨激昂”,绝非“娜拉出走”式的举动。那是理智、实际的考虑之后做出的决断。她母亲得知她想出逃的意图后秘密传话给她:“你仔细想一想。跟父亲,自然是有钱的,跟了我,可是一个钱也没有,你要吃得了这个苦,没有反悔的。”张爱玲那时虽然在囚禁中,渴想着自由,对父亲的家又充满愤激情绪,可是这样的现实的问题还是给她带来困扰,一度让她犹豫、彷徨。“痛苦了许久”才得出的结论是:“在家里,尽管满眼看到的是银钱进出,也不是我的,将来也不一定轮得到我,最吃重的最后几年的求学的年龄倒被耽搁了。”这就是说,她对她出逃后面临的“窘境”——包括将来的和现在的——并非全然没有心理准备。但是她没有想到银钱上的窘迫超出她的预料,更没有想到“窘境”还将包括这样的内容:她与母亲在心理上、感情上的障碍。
在这里,就张爱玲的母亲以及她们母女二人的关系多作一些探讨也许是必要的。谈到张的家庭和她的早年经历,人们似乎总是理所当然地指责她的父亲,而对她的母亲采取同情的态度,其根据是不言而喻的:她父亲是个典型的遗少,母亲则属开风气之先的一代“新女性”;二人虽然都是旧婚姻制度的受害者,但前者被其同化,不仅自甘受缚,而且想以此缚住别人,后者则有个性意识,不惜作出牺牲,最终冲决罗网;在对子女的态度上,前者是个地地道道的封建家长,甚至可以说是个专制暴君,后者作为母亲虽然未能恪尽职守,那却是为了争取女权不得已而作出的牺牲,情有可原。对于这本传记而言,重要的不是就张的母亲作出公允的评价,而是她在我们的这位传主的成长过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她的举措对传主的心理有何影响,以及传主对她的复杂态度。从这些方面考察得出的结论,对于这位“辽远而神秘”的西洋化漂亮夫人显然是不利的。
张爱玲无疑乐于接受母亲的某些信条,尤其是争取个人权利的那部分,她心里赞同母亲离婚就是明证。她得到的关于另一种生活方式的明确信息,最初就来自母亲,而且在她早年生活中面临抉择的几个重大时刻,母亲的支持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使她得以完成西式的教育,并最终走上职业妇女的路途。但是一个女儿所要求于母亲的,决不止于这些。且不说她母亲远非一位循循善诱的教师,就算她在某种意义上碰巧扮演了人生导师的角色,站在孩子的立场上,张爱玲也还有生活原则以外的、她更想得到的东西,那就是母爱。不幸,她母亲显然是一个情感淡漠的不称职的母亲。她让女儿进学堂,让女儿学做淑女,更多的是出于对她信奉的价值观和原则的执著,而非出于对女儿的关怀。她第一次出洋,上船前大哭不止,但那似乎不是因为与儿女难分难舍,佣人把四岁的张爱玲推上前去,“她不理我,只是哭”。第二次出洋,张爱玲已在学校里住读,“她来看我,我没有任何惜别的表示,她也像是很高兴,事情可以这样光滑无痕迹地度过,一点麻烦也没有,可是我知道她一定在那里想:‘下一代的人,心真狠呀!’”她只对女儿没有恋母的表示感到遗憾,自己却并无多少不舍之情——至少在张爱玲眼中,她母亲似乎并没有感到抛下儿女是太大的痛苦,因为原本对儿女并无很深的情感,也就是很难说她在这方面是作出了什么了不得的牺牲。张爱玲可以接受母亲的选择,可是没有真正的矛盾和痛苦,就这样轻松地在感情上把女儿“牺牲”掉,这又是张日后——特别是与母亲有了芥蒂之后——想起时终不能释然的。
与父亲相比,张爱玲显然对母亲有更多的期待,这不光是指她原先对母亲的崇拜艳羡,而且一般说来,温情、眷恋一类的情感总是更多地与母亲的形象联系在一起。也正因如此,当她领教了母亲待她的冷淡之后,更觉得难以接受。细读她的自传性散文,我们可以感觉到她对母亲的态度复杂微妙,一方面她时时要说到她的“忘恩负义”,另一方面又不能释然地为自己辩解着。她对父亲从未有太大的希望,所以也无太大的失望,事过境迁之后,她可以以一种相当平和的心境说起父亲。她没有忘记父亲对自己的虐待,她没有忘记父亲曾扬言要打死她(而且不光是扬言,她在重病中他真是不管她死活的),即使如此,她甚至仍然能在某种程度上同情他的处境。当我们读到“我知道他是寂寞的,在寂寞的时候他喜欢我”的句子时,决不应怀疑“我知道”这三个字里面的低徊、沉痛之意,后面加上的一句话也不能减轻它的分量。她同样谅解母亲的处境,但是你总能感觉到她的同情中多少夹杂着勉强之意,她似乎是在勉强自己去理解母亲的苦衷,不想提起与她之间的恩怨,然而又忍不住要计较母亲给她的那些“琐屑的难堪”。胡兰成说,张爱玲“对好人好东西非常苛刻,而对小人与普通东西,亦不过是这点严格”,她母亲不是这个意义上的“好人”,她也不会把父亲看成“小人”,但是只要将二词置换成“意欲亲近的人”和“未抱幻想的人”,这个句子就可以用来解释她后来对父母态度上的微妙之处。
当然,我们也可以尝试作其他的解释:因为张爱玲差不多一直生活在一个女人世界里,她对男人虽也有透彻的了解,却毕竟有某种距离感,她对女人的弱点和心理则可以做到一览无遗,像她的小说、散文表明的那样,她对男人更容易达到宽容,而对女人有更多的挑剔和计较,她对父母态度的差异是否多少是这种倾向的延伸?此外,她与父亲之间也许有着一种爱恨情结,不是弗洛伊德式的恋父之类,而是指她父亲对她显然比对她弟弟更有一份亲情,站在他的立场上,甚至可以说他对女儿并不是没有一种父爱的,尽管这种爱不可避免的是出自以他所理解的那种遗少加封建家长的方式,你却不能不承认那里面有父女间特有的一种情愫。张爱玲不止在一处提到过父亲对她的喜欢,虽说每一次都加上了限制性的饰语。顺此想下去,父亲最后对她的施暴也不是没有由喜欢到憎厌的情绪在作祟。
她母亲对她则没有流露过喜爱之意,即使在两人没有芥蒂之前,张爱玲感到的也只是一种生疏。总之,除了淡漠还是淡漠,而这种淡漠你没有可能将其解释为任何形式的母爱。所以并非偶然的,张爱玲多次流露出她对母爱的怀疑和不信任,而她的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几乎无一例外地是在缺少母爱的环境中长大的。
张爱玲母亲的淡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性情的索然寡味。她属于张爱玲后来反感的那种被各种定型感情和生硬的条条框框所拘囿的人。张爱玲提供给我们的关于她的几组镜头——读周瘦鹃的“哀情小说”伤心落泪、与女友一起模仿电影中的恋爱场面、一本正经地告诉张爱玲关于“淑女”的刻板细则——在说明她只会按照公式化的情感行事:另一种形式的“明于知礼仪,陋于知人心”。因为有一套“先进”的公式做后盾,她也有一般“新女性”的毛病,自以为是地执著于她的标准,没有自省的能力和习惯。其结果是她成了一个对姿态比对内心的感受更感兴趣的人,几乎丧失了对于本然的情感的体验能力,包括对母爱的体验。当她尝试对女儿实施她的淑女培训两年计划时,她的这一面愈发暴露无遗。她不体谅女儿的苦衷,只是一再用她刻板生硬的“淑女”标准,用她不时流露的怀疑,用她的不耐烦提示女儿的不合格。事实上,她的那一套标准已经成为对张爱玲天性的压抑,而那一番训练对于张爱玲也成了一种不折不扣的痛苦折磨。如果张在父亲家的遭遇是一枚苦果的话,那么她在母亲家里尝到的仍是苦果,而且不见得比那一枚更易于吞咽。重要的是,母亲的苛责使她在心理成长的这个决定性时刻丧失了她最需要的东西——自信心。
张爱玲称母亲在国外的那段时间,她在学校里得到“自由发展”,这与她说自己学生生活过得不愉快并不矛盾。她的懒散、生活自理能力差虽然在同学中传为笑柄,她的优异成绩,尤其是写作方面的天赋却令同学佩服,且得到老师的称道,在这样的特别需要来自外界肯定的时期,她当然是从中找到了自信的根据。在父亲家中,她虽然得不到家庭的温暖,但父亲对她在写作方面的天赋是引以自豪的,而且不吝于鼓励和褒奖。他不是随便说说而已,他是真的器重女儿,他曾鼓励女儿学作旧体诗,又要先生为她评改。张爱玲别无所长,可以说那段时间里,她的优异成绩和写作方面的天赋是她的“日益坚强”的自信心的全部源泉。
但是她母亲更关心的显然是她是否具备了淑女的风范,而对她的写作才能毫无兴趣。或者是因为她缺乏鉴赏力,或者是她以为女儿的才华只有成为淑女风范、淑女式教养的一部分才有意义,总之她在这方面没有给过女儿任何鼓励。她对女儿在应付淑女环境时的笨拙、迟钝一再流露出来的不耐则无异于暗示张爱玲,她的那点才华没有什么了不起。张爱玲自己的一套人生见解和生活方式那时还未形成,她没有有意识地抵抗母亲对她施加的影响,也无力抵挡这种影响。而一旦采取母亲的立场(哪怕是部分地采取),她的自信便岌岌可危,又因为处在情绪最易波动、最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时期,自信甚至很快地走向了它的反面——自卑:她所自恃的一切现在被认为是不足以凭附的,那么除此以外她还有什么?她发现自己一无是处:“我发现我不会削苹果。经过艰苦的努力我才学会补袜子。我怕上理发店,怕见客,怕给裁缝试衣裳。许多人尝试过教我织绒线,可是没有一个成功。在一间房里住了两年,问我电铃在哪儿我还茫然。我天天乘黄包车上医院去打针,接连三个月,仍然不认识那条路。总而言之,在现实的社会里,我等于一个废物。”
在过度的自夸与自鄙相纠结消长的一团惶惑中,她的两年培训计划彻底失败。她不无怨意地说:“除了使我的思想失去均衡之外,我母亲的沉痛警告没有给我任何的影响。”“思想失去均衡”当然是丧失自信、心理受到挫折的另一种说法。我们不能说她在父亲那里除了受了皮肉之苦外,她的心理没有受到影响,但她的闷闷不乐、郁郁寡欢多是由外部环境而起,如果她有自卑的话,这种自卑也不是由于她本人的原因,而在母亲这里她被引向了自我怀疑。从心理成长的角度看,她在后者那里遭受的挫折也许更大。当然,不论是在哪一个家,环境加予她性格发展的指向都是一致的:朝着内省、敏感、自我封闭的路上走,而孤独与寂寞则不可避免地成了她早年生活中最重大的情感体验。
张爱玲的寂寞与孤独中包含的内容是多重的,而安全感的匮乏构成了它的核心。她把自己从父亲家放逐出去,可是因为做不了合格的淑女,也不能顺利地走进这个新家。所以她在家庭生活中是个边缘人,关键是自她年纪稍微大一点,比较懂事之后,她一直没有找到一种家的感觉。她有家,而且这个家可以供给她优裕的物质生活,但是在心理的、情感的意义上,这个家等于不存在。家通常具有的避风港、庇护所的意味对于她都很快地消失了,在自己的家里她反倒更尖锐地感到缺少安全感,像她自己描述的那样,她觉得她是“赤裸裸地站在天底下”——用“赤裸裸”来形容得不到保护的感觉实在是再准确不过了,所以她一再陷入自怜与自卫相混合的奇特心态。如前所述,在禁闭室里,在病中,在公寓屋顶的阳台上,呈现于她意识中的家是一个异己的世界。她还在一篇散文中记述过她的一个梦,梦中她在一个雨夜又回到了香港:
……船到的时候是深夜,而且下大雨。我狼狈地拎着箱子上山,管理宿舍的天主教僧尼,我又不敢惊动她们,只得在黑漆漆的门洞子里过夜。(也不知为什么我要把自己刻画得那么可怜,她们何至于这样地苛待我。)风向一变,冷雨大点大点扫进来,我把一双脚直缩直缩,还是没处躲。忽然听见汽车喇叭响,来了阔客,一个施主太太带了女儿,才考进大学,以后要住读的。汽车夫砰砰拍门,宿舍里顿时灯火辉煌。我乱向里一钻,看见舍监,我像见了晚娘似的,赔笑上前……
第二天她将这个梦说给她姑姑听,“一面说,渐渐涨红了脸,满眼含泪;后来在电话上告诉一个朋友,又哭了;在一封信里提到这个梦,写到这里又哭了。简直可笑——我自从长大自立之后实在难得掉泪的”。她一再想到并对人说起这个梦,每说起又都会触动隐情,可见这个梦已成她意识背景的一部分。而且她做此梦已是在她功成名就、境遇大大改善之后,因此也就更值得玩味。精通弗洛伊德释梦术的人也许会从这个梦里分析出张爱玲的自虐倾向,因为张似乎愿意让自己在假想中处于一种不堪的境地,而又乐意反复地提到这个梦。但是我们宁愿选择一种更接近常识的解释:这个梦反映了张爱玲由大家闺秀跌落为穷学生的莫名委屈,而在更深的层次上,它所提示的是一种深入骨髓的不安全感——无家可归,走到哪里都仿佛是寄人篱下。如她自己所说的那样,实际的情形并不像梦里想象的那么糟糕,然而这倒更说明那种不安全感如影随身,挥之不去。要重建自己的信任,要重建自己的安全感实在艰难,尤其是她养成了内省、多疑的习惯之后。她在一首诗中写道:
曲折的流年,
深深的庭院,
空房里晒着太阳,
已经成为古代的太阳了。
我要一直跑进去,
大喊:“我在这儿!
我在这儿呀!”胡览乘:《张爱玲与左派》,载《天地》,1945年6月号。该诗未见在她本人的文中出现。胡览乘当是胡兰成无疑,不仅因其文风,而且别人似不可能有机会引用张未发表的诗作。
这里面有一种疏离的性质,不安全感几乎要发展为梦魇式的恐怖。虽然可以有更广大的解释,但它无疑也贴切地传达出她感到自己被遗弃的真实感受,这种感受最初是由她的家庭让她领略到的。日后她将把她的不安全感发展成为某种对人类普遍处境的认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时代重压下的无家可归的孤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