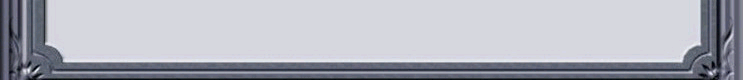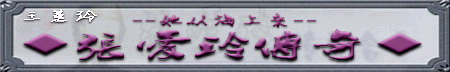
第52章 在押解的囚车上
胡兰成胸口紧紧一缩,抽了一口气,那致命的痛使他有了感觉,但是似乎晚了,张爱玲那最忧伤的一刻随着话出口,宛如裂帛,已经成千古绝响。雨水从伞篷裂缝滴到胡兰成脸上,竟像他的眼泪。张爱玲拿出手绢,替他擦去,脸上无限凄然惨伤,却还能一笑。他握住她的手,蓦然觉得手心里是空的。
两人兜转回来,也还有家常可说,只是那背后的惨伤要张爱玲独自咀嚼,她请求说:“我该回去了!走前总让我去看看你住的地方吧!”胡兰成默默引她,到了门前,他松开手,张爱玲又笑,嘴角上是说不尽的哀伤。
那柴门开合声,呼唤声,偶尔也有乡间的狗叫声,和斗室里一张竹床,一切都昏昏黄黄地罩在油灯里,张爱玲觉得自己恍恍如在另一个世界。外婆避出门,秀美跟去叮咛,无疑是留出空让胡兰成对张爱玲解释。胡兰成试着说明,但语气表情并不自然:“秀美为了让我安心住她娘家,只能跟左邻右舍说我是她丈夫!乡下地方,我也得顾虑秀美的难处……”
张爱玲倒也点头,没有说什么,这间屋一角还漏雨,用木桶接着,滴滴答答。张爱玲问他夜里冷不冷,又看房间的床,是两个枕头一套被褥。屋里另有一张板床也搁着被褥,她不愿意多想,胡兰成看到她的眼光,也没有再解释。范秀美这时回来,见他们坐在床上,就坐到床边凳子上。胡兰成神情讷讷地让她安心,勉强笑道:“我还一个劲儿催她回上海!这天又湿又冷……”
秀美答得却随意:“也不会是天天这样!我看张小姐住下来吧!你在,他有人说话,日子好过得多了!”张爱玲看她说话,做针线活,讲到“他”时,自然又亲,看得眼睛又要泛起水雾来了,既是委屈,又是羡慕,还要称赞,她是见了别人一点好处,也不肯骗自己的,口中夸道:“我刚才看你绣的这只狗,绣得真活!那头就偏那一点,就不一样!”
范秀美喜滋滋看着手里的活说:“是吗?我是打发时间!难怪胡先生常说,得抛一赞胜黄金万两!我现在也明白了!”胡兰成看见张爱玲那眼里的恋恋不舍,她是恋着有他的地方,对她,那是人世间最温暖的所在。
张爱玲走时仍阴雨绵绵,胡兰成拿伞罩着张爱玲,一路撑到码头船上,又把伞给她:“你拿着!这雨会一路下!”
张爱玲声调突然转为急促:“不拿伞!”
胡兰成明白她那苦而矛盾的心情,她是不要散啊!他笑着安慰她:“拿布伞!拿着!”他拿给她的是一把油布伞,这一转是不散,就海阔天空了。
张爱玲痴望着他,眼里有无限的仓皇。船开动,离岸渐远,船上的人声嘈杂推挤,她无动于衷,紧紧靠在船舷边望着,他还站在那里,还站在雨里送她。她的泪水再也忍不住滔滔而下,她哭她的爱,哭她心里的委屈,哭她的绝望但又不能心死,她爱胡兰成这样深,他的感情却像这千古的浊浊黄滔,不能清澈见底,而她无能为力。这一路回去也无风景可赏了,只是灰灰的天,蒙蒙的雨,山也远了,人也远了,惟有一把油布伞,是她千辛万苦得来的情感归宿。
张爱玲回到拥挤的上海,重上拥挤的电车,她的命运正如在车里一样,退了又退,避了又避,蜷缩一角,只求能有一方立足之地。然而终究还得下车去,另寻安身立命的天地。
张爱玲仍继续给胡兰成写信,这是她循例的倾诉方式:“船要开了,你回岸上去了,我一个人雨中撑伞站在船舷边,对着滔滔黄浪,伫立涕泣久之!随信附上汇票一张,想你没有钱用,我怎么样都要节省的。现在知道你在那里生活的程度,我也有个打算,你不要为我忧心!”
温州外婆家附近,平日安静的巷道也突然出现了士兵,胡兰成与范秀美两人犹如惊弓之鸟,避到诸暨斯家。范秀美一路伴着胡兰成逃下来,他满心的抱歉,却还贪恋她的温存呵护。欠债欠得还不胜还,惟有不还。
一九四六年夏初,局势稍稍和缓,有人请苏青去编副刊,条件只有一个,就是要她改名。张爱玲老老实实劝慰她说:“现实也得考虑!你去当主编,我也有条出路可走!我是不介意改名的,我这名字是一直都嫌它俗气,趁机改了也好!”
苏青显得很沮丧,她办刊物那意气风发的神采已经不见了,悲苦地说:“你算好的!有个姑姑给你挡一挡,靠一靠,我这一转身,老的老小的小,谁让我靠?现在又这样恶名在外,再嫁也没有人敢沽问斤两,我预备把自己挂在绳上,就这么风干了算了!”
烦心事既解决不了,索性不再去想,苏青转而关心张爱玲,问道:“有他的消息吗?”
苏青谨慎地问,张爱玲微微摇头,她现在不能相信任何人,苏青的话如雪上加霜:“真是天罗地网要捉南京那帮人,听说周佛海在押解的囚车上,哭得一塌糊涂!他太太也被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