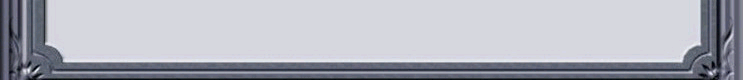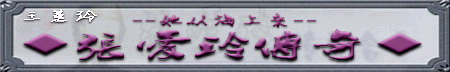
第36章 一种言语不可及的静谧
张爱玲翻着画,状似平常地答:“好呀!”
胡兰成又追问一句:“好过我在?”
张爱玲答得风轻云淡:“没想过呢!”胡兰成听了竟也释然,头枕着墙,想着自己在南京的心情说:“我也不怎么相思!只是逢人就要说到你!”
张爱玲又把心思转到画上,胡兰成指着一页说:“怎么我看来只觉得这女人横竖都不快活,脸上就写着悲哀!”
张爱玲若有所思地说:“那是为理想吃苦的人,发现理想剩得很少了!剩下的一点,又那么渺茫!可是因为吃过苦,剩下的那一点又要比从前满怀希望好!都明白了!不再只是当初那样一味地失望和忍耐!女人的爱,到这里也已经到头了!”她嘴里说着别人,却好像看到了自己未来的光景。
胡兰成听张爱玲说话,饶富滋味,马不停蹄地追赶着她的思维,求知欲到了贪婪的程度问道:“你是我认人认事以来,第一次知道有天才!现在知道天才多半命苦,又替你担心了!你长大的过程也这样辛苦吃力吗?”
张爱玲笑着,她的心却是被他的话语暖着了:“我不是天才!我也说我是不会委屈我自己的!只是碰上了父母失和,难免受点波及。自己以为是吃过一点苦,但和别人比来又不算什么了!想捏造一点天才的传奇色彩,材料还嫌不够哪!”
胡兰成也举重若轻地说笑着问:“跟爹娘哪一边亲?”
胡兰成问话是很体己的,张爱玲也就以本心来答他。她显露出来的淡漠是真实的情绪:“哪边也不亲!小时候对母亲还有些幻想,因为她老不在,真的在一起生活,才知道活在别人标尺下的痛苦!但又不能反抗,因为是母亲!父亲是做到绝断,足够让我去恨他一辈子了!但又不能真的去恨!”
“因为是父亲?”
张爱玲思索一下,她已经太久不去想起父亲和自己的关系,说道:“因为知道他的可怜!一面恨又一面可怜着,太辛苦,干脆忘记这个人!”
胡兰成很难想象,人与父母之间会是这种关系,又追问:“弟弟呢?你只有一个弟弟!连弟弟也不亲吗?”
张爱玲说时态度很冷淡寡情:“那又是另一个可怜人,但他们自己都不觉得,与我也无关系!我是把我自己照管好就不容易了,其他的我也管不了那么多!”胡兰成感到惊讶,她说得这样理直气壮。胡兰成思索她说的话,揣测这话后面的心理背景。
张爱玲翻到一张画,屏息看了很久。画里是一间裂开的破屋,中午的太阳,草生得高高下下的,通到屋子的小路都已经不见了。就在日光下,一切看起来也都惨淡没生气,真是哽咽的日色!
张爱玲被画面震慑着,喃喃地说:“这里没有壮丽的过去,只有那种中产阶级的荒凉,所以是更荒凉,更空虚的空虚!是上海劫后余生的面貌!”她掩上画册,仿佛不愿意再想起过去那个画面:张家老宅空屋被封死的窗,正是那一栋闷到要震裂的独眼空屋。在炮弹轰炸中,窗外正是那淡白日色下的荒凉。
似乎从遥遥远远处传来胡兰成的声音:“如果劫后还有余生,一定是为了来见你!”
张爱玲怔然抬眼,那句话已经不可捕捉,但余音仍在空气中,胡兰成一只手按住张爱玲的手,张爱玲挣扎着婉拒,这一触两人都僵住,这一步越过了就再也退不回来。胡兰成臣服地低着头,一只手摊开在张爱玲面前,他要张爱玲自己的心意。
张爱玲轻轻地把自己的手覆上,两人的手指交迭着。胡兰成握着她,细细抚弄她的手指,揉着她中指拿笔磨起的茧子,两只手缠绵着。
胡兰成嗓音喑哑地说:“我要坏个彻底一点又不能!怕你又不见我!”
张爱玲低着头,气都虚了:“这也不由我了!”
两个人都像给罚了一样,呆坐着。胡兰成去勾张爱玲的脸,张爱玲只是一个傻姑娘样,所有文字里的老练成熟都破解了,就是这样一个纯净的孩子而已。胡兰成忍不住要低头去吻她,先是吻她的额头,轻声问:“怕不怕?”张爱玲摇摇头,不知道该要怕什么。胡兰成长吁一口气,喟叹地笑自己:“我是在问我自己啊!”他又去吻她,这次是吻她的唇,只轻轻地一啄,两人相对痴痴地望着。张爱玲的话细不可闻:“原来你在这里!” 胡兰成说:“草长满了,路都不见了!还是我自己找来的!”
窗外是萧飒的烟雨,张爱玲拉着胡兰成到顶楼的屋顶阳台,两人贴在窄窄的檐下墙边,看雨珠像帘子一样挂在面前。
张爱玲把手掌伸出去,让雨珠在她的掌心跳舞,胡兰成点起一根烟,白白的烟吹进雨里,灰蒙蒙要昏暗了的天。
他们就这样静默无语地靠着站在一起,虽然只是檐下一方立足地,却感觉是天宽地阔,雨围绕着他们,有一种言语不可及的静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