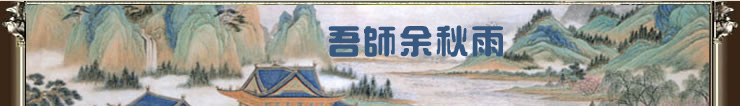 |
 |
|
寻找传说与现实中的场景(刘胜佳)
|
 |
 |
|
大学时代,非常迷恋易卜生的诗剧《培尔·金特》和艾略特的长诗《荒原》。转眼间二十多年过去了,经历了人生的多次角色转换,但在心中,我一会儿是培尔·金特,一会儿又是那个寻找圣杯的少年。
城市使我寂寞。
我常常选择远行,无数次出发,又无数次归来。
我无意模仿我师余秋雨,有些东西是与生俱来的,是流淌在血液里的,这只有同道人理解。人生活在时间里,历史也是由时间形成,因此任何事物的意义又都离不开时间,对于一个人来说,他有种种经验,但在当时都无法完全理解,只是以后才能认识到意义,这就是过去的时间,现在的时间,将来的时间的复杂关系。过去(现在、将来)的时间,时间中发生的一切,怎样才能拯救呢?
无数次行旅中,有一次经历让我刻骨铭心。这就是云南迪庆藏区著名的灯会。藏历正月十五日的夜晚,覆盖白雪的群峰在星光照耀下,现出梦幻般波动的幽蓝。忽地,在冷寂的蓝色中浮现点点嫩黄,这黄灯渐渐幻为五彩花灯,在冰雪的映照下灿然连成线、连成片,静穆而灿烂,辉映出一个超凡的境界。在朦胧的月色雪影里,灯会上人们燃灯朝拜,梵音在寂静的山谷回荡,空远寂寥,送入苍冥。《华严经》里描写的华藏世界海,正是通过无边无际的灯海与明月之境的辉映,使人进入一个参悟大化、梵我同一、超越时空和凡尘物我的净界。这是一种如禅的诗境:
“一个人在孤峰顶上,无出身之路,一个人在十字街头,亦无向背,哪个在前,哪个在后?”(《古尊宿语录》卷四)
“没有惊怖,没有颠倒
一番花谢又是一番花开
想六十年后你自孤峰顶上坐起
看峰之下,之上之前之左右
簇拥着一片灯海——每盏灯里有你”
(周梦蝶诗)
这灯海,或许正是佛性遍在的象征,佛国净土的意象。此次的游历归来,我似乎给余秋雨先生写过一信,谈及我当时的感悟。那时,余先生的《文化苦旅》正热遍华人文化圈,也陪伴我度过无数孤旅长夜。
我与余先生的师生之缘始于八十年代初,他以自己广博的学识、高超的语言天才和丰沛的才情,使不仅仅是戏剧学院的莘莘学子们为之倾倒,也引领着我们快乐地阅读和获得知识的快乐。
在我成长过程中,有许多的师长影响着我,但我心中以为对我影响最大者有两位,一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的马昌仪先生,一位是余秋雨先生。马先生是我大学毕业考神话学研究生时的指导老师,由于在校时读书颇杂,对我们民族文化的口头形态——神话、传说、歌谣,民族文化的行为形态——巫术、祭典、仪式,等等,尤为感兴趣,所以一门心思想考神话学研究生。马先生是位善良的长者,她无私地引导着我探究数千年文化潜伏在我们集体意识中的文化震撼,神秘的朦胧涵盖在时间与空间之上,模糊了地域与历史、传统与现代、视像与幻像、生命与心灵、人与自然的界限,暗示着一种无始无终、无边无际的永恒。
对我的人生态度、文化态度和价值取向,影响最深者当属余秋雨先生了,无论是在上海、北京,还是后来的深圳。这不仅仅因为我是他的学生,也不仅仅是他文章的阅读者,大多源自于感知和想象。维特根斯坦曾经说过:“想象一种语言也就是想象另一种生活。”在雪域高原,在茶马古道,在丽江大研古镇,在“斜晖脉脉水悠悠”的徽州古村落,在“三生花草梦苏州”的江南小镇,或是在山崖,在庙宇,在山风呼啸山丫,在烟火熏黑的祖屋,在古蔓荒藤遮盖的岩画前,甚至在异域的“加州旅店”,这种想象和感知是挥之不去的,是温暖的,是刻骨铭心的,如冬天雪夜里温热的老酒,如遇多年不见的知己。
在这种想象与感知中,我尤为激赏的是余先生关于“学者要有民间情怀,文化要有民间情怀”的呼吁。这是一个纷杂多元的社会,“走出书斋,去实际看看,在文本文明之外接受时间文明”。这是文化转型期的现代学人都要面对的问题。熟读余先生文章的人,都会感知到一种跨越历史与现实的人文精神和浓浓的家园意识,同时也会感知到余先生对构建城市文明的渴望和对当下经济发展的关注。余先生从中华文明出发,到阿拉伯文明,再到欧洲文明,在人类历史上发生过整体性影响的文明,基本上都被他涉足。在我眼里,余先生既是文化的探求者,更是文化的实践者和文化的体验者。
美术评论家王广义曾提出“清理人文热情”的观点,他指出:“我提出‘清理人文热情’这观点主要是希望理论界尽量避免对一幅作品过度放大它的意义。我现在觉得这个观点在当时更为重要的一点是——这样无休止地放大,对人文热情的过度投入,可能使画家远离生活。”现在,有人甚至将学者分为专业学者与媒体学者,前者指的是那些固守书斋、专心研究学问的学院派,后者自然指的是那些除了研究学问外,还频繁在公共领域,就国计民生发挥作用的知识分子。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两者之间要人为地二元对立。人的学养不同,研究的领域不同,治学方法和人生态度也就不尽相同。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言必称韦伯”时,人们津津乐道地“以学术为业”与“为艺术而艺术”,是韦伯对韦伯偶像崇拜者带来的误区,这样的命题可以成为一种分析角度,但命题本身是幼稚而造作的。远的不说,我们的先人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较之不是有更为高昂的学者主体性吗?
有些人将余秋雨先生,还有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顾晓鸣先生称之为“媒体学者”,将陈逸飞先生称之为“媒体艺术家”,甚至直称其为“文化商人”。我个人认为在当下中国语境下,这个问题可以说是一个伪问题。余先生长期与媒体的良好合作自不待说,顾晓鸣先生被IBM邀请作为品牌的代言人,广告的主题是“世界最具创新思维者的选择”。有人质疑顾晓鸣作为文化人,不应该凑热闹搞什么广告,甚至有人指斥他忘了知识分子的本职是什么。多年前,在江南水乡小镇,我跟陈逸飞先生有些交流,他认为自己是个视觉艺术家,而不像有些
人期望他只作为专职的油画大师。顾晓鸣先生面对质疑时有过这样的回答:“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活法和价值观以及人生的态度和策略,无论穷富尊卑,每个人都是上苍精心创造的伟大作品,都有不可替代的价值……”这一点,我深以为然。
“著书皆为稻粱谋”,这是中国古人说的,时尚把小便壶弄成艺术品,那么多的“艺术家”和“学者”和“教科书”都对之吹捧有加,引为经典,再端什么“者”和什么“分子”的架子,不是比小便更为酸臭了吗?很难想象,在当今时代,学者可以自鸣清高,面对社会责任和经济发展可以作壁上观。实际上离开学者的经济是不存在的,黄仁宇对明代簿记和中国资本主义发生问题的研究都已成为常识。所以,学者的神化、泛化,或者过分与媒体的对立,都大没必要,学者也要在变化了的世界中贡献自己的一份创造。不这样做,何处安身立命?学者也是人,你以为人是什么?首先是一个吃喝拉撒睡会死的动物。
IBM另一系列的品牌代言人,是《美丽心灵》的作者西尔维娅·娜萨,当世美国正统历史学家第一人布尔斯廷,就写有重要当代传媒批评著作《假事件》,语言学大师乔姆斯基一直在做“媒体学者”。我不知道与媒体绝缘的学者是什么样的?也许他只是活在自己的神话里。
过去,有权就可以大干快上,干惊天动地的蠢事,比如填滇池“围湖造田”;现在权力加上钱,如果还出洋“考察”过几天,更可以干愚蠢的壮举,比如拆了真的老街建造仿造老街,砍掉古庙的弯扭古树,像法国一样把树修整齐,种上开阔的带有几何图形的草坪,在火山上修笔直的大台阶,更有异想天开的,给滇池边睡美人山“隆胸”,过度的欧陆风情的房产开发和造镇计划,若干年后中华大地上都是如雨后春笋般的欧美小镇……所以,在旅游经济发展可能过快,头脑可能过热,权力和金钱可能控制性过强的情况下,必须有相应的制约机制,有所为和有所不为的胸襟和气度。其中,知识或理智的制约力不能忽略。像余秋雨、顾晓鸣、陈逸飞这样的学者和艺术家不能沉默,还需要有更多有社会良知的学者的声音。
作家阿城在云南曾感慨道:“现代文明常常会使我们养成一种傲慢,对此前的生活或者生活方式不屑,又或者反过来,对此前的生活或者生产力方式有一种媚,我觉得都不足取,都难免会盲目。”我深以为然。
在秘境云南的茶马古道,每次踏着嵌着二寸许深的马蹄印的石板上,都会有一种异样的感觉,都能体验到中国西南特有的文化所具有的一种摄人心魄的内核:它自古至今延绵不绝的血脉文化,它包孕了那么多的民族群体文化,它产生了那么多的“个体”文化及“混合”文化……
中国需要书斋里的学者,更需要大批走出书斋的文化实践者。我们日益变化的世界,太需要“学者的民间情怀”和“文化的民间情怀”。为了心灵不再干涸,为了美景不再破坏,为了家园不再是荒原,为了城市不再寂寞,为了文明得以延续,为了更多出行者不再孤旅,人在路上,络绎不绝……
|
|
 
本书由“啃书虫”免费制作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