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成功到来之前的许多环节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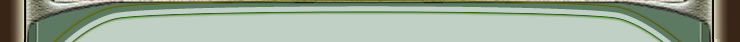 |
 |
|
以后太多的人听说我是学戏剧的后,大惊小怪地看我。我也学会了自嘲。我干笑着说,不好意思,我和戏剧“邂逅”了三年。
终于还是没有走上做学问的路,三年研究生生活也没能帮助自己沉浸下来。我那时还在断断续续地写着小说,记得一位和我年龄相仿的《上海文学》的小编辑看过我的小说,喜滋滋拿去奉给主编,却被主编轻慢、教训了一通。他只好安慰我,说他将来混到了主编的位子
,一定发我的小说。我像许多现在20几岁又有点想法的年轻人,每天都在认真地问自己:我是做学问呢,还是写小说?结果就是我既没做成学问,也没写好小说。
我有时觉得自己这一点和余秋雨老师倒有点相像,既有理性,也不乏感性,不同的是他学问做得好,散文写得又独领风骚。应该说他把自己开发得很好。
人们总是更容易看到对方的成功,很少贴近地去想成功背后的众多努力。我就知道在我的一些朋友中,大多都是才华横溢的,但他们也和我一样,基本上都还停在“愤青”阶段,沉不太下来以自身的才能去创造些什么,去获取社会的认可,这使他们产生了另一种不理智的心态:在他们眼里,凡是社会认可和接受的,就是媚俗和不光彩的,凡是日子比自己过得好的,就是不正当的。就像他们有的说到我的老师时,总是要冒出几句“愤青”式的话语,有时会连带着把我也攻击一番。我站在他们中间,对谁都客观、体恤。
有时会想,像我这样“无法无天”“目中无人”,如果不是因为余秋雨是我的导师,如果不是因为他又正好是我喜欢和欣赏的人,我会这样把心态放得平平的来阅读他、追随他、进入他的世界吗?
真把自己问得吓了一跳。
在我结交的朋友中,大多不乏才气,也大多埋没于俗间,与社会格格不入。当然这种格格不入,有的属自我放逐,有的则纯属无可奈何。他们可以无保留地推崇某一位远在天边的西方作家、艺术家,无论死去的还是活着的,但无论如何,对自己周边冒将出来的新锐人物,是不会轻易服气和认同的,除非是自己的狐朋狗友。这里头有骄傲、嫉妒、不平、不屑等等复杂情绪在作怪,让我们自愿放弃了与同时代另一些同样有才华的人群的沟通。
记得早年有一回我和女友去文化宫书市淘书,要淘的当然都是外国文学类,那时是很不屑光顾中国文学的。走过一家书摊,看见那里贴着张海报,是一位永远在写知青小说的作家在那里签名售书。我们都从没耐心读完过他的任何一部小说,却对他照搬生活毫无想象力的所谓写实深怀恶感与不屑,我们就决定损他一把。瞅了个没人的空档,我和女友肩并肩朝他走过去,满脸文学女青年表情。就在那人想当然要接受我们的崇敬时,我们小脸一变,扭头就走,给他个不尴不尬自讨没趣。跑出了老远,我们还蹲在地上笑得起不来。
这就是我年轻时干的众多好事之一。
现在想那当然是很伤人很不人道的,其实我从来也没有心平气和读过那人的作品,就因为大多数人喜欢他的东西,就让我反感他,不稀罕他。
其实还是余秋雨说得好,作为各自独立的作家,最好不要随意把自己的艺术尺度用在别人身上。
有一回,我对他说,我的朋友某某(也是一位大名人)不知从哪儿听说了别人对你的议论,对你很有看法呢。他无奈地望着我笑,不知说什么好。
我说我告诉我那位朋友,名人都是要被人议论的,中国人爱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何况人家传你的那些“坏事”根本就是无中生有莫名其妙。在认识你老兄之前,我也听到过不少对你的议论,如果我不是后来有幸认识你了解你,成为朋友,你在我心目中也是另外一个样子。现在怎么样,现在我到处跟人说你老兄其实是个非常好非常体贴细致的男人,尤其对老婆好。我成了你的业余宣传员了。所以什么事最好是自己亲眼所见亲身所为,才好相信。就像别人议论余秋雨,许多是以讹传讹,挺不负责任的。有一次我看到记者采访陈道明的报道,他就说自己一直在抵制“听说”这两个字,先是根除自己嘴里的“听说”,然后是拒绝听别人嘴里的“听说”。我觉得他挺智慧挺有脑子,我们都要跟他学。
余秋雨听着我的话,一直在说“谢谢谢谢”,我感觉得到他的真切。
冷静下来想,其实我们这些相对年轻的人,在观念与心态上,很多时候比年纪大些的余秋雨,反倒要老旧、迟缓得多。他有时像是一面镜子,我看到他现在呈现出来的状态,会蓦然联想起这状态到达之前的许多环节,看到他一次次强有力的行动,更会照见自己死气沉沉和怨天忧人的样子。广告里说“脑白金年轻态”,“年轻态”三个字送给余秋雨很合适。
21世纪了,年龄在一天天增加,我想大多数人到死也找不到自己那个位子的。眼看“愤青”成了“愤中”,再一不留神,就该到“愤老”的岁数了。一些笨人和蠢人,每天在那里可怜巴巴或愤世嫉俗,那是他活该,谁叫他无能又缺才。而另一些懒人,完全可以让自己活得更愉快和富裕。
此话算是共勉。
|
|
 
本书由“啃书虫”免费制作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