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那几年他的内心也正处在选择当中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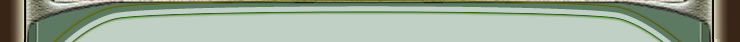 |
 |
|
回头再看那年夏天,看见自己坐在那儿,面向余老师,背靠一整面倚墙而立的书架,手上傻乎乎捏着个他家冰箱里取出的冰激淋,满脸迷惑。
三年研究生生活结束在即,又一次选择,我还是不能完全肯定自己想去哪座城市,想干什么。天生不是一块咬定青山的料,因为没有爱情,我找不到东西来束缚住自己固定下来,我又开始想换一个城市去一个新地方。还好这回没有想到要考个博士生什么的。
我在学校发的职业选择意向栏里填了“清洁工”,被研究生教务处处长臭骂了一通。我说我不是开玩笑的,我说的是真的,清洁工天没亮出来劳动,那时整座城市都是他的,他自由自在地扫着大街。等到城市醒来,大多数人疲于奔命完全被城市淹没时,他却在蒙头大睡。“老惬意老潇洒咯,”我说。
我这时老老实实对余老师说我真的想成为一名体力劳动者。看的书太多,脑子里面太活跃,有时候觉得自己无所不能,什么都能染指一下研究一下,有时候又很害怕自己进入固定的生存模式,觉得研究别人毫无意义浪费生命,关键是我得不到太多的乐趣。我还是不知自己想要“搞”什么。我好像被困住了,也许体力劳动可以解放我的脑子。
毕业在即,必得选择。我思想动乱,跃跃欲试,又不知朝何处用力。我在余老师面前毫不掩饰,滔滔不绝自说自话。
许多年以后我知道他习惯夜里写作白天睡觉,每次打电话找他,我会老老实实在中午12点以后。
那次也许他刚工作了一整夜,也许刚刚才离开书房躺下,总之我这个不速之客搅了他的好梦。他坐在书桌前微笑着,指我手里:你先把冰激淋吃完,都化了。我才意识到自己的嘴一直忙于出声儿,没顾得上吃。因为从他那里感觉到,他不仅不反感我那些乱七八糟的想法,他还很愿意接住我的话往下说。
那是我三年里惟一一次如此坦诚向他表露自己的困境,他听得非常认真,耐心,他还有那么点拿我不知道怎么办的样子,沉吟着,说你的问题不是非要从事某种体力劳动才能解决,应该还有别的方式存在。
很久以后我从余老师的文章中读出,那时书斋中的余秋雨,可能也正面临与学生类似的问题与困惑。
“我记得,那是一个春节的晚上,我在安徽一山头独自赶路,四周静悄悄,很恐怖。我边走边想,这次考察所看到的东西,老百姓平常看的戏,我这个戏剧教授,事前竟一点都不知道。”
那是2001年余秋雨结束“千禧之旅”时说的话。
“我相信,闭门研究文学和戏曲的方法,可能是错误的。”
后来在《行者无疆》自序中,余老师又提到那一次的经历:“我说话的对象,不是别人,正是十五年前的自己。十五年前那天晚上,也是这个时辰,刚看完一个僻远山区极俗极辣的傩戏,深感自己多年来的书斋著述与实际发生的文化现象严重脱节,决心衔耻出行。是从事社会义务?还是投身考察旅行?当时还不肯定,能肯定的只有一项,这个决定充满危险。你看这么一次实地考察,为了去赶清晨的早班航船,不得不独自在山间赶路,还捡了块石头捏在手上防身。文人离开书斋总是危险的,离开越远危险越大。”
现在知道,那几年他的内心也正处在选择当中。不同的是,他依然怀有使命感,坚守在学者、文化人、艺术家的位子上,思考着如何从象牙塔中出走,叛逃,用自己的方式,完整和高扬自身生命的意义。那时他人还在那条轨道上,但离心力正悄然发生着作用。
而我,年少轻狂,无知无畏,决定扔掉一切书本轻装上阵。那天我卖掉了负笈求学以来所有的书籍、资料积累,甚至都没有耐心去找一家回收旧书籍的书店,我把它们连同一双绿色的长统胶鞋一起卖给了上戏边上的废品收购铺,其中包括一本上大学时父亲送的《康熙字典》,以及一本厚厚的听余老师课时记的笔记。就这么狠心和决断。我把卖废品得来的钱全部买了冰激淋,恶狠狠吃到要吐。
我对余老师说我要从事一项不过脑子的工作,要和一个做生意的人结婚,要去北京。
那时我完全像一个问题青年,如今被称之为“愤青”的那种,吃完了余老师给的两个大大的冰激淋,还是一脸恍惚。
那时刘索拉在艺术院校很有市场,宿舍里的人看过我写的那些发不出去的小说,就有人说我是刘索拉第二,我也每天会来上几句“LET IT BE”。倒是最后坐在余老师的书房里,我“LET IT BE”不起来了。我毫不掩饰,也再无意假装潇洒。在他面前,迷乱,郁闷,不知所向,都可以老实、真诚地表白出来。
我完全是个不争气的学生,晃荡了一年又一年,一直都像人们常数叨的那样“高不成低不就”。我坐在那里,毫无建树,肯定不是他最初所希望的,不知他是否懊悔过收我这么个学生。
我真替你着急。他说。
我感受到他话的诚意,他希望他的学生至少应该是快乐的。我还感受到更大的宽宏,他只说替我着急,并无意校正或否定我什么,他好像比我自己还了解我,好像知道我不会永远如此,知道我有一天会醒过来。我需要的只是时间。
他是对的,很多年以后我会摆脱现状,成熟起来。不过那时,我一味地沉沦,无力自拔。
那仿佛也是那个时代的一种时髦病,一种氛围。一些过于精神的东西压得我喘不过气来,让我无法面对和适应现实社会。年轻的我一边陶醉在自己的时髦里,一边又急于让自己以最快、最直接的方式,开始全新的生活。相对于那个拉着自己的小辫儿要上天的人,我正吊住自己的双脚一个劲儿地要落地。
我的倾吐,没有被打断,也没有被责怪。他是何等聪颖的人,自始至终,洞穿一切。倾
听,理解,并包容。他的话和表情,很多年的时间里都让我得到鼓励,让我更加地不被约束,让我一边无限自我膨胀着,一边又暗地悄然返归。
很奇怪,不知是我这个学生毕竟还存了些慧根,还是他那后来被许多人惊奇的预感能力在起作用,他对我这个学生一贯的纵容与理解,不仅没有让我一路下滑一跌到底,反倒一直是一种暗中的强有力的鼓励,一直让我自信无比,一直让我感到有能力证明自己,至少是向他证明我真不是个糟糕的、不值一提的学生。
我喜欢说自己从不在乎别人怎样看我,心中自有红太阳,别人说什么我都无所谓。我自己知道我是谁。而事实上,很多自信来自于肯定,来自于你喜欢、在乎的人对你的肯定,完全脱离社会并不可能。在我身边,父母、兄弟、数量少得可怜的朋友、偶尔倒霉地爱上我的男人,他们的言行总是对我充满了肯定,充满了宽容,是我能够灿烂得起来的动力。
我一直非常在乎余秋雨老师对我的肯定,因为他是我尊敬和认同的老师、朋友。另外我不能欺骗自己,也因为他是一位名人。我不明白自己,余秋雨越是有名,暗地里,我对来自于他的肯定就越是在乎和得到鼓舞,而他又总是那样慷慨和宽厚。这是不是表明我还是有虚荣心的呢?
有时我注意到,他甚至总是那样慷慨和宽厚地对待每一个他身边的朋友,他会认准对方的一个状态,完全从积极的意义上及时地给予赞赏和称颂。不知有多少人从作为老师、作为朋友、作为名人的余秋雨这里,得到过信心与支持。
这一点总让我佩服不已。我自己对朋友的肯定或赞赏方式,不过就是有兴趣肯跟他在一起呆着,混着,从来就不懂得、也不善于开口去表达,去给予。就像被周围人夸得合不拢嘴的一位女友说的,我们这都十好几年了,我画的画儿写的诗,从没听你夸过。我说人家都夸你,我干嘛还夸你,你应该感觉得到嘛。
我现在也总爱要求喜欢我的人夸我,使劲夸。
我这篇东西写得好吗——快夸我。
做了一盘菜,好吃吗——快夸我。
打扫房间了,多贤惠——快夸我。
甚至要求女儿——妈妈漂亮吗,妈妈年轻吗,快夸夸妈妈。
我就是喜欢别人夸我。对那些贬我的人,我会想反正我和你也没有关系,你爱贬不贬,你说我是狗屎我也不管。小时候总被教导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听到表扬还假装不太高兴,现在没人管得着了,现在一有人夸就眉开眼笑的,管他真的假的,高兴就好。
不知道余老师夸我,是不是也只是为让我高兴。管它呢,反正我从他的夸奖里得到过无比的信心,至少它的结果是令人振奋和愉快的。
真希望有一天沉淀下来的自己,也能和余老师一样地平和,善意,也会恰到好处地表示自己的欣赏与赞美,让身边的家人、朋友,也从我这里得到信心与动力。
曾经从一位在西方和美国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的人那里得知:
“西方的文化是善于表扬、奖励的文化,是一种善于把感情外现的文化。只要你做出一点成就,你马上会得到社会的认可、鼓励,哪怕你的成绩很小,这种热情的认可足以构成一种良性的刺激,使你保持良好的创造激情,转为一种良性的循环。”
我就喜欢这样的方式。
甚至想对所有的人说,一定要及时地、大力地赞美你欣赏和喜欢的人,你的父母,好友,爱的人,他们从你这里得到的,一定比你想象的多得多。
|
|
 
本书由“啃书虫”免费制作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