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看余秋雨告状金文明 余秋雨涉嫌剽窃一例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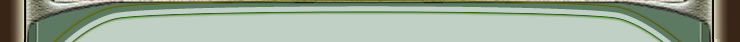 |
 |
|
凡从事学术研究的朋友都知道,“引用”和“剽窃”这两个概念,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我这里先把事实摆出来,供大家讨论和分析。
余秋雨先生在《笛声何处》下篇“世纪的丰收”《长生殿》一章中谈到这部古典戏剧的作者洪昇时写道:
洪昇在幼年时期就跟随陆繁招学习,稍后又从毛先舒、朱之京受业。陆繁的父亲陆培在清兵入杭州时殉节而死,繁秉承着父亲的遗志,不愿在清廷统治下求取功名。毛先舒是刘宗周和陈子龙的学生,也是心怀明室的士人。同时,与洪昇交往相当密切的师执,像沈谦、柴绍炳、张丹、张竞光、徐继恩等人,都是不忘明室的遗民。这些人物的长期熏陶,自不能不在洪昇思想中留下应有的痕迹。加以洪昇的故乡杭州,本就受着清代统治者特别残暴的统治,不仅当地人民处于“斩艾颠踣困死无告”的境地,连“四方冠盖商贾”也“裹足而不敢入省会(杭州)之门阀”(吴农祥《赠陈士琰序》)。而在洪的亲友中,又有不少人是在清廷高压政策下死亡、流放和被逮的。例如他的表丈钱开宗,就因科场案被清廷处死,家产妻子“籍没入官”;他的师执丁澎也因科场案谪戍奉天。再如他的好友陆寅,由于庄史案而全家被捕,以致兄长死亡,父亲陆圻出家云游;他的友人正严,也曾因朱光辅案而被捕入狱。这种种都不会不在洪昇思想中引起一定的反响,因此,在洪昇早年所写的诗篇里,就已流露出了兴亡之感,写出了《钱塘秋感》斗“秋火荒湾悲太子,寒云孤塔吊王妃。山川满目南朝恨,短褐长竿任钓矶。”一类的诗句。(《笛声何处》第133-134页)
这一大段文字,是有关洪昇父辈、师执和好友等社会关系及交往经历的专论。全文总共435字。一般的读者看过以后,除了感到内容丰富,叙事翔实,逻辑严密,条理分明,写得很好以外,恐怕提不出什么别的意见。
说来也实在凑巧,意想不到的情况偏偏让我给碰上了。去年冬天,我因为对余秋雨先生的历史散文指错,同复旦大学的章培恒教授发生了一点文字上的纠葛。为了准备辩论,我找来章教授的几部著作仔细拜读。其中有一部《洪昇年谱》,由于搜罗广博,考证详密,深受我的喜爱,差不多读了两遍,对一些著名的人物和史事比过去熟悉了不少。所以时隔半年,再来读余先生这段文字,第一个感觉就是似曾相识。于是便从书架上拿来《洪昇年谱》,在“前言”的第4——5页上,找到了跟《笛声何处》中那段内容雷同的文字,逐字逐句地核对起来。真是不核不知道,一核吓一跳。这两段来自两位学者两部不同著作的文字,不多不少,竟然都是435个,不但句句相同,词序和语序完全一致,就连用字和标点也达到99.5%以上的高度密合(所不同者,是余先生写错了一个人名)。这个现象,恐怕只能有一种解释,那就是其中的一个人抄袭了另一个人。
究竟谁抄谁呢?章教授的《洪昇年谱》出版于1979年;余先生的《笛声何处》杀青于2004年,而其中论述洪昇的这段文字,全部来自他问世于1985年的旧著《中国戏剧文化史述》。因此可以断定,是余先生抄了章教授的。本来我以为,章教授是潜心研究洪昇的专家,余先生是大面积泛论昆曲的行家,就水平和探索的程度而言,难免有高低深浅之分。因此后者从前者那里得到一些启发和借鉴,或者移植几个新颖的观点,或者引用几句精彩的论述,甚至按照余先生的习惯,以自己生动流畅的文学语言,来个换汤不换药的形象改装,都是无可指责的。这种做法,在当代的学术研究中早已司空见惯,一般不会有人出来说闲话。如要以防万一,就在哪个角落里注上参考或引自某人某某著作就行了。
可余先生这次做得实在太过分、太不聪明了。即便是抄,也得有个规矩和章法,有点节制和顾忌,怎么能把人家章教授精心构思撰写的长达435字的人物专论,不作一点删节,不加任何修饰,就一古脑儿地搬进自己的书里呢?而且对于原创者是谁,抄自他的哪一部学术专著,都没有一言半语的交待。这算什么行为?是参考、引用,还是抄袭、剽窃?要知道,章教授原著的那段论述,虽然只用了435字,内容却高度浓缩,语言也是极其精炼的。其中一共涉及十八人,尤其是钱开宗、丁澎、陆寅、正四人的事例,每人都只用了一句话来概括。例如章教授说:“他(洪昇)的友人正严,也曾因朱光辅案而被捕入狱。”这句话看来简短,但章教授却在《洪昇年谱》第86-87页详细引用了《三冈识略》、《净慈寺志》、《清波小志》、《稗畦续集》等四部典籍中的六种资料,通过论证才得出的,可谓要言不烦,惜墨如金。余先生不但不费吹从之力照单全收,还把正(亦作、岩)法师的名字误成了“正严”。可见他连那些原始材料都没有看过。
这种连菜带盘全部攫为己有的做法,算不算剽窃?读者诸君可以讨论分析,余先生也可以据理力辩,但希望千万不要回避,别再闷声大发财。因为问题一经提出,全国的莘莘学子、硕士博士,都在等着结果哪!如果余先生这样的抄袭不算剽窃,而且合情、合理、合法,那他们必然会群起响应,向心仪已久的文化名人学习,到前贤的著作里东抄西撮,轻轻松松地写好毕业论文,或者拼凑几本学术新著捞点实惠,谁都别再去批评和指责他们,因为人家可以拿出余先生的榜样来为自己作“义正辞严”的辩解。否则,就应当如实地告诫他们,这样做是不行的,是对他人研究成果的剽窃,一旦被揭露曝光,必将声名狼藉,难见江东父老之面!
文章千古事,岂能乱弹琴?治学为文,特别是从事传统文化研究的人,必须坚持严谨踏实的作风,以科学诚信为本,来不得半点弄虚作假。某些不良的行为,看来似出偶然,却反映了治学者文品和人品的缺失。尤其是我在本文最后提出的问题,关系到后学成才和成人的百年大计,希望余先生能引起警惕,万勿以危言耸听视之。
(《文学自由谈》2004年第4期)
|
|
 
本书由“啃书虫”免费制作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