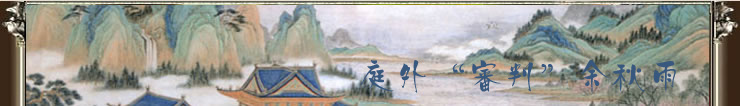 |
 |
|
看余秋雨告状左柏生:正版中的盗版(2)
|
 |
 |
|
而更加叫人难以接受的是,不管刘东先生对法国学者的那一番补充,是否可以帮助我们获得对于谣言的完备理解,但我们总还可以平心地认为,这位作者本意上是希望大家的理解更加甄于完备的。余秋雨先生却不然,他不仅粗暴地切断了别人的文脉,让读者再也看不出人家原有的探求过程,而且武断地对别人的引文掐头去尾,只摘抄出三个定义中的一个,哪怕明知道这样会使读者对于谣言的理解更加残破。当然话说回来,要把原有引文中的全部三个定义统统挪下来,的确是有点太露骨了,大约余秋雨先生还不忍这么做。不过这样一来,他那段看起来是在补充别人的文字,究竟又置广大读者于何地呢?不是在成心地和人为地愚弄他们么?
由此方知,恐怕不光愚钝如我,整个知识界对于“剽窃”的理解都还太过肤浅。大家只把学术打假的目光集中在像王铭铭那样的恶劣例子,殊不知此君的手段实在太拙劣太愚不可及了,要想瞒天过海简直就是妄想。而相形之下,余秋雨先生就显得精明得多:他表面上并不讳言别人的思想和出处,还一本正经地把它摘引出来讨论,然而,他却微妙地掉换一下引文的次序,以便把别人的成果悄悄地据为己有;另外,他也决不像王铭铭那样贪得无厌,一下子剽窃多少万字,一旦被捉就惹出众怒哑口无言,而只从别人那里稍许拿那么一点,甚至就连这么一点,也要尽量精简尽量删削,尽量不要露出蛛丝马迹。
此外更加重要的是,王铭铭之类的行为,由于太过露骨太过张狂,早已为全社会所顿足所不齿,他本人也受到了相当的惩处,足以作为一种反面的警戒。可是像余秋雨这样的行为,尽管在性质上同样恶劣,在道德上同样低下,到现在为止仍然堂而皇之瞒天过海,不揭露其中的欺骗性行么?
正因为这般堂而皇之,就像我们一开始所得悉的,余秋雨总是以正面的形象出现,不是被迫坐在被告席上,而是主动坐在原告席上,而且不是要打一个官司,而是要打一系列官司!
说实在的,我既不了解也不想了解余秋雨先生的诉讼内容,更是无从判断其中的是非曲直。讲得极端一点儿,我甚至倾向于认为,就算是“贼喊捉贼”也没有什么不好,——如果天下的小偷都能拿起法律的武器去防范其他的小偷,那么终究会“负负得正”,根除掉偷窃这种丑恶现象。但即使如此,我仍然有理由遗憾地感到,当一位学者道貌岸然地以诉讼事件来吸引公众注意的时候,当一位学者口若悬河地在大众传媒上扮演文化明星的时候,要是他本身的人格能够更加无懈可击,那么整个社会为此而承担的信用风险就会小得多。
只可惜,具体搁在余秋雨先生身上,由于前面揭露的事实,上述指望只能是大大落空了。但无论如何,我仍要对人性寄以最低限度的希望。我的意思是说,就冲就这样一个不大不小的文字失窃事件,是否也要打官司索赔精神或名誉损失,那要由刘东先生自己去选择去决断,而我们作为读者,却只能指望余秋雨先生向我们做出起码的交代。众所周知,曾经有数以几十万计的读者掏钱买了这本《霜冷长河》,否则余秋雨先生的打假积极性也不会那么高。然而,我目前所购买并引用的这本正版书中,却出现了如此令人遗憾的内容,使我们岂能不向余秋雨先生讨个说法--你用这种写作方式制造出来的东西,其本身究竟是正版还是盗版?应当不应当向出版社和广大读者认罚?或者至少公开而明确地向公众道歉?
(《中华读书报》2002年8月21日)
|
|
 
本书由“啃书虫”免费制作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