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我和余秋雨打官司 致作协的一封公开信(2)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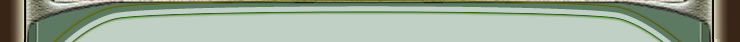 |
 |
|
由此可见,我文章中有关余秋雨先生的材料均有据可查,并无捏造。本人从未见过余秋雨先生,与他没有任何个人恩怨和利害关系,主观上不存在“用极端化的造谣方式”诽谤他的动机。何况,我的文章的发表媒体并非无聊的小报,而是刊登在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文艺报》、鲁迅博物馆主办的《鲁迅研究月刊》、安徽省社科联主办的《学术界》等严肃的学术刊物上。我并不是余秋雨先生“文革”期间参加写作组这一事实的原创者或曰“捏造”者。在原创者与媒体之间,我居于第三位。余秋雨先生把我当成第一被告,是一种严重的角色错位。我写这些文章的宗旨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已有如下说明:
……这些在“文革”结束后作了结论的事本来也用不着重新翻出来,我们也不能强迫别人“忏悔”,“文革”中的问题主要是时代的错误,不应过分追究个人的责任——尤其是一个刚出大学校门的青年。我们同样不能把“文革”中的问题迁怒于余秋雨一人。但鉴于余秋雨矢口否认这些往事,并倒打一耙说别人讲的事实真相是“政治谣言”和“政治诬告”或为了想借批名人出名,还把自己文过饰非的行为标榜成“留下为文和做人的起码规矩”,故为了对历史负责,并为研究“文革”史的人提供点资料,以让患了健忘症的共产党员作家余秋雨重新恢复记忆,讲点共产党人的实事求是的“起码规矩”,能按江泽民总书记的“三个代表”的严格要求反思历史,作一次高尚的精神拯救和心灵涤荡,我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史料工作者只好把别人披露的和自己调查了解到的真相说出来。
由此可见,我的批评属健康、说理而非诽谤性的。正如北京大学教授谢冕在接受《中华读书报》采访时所说:“看过古远清的一些文章,感觉古远清还是在说道理”。余秋雨先生状告我显然侵害了我在学术讨论中的言论自由权,同时也侵害了广大读者对公众人物的知情权。他把我十多年前赞扬他的话和文章中使用带引号的“狡猾”一词,作为告我的一个重要内容,这势必造成文坛官司满天飞,导致文艺界的混乱。显然这一事件已超出文学批评的范围,而牵涉到文学研究者的正当权益,特吁请贵委员会聘请权威性的文学评论家组成评审委员会,对我发表在《文艺报》等媒体上的有关余秋雨“文革”问题的四篇文章给予公正评审,就拙作是否“用极端化造谣方式”写就做出判断,对这一事件的是非曲直做出仲裁,以依法保护我作为一位文学评论家的合法权益,并将判断和仲裁的结论公之以众。
此致
敬礼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北作家协会理事
古远清 2002年8月16日
附件有:余秋雨先生的诉讼请求书、胡锡涛先生的《余秋雨要不要忏悔?》、孙光萱先生的《正视历史,轻装前进》、本人写的《论余秋雨现在还不能“忏悔”》等四篇文章复印件及《中华读书报》、《武汉晚报》、《南方都市报》、《长江日报》、《湖北日报》、《楚天都市报》、《作家文摘》、《新闻周刊》、《羊城晚报》、《中国青年报》、香港《信报》和《明报》、台湾“中央社”电讯稿、菲律宾《菲华日报》等有关报道和文章
《中国青年报》得知此公开信后,在8月20日《文化》专版进行大幅报道,其通栏标题为《余秋雨诉古远清侵犯名誉权案最新进展:被告上书中国作协辩白原委》,同时配上该报记者徐虹采写的两篇报道:《古远清:这场官司的文化意义值得深思》、《余秋雨:千万不要把这件事与文学批评联系起来》。“公开信”的全文则由广州出版、发行量据说仅次于《人民日报》的《羊城晚报》9月18日刊出。《羊城晚报》此专版除“公开信”外,另有我写的答该刊记者问、《余秋雨为什么不敢打开历史黑箱》和郑雪来的《我看“余秋雨状告古远清”事件》。该报和我没有什么特殊关系,派来的记者与我也素不相识,他们却做了两次专版一边倒支持我,可见余秋雨打官司不得人心。
|
|
 
本书由“啃书虫”免费制作 |
|
 |
|
 |
|